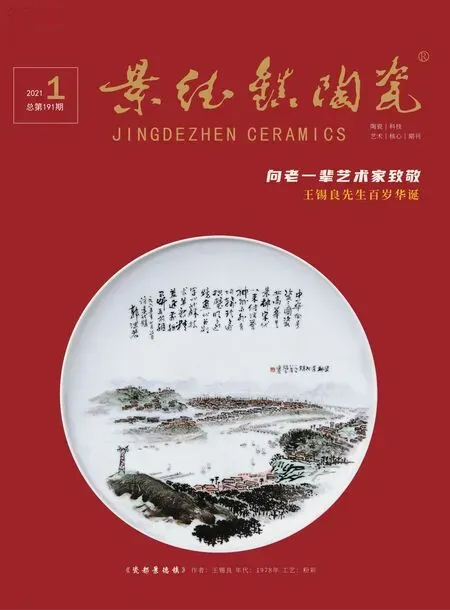柴燒工藝考辨及傳統美學蘊含微探
杜永強 李 莉
火為人類帶來了文明,早在遙遠的新石器時期,人們已經能夠熟練的運用火來燒制陶器。陶器的出現是文明高速飛躍的標志之一,而這一切都離不開柴燒。在煤窯、氣窯或電窯等現代化的燒成工藝出現之前,柴燒是陶瓷燒制的主要方式,其已經成為了中國陶瓷史乃至世界陶瓷歷史見證者與參與者。隨著科學技術的日益發展和陶瓷工藝的不斷變革,陶瓷燒制方式開始向煤、氣、電窯變革,逐漸取代了柴燒。但是近年來隨著現代陶藝的發展,質樸本真的審美風潮興起,“柴燒熱”又引起人們的興趣和關注。
一、傳統到現代——柴燒工藝的古今流變
1、追求“無暇”的古代柴燒
在我國,柴燒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期,彩陶文化就是對其最有力的佐證。可以說,我國的柴燒制瓷史就是古代陶瓷的發展史。不論是“陶”的發展還是“瓷”的演變,古代的燒制工藝就是以柴燒為主。在這一整個制瓷歷史過程中,由于受到審美局限的約束,柴燒中最常出現的“火痕”“落灰”等現象被認定為壞品和瑕疵,不被大眾所接受。人們為了得到更加“無暇”的陶瓷而不斷地向完美掌控柴燒而努力。一直到清代,柴燒陶瓷工藝已經能夠做到“完美”程度了。但正是得益于柴燒工藝的不斷精進,才有了我國傳統陶瓷工藝像青花瓷、五彩瓷等如此多的工藝珍寶,使得世界人民看到了我國豐富形式的陶瓷技藝。

作者:李莉
2、返璞歸真的現代柴燒
近年,隨著審美觀念的悄然變化和對物象本真的追求,各種追求“自然”形式的柴燒工藝受到人們的追捧。究其原因,個人認為,主要緣由是對個性化作品的追求,對陶瓷“完美形象”的審美疲勞以及對傳統程式拘束的厭倦。
從追求“無暇”到返璞歸真,現代柴燒以一種接近“無為”的表現形式呈現在大眾面前。“火痕”和“落灰”等受到古代審美排斥的陶瓷燒制現象在現代柴燒中被奉為“自然的恩賜”。火痕就是燒制過程中火焰流動所產生的路徑痕跡,燒成后留下或黃色、或橙色以及或黑褐色的痕跡,表現形態各異,大多呈擴散狀。“落灰”柴燒也是現代柴燒的主要方式之一,其摒棄了傳統施釉的方式,無釉入窯。當木材在燒制過程中完全燃燒,產生的灰燼在窯爐中自由飄灑,灰燼在附著坯體的過程中發生反應,形成形態各異的斑駁層次和豐富的斑斕色澤。這些從前作為“瑕疵”的存在變成了新的裝飾語言,以一種直觀的方式向人們展示著自然的能量。

作者:杜永強
二、自然本位的日式柴燒
現代柴燒的快速發展也離不開日式柴燒的影響,這種以“自然”為本位的柴燒理念在日本影響深遠。早在唐宋時期,茶和陶瓷文化傳入日本國內并受到追捧,日用陶瓷在日本開始了高速的發展,也就形成了著名的日本六大制瓷園區,即:備前燒、瀨戶燒、信樂燒、常滑燒、丹波燒以及越前燒。日本的茶道文化盛行,那么與樸素清淡的茶藝文化相契合的“自然”柴燒也就受到了民眾的追捧。
日式柴燒大多采取“裸燒”的形式,以最大程度的迎合茶道禪宗精神,并各有特色。備前燒窯址位于日本岡山縣備前市,其燒制的產品鐵的含量很高,原材料取自稻田,木材以紅松為主。備前燒的裝飾依托于火痕與落灰的變化,有著粗獷的藝術魅力;瀨戶燒是日本最具盛名的古窯,位于本州島的瀨戶市,和我國的景德鎮類似,其擁有豐富的陶土和高嶺土,有著得天獨厚的瓷業發展優勢。“瀨戶黑”“志野”、“織部”等都是享譽世界的代表柴燒工藝;越前燒則以灰著釉為傳統,有著隨性質樸的藝術特征;還有丹波燒、常滑燒和信樂燒,雖然它們在燒制手法與表現方式上不盡相同,但是傳達的精神內核都是以樸素自然為本位的柴燒藝術。
三、繁復嚴苛的柴燒工序
1、對燒制氣氛的把控
不論是古代傳統柴燒還是現代柴燒,對燒成工序的把握與控制都非常重要,也正是因為有傳承了千年古代柴燒工序的經驗基礎,才為現代柴燒刨去了很大一部分的經驗成本。對于以人為控制為主的現代柴燒來說,燒制氣氛的把控顯得尤為重要,因為要想得到與期望相差不大的“火痕”或者“落灰”表現,就必須通過多次實驗進行調節。升溫曲線的設計對于燒制氣氛把控非常重要,升溫曲線就是對什么時間要達到的溫度數據作出的控制。烘多久的窯?采取多少溫度?沖溫的時間是多少?預計燒成的天數?等等諸多問題要不停的提出并解決。
2、燒成工藝的抉擇與區別
在傳統的柴燒中,人們對于成品的期望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無暇”。所以在傳統柴燒中,不同的陶瓷種類燒制都有特定的程式,有專職的燒窯工匠,他們追求的是怎樣達到最高的“成品率”,在代代相傳的柴窯燒制中是以機械重復為表征的。燒制瓷器的過程中,窯工只是陶瓷作品中的一小部分參與者,是無法在柴燒過程中表達自我意識的。而現代柴燒中,燒制的角色大多由藝術家本身扮演,他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對燒成結果有著自我意識的控制。
柴燒的燒成方式大致可以分為釉燒、裸燒、套燒。釉燒顧名思義就是上釉后燒制,不論是釉上彩、釉下彩還是釉中彩都屬于釉燒的范疇。這也是傳統柴燒工藝的主要方式,代表瓷種有青白瓷、青花瓷、五彩瓷等等。無釉燒是現代柴燒和日式柴燒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裸燒”,火痕和落灰效果的柴燒陶瓷都屬于這一范疇。還有就是“套燒”,在傳統柴燒中,套燒是為了防止火和灰在陶瓷上留下痕跡,因此套上匣缽。而在現代柴燒中,套燒的方式并不是完全將坯體套住,而是為了更好的控制這些痕跡在陶瓷上的不同表現。
四、傳統美學浸染下的柴燒工藝
很多人認為現代柴燒藝術完全是受到外來的日式柴燒器風格的影響,是一種崇外的體現。其實不然,且不說日式柴燒亦是受到我國唐宋時期的影響,這種對質樸本真的渴望和追崇是我國自古以來就有的。早在莊子時,“自然美”就已經根植于國人心中了,這次“柴燒熱”的興起,倒不如說是我國傳統美學思想的喚醒與回歸。
在《莊子·山水篇》中就有“既雕既琢,復歸于樸。”在《莊子·天道篇》中又有“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也就是說,莊子對美的理解是樸素的、本性的。而老莊美學在我國傳統美學中的地位是崇高的,以“無為”為中心的莊子思想在藝術的領域承擔著重要的職責。這一點,不論是在寫意國畫中還是在文人畫中都體現得淋漓盡致。表現在現代柴燒中,這種“無為”的審美情趣正是與之契合的。火焰的流動、木材的燃燒、泥土的成型,這些動作都以一種近乎直接的方式體現在柴燒器上。
五、結語
柴燒器皿源于自然,創作者又能動的在器皿上表現自然,抒發對自然的尊崇。不論是傳統古代柴燒還是現代柴燒,亦或是日式柴燒,都是大自然對人們的恩賜。尤其是裸燒的柴燒器皿將這種質樸的美表達到了極致,完全將器皿交與泥土、木材和火焰,這種無為的、純粹的、不可復制的美,正是人們對物性本身的敬畏和對回歸自然的情感寄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