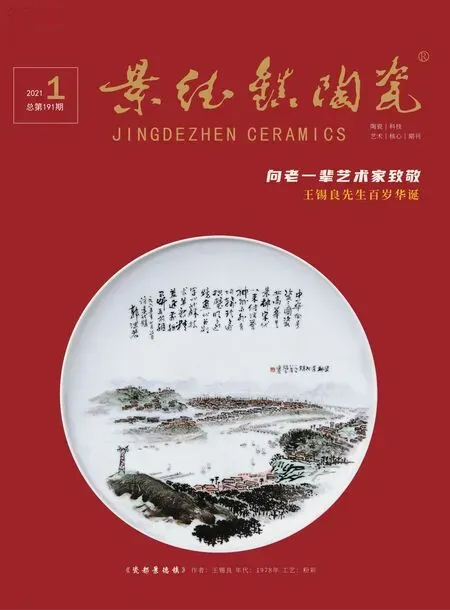古風古韻“竹韻壺”創作漫談
周小軍(江蘇 宜興)
在學習和制作紫砂壺的過程中,必定會了解到一些特定的紫砂壺造型帶有特定的文化內涵,在眾多的紫砂造型之中,這種現象并不鮮見。很多經典的優秀的紫砂壺式造型中,表現美感動人的元素各有不同,但往往都具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古”。摹古崇古是國人的一種習慣,這種習慣深度地融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甚至在某些時候極端地認為只要是“古”那就等同于“好”,這樣的思維源自于我們古老的文化傳統。
紫砂壺古風古韻的產生,與我們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有很大的關聯。我國是一個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在數千年的歲月中,儒家文化一直占據著社會主流。以儒生為代表的文人階層,長期主導著社會的文化生活,這自然影響到了社會整體的審美大觀。而儒家文化為維持自身長久的影響力,總會援引先賢諸圣的言行來證明自己的正確性。久而久之,這種借古引古就成為了習慣,并逐漸發展成為了尊古和崇古。
當今雖然進入現代社會,但社會整體的文化慣性依然存在,傳統文化與大眾的融合,更加深了原本的文化審美習慣,因此,在藝術創作領域對古風古韻的追逐仍是一種風格,藝術創作者們在發展中種種的智慧閃光鞏固了這種審美的藝術地位,在一些特定的藝術領域蓬勃興旺起來,紫砂恰巧符合這種興旺的條件,因此在紫砂藝術創作中古風古韻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作品“竹韻壺”的創作便是如此。

一、“竹韻壺”的造型來源
“竹韻壺”的造型來源于日常生活中用來打水的竹筒,“竹筒打水”本身是一句歇后語,意為直來直去。這樣的內涵顯然跟竹子的生長特性有關,竹子都是一節一節向上生長,所以選擇用打水用的竹筒作為茶壺的造型本身,亦帶有這種文化意蘊上的設計考量,用曾經在現實中存在過的器物來塑造紫砂壺的外形,并根據茶壺的實際情況作出合理的變化,這就形成了作品“竹韻壺”的造型。
二、“竹韻壺”的制作
這把壺從外形上屬于紫砂圓形器,圓形器制作需要先拍打泥條泥片,將其拍打成厚薄均勻的薄片,然后根據壺身的大小高度進行裁切,將泥片裁成長方形,然后用圍身筒的方法,將泥片兩頭圍攏成一個圓柱形,在邊緣處涂上脂泥然后鑲接,這一步制作完成以后要先清理掉內部多余的脂泥,然后將鑲接的痕跡處理干凈。由于竹筒的造型壺面呈垂直的圓柱形,所以并不需要像掇球之類的壺形那樣拍打塑形,可以直接制作底片和滿片,將圓柱形的身筒兩頭封口,鑲接的過程基本相同。此時坯體已經形成一個內部封閉的圓柱形,這個時候不要著急開口,應靜置一段時間,先制作壺蓋,壺蓋采用嵌入式,蓋面微微帶有曲線,圓柱形的竹節壺鈕以暗接的方式鑲接在壺蓋頂端,兩者的線條如同生長出來的一樣自然順暢,壺鈕的造型取竹節分斷,這樣的造型帶有一種人工加工后的痕跡,這與整體的“竹筒打水”的主題相契合,因為能夠用來打水的竹筒當然是被加工過的竹子。
壺蓋制作好以后,再進行壺口的制作,嵌蓋配合平肩的樣式讓兩者能夠結合在一起,壺鈕的形制延伸到壺身筒之上,壺口部分的制作就需要能夠與壺鈕相互搭配。首先是平肩的制作,最外層一圈要進行竹節化的處理,就如同壺鈕頂端一樣,采用先壓后刮的形式,塑造出壺肩的雙層圈線,然后中央開口,打開壺蓋相適合的大小,這個時候由于蓋面帶有曲線,所以并非完全嵌入的形式,所以要在原本的平肩之上再加上一層薄薄的圓圈形的泥片,這一圈泥片比壺身筒直徑略小,跟壺肩疊加以后形成的造型就如同壺鈕頂端的造型一樣,形成了對應,且這樣一來壺蓋亦可以完全嵌入壺口,形成牢固的支撐。
然后是壺身竹節的塑造。這部分的制作相對比較簡單,用環繞的泥片以外貼的形式鑲貼在茶壺表面,然后用暗接法抹平兩者之間的痕跡,最后用明針在隆起的壺面上刻出一道圈線,上下兩節的竹節都是用這種方法制作而成的,這樣的造型不需要額外的裝飾,其本身就將紫砂制作的工藝性凸顯了出來。
最后是提梁的制作,提梁采用對稱的造型結構,前后雙柄,中央竹節,整個提梁被分成了三段,造型由壺面的圓過渡到提梁的方,這種結構上的對應進一步地展現出竹子被加工后的痕跡,因為自然生長的竹子很難產生這種嚴格的對稱關系,刻意在最上端的提梁造型上強調這一點,就是為了突出竹子被改造后的造型特點。結合之前壺鈕、壺肩部分的對稱感,整個茶壺造型都在強調一點,那就是這并非是自然界中的竹子,這是經過改造,帶有文化韻味的竹筒。
從竹子的造型上看,在這樣的竹筒之上,已經產生了人為改造的痕跡,無論是竹筒的表面,還是茶壺的壺面,就都顯得過于空曠,這個時候就需要加上適當的裝飾來進行填補,借著這種視覺上的填補,運用陶刻篆字的方式加深其中的文化韻味就成為了很好的一種裝飾手段。
三、“竹韻壺”古風古韻的產生
古典的味道并不是憑空產生的,它首先需要標注,其次需要引導。竹筒的造型本身帶有一定的標志性,因為打水用的竹筒在古代社會是生產生活中常見的工具,但在進入現代社會以后,人們在生活中普遍用上了自來水,打水的器具也變成了各種各樣的工業品,打水的竹筒也就逐漸消失了。這種古時曾經存在,但當下已經消亡的現實對比烘托出了造型本身的時間性,古的韻味也就產生了。但是這樣的味道還不夠強烈,因為竹筒雖然少見,但在當下的時代并非完全不存在,其時間的指向還不夠明確,這個時候就需要依靠后續的裝飾來進行引導。作品“竹韻壺”上陶刻一方面成為了整體主題意蘊的釋放,古篆字本身亦帶有鮮明的古代時間特性,因為我們現在所使用的無論簡體字還是繁體字都是近代社會以后才出現,在這之前的文字都可以籠統的歸列為古代。
篆字陶刻結合竹筒造型,構成了兩者明確的時間指向,這種指向明確了時間位置,形成參照,讓作品“竹韻壺”的主題內涵可以結合古代的語境來抒發,這就形成了本文之前所說的紫砂創作中的古風和古韻。
作品“竹韻壺”塑造了竹子的外形,但并非是為了表現竹子本身的美,而是透過竹子營造出帶有古風的味道,從而加深“竹筒打水”,直來直去這一情感意蘊的表達,這樣的表達才是藝術創作的核心,也正是通過這樣的表達,讓人領略到了傳統文化美好,傳承文化的重要,從而更多地關注歷史,展望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