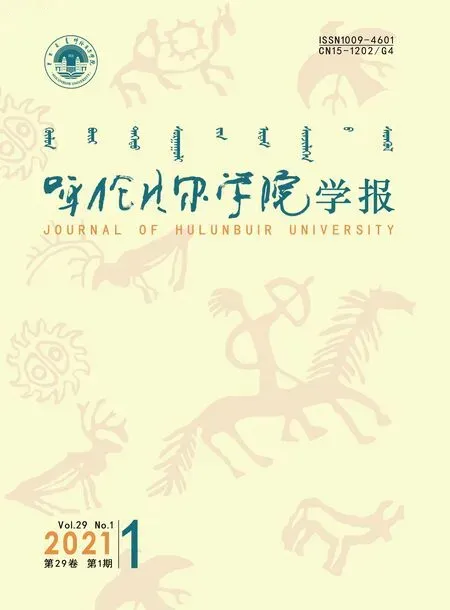崇高及其限度
——論烏熱爾圖小說中的主體生成
戴 琳
(中央民族大學 北京 100081)
烏熱爾圖,上世紀80年代國內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曾憑借1978-1992年間的創作,多次斬獲主流文學的獎項。在許多文學史敘述中,烏熱爾圖被歸于“尋根文學”作家群體。他筆下流淌著濃郁的少數民族風情。現有研究也自然關注他作為鄂溫克文化闡釋者的面向。這些論文以社會歷史批評的角度,偏重挖掘小說蘊含的宗教意識,圖騰形象或原始儀式,評估其具有的民俗學、人類學價值。①也有人運用生態批評的理論進行分析,認為烏熱爾圖極具生態學的警示意義。②
“民族-作家”的鏡像結構作為不言自明的前提存在于論述中,構成了烏熱爾圖研究中被忽略的問題。因為這個認識框架既是研究的前提,也是大多數研究的結論。反思以往的研究,我們必須再度真切地走進文本之中。這要求我們首先懸置起閱讀積習,以更感性的心態去注視細節。
一、作為精神象征的圖騰
觀察人物的建立,不妨先從圖騰視角切入。“圖騰”是社會學家涂爾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的概念。涂爾干認為,圖騰就是用來命名氏族、群體的動物或植物,它們與群體而言具有凝聚性的象征力量。在小說中,烏熱爾圖則有意運用動物形象,把它們“圖騰化”,將崇高的情感寄予其上。人物常常通過對圖騰的認識、遭遇和記憶,獲得部落推崇的精神氣質。
(一)“鹿”與生存經驗
在使鹿鄂溫克部落中,鹿是生活經驗中極為核心的要素。在早期《鹿啊,我的小白鹿》(1980)《七叉犄角的公鹿》(1982)等小說中,作家選用“成長小說”模式,以人物的沿途遭遇構成情節的動力。作家筆下,孩子們都是以尋找鹿為出發而完成成人儀式。《七叉犄角的公鹿》對鹿的生活習性有詳細的描述。小說中,敘述者“我”為了成為一個真正的獵手,帶著勇氣,獨自放足于兇險的森林。在發覺鹿的行蹤后,“我”便一路跟隨。于是,故事就演變成一場關于追隨的儀式:“我”從隱蔽處觀察鹿,見證鹿與狼的搏斗,聞著鹿特別的氣味。鹿是“我”追隨的目標、狩獵的對象,同時也是“我”精神勇氣的投射對象。
《鹿啊,我的小白鹿》中講述兩個小孩兒對鹿的追尋。川魯和巖桑一路跟蹤小鹿,當他倆感到饑渴,但是沒有帶鍋而無法燒水。整個故事,在講述追尋小白鹿,但也是在講述兩個孩子如何借追尋的契機練習生存、實踐技能。鹿不僅是一個狩獵目標,它還啟動了青少年主人公的自我認知。燒好茶后,巖桑得意地說到:“這是從爺爺講的故事里知道的。過去,很早很早的時候,咱們鄂溫克人的祖先就是這樣燒茶喝的。”③傳統是記憶,也是此刻必需的生存手段。巖桑認出了由爺爺所代表的、由積累的生存經驗而形成的族群記憶。尋鹿帶來豐沛的結果,其中之一是巖桑的認識超越了此時此地。那一刻好像爺爺、孩子、鹿以及更多的鄂溫克人在森林中,共同圍繞茶火而坐,連結為一個超越時空的共同體。
(二)“熊”與精神力量
在精神象征的意義上,“熊”是另一個在烏熱爾圖小說中了占據分量的角色。《叢林幽幽》(1993)里,主角額騰科的身體、行動就時刻關聯著熊。額騰科不同尋常,身形如熊,充滿著雄性荷爾蒙,代表著男性的生殖力量。但由于額騰科被認為是不潔的孩子,他的力量總是處于壓抑之中。在營地,人們對他始終抱有敵視。再加上烏里阿老祖母也是被熊擄走的,讓這種敵意尤甚。但當他被人們驅逐之后,營地竟陷入了不詳之中,直到一位薩滿出現后才改善。這位薩滿揭示了真相:人們之所欲遭遇不幸,是因為他們的記憶是殘缺的。喚回的記憶終于道破了額騰科的寓言和真相。薩滿在入神時提示額騰科實際上是光芒而神圣的存在。人們通過重獲的記憶,也認出了額騰科是森林生殖力、生命力的代表。如此,過去的記憶、儀式被重新找回,并幫助治愈當下的創傷。經歷曲折之后,族群文化被更深邃地刻寫進族群成員的記憶中。小說有一個細節引人矚目,暗示作家在創造人物時具有的宗教思維。當擄走祖母的熊被殺死后,人們發現這頭熊竟帶有老祖母的遺物。若根據《金枝》對于交感巫術的解釋,人跟事物可以通過食用或使用來產生聯系,并將自身投射到物品上。將人身與事物連結起來可以延長人的生命;也可以從通過殺死或者食用這種事物、動植物,獲取其代表的精神象征力量。④當熊孩與母親合力殺死巨熊,人們又在巨熊體內發現死去的老祖母的遺物時,一種隱秘的血脈連續起來。整個關系表現為“老祖母-巨熊-妻子-熊孩”這一血脈連結。因此也不難理解,熊孩一旦被驅逐而脫離這一連結,總有倫理的破壞降臨。通過反向的宗教邏輯,也就是證偽的情節,作家建立了熊和熊孩代表的象征性力量。
二、 英雄的再造
在烏熱爾圖筆下,“鹿”和“熊”不僅是森林常駐的生靈,而且擔當著人們精神生活的出發點。不過出發之后,人物主體的真正生成還仰賴于人物由此而展開的一系列行動。廣義上的行動訴諸于人物的言語、神情、動作,以細節的生動性透視人物個性,彰顯他們的存在。
(一)追尋圖式與主體
烏熱爾圖的多數小說都以兒童作為故事的主角,“追尋”是它們共同的主題。如前文提及的,主人公通過尋鹿來習得鄂溫克的生活習慣,實現一種精神上的蛻變。縱觀他的創作,不管是前期還是后期,“追尋”作為契機為情節提供動力。若從幾篇小說的敘事目的、敘事阻力和敘事結果進行分析,便能清晰看到人物行動的要素構成。
如表1中列舉的小說的敘事結構,人物懷揣著強烈的動機出發。他們或尋找,或追擊,或為奇異的事情困擾而企圖找到背后的原因。作為小說情節的一種完整結構,圖式講求完整性,具有美感效果。烏熱爾圖對情節的完整性有一種偏好:人物經歷一番波折之后,必定抵達某個終點。作家對完整圖示的偏好,也是對人物精神完整性的偏好。誠然,“完美圖示”帶來故事的完整性,但它并非小說水準的保證——人物因此會單薄。小說理論家福斯特認為圖式的建立雖使小說具有完善的結構,但必須付出犧牲人物復雜性的代價。從這個角度審視烏熱爾圖的創作會發現,他許多的主要人物都分享同一種性格,完善的圖式造就了人物的英雄氣質和美好品格,但也使得他們淪為“功能人物”。

表1 敘事結構表
(二)“文化間性”中的人物行動
大多數漢語讀者會下意識地把烏熱爾圖的小說當作鄂溫克的“真實”反映,然而在細讀下會發現,鄂溫克部落的世界雜蕪叢生。“文化間性”常被用作社會學意義上的群體分析,但在烏熱爾圖那里,這個概念也發揮著作用。《琥珀色的篝火》(1983)的主人公尼庫的妻子病重,他正帶領妻子和孩子前往醫院,跋涉在灌木叢中。途中他發現林中有人的蹤跡,憑經驗他立馬就判斷一定是外鄉人在森林中迷路了。對此他表面若無其事,心里一直擔心:因為不掌握林中行路的技能,他們很快就會因缺乏食物而斃命。然而這時,他若去救迷途者,妻子的處境會更加艱難。他一度陷入兩難境地。最終,他決定先去拯救迷途的外鄉人。
主人公尼庫返回救助時,小說以十分詳盡的動作描寫來展示他的對森林的熟稔。這些描寫用意明確,短促的句子是為配合尼庫行動時身手敏捷、干凈利索。作家不惜筆墨地說明主人公勞動量之大,能力之強。但作家也為尼庫賦予另一層特別意味。它使原本屬于生存所需的勞動,帶上了某種“表演”涵義。首先,尼庫返回是為救助“城里人”,而他所使用的技能于后者恰是陌生而奇異的。他們的遭遇也是兩種文化的遭遇。尼庫救助“城里人”不啻是一個隱喻,提醒我們必須在文化間性的關系中去解讀主人公的一系列行為。除道義之外,尼庫對他眼前的被救者似乎有一種暗中訴求。小說寫道,在他安頓好“城里人”后,“他最后望了他們一眼。他想:有一天,在他們的城里見面,能認出他來,就行了。”⑤他以回望向“城里人”索取另一樣東西:尊重。這種無聲的訴求邀請我們想象另一幅場景:某一天尼庫到了城里,那他是否能被城市人報以今日般的尊敬的目光?不論如何,在離別之際兩者之間、兩種文化文化之間目光的詢喚,催生了一個人格平等的場域。
三、“時代語境”中的主體性
如果說,文化間性的角度主要從小說內部透析寫作動機,那把作家放在時代語境之中則能看出更多外部關系。“時代語境”提示研究者去追溯作家寫作的語境,看他如何與彼時的思想、情感互動。作為民族文化的“闡釋者”,烏熱爾圖自身的心路歷程也像一個文本,屬于他文學創作的一部分。
(一)故事內外的語境
尼庫的行動除卻“文化間性”之外,小說實際上還暗示山外已是一個“現代”的世界。歷史的維度被作家有限地暴露出來,這種特征在其它的小說中同樣存在。人物在森林中踏上精神追尋之前,實際上常常都是剛從外界的失落中返回。而山外的世界不僅是空間上的異域,還總粘帶提示著時代氣候。盡管小說的主角是林中獵民,但是他們的行動在某種意義上是對外部歷史的回應,包括勞改、“文革”、抗日戰爭等等。森林人物總在中國社會的主流歷史中生成,盡管后者總是被做了虛化處理。而這些被輕描淡寫的部分,在作家文學精神的源頭處也可瞥見。
烏熱爾圖的文學源頭,首先是他對鄂溫克母族的體認。在自傳性散文《我在林中狩獵的日子》(2012)中,他回憶了與鄂溫克產生認同的時刻。在他的描述中,那是具有啟示意味的時刻,意外、神秘,但又命中注定。他的認同產生于對母族口語的聽覺回應。他寫道,他與父親重逢在根河車站,那里人聲嘈雜。但擁擠的車廂里,鄂溫克語使他感到整個世界突然變得開朗明晰。鄂溫克語如同一道亮光,讓他“不再懼怕任何威嚇與欺侮了”。這里的“何威嚇與欺侮”并非泛泛而談,而有特定所指。烏熱爾圖在“文革”期間命運多舛,遭受了許多精神創傷。對17歲的少年烏熱爾圖來說,他工作和精神上受到打擊都是深刻的。散文中寫道他因為政審條件不好,沒有分到好的工作而只能孤獨流浪。我們不難理解,少年烏熱爾圖與父親重逢也是他與母族相認的時刻,孤獨的心靈被鄂溫克母族接納——這完全是由于精神撫慰所需。
(二)不合時宜的人物
作家的心靈經歷讓我們想到,他的小說人物總能在狩獵、追尋行動中,克服來自外界的種種精神壓力和創傷。他帶著記憶寫作,許多成長小說也帶有自畫像的影子,筆下的人物也好像回蕩著歷史的余音。但是正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歷史敘述的年代,而是敘述歷史的年代。
烏熱爾圖創作期集中在八九十年代,也就是現在被普遍稱為“后社會主義”或“后革命”的時期。80年代被認為是“理想主義”的年代,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的全面開放,所謂的“理想主義”也遭遇沒落。但也有學者如賀照田指出“理想主義”的失落在實際上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發生。⑥。80年代精神主體的失落就已經開始蔓延,只不過等到90年代整體新的破碎更為劇烈。在這樣的精神語境下,重審烏熱爾圖小說人物的主體性光亮,能發覺他與主流思潮對話的意圖。不妨把他的人物與“新寫實”小說對比,后者清晰地反映了80年代中期以來人們價值觀和精神狀態的變化。“新寫實”以市民生活的平常瑣事為主要題材,鮮有激動人心的傳奇。“新寫實”充斥著個人生存的矛盾,理想主義消失地毫無蹤影。反觀烏熱爾圖的同期小說,主人公充滿力量,始終持有一個明確而神圣的行動目的。與許多作家在技巧和思想上走向現代主義不同,烏熱爾圖繼續用一種前現代的傳奇手法在塑造“典型人物”,用以回應理想的崩塌。作家的迥異的創作思路中,顯然內蘊著一種對現代性的回應。不過,同執著于“完美圖式”而造成的后果類似,作家的“典型人物”也有過于簡化的缺點。當時代的氣候作用于作家時,他缺少一種更內在的轉化意識。在現代性的腥風血雨中,他讓人物緊握“崇高”的劍柄,但這種崇高缺乏心靈的邏輯依據。
結語
烏熱爾圖在鄂溫克族文學創作上發揮了開荒者的作用。他在《不可剝奪的自我闡釋權》中認為,族群的外來者并不具有權力去篡改他人的形象。對于弱勢群體來說,自我言說和闡釋是不能讓渡的。烏熱爾圖寫道:“強烈的述說與自我闡釋的渴望,使生活在人類早期社會的人們本能地意識到自我闡釋的權利存在于他們之中,存在于他們全身心溶入的部族意識里。”⑦因此,他提出著名的“不可剝奪的自我闡釋權”,說明來自族群內部的闡釋的合法性。
然而,對烏熱爾圖的“民族化”評價,終究是落入了循環闡釋的二元結構中。姚新勇追問到:“究竟存在不存在絕對、純粹、天然的民族文化之聲?”⑧他進一步指出,強調本民族的尊嚴固然不錯,但是分析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關系時,不應該武斷地把問題與某種本質化的民族特性相聯起來,也不應把問題的判斷局限于簡單的二元對立的闡釋模式中。
通過文本細讀,我們已看到烏熱爾圖小說中主體的復雜性:他們是孤獨的,但處于文化間性的關系中;他們行動利索,但攜帶著時代的創傷記憶;他們看起來昂揚崇高,但更多是一種先驗氣質。從作家本人的傳記看,他民族意識的生成伴隨著駁雜的歷史經驗,只有考慮到他少年時代的革命遭遇,才能深刻理解他對鄂溫克的追尋。在“自我闡釋”性質的檔案化寫作中,被轉碼的不僅有族群內部的經驗,族群以外的力量也無形地滲透其中。鄂溫克之外的力量像一只手,無形中影響著作家思想。因此,烏熱爾圖自詡的“自我闡釋權”也并不是“純粹”的鄂溫克的闡釋之音。在族群與外部之間、作家與讀者之間、個人經驗與時代語境之間、小說寫作與歷史寫作之間,充滿著動態的能量的交互。烏熱爾圖的小說寫作,就是這些多種力量博弈、制約、互動的結果。
注釋:
①此類研究的代表性論文有:王瀾:《落日余暉的籠罩──烏熱爾圖小說中的文化思考》,《海南師院學報》,1996年第2期;陳鈺:《鄂溫克文學的話語轉型和建構——以烏熱爾圖的創作為例》,博士學位論文,浙江大學,2013年;孫洪川:《鄂溫克民族靈魂的雕塑——論烏熱爾圖“森林小說”中的獵人形象》,《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王云介:《論烏熱爾圖小說的性別角色》,《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06期;楊蘭:《烏熱爾圖作品中的老人形象淺析》,《文學界(理論版)》,2010年第04期;卜晶磊:《烏熱爾圖小說(1983-1993年)中的人物形象研究》,碩士學位論文,中央民族大學,2017年;王建芳:《烏熱爾圖小說意象論》,碩士學位論文,內蒙古大學,2011年。
②此類研究的代表性論文有:王靜:《自然與人:烏熱爾圖小說的生態沖突》,《民族文學研究》,2005年第3期;王云介:《烏熱爾圖的生態文學與生態關懷》,《黑龍江民族叢刊》,2005年第3期。
③烏熱爾圖:《鹿啊,我的小白鹿》,《七叉犄角的公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頁。
④關于“交感巫術”的理論闡釋,詳見于:[英]弗雷澤:《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徐育新/汪培基譯,大眾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
⑤同上,第60頁。
⑥賀照田:《中國革命和亞洲討論》《當代中國的知識感覺與觀念感覺》,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頁。
⑦烏熱爾圖:《不可剝奪的自我闡釋權》,《讀書》,1997年2月。
⑧姚新勇:《未必純粹自我的自我闡釋權》,《讀書》,1997年第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