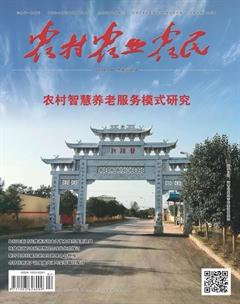精神扶貧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意蘊
謝芳芳
摘 要:在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進程中,精神扶貧思想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立足中國扶貧實際,圍繞動力源泉、核心要義、基本方法三個向度回答了“扶持誰、依靠誰、做什么和怎么做”等理論與現實問題,充分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本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具體運用。
關鍵詞:精神扶貧;馬克思主義;鄉村振興
當前,脫貧攻堅已全面收官,隨著“兩不愁、三保障”脫貧政策的穩定落實,以物質生活貧乏為主要特征的絕對貧困問題已成為歷史。物質層面的絕對貧困可以徹底消除,但精神層面的相對貧困仍將長期存在。探索精神扶貧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筑牢可持續脫貧基礎、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的必由之路。精神扶貧思想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以動力源泉、核心要義、基本方法為向度回答“扶持誰、依靠誰、做什么和怎么做”等理論與現實問題,構成了中國特色扶貧開發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
一、精神扶貧彰顯馬克思主義的人本思想
馬克思主義理論始終以解決工人階級貧困現狀、實現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所有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價值依歸。對馬克思而言,無論是在被資產階級占有全部剩余價值所導致的外部世界貧困中,還是在受商品拜物教所束縛而導致的內部世界貧乏中,作為實踐主體與價值主體的人都被工具化和抽象化了。而其中首要的原因在于工人階級精神生產的萎靡不振與批判意識的消失殆盡。工人階級要擺脫貧困,首先必須恢復自身的主體間性,從“自在”階級變成“自為”階級,亦即實現自身精神的健全與豐滿。在解決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問題的當下,無論人們要實現生存或者生活的最低需要,還是要滿足擁有豐富社會資源的多維需求,僅僅靠“家長式”“輸血式”由外向內式的援助和“拍腦袋、瞎指揮”的辦公室式扶貧方式,往往會使作為主體的貧困者被遮蔽在自上而下的決策計劃之中,最終成為被動服從的客體,一旦失去外在幫扶,貧困者將陷入長期貧困。因此,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的消除和緩解,應該始終堅持扶貧先扶“智”與“志”,引導貧困群眾樹立主體意識,把精神扶貧放在統領解決貧困問題的首要位置。
作為新時代精神扶貧工作的主體,人的自主性和創造性即是主觀能動性,是實現精神脫貧的動力源泉。人的主觀能動性不僅表現在精神領域的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也表現在將觀念轉變為現實存在的實踐活動中,表現在人們的物質交往中。精神貧困大致源于內生性和外生性兩種誘貧類型:前者包括先天稟賦不足,貧困文化基因代際相傳等;后者包括教育資源匱乏,經濟條件落后,社會救助體制失靈等。因此,精神扶貧必須從內生動力和外在動力兩個方面同步推進,既要激發他們求知求上求富的意識能動性,也要催生他們改變生活面貌,完善和創造生活條件、生活環境的實際行動力,全面增強貧困群眾的“自我造血”功能。
二、精神扶貧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
首先,精神扶貧的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契合馬克思主義社會分工理論。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分工能夠提高勞動的生產力,增加社會的財富,但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舊式分工造成勞動的分離和獨立,造成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二元對立,引起工商業勞動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在共產主義社會,腦體勞動對立和城鄉對立將消失,人將得到全面發展,從而真正促進生產力的高速發展。在中國特色扶貧實踐中,要解決農村人口的精神貧困,關鍵在于剔除舊式分工思維。一方面要加快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另一方面要避免現代社會中工具理性、消費至上、面子工程等負面思想侵蝕鄉村社會群體的傳統價值觀念,建設立足鄉土社會、富有鄉村特色、承載田園鄉愁、體現現代文明的升級版鄉村。
其次,精神扶貧的制度完善之路繼承與發展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馬克思、恩格斯通過深入考察資本主義現實經濟生活指出:“工人階級處境悲慘的原因不應當到這些小的弊病中去尋找,而應當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去尋找。”奠基于資產階級社會的“現代國家制度”是造成和固化貧困的根本制度因素。改變勞動者貧困命運的根本途徑在于進行針對社會制度的革命實踐。新時代中國精神扶貧注重筑牢制度根基,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堅持黨在精神文化發展領域的集中統一領導,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農村文化體系和思想道德建設。同時應不斷實現制度改革與創新,在扶貧過程中健全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機制,在扶貧工作評價指標中納入思想道德、文化素質等精神元素。
最后,鄉村文化振興建設充分詮釋馬克思主義精神生產理論。馬克思主義認為:“勞動的對象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人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動地、現實地使自己二重化,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精神生產是在實踐基礎上實現主體客體化和客體主體化的雙向互動過程,是關于思想、意識、觀念的生產,是人與自身,人與社會之間的相互統一。鄉村文化振興建設作為精神扶貧的重要實踐路徑,就是要統籌協調好農民情感取向、心理需要、文化需求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實現群眾個體與鄉村社會的協同發展。
三、精神扶貧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具體運用
第一,精神扶貧立足實踐觀點分析現實問題。精神扶貧從脫貧攻堅實際出發,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強烈的問題意識分析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共同富裕的精神短板。“干部干,群眾看”“等靠要”思想、“靠著墻根曬太陽,等著別人送小康”等問題是扶貧開發的“硬骨頭”。實踐是連接認識短板與補齊短板的橋梁。精神扶貧旨在引導貧困群眾樹立“寧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觀念,認識脫貧致富道路的艱辛曲折,發揚“滴水穿石”般的韌勁和默默奉獻的艱苦創業精神,用自己勤勞的雙手實現脫貧摘帽,開啟新生活的新奮斗征程。
第二,精神扶貧在聯系和發展中整合力量資源。精神貧困不是一個單面向的問題,有安于現狀、不思進取的“無志”態度,有封建迂腐、自我封閉的“無智”意識,亦有好逸惡勞、爭當貧困戶的“求貧”心理。同時,精神貧困也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它與社會、經濟、教育、文化等環節密切相關。因此,精神扶貧中注重扶思想、扶觀念、扶志氣、扶信心多方施力,也強調做好教育工作、維護社會公平、加強就業指導等多措并舉。扶貧工作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特別是從絕對貧困治理到相對貧困治理轉變的過程中,精神貧困特征也會隨之發生相應變化。比如表現出更深層的能力發展障礙,相對更高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多的物質消費欲望等,所以精神扶貧須不斷調整方針政策以適應現實條件的變化。
第三,精神扶貧在對立和統一中充分把握扶貧規律。在落實精神扶貧過程中,正確處理整體與局部的關系。一方面立足于鄉村振興戰略全局,運用整體思維把握未來扶貧中精神與物質、精神與貧困的對抗性關系,確定戰略步驟分階段解決精神貧困問題;另一方面針對不同地區不同人群的精神貧困特征和文化環境特性,運用精準思維制定突出差異化、個性化的精神扶貧方案,全過程、全方位確保精神扶貧的有效性;同時準確把握重點與非重點的關系,深入分析精神貧困現象在城鄉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的不同表現以及背后的根源,著力解決主要矛盾,突出補齊短板,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
參考文獻:
[1]《習近平扶貧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版.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習近平:《擺脫貧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基金項目:潮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課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重要論述的實踐路徑研究”(2019-A-04);廣東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課題“基于大數據的高校思政課“四理貫通”教學理路與實踐圖景研究”(2020GXSZ070)
(作者系韓山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法學博士,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