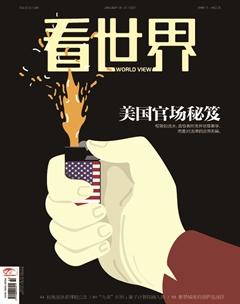“世界最危險街區”里的少年劇團
張侃

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的Livezilor地區
2020年初春,我在羅馬尼亞旅行。首都布加勒斯特的繁華與舒適,讓我很難把這里同“歐盟最貧窮的國家”聯系到一起。“布加勒斯特有窮人嗎?”我終于忍不住,問在這里生活的中國朋友。
“他們在南邊,一個叫Livezilor的地方。”朋友看出了我的心思:“但你別去,那里太危險了,都是吉普賽人。吸毒、犯罪,什么都有。我在這里生活了十幾年,從沒去過那里。”
我又找到羅馬尼亞朋友,想了解更多那邊的信息。如果說中國朋友的語氣還只是略有恐懼,這位土生土長的布加勒斯特漢子,則絲毫不掩飾他的厭惡:“你去那種吉普賽佬的地方干啥!不要命啦?”
“來吧,白天沒事”
我第一次聽到“吉普賽人”這個詞,還是緣于電視里對西班牙弗拉明戈舞的介紹。我曾以為,發明了弗拉明戈舞的他們,只是歐洲一個能歌善舞的少數民族。然而到了歐洲,我才發現平時處處號稱“平等與包容”的歐洲人,卻獨獨對這個外來民族厭惡到骨子里。“小偷”“騙子”“乞丐”,是我聽到的最多對他們的形容。
事實上,“吉普賽人”(Gypsy)本身就是一種蔑稱。這個叫法源于“埃及人”(Egyptian),起因是歐洲人以為這群棕色皮膚的人來自埃及。可他們真正的老家是東方的印度,正確的稱呼應該是“羅姆人”(Rom)。這個以“流浪”為信條的民族,千年前一路從印度漂泊到歐洲,卻始終固守自己的生活方式,拒絕一切融入當地社會的可能。他們常沒有“正經工作”,主要靠手工藝、歌舞與占卜為生,其中也不乏雞鳴狗盜之徒,而這也導致很多歐洲人對他們恨之入骨。
然而,我從不知道那些羅姆人住在哪里,過著怎樣的生活;那個被近乎妖魔化的Livezilor,到底是個怎樣的地方?
把“Livezilor”輸入搜索引擎,蹦出來的第一個網頁,是一位瑞典記者在2015年花3個星期深入其中調查后的報道,其中絲毫沒有掩飾這里環境之惡劣、毒品之猖獗;第二個網頁,Livezilor “榮登”一家英國媒體評選的“世界10大最危險街區”第三名。
然而第三個網頁卻讓我眼前一亮。這里居然有一家名為“Playhood”的劇團,成員全部是這個街區的少年!他們是一群怎樣的人?為何會組建這樣一家劇團?
我給劇團的Facebook主頁留言,很快就收到了英文回復。對方告訴我,他們就在Livezilor街區的某處,當天下午有排練,歡迎我去參觀。而關于我對“去那里是否安全”的疑慮,他的答復很簡單:“來吧,白天沒事。”
懷著半信半疑的態度,我踏上了開往Livezilor的電車。下車以后,還需要穿過大半個Livezilor街區,才能到達他們的地址。一路所見,除了街道臟一些,樓房破一些,并非我想象中危機四伏的貧民窟模樣。孩子們在踢球,歡聲笑語傳遍整個街頭。他們看到我這張陌生的臉孔,爭先恐后地對我喊著“Hello”。
被社會拋棄的“自由人”
網上跟我對話的先生,帶我走進一座(大概是整個街區最整潔的)公寓。院子門口那扇厚重的大鐵門,把這里同外界完全隔離開來,也提醒我:門外的世界,也許并不像我剛剛看到的那樣美好。
他說著同網上一樣流利的英語,卻有一張完全不像羅姆人的臉,年齡就更不像“少年”了。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幸好他及時自我介紹,解答了我的全部疑問。
他叫Ionut,來自北邊的城市錫比烏,在羅馬尼亞最著名的戲劇學院拿到碩士學位后,曾做過演員,后來便把所有精力投入幫助這里的孩子組建“Playhood”劇團。與他一起“并肩戰斗”的,還有他的未婚妻Madalina。
電線是居民私拉的,自來水根本沒有,垃圾遍地,發出陣陣惡臭。

電影預告片中出現的Pl ay h o o d劇團前成員
談到自己的初衷,Ionut說得“感謝”之前看到的一段網絡視頻:一位來自Livezilor的羅姆少年,在沒有任何專業指導的情況下,展現出驚人的表演天賦。那時的Ionut,跟大多數羅馬尼亞人一樣,提到Livezilor和羅姆人,心中只有恐懼與厭惡。而那一段視頻徹底改變了他,他開始有意識地接觸Livezilor的孩子們,直到把“幫助他們”作為自己和未婚妻的人生主題。
“Livezilor的居民都是羅姆人嗎?”“其實也不盡然,也有一些其他族群。但每個家庭都有一個悲慘的故事。”Ionut打開了他的話匣子。
Livezilor曾是布加勒斯特最早的工業區,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80年代“東歐劇變”的近百年時間里,這里一直都是產業工人的聚居地,繁榮而祥和。政治劇變后,這里的國營工廠也失去競爭力,紛紛倒閉。“下崗工人”先后搬離,去別處另尋出路。昔日熱火朝天的Livezilor,逐漸變成一座如美國底特律一般的“工業廢城”。
而在社會主義政府期間被強制上學和分配工作的羅姆人,很多被新社會拋棄,房租足夠低廉的Livezilor就成了他們的樂園。“你相信嗎,就那座樓,20歐元就可以租一整個月!”Ionut指著窗外那幢典型赫魯曉夫風格的老工人宿舍樓說。
擁擠混亂的居住環境,超過80%的失業率,讓這里成為了毒品與犯罪的天堂。唯一沒有的犯罪是入室盜竊—因為他們家里實在沒什么可偷的。很多人幾乎把所有收入都用來買毒品,除此之外唯一的“娛樂”就是生孩子,生一大群孩子。
所謂“融入”,絕不應伴隨著對自身少數者文化的無情拋棄。
政府早就把這里徹底放棄,不再提供任何公共服務:電線是居民私拉的,自來水根本沒有,垃圾遍地,發出陣陣惡臭。學校僅在理論上存在:家長把孩子送去學校,學校會接收,但很多家長根本不愿意孩子去上學。在他們看來,養孩子唯一的目的,就是讓他們盡早出去賺錢(無論是靠正經工作還是犯罪),好供養自己吸毒。

I o n u t帶著孩子們排練劇目臺詞
即便有幸去了學校,孩子們接受的教育也極其荒謬可笑。據Ionut說,學校只教他們31個羅馬尼亞字母的讀音,好讓領導檢查的時候,讓學生裝作能夠“流利朗讀”一篇課文。但學校并不教他們每個單詞的含義,因此他們其實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讀什么,甚至有上了初中的學生,還不會正確地讀“201”和“2001”!
因此,比起“劇團”,Ionut更喜歡稱Playhood為“少年社區組織”。為了讓孩子們看懂表演的劇本,他不得不像小學老師那樣,從零開始教這群大多已十幾歲的少年最基本的文化知識。他憶起剛來這里的時候,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街頭跟孩子們搭訕,問他們想不想一起做點“有意思的事情”。
沒想到,他遇到的最大阻力不是來自孩子本身,而是他們的家長。在那些家長看來,任何阻止孩子早早出去賺錢的事,都是不務正業。“這種情況,直到Playhood開始接到有償演出的邀請,孩子們也有了收入,才變得好一些。”Ionut苦笑著說。
做一個“驕傲的羅姆人”
現在,已經有20多個Livezilor少年加入了Playhood。這間不足30平方米的出租屋,不僅是Ionut和Madalina的小家,更充當著Playhood的工作室。客廳兼廚房是孩子們的“教室”,而狹小的臥室則是他們練習的場所。
帶這群貧民窟少年演出,他們中的大部分又都是羅姆人,會遇到麻煩嗎?Ionut回憶起曾帶他們參加一場觀眾眾多的演出,結果在他們下車走到舞臺時,就遭到了無數歧視與侮辱。觀眾沖他們吹口哨、喝倒彩、大喊歧視的語言;更有甚者,直接朝他們吐口水。

Playhood成員在一家咖啡廳演出
那場演出是Ionut精心設計的一個暗喻:一群人,每人都舉著紅牌子,只有一個人孤單地舉著藍牌子。很顯然,他遭到了所有人的疏遠,陷入了迷茫與彷徨。最終,他無奈地扔掉了自己的藍牌子,舉起了一張與他人毫無二致的紅牌子。
這何嘗不是Livezilor的現狀?先前大多對羅姆人的“幫助”,都是想讓他們掌握現代工作技能。有一些羅姆人走上了這條路,變成“成功人士”,但融入了現代社會的他們,很多卻從此以自己的同胞為恥,甚至再也不承認自己是羅姆人。在Ionut看來,所謂“融入”,絕不應伴隨著對自身少數者文化的無情拋棄。他希望可以挖掘羅姆少年民族傳統中的演藝天分,加以科學與現代化的指導,從而讓他們在演藝中找到自我與自信,做一個“驕傲的羅姆人”。
可惜,短短一場表演,遠不能改變人們心中千百年來的成見。演出結束,他們依舊在一片倒彩聲中黯然離場。但有一位老婦人,專門去后臺找到他們,眼含熱淚,同他們一個個擁抱。她說,那場演出徹底改變了她大半輩子以來的認知。
距離Ionut萌生幫助Livezilor孩子的想法,已經過去了3年。他的第一批成員大多已“畢業”,其中有好幾人,在布加勒斯特的劇團里找到了正式工作,甚至有人在羅馬尼亞最著名導演的電影里謀到了一個角色!
“但是,也有人沒能最終走向正途。就在上周,我們一個成員被關進了監獄。”Ionut遺憾地說。
Playhood的成員們用一場臺詞合練歡送我的離開。盡管聽不懂他們說的每一個字,但我依舊能感受到他們飛揚的青春與自信。
我本想去對面那座幾乎成為Livezilor象征的老工人宿舍樓拍幾張照片,但Ionut阻止了我。他說過去幾年里,有太多獵奇者去那里拍照,其中有人根本是把那里的居民當成動物。因此,曾經發生過好幾起外來者被居民攻擊的事件,特別是那些吸了毒的居民。他不想讓我受傷害,也不想讓那里的居民受傷害。
但他和Madalina還是陪我去那里轉了一圈。我看到的景象,同之前在網上看到的別無二致:垃圾遍地,充滿絕望。而這里,就是剛剛那群排練時神采飛揚的孩子一會兒要回的家,那些在樓下徘徊著、眼神迷離的癮君子,就是他們的父母和家人。我從未見過哪里,“希望”與“絕望”的距離如此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