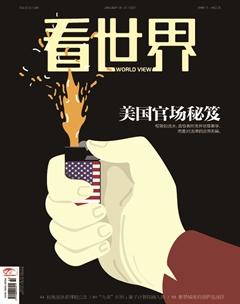致死率高、傳播快的“X疾病”來了?
鄧晨

2014年10月5日,利比里亞,醫護人員抱著一個懷疑染上埃博拉病毒的孩子
2020年年末,據說一種神秘疾病出現在非洲剛果(金)北部的印根德(Ingende),消息最早經過CNN的報道傳遍全球,指出當地有位婦女出現類似埃博拉出血熱的癥狀。但如果查出不是埃博拉,它是否可能是更嚴重的疾病—既有著埃博拉高達90%的致死率,又加上新冠病毒的高傳染性?
這一切還都只是猜測,記者或許是想藉此讓大眾想象未來有可能發生的新型傳染病,但是經過全世界的轉載報道后,信息發生了改變。許多報道都以驚恐的語氣敘述剛果已發現了一位“零號病人”,以為是埃博拉病毒但檢測為陰性,而新病毒可能具有新冠的高傳染性,專家所害怕的“X疾病”恐怕已經到來。
但是,“X疾病”并非指某種特定的疾病。2018年世衛組織列出目前威脅人類最嚴重的傳染病名單,并且在最后加上一項“X疾病”,用意是讓全世界的醫療機構、公衛體系與社會群體建立應對未知傳染病威脅的有效措施,而非讓人們對號指認:“X疾病是否要來了?”“新冠是不是就是X疾病?”“剛果出現X疾病了嗎?”
信息傳播的速度,顯著高于病原體傳播的速度。研究復雜系統效應的科學家杰弗里·韋斯特推算,如果每位新冠患者的平均傳染數是2.5左右,推特信息的“傳染力”就大概是5,關于“X疾病”的新聞傳播肯定又要更快。在這個意義上倒也可以說,“X疾病”確實得到了全球性的傳播推廣。
應對X疾病的措施
埃博拉初現癥狀后的病程約為7~14天,剛果的“神秘疾病”新聞已超過兩周沒有更新,但“X疾病”這個概念已經快速傳播全球。
“X”是指一種“未知”,因為人們還不知道哪種病原體將造成大流行,但又不是對其一無所知,因為我們憑借過去的經驗可以推測它的來源,也能預想應該如何應對未來的大流行。它是一種“可知的未知”。
經過疫情的沖擊,大多數人都已經被科普過冠狀病毒從蝙蝠傳播到果子貍、穿山甲,再進一步傳染給人類的過程。10年前的美國電影《傳染病》則用影像故事把傳染過程呈現給一般大眾,其劇情是基于1997年尼帕病毒在東南亞的散播過程:宿主蝙蝠的唾液進入養豬場的飼料槽、人類所食用的椰棗果汁里,再透過豬和人、人與人之間的傳播擴散。尼帕病毒的傳播是流行病學上最明確的實例之一,而對于現在的新冠流行,我們還很難明確知道中間經過了哪些動物。
既然跨物種傳播已經是新型傳染病常見的途徑,盡管不知道下一個疾病會是什么,但人們卻可以嘗試從這方面下手。例如,學術團隊就開始到荒野中大量采集各種動物身上的病原體,帶回實驗室建立資料庫。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疾病預測項目從2009年開始,收集了超過14萬個樣本,從里頭辨識出大約1200種有可能致病的病毒,包括160種以上的新型冠狀病毒。
由流行病學家丹尼斯·卡羅爾領軍的“全球病毒組項目”范圍更廣大,計劃花費12億美元,收集60~80萬種對人類可能有害的病毒進行測序,定位每一種病毒的特性、宿主、地理分布,構筑起全球的病毒監控網絡。那么,當任何一種病毒從動物傳播到人類的時候,有關機構都可以立即響應,利用資料進行診斷、治療或疫苗研發。
尼帕病毒的傳播是流行病學上最明確的實例之一。
另外一種方法是,檢測人類社群的新陳代謝產物。根據西班牙巴塞羅那大學團隊的發現,當地2019年3月的下水道樣本中,疑似已有新冠病毒基因的存在;意大利、巴西也有類似的報告,雖然只是提出了可能性,但是監控污水中排泄物里的病原體,確實可以用來偵測傳染病。
如果上面幾個計劃是與病毒交手前的“敵情偵測”,那么還有很多工作是為實際交手做準備,例如建立各種行政部門的應變方案,在合適的地點建立醫療站等等。像是疫苗,就需要有效的冷鏈運輸,才能將其送到各地。輝瑞的mRNA新冠疫苗需要零下70度的低溫保存,世衛在剛果也曾利用零下70度的冷鏈配送30萬劑埃博拉疫苗。冷鏈的環節必須得到縝密維護。

非洲剛果(金)北部的印根德
跨物種傳染,經常來自人們進入叢林開發或捕獵,使物種間發生越來越頻繁的接觸,那么在“同一健康”的架構下,把環境、野生動物保護與公共衛生結合在一起,或許才能真正避免野外病原體源源不斷引發疫情。例如,環保組織ASRI在印度尼西亞的婆羅洲等地推動“電鋸換健康”的計劃,規定凡是放棄非法伐木者,都可以享有醫療優惠或獲得就業協助。由此,當地不僅盜伐下降了90%,兒童死亡率也降低了2/3。
顯微鏡下的全球交流
在新冠肆虐的時代,或許人們會比較容易領會到我們既是人,同時也是一堆細胞所組成的,如果要對付傳染病,就必須進入細胞與病毒的微觀視角。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視角就像電影里的“蟻人”,不斷在大與小之間切換。
多細胞的人類個頭太大,必須用顯微鏡才能看見自己也是由無數細小零件組成的。肽組合成氨基酸,氨基酸裝配成蛋白質,而蛋白質可以組成細胞、病毒等能夠不斷復制、繁衍的形態。
6億年前,單細胞生物開始轉變成多細胞動物,每具人體據估計有30萬億~60萬億個細胞,還有眾多的細菌與病毒藏在人體里,包括遠古時期感染的病毒片段也存留在我們體內。病毒是由核酸長鏈(DNA或RNA)與蛋白質外殼構成,帶有遺傳訊息的DNA片段被稱為基因,人體有8%的基因是來自病毒。
人體有8%的基因是來自病毒。
對于微生物來說,我們的身體就如同綿延起伏的崇山峻嶺,生物學家會研究它們如何在身體不同區域形成群落,或者建立互賴共生的關系。例如,最為人熟知的腸道菌群,就與人體運作有極為密切的連結。不過,這種關系有時是很微妙而脆弱的—人們可能不經意就破壞有益的腸道菌群,而腸道菌也可能侵入人體,尤其是在人死后,很快便開始吞吃身體器官,一點也不顧情面。

1996年4月12日,剛果基威特一家醫院內生病的孩子
在人體之外當然也到處充滿病毒,科學家估算地球上的病毒數量可能達到10的31次方,但是絕大多數病毒個體都不會造成人類的疾病,倒是在生態系統里有重要的作用。例如,海洋里的噬菌體病毒每天會消滅大量藻類與細菌,形成一種生態平衡,讓浮游生物不至于被細菌欺負。這些浮游生物估計產生了地球上一半的氧氣。
海底也有大量病毒存在,在海底火山活躍的地區,通常有很多所謂的“海底熱泉”或“海底煙囪”,其周圍的微生物十分耐熱。科學家利用在這些地方找到的噬菌體病毒,可以制出特別抗高溫的耐熱酶。這類耐熱酶使得對抗新冠病毒所必需的核酸檢測PCR技術,變得更為低成本且快捷。
可是,除了對海底熱泉的生物學研究之外,特別熱衷海底資源的還有采礦企業。大規模的海底采礦作業,可能造成嚴重污染與生態破壞。陸地上的人們覺得海床上貌似只有沙石淤泥與丑陋的怪蟲,但是其中蘊含的無數細菌及病毒,對于海洋生態系統的碳循環起到重要的作用。就像雨林生物蘊含著豐富的知識寶藏,生物學家也希望保全海底病毒的原生態—很可能當中還有像耐熱酶一樣重要的生物資源。

2019年8月31日,國際紅十字會和剛果紅十字會工作人員走訪當地社區,調查埃博拉疫情
把海床與雨林的例子聯系在一起看,其實可以讓問題的樣貌顯得更加清楚:人類不斷在探索開發自然界,不論是實驗室里的白袍研究人員、海洋深處的地質探勘鉆子,還是雨林里的開墾農民,都在不停擴張人類科學知識與經濟資源的前沿,各種力量使得人們往雨林與海洋的更深處前行。在這過程中,我們會與陌生的微生物發生越來越多的接觸。伴隨著物質與人員的流通進入世界各地的,有時是新冠病毒,有時是核酸檢測用的耐熱酶。
模糊的“人類”與“自然”
雖然新冠已被證明與生物武器無關,但就技術上而言,人造合成生命的研究早已如火如荼地進行著。雖然X疾病未必會是生物武器,但根本上人類已經在進入人造合成生命的時代。相較于把風險設想為在野外的病原體,人造合成生命是把危機放回了人類社會內部。
事實上,讓人們不斷往雨林和海床開掘資源的,一直都是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力量。不過,隨著高科技操縱自然的力量越來越大,實驗室與工廠的倫理責任會更加受到關注。
1930年代福特汽車公司在亞馬孫雨林開辟橡膠園,在瘧疾的肆虐與工人罷工下悻悻然退出叢林。后來,人造橡膠工業興起,但也并未完全取代天然橡膠。人造與自然會處于并存的狀態,或許未來的病毒也是如此。
其實從病毒的視角來看,人與自然的界限從來都不明顯;科學家發現,新冠病毒其實已經“重回野外”,出現在野生水貂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