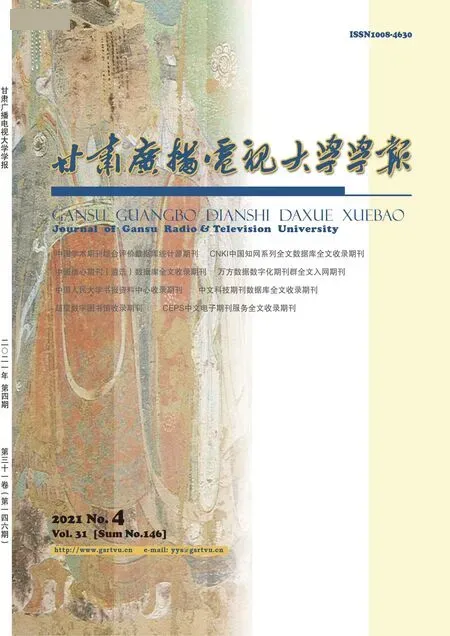蒲松齡文章的文體特征
——兼與《聊齋志異》小說文體進行比較
楊 超,任競澤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119)
清代的蒲松齡素以文言短篇小說《聊齋志異》享譽古今,并不以駢、散文寫作名世,歷來研究蒲松齡的文章論著中也較少提及其于《聊齋志異》之外的創作。但實際上,據蒲松齡世孫蒲庭橘所撰《〈聊齋文集〉志》記載,清代《聊齋文集》收錄蒲松齡駢、散文“共計四百余篇”[1]428,經后人遞相摭拾,1998學林出版社出版的盛偉編《聊齋文集》收錄文章已增至六百余篇,其中賦、傳、記、引、序、疏、論、題詞、文告、婚啟、行實、祭文、雜文等“諸體皆備”[1]428。王士禛評蒲松齡之文“卓乎成家,可傳于后世無疑也”[2]541。清人朱子青亦題辭評其文“蒼潤特出,秀拔天半,而又不費支撐,天然夷曠,固已大奇;及細按之,則又精細透削,呈嵐聳翠,非復人間有”[2]541,可見聊齋之文不僅數量眾多,兼備眾體,且具有頗高的藝術價值。
一、應用類文體中的民本思想
文學產生之初即是為社會政治服務的,因而中國文人歷來十分重視文學的社會政治功用及應用類文體的寫作。孔子曾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3]1106(《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其中的“言”,指的是有外交之用的辭令,孔子認為晉國成就霸業,鄭國攻陷陳國,外交辭令起了重大作用,充分肯定了實用性文體的價值。曹丕也在《典論·論文》中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4]159,標舉文章的政治實用功能,又提出“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4]158四科八體論,其中奏議、書論、銘誄三科六體皆為應用文體,并說:“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4]158,對應用類文體的審美價值予以充分的肯定。此外,劉勰在《文心雕龍·書記》篇中也為事務文書等應用類文體正名:“并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疏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5]460可見劉勰雖偏愛文學性文體,但也反對文人徒追求浮華辭藻而忽視事務文書等應用類文體的寫作。又在《程器》篇中強調:“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于政事哉!”[5]720認為為文要經綸政務,文學創作的才能也應發揮于應用類寫作方面。于此方面,蒲松齡也在《〈古香書屋存草〉序》中道:“自古文人,多為良吏,可以知弦歌之化,非文學者不能致也。”[2]37在充分肯定文學經世致用之社會作用的同時,也表達了文章須有益于民生教化的要求。
清初蒲松齡因家境貧寒而長期在縉紳人家坐館謀生,其間便代當地的縉紳名流寫了大量實用性文章,蒲松齡在《聊齋文集自序》中曾說:“吾邑名公鉅手,適漸以凋零,故搢紳士庶,貴耳賤目,亦或闕牛而以犢耕。日久不堪其擾,因而戲索酒餌,意藉此可以止之;而遠邇以文事相煩者,仍不少也”[2]1。蒲松齡所作雖多是代人歌哭的應酬文字,但他也曾是貧窶大眾的一員,飽受生活貧困與科舉失意之苦,深刻關切并同情同樣苦難深重的百姓,因而其應用類文體的寫作中也包含著濃厚的民生意識。除其在做知府幕僚期間代人寫了諸如《代王侍讀與布政司何書》《正月七日上總督麻(代孫蕙)》等反映民情、為民請命的公文之外,他自己的文章也體現著舊時代知識分子關注廣大勞動人民生活境遇、同情百姓疾苦的民生意識。據路大荒《蒲松齡年譜》記載,康熙四十三年(1704),淄川接連發生了水災、蟲災、饑荒等,蒲松齡寫下《康熙四十三年記災前篇》《秋災記略后篇》。在這些篇章中,蒲松齡不僅記錄了自然災害之景象,更用大量筆墨寫出了災害引發的民生凋敝、哀鴻遍野、盜犯橫行之慘狀:“家中粟盈斗,錢盈貫,箱有完衣,目即莫敢暝,防少懈,白刃加頸矣,故有朝而素封,夕而丐食者”[2]18,“去歲道有棄兒,慈者猶或收育之,今則號嘶路側無顧者”[2]22,“去年天作孽,邑絕貧民;今年再作孽,邑無富民。今年之天,又作來年之孽,恐邑少生民矣!”[2]22蒲松齡更在《救荒急策上布政司》一文中提出諸種賑災救災之策,字里行間透露著他以救民為己任的民本思想。
蒲松齡不僅悲憫于百姓所受的自然災害之苦,對于官弊病民現象也表現出為民請命的自覺意識。康熙四十八年(1709),淄川縣新任漕糧經承康利貞“妄造雜費名目”[2]132,盤剝百姓,民不堪命,然而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邑中已革漕糧經承康利貞,厚賂新城已罷刑部尚書王士禛(漁洋)、同邑進士譚再生(無競)為之關說,復其舊職。合縣聞之皆驚。先生憤然致書王士禛,并同張益公致書譚再生,直陳此事。據此可知當時鄉宦之行為與先生關心合縣人之利益也”[6]57。蒲松齡憤然連書《上王司寇書》《與孫艾文轉示吳縣公》《與張益公同上譚無競(再生)進士》三封書信,“直陳此事”[6]57,為民奔走呼號。在《上王司寇書》中,他直陳“適有所聞,不得不妄為咨稟:敝邑有積蠹康利貞,舊年為漕糧經承,欺官虐民,以肥私橐,遂使下邑貧民,皮骨皆空”[2]130,進而勸王士禛與淄川知縣“別加青目,勿使復司漕政,則浮言息矣”[2]131。在《與孫艾文轉示吳縣公》中,蒲松齡憤然反詰:“小民有盡之血力,縱可盈取,橐役無底之貪囊,何時填滿?官不知為民賊,而視為良臣,牢不可破,如何如何!”[2]132又于《與張益公同上譚無競(再生)進士》中痛批康利貞欺官虐民的行徑:“想一啖人肉而不忘其美,故不惜重金以購之也,聞者莫不失色!”[2]132其為保護淄川百姓的利益奔走呼號,彰顯蒲松齡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蒲松齡在書、序、疏、呈中也表現出對百姓日常生活的關心。《〈藥祟書〉序》體察山村百姓“不惟無處可以問醫,并無錢可以市藥”[2]35之苦楚。《粟里建橋疏》關注農村基礎建設之不足,呼吁“共發微愿,創小橋以便行旅”[2]92。《請表一門雙節呈》以一腔熱血為淄川婦女王氏的貞烈之節求“一字褒揚”[2]239,以彰其德行,樹淳樸民風。甚至在《與邑侯張石年(嵋)》《又與李希梅》等私人書信中,蒲松齡也在為涉及百姓的種種瑣事而籌謀。總之,蒲松齡在各種體類的應用性文章中,都表現出對清初百姓生活的關注,以及對底層人民悲慘生活狀況的同情,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和民本意識。
二、聊齋文的駢體書寫
清代被視為駢文復興的朝代,“有遠承唐宋、超邁元明的氣局”[7]19。受文化環境的影響,以及為人做幕的應酬需要,蒲松齡的大量文章都以駢體書寫,且其甚長于駢文寫作,“豹巖太史目以單行之神,作排偶之體,一切開闔動蕩,音韻鏗鏘,無不膾炙人口,神妙不亞六朝;漁洋司寇,亦稱可與陳其年相伯仲,非尋常流輩可及也”[2]542。蒲松齡的駢文,大多為應酬往來而作,其代孫蕙所擬《十一月二十三日賀濟南太守》《十二月初六日賀曹太守署淮陽道印》《二月二十二日答徐山卓書》等都是典型的應酬文字。這些文章以“伏以霜節高懸,四履慰甘棠之愿;星標孤峙,五馬生繡豸之輝”[2]167一類的恭維語開頭,以“謹恪將乎芹悰,聊鳴歡于賀燕,仰希叱茹,不禁榮施。臨稟曷勝瞻切忭舞之至”[2]167之類套話結尾,是標準應酬文字的體式。此外,蒲松齡也用駢文寫作了諸如《重修玉谿庵碑記》《募建西關橋序》《賀周素心生子序》《〈我曰園倡和詩〉跋》《唐太史豹巖先生命作生志》等大量碑記、序跋等應用文。
以駢文體式寫作官府公文、應酬文字等應用文的傳統由來已久,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道:“從當時(六朝)的文集來看,除詩賦的明顯駢化以外,舉凡一切公牘文如詔、令、表、疏,和一切應用文如碑、銘、誄文、祭文,以及書信之類,已經都用駢體了。”[8]155到了宋代“舉凡一切官府文書如章、表、制、誥等,均用此體,并且四六句的格式更嚴,更趨于定型化”[8]147。宋以后,“所謂散、駢之爭雖然還幾度起伏,但駢文只在公文、應酬文中還可以逞其余技”[8]162,而蒲松齡不僅用駢文形式寫了諸多應制之文和官府公文,還把日常生活瑣事引入駢文的書寫范圍,擴大了駢文的題材,為駢文增添了趣味性。如《為花神討封姨檄》開篇即控訴風神“飛揚成性,忌嫉為懷。濟惡以才,妒同醉骨;射人于暗,奸類含沙”[2]370,之后以“昔虞帝受其狐媚,英皇不足解憂,反借渠以解慍;楚王蒙其蠱惑,賢才未能稱意,乃得彼以稱雄。沛上英雄,云飛而思猛士;茂陵天子,秋高而念佳人”[2]370一系列典故責斥封氏狐媚邀寵,日益恣肆,以趣味之筆表達出作者憎惡豪強、同情弱小之心。在《責白髭文》中,作者以戲謔之筆責怨髭神:“官有汝則致惡于大僚,士有汝則取厭于文宗。馮唐于焉淹蹇,顏駟因而飄蓬。嗟汝白髭兮胡不情?汝宜依宰相,汝宜附公卿,勛名已立,尚不汝驚。我方抱苦業,對寒燈,望北闕,志南溟;爾乃今年一本,明歲一莖,其來滾滾,其出營營,如褦襶之客,別去復來,似荒蕪之草,鏟盡猶生,抑何顏之厚而不一頳也?”[2]375通過寫與虛幻髭神的辯論,感嘆自己懷才不遇、垂老無成的忿懣。
駢文寫作歷來注重辭藻華美、對偶精妙、音韻鏗鏘等形式,乃至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片面追求文采,缺乏真實內容情感的弊端,正如褚斌杰先生所言:“它卻往往以形式和技巧的追求來掩蓋空虛貧乏的內容。”[8]155劉勰也曾在《麗辭》篇批評此類駢文“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5]589。而蒲松齡的駢文克服了徒事形式而缺乏內容、情感不足的積弊。《陳淑卿小像題辭》用近千字深情緬懷陳淑卿,“所恨離奢會促,孫子荊怨起秋風;可憐樂極哀生,潘安仁悲深長簟!香奩剩粉,飄殘并蒂之枝;羅襪遺鉤,凄絕斷腸之草!半杯漿水,呼小歲之兒名;一樹桃花,想當年人之面。”[2]104情濃意切,融入了作者無限情懷。《公祭西河王粹中先生》中以駢文形式述王粹中生平經歷:“嗚呼!自古及今,人誰無死?行路傷心,獨我夫子!竊于立雪之余暇,悉平生之逸軌。生困苦而艱難,質聰明而秀美。其就傅在垂髫之年,而入泮猶弱冠之士。學洛緯而濂經,文蛟騰而鳳起。設絳帳于顏山,倡絕學于范水。濟濟者半出門墻,英英者悉為桃李。”[2]314還表達出了深切的惋惜和痛心:“何文人國士,偏逢百罹?少陵每多險阻,仲宣乃有流離。旻天不吊,靈椿萎矣!閔兇再遘,庭萱摧矣!雜英滿地,揚風吹矣!憂刀割腸,架衣悲矣!煢煢一身,形影相依。遭逢若此,真所謂有一無兩,不可思惟者矣!”[2]314全文在兼顧駢文形式特點的同時,具有感人肺腑的情感力量。另《祝辭》控訴貪官惡吏于民之害,“設宏霸一日不死,則床寢難安;脫魚宏半載猶留,則人民欲盡”[2]367充滿填膺之義憤;《賭博辭》警勸賭博傾產亡家之危,“門前賓客待,猶戀戀于場頭;舍上煙火生,尚眈眈于盆里。忘餐廢寢,則久成入迷;舌敝唇焦,則相看似鬼。”[2]369諷刺警戒意味尤甚。總之,蒲松齡駢文寫情者,情感充沛感人;描事者,內容廣博真實,在兼顧文辭華美等駢文藝術表現形式的同時,豐富了駢文的表現內容,為駢文發展注入了新鮮活力。
三、聊齋文“尊體”特點與《聊齋志異》“破體”之比較
《聊齋文集》與《聊齋志異》雖同出于蒲松齡之手,但二者卻表現出不同的文體意識。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評價《聊齋志異》文體:“《聊齋志異》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劉敬叔《異苑》、陶潛《續搜神記》,小說類也;《飛燕外傳》、《會真記》,傳記類也。《太平廣記》事以類聚,故可并收。今一書而兼二體,所未解也。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今燕妮之詞,媟押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之?又所未解也。”[9]472雖是批評之語,卻一語道破《聊齋志異》對傳統文言小說體例的突破,“一書而兼二體”[9]472點明了《聊齋志異》的破體特點。馮鎮巒《讀〈聊齋〉雜說》也道:“此書即史家列傳體也,以班、馬之筆,降格而通其例于小說。……《聊齋》以傳記體敘小說之事,仿《史》、《漢》遺法,一書兼二體,弊實有之,然非此精神不出,所以通人愛之,俗人亦愛之,竟傳矣。雖有乖體例可也。”[10]924雖認為《聊齋》之體“弊實有之”[10]924,但也肯定了《聊齋志異》“有乖體例”[10]924的破體特點。魯迅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點明了《聊齋》在文體上的突破與創新:“《聊齋志異》雖亦如當時同類之書,不外記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寫委曲,敘次井然,用傳奇法,而以志怪,變幻之狀,如在目前;又或易調改弦,別敘畸人異行,出于幻域,頓入人間;偶述瑣聞,亦多簡潔,故讀者耳目,為之一新。”[11]167認為此書寫神仙鬼怪故事,形式上“用傳奇法,而以志怪”[11]167,完全打破了傳統志怪小說粗陳梗概的寫法;內容上“易調改弦”[11]167,不同于傳統志怪“發明神道之不誣”[11]41的套路,這樣的文體創新突破傳統,打破窠臼,因而“讀者耳目為之一新”[11]167,既指出了《聊齋》的破體特點,又對此予以了充分認可。
不同于《聊齋志異》對傳統文言小說體例的突破,聊齋文則表現出鮮明的尊體特征。正如劉勰在《通變》開篇所言:“設文之體有常”[5]519,即特定的言說內容要放入特定的文章體制中,且文章體制的安排有一定的規范。其書信諸如《與李淡庵》《又呈崑圃黃大宗師》均“本在盡言,言以散郁陶,托風采”[5]456“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5]456,為“心聲之獻酬”[5]456;奏箋如《上孫給諫書》《上王司寇書》等,“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5]457;《徵畢信涉逸老園詩啟》《邀景夏孫學師飲東郭啟》等啟文“斂飭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5]424;《責白髭文》《為群卉揭乳香劄子》等雜文“發憤以表志”[5]255“淵岳其心,麟鳳其采”[5]255,等等,聊齋它的諸種文體皆合各體之大要,寫作方式體現出尊體為文的特點。
劉勰在《文心雕龍·風骨》中關于文學尊體有云:“若夫熔鑄經典之范,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騖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經矣?”[5]514他認為創造新穎的文意,要以學習經典,通曉文體文情為基礎。蒲松齡曾投身舉事,又作為坐館先生教導學生潛心舉業,學習儒家經典自然不必多說。蒲松齡又在《聊齋文集自序》中說自己“每于無人處時,私以古文自效”[2]1,張元所撰《柳泉蒲先生墓表》中也記載,蒲松齡落第之后“肆力于古文”[6]72,可見其對古文經典的重視。王士禛在《題〈聊齋文集〉后》言:“八家古文辭,日趨平易,于是滄溟、弇州輩起而變之以古奧;而操觚家論文正宗,謂不若震川之雅且正也。聊齋文不斤斤宗法震川,而古折奧峭,又非擬王、李而得之,卓乎成家,其可傳于后無疑也。”[2]541也從側面肯定了蒲松齡對前人經典之作的學習。蒲松齡在《聊齋志異·司文郎》中借僧人之口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歸、胡何解辦此!”[10]743表達了對“卓然成大家”[12]351歸有光的推崇。正是在學習古文經典,通曉古文文體文情的基礎上,其文章才達到“穎發笤豎,詭恢魁壘,用能絕去町畦,自成一家”[6]72之成就,亦即《風骨》篇所言“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5]514之境。但其實不論是聊齋散文之尊體還是《聊齋志異》之破體,都是殊途同歸,正如《柳泉蒲先生墓表》中所云“要歸于警發薄俗,而扶樹道教”[7]72。
綜上所論,蒲松齡作為有清一代文學大家,其文學成就的光輝不應僅集中于文言小說《聊齋志異》。雖曹丕認為“文非一體,鮮能備善”[4]158,但蒲松齡實可謂通才,其文章創作不僅兼備眾體,各體皆具特色,且能在尊其體例的基礎上,拓寬題材表現領域,融入主體思想傾向,并以鮮明的個人特色為多種體類文章的創作注入新鮮活力。其文章中表現出的儒生情懷上承杜甫,其寫作大量的駢文下開清代駢文之“復興”之勢。研究蒲松齡各體之文,對于研究清代文學發展源流及中國文學文備眾體的民族特點,無疑是極具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