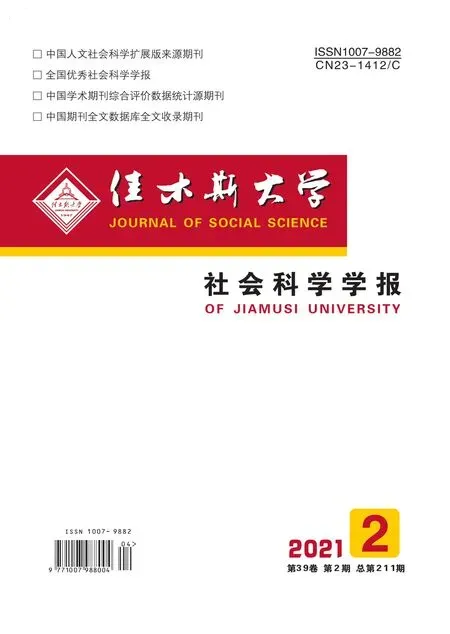李賀神鬼詩的無意識解讀*
呂曉波,孫惠欣
(1.延邊大學 朝漢文學院,吉林 延吉 133000;2.大連大學 文學院,遼寧 大連 116622)
一、李賀生平及無意識理論
李賀,字長吉。他短短27年的生命里,經歷中唐德、順、憲三朝。創作了 233 首詩歌,在詩歌史上做到了獨樹一幟,其詩歌體裁類型多樣,尤其是描寫天神、鬼魂的詩歌為歷代文人所喜愛,同時也奠定了其“詩鬼”的稱號。據學者陳友冰統計,神鬼詩在李賀詩歌中約占 60 首,是其創作總量的四分之一[1]80。以往對李賀神鬼詩的研究更多地傾向于其藝術特色以及詩歌所抒發的思想感情,但是很少有人從無意識理論的角度探尋李賀神鬼詩中所隱藏的潛意識。弗洛伊德曾在《自傳》中說道:“一個幸福的人從來不會去幻想,只有愿望難以滿足的人才去幻想,而文學中每一個幻想即是一個愿望的滿足,都是對令人不滿的現實的一種補償。”[2]429李賀作為一個短命詩人所創作的神鬼詩中充斥著光怪陸離的種種幻想,這些幻想即是李賀在現實中難以滿足的愿望,通過將這些神鬼詩的無意識解讀,我們將可以對李賀的認識更深一步。
弗洛伊德在 1900 年發表《釋夢》,就開始為文學解析在精神領域打開了一扇窗,運用弗洛伊德的理論,解析文本表層之下的作家心態以及他們的潛意識心理[3]87,對于了解作者創作動機理解文本有著重要意義。弗洛伊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將人的潛意識中的核心都看作是性本能,認為文學創作是被壓抑的性本能的升華釋放。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弗洛伊德發現原先的自我本能與性本能難以說明戰爭中的挑釁、分裂、屠殺、破壞等現象,因而在 1920 年發表的《超越快樂原則》中又提出了生本能與死本能理論作為補充來揭示人性中的破壞性與建設性。本文將從弗洛伊德無意識理論中的生本能、死本能以及戀母情結的角度對李賀的神鬼詩進行解讀。通過對其神鬼詩的無意識解讀,我們可以從李賀神鬼詩光怪陸離的表層之下,找尋其隱藏在心間的潛意識,進而把握其詩歌意蘊并更為深切地了解這位短命詩人的心理狀態。
二、李賀神鬼詩中所表現的無意識
(一)強烈的生本能意識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綱要》中談到所謂生本能,即表現為一種愛與建設的潛意識。這種愛可以包括對人類、對萬物的愛,通過這種愛來抵御死亡。這種建設包括建設美好之物,將其生命投入建設之物中以獲取長生。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渴望生命,渴望美好的意識狀態。李賀的神鬼詩中表現出強烈的生本能意識。
李賀,字長吉。在《說文解字》中:吉,從士口,善也。善也就是好,長吉則是隱喻著李賀父母對其生命的期望。在李商隱所做的《李長吉小傳》中得到了李賀的樣貌:“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4]4李賀在《 春歸昌谷》:“終軍未乘傳,顏子鬢先老。”[5]226終軍是漢代的一名十八歲的將軍,十八歲時得到了漢武帝的重用,而李賀還未到十八歲便已經白頭,而少年白頭正是早衰的癥狀。另外在《詠懷二首》中:“舊夕著書罷,驚霜落素絲。”[5]46在《傷心行》中:“秋姿生白發, 木葉啼風雨。”[5]115李賀都在反復提到自己早衰生白發的身體狀態。從以上可以得出,李賀自小便多病,在成長的過程中又產生了早衰癥狀,包括其27歲的早逝都說明了李賀短暫的生命是時刻受到威脅的,越是受到死亡的威脅,他便越發瘋似的創作,越發瘋似的吮吸生命中的美好。在他所創造的神鬼詩中,則幻想建設美麗的天界,逍遙的神仙,對屈死冤魂的憐愛。
如《天上謠》:
天河夜轉漂回星,銀浦流云學水聲。
玉宮桂樹花未落,仙妾采香垂佩纓。
秦妃卷簾北窗曉,窗前植桐青鳳小。
王子吹笙鵝管長,呼龍耕煙種瑤草。
粉霞紅綬藕絲裙,青洲步拾蘭苕春。
東指羲和能走馬,海塵新生石山下。
[5]70
在這首詩中李賀創造出了一個美麗的天界,天界的一切分外的美麗,由玉所制成的宮殿旁種植著桂樹,桂樹的花朵又長久地未落,美麗的仙子穿著綾羅飄帶采著桂香,秦妃居住之地窗前種植梧桐,飼養小鳳凰。有仙人吹笛,有神物勞作。更為讓人羨慕的是,天界與人間的時間變化之大。天界時間似乎是靜止的,在這樣幻想的天界,李賀沉醉其中,所書寫的天界是充滿魅力的,令人所向往的。他在現實世界的失望,促使他對于這天界景色進行美輪美奐的創造,創造的越是美麗,便越是李賀對其生命本身濃烈的熱愛。
在《夢天》中:“玉輪軋露濕團光,鸞珮相逢桂香陌。黃塵清水三山下,更變千年如走馬。”[5]92天界美妙的月光中,詩人與仙子相遇在天界,而此時人間的時間更是千年如走馬般地流逝,以人間時間的快速流逝來凸顯天界的時間永恒。李賀所創造的天界是美麗的,時間是近乎靜止的,而時間也即是意味著生命的永恒。李賀的早衰以及多病使他日夜感到生命的短促,因而作為其所幻想的神鬼詩變成了他的寄托,他希望通過自己所建設的神界以求獲得生命的長久。在李商隱所做《李長吉小傳》中:“恒從小奚奴,騎巨驢,背一古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并且非大醉及吊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4]29李賀對于詩歌的創造的熱情幾乎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越是瘋狂地創造越是顯示出其內心對于生的渴望,這一切正是其潛意識中強烈的生本能的展現。在《綠章封事》中:“愿攜漢戟招書鬼,休令恨骨 填蒿里”[5]99。在《秋來》中:“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李賀對于死去的鬼魂也是抱著極大的同情與憐愛的,他由自身的痛苦遭遇想到了已經死去的冤魂,并且為這些鬼魂鳴不平,為其招魂。之所以在后人看到李賀神鬼詩中的鬼魂并不覺得恐怖,反倒有一絲的同情正因為李賀在詩歌中所創造的鬼魂形象所灌注的正是對這些屈死鬼魂的憐愛,而這憐愛與同情,正是人類所共有的對于生命本能的熱愛,故而能引發產生強烈的共鳴。
(二) 無助無望的死本能意識
死本能意識即一種向死的意識,人類的最終歸宿是指向死亡的。其表現為某種侵略本能、自我毀滅的本能,是追求生命的終結,將有機體的生命帶回到無生命狀態。根據弗洛伊德闡述,死本能包含了兩種形式:一種是向內的,如人的自我譴責、自我懲罰、自殺等等。第二種是一種向外的形式,表現為毀滅規則、毀壞他物等等[6]180。雖然人生的目的最終指向死亡,但現實中卻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輕易地選擇死亡。當人生遭遇到巨大的挫折或難以克服的心魔時,這種潛藏在心間的死本能意識便會涌現出來。
李賀在其短暫的27年生命里,在他人生的前17年里,他有很多時間都在河南福昌的昌谷縣度過,那里美麗的鄉間田野,俊秀的山峰給李賀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作為皇室后裔的個李賀。在他的詩中反復申明自己的皇族后裔身份,這樣的皇室身份的他應當有所作為,應當出人頭地,故而他發奮讀書,渴望功名希望重振家世,光耀門楣。在15歲時便以樂府歌詩名于時,可謂初嶄頭角,在他認為這一切應當順利的,可是卻因為其死去的父親之名晉肅,時人抨擊他,挖苦他,他最終未能參加進士考試。這一打擊對李賀而言似乎是巨大的,在強大的世俗面前他是無助的。雖然之后李賀又輾轉各地求取官職,但究竟無 所得,最后在二十二歲那年獲得了一個從九品的管祭祀的奉禮郎,他皇室王孫的身份卻做了一個管理繁瑣祭祀的小官。他無望地在長安待了三年,最終病歸故里。仕途的無望加上常年的多病,讓他求死而不能,這期間在的神鬼詩中大量書寫的都是一些具有破壞與毀滅性的形象。弗洛伊德認為:“藝術家在創作中從現實轉開,并將全部本能沖動轉移到他所希望的幻想生活的創造中去。”[2]430當李賀從苦難的現實生活中移開,將潛意識中的死本能釋放在他所創造的神鬼詩中,在他的神鬼詩中便呈現出的是譴責,或是破壞,或是毀滅,所表現的正是其無助無望的死本能意識。
以《金銅仙人辭漢歌》為例:
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
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
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
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
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
[5]199
這首詩作于李賀辭官從長安回昌谷的路上,念及金銅仙人的歷史事件,遂做此詩。在這首詩中,當年不可一世的擁有至高地位的漢武帝的鬼魂已經不再是帝王了,擁有法力的仙人會哭泣,送客的蘭花也是凋謝的生命狀態,作為萬物主宰的天也將變老,在這首詩里李賀創造出一種對權力進行破壞的景象,曾經在人間擁有至高無上的漢武帝死后也只能是一個孤魂野鬼,神話傳說中的仙人在人間的變動面前也只能默默流下眼淚,曾美麗的蘭花在此時也只能是慘敗的模樣,主宰萬物的天如若有情,也會因此而變老衰亡。這首詩呈現出異常的衰老與無力感,而這衰老與無力便是指向死亡本能的意識。
在《苦晝短》:“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吾將斬龍足,嚼龍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5]89李賀開始懷疑自古以來神明的存在性,懷疑神明世界的種種秩序,并且要破壞代表神明世界的神物——龍,甚至要斬龍足,嚼龍肉。這是一種超前的毀滅,一種近乎瘋狂的破壞。這是本壓抑的死本能的外化。如果說《苦晝短》還是在對神界的代表物進行破壞與毀滅的話,在《官街鼓》中:“幾回天上葬神仙,漏聲相將無斷絕”[5]85。則是對神明的永久性生命進行破壞與毀滅。自古以來,神仙們擁有著永久的生命,他們逍遙自在,為凡人所崇拜。可是在李賀這里神仙的生命是有限的,凡人們所認定的天上的秩序被李賀所破壞,凡人們敬拜的神明也將死去。正如德國哲學家尼采曾言:上帝死了。實則都是對既有神明秩序的破壞與毀滅。在李賀的一些神鬼詩中連主宰萬物的神明都將死去,作為凡塵之人又談何永久的生命呢?正是出于這種無助無望的死本能,李賀在其神鬼詩中表現出大量的破壞與毀滅,在杜牧所做《李長吉歌詩敘》中:“荒國陟殿,梗莽邱壟,不足為其怨恨悲愁也。”[4]3李賀所怨恨悲愁的不正是其生命受到難以言明的挫折并且時常受到死亡的威脅,這種狀態下,他潛意識中的死本能不斷地涌現出來,在神鬼詩的創造中流露出來,表現出來的就是破壞與毀滅希望,以及強烈的控訴感。
(三)戀母情結
弗洛伊德在《釋夢》中提出了戀母情結這一概念。戀母情結并非愛情,而大多數產生于對母親的欣賞與依戀。[2]135而在現實生活中卻很難體現,但是在文學創作中卻會無意識地流露出來。李賀在其神鬼詩中描繪出了不少的女神形象。但是其所創造的女神形象并不像屈原、曹植、宋玉等等所創造的那一類綽約曼妙的女神。在他的神鬼詩中他描寫了“蘭香女神”“貝宮夫人”“ 嫦娥”“ 巫山神女”“ 秦妃”等多個女神形象。李賀詩中的女神大都呈現出的是凄苦苦悶的形象。
從李賀與其父的關系在現存的記載中很難詳知,但是可以知道其父是縣官,四十歲得子。而且其父早逝,他與他父親的交流應該不多。弗洛伊德說:“愛雙親中的一個而恨另一個,這是精神沖動的基本因素之一。”[2]146通過對李賀生平的考證,不難得出李賀的精神寄托應是其母親,在日常的生活中與其母親交流則是較多的。作為家中的長子,李賀自小自然就受到了來自母親過多的關愛,他每日作詩歸來是其母親叮囑她:是兒嘔出心血爾。當其踏上求仕之路后,每當遇到挫折便會返回故鄉,當其去世之時,是其母親守護在他的左右。李商隱在《李長吉小傳》中當緋衣人召長吉上天時,“賀言阿奶老且病,賀不愿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4]14即使李賀所夢想的天界終于為他打開大門時,他猶豫時的原因竟還是對其母親的留戀,可見李賀對其母親的依戀之情。當這種內在的戀母潛意識在充滿幻想的神鬼詩被釋放出來時便呈現出不同的形象特點。
如:《貝宮夫人》:“長眉凝綠幾千年 ,清涼堪老鏡中鸞”[5]19。他所創造出的貝宮夫人是一個已經活了數千年的女神,但是李賀所描寫的卻不是一個自在自由的女神形象,反而是個永恒無聊寂寞的狀態,雖有長久的生命卻無人相伴的恒久寂寞與無聊。在《湘妃》中:“筠竹千年老不死 ,長伴秦娥蓋湘水。”[5]29湘妃儼然成為了一個活了數千年的女神形象,而與她相伴的只有千年老不死的筠竹,這種千年的孤寂與無聊卻是一種無法排解的苦悶。相比與屈原《九歌·湘夫人》中所描寫的飄渺自在、輕靈婉轉的女神樣貌,李賀的女神形象則更加一種人間孤苦孤寂的婦人形象。從李賀的生命中看出,當他父親在世時忙于政務無暇顧及家人, 年幼的李賀陪伴在母親身邊,自然他所看到的便是其母親的孤苦與寂寞,當其父親去世后,他的母親更是孤苦一人,他所幻想的女神中不經意間便流露出了他母親孤苦的狀態,而這正是對其母親的深深依戀。
李賀短暫的一身,身邊的女人只有她的姐姐以及他的母親。可以想象這樣一個體弱多病的兒子,受到了來自其母親的特別關照。自然對其母親產生了較深的依戀。而在其18歲踏上求仕之路,與母親更是聚少離多,求仕路上的磕磕絆絆自然會反復讓詩人產生波動,這些波動使得在其神鬼詩中描寫的女神大都是女性超過神性,因此在李賀神鬼詩中的女神便是其苦悶的孤寂的母親的外化。
三、 小結
弗洛伊德在談及作家創作時說過:“創作家所做的就像游戲中的孩子一樣,以非常認真的態度來創造一個幻想的世界,同時又明顯地把它與現實世界分割開來。”[6]80李賀正如孩童沉浸在游戲一般,沉浸在自己所創造的充滿幻想神鬼世界里,李賀建設了一個美麗的神鬼世界,這個世界與現實隔離使得他沉醉其中無法自拔,最終去世時也是幻想自己被仙人接到天界居住。對李賀的神鬼詩解讀歷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弗洛伊德的無意識理論中的生本能與死本能以及戀母情結的角度對其神鬼詩進行解讀,讓我們看到了那個短命天才在生與死的邊緣掙扎的內心世界,以及他對母親的深深地眷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