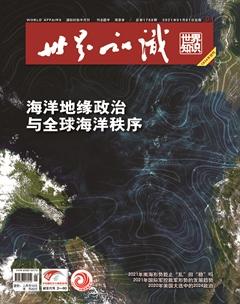政治印度教的“團黨平衡”:新變化與新挑戰
張忞煜
隨著2019年5月莫迪第二次當選連任,印人黨政府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更加熾烈。站在印人黨背后的“精神導師”——國民志愿服務團(RSS)的影響力也日益凸顯。長期以來,服務團秉持“不介入政治活動”的低調姿態,將活動自我限制在意識形態工作領域。近年來,隨著印度政治大風向的持續右轉,服務團的活動方式也逐漸發生了改變。印度首次同時出現高調的服務團“最高領袖”和強勢的印人黨總理,這對政治印度教框架下既有的“團黨平衡”造成了沖擊。
?“服務團—印人黨”平衡傳統
1948年1月30日,印度國父圣雄甘地遭印度教右翼極端分子戈德賽刺殺身亡,印度舉國震驚。總理尼赫魯擔心這是在他看來與納粹無異的印度教右翼組織國民志愿服務團(以下簡稱“服務團”)對新生的印度共和國發動全面進攻的前奏。2月4日,印度政府下令取締服務團,包括“最高領袖”戈爾瓦爾卡在內的約兩萬名服務團成員被捕入獄。然而,戈爾瓦爾卡通過一貫同情服務團的時任副總理帕特爾向尼赫魯求情,強調服務團致力于社會文化活動而非參與政治,并直言服務團可以幫助尼赫魯抵御共產黨人對年輕人的“赤化”。同年8月,戈爾瓦爾卡獲釋出獄,服務團也恢復了活動。
險遭滅頂之災的經歷一方面堅定了戈爾瓦爾卡對服務團的規劃理念,即服務團應扮演類似古代“王師”的角色,引領而非直接介入“政客”的具體活動;另一方面也促使服務團進一步將矛頭指向各國共產黨、印度共產黨人或國大黨左派領導的工農學商組織以及穆斯林和基督徒這樣的宗教少數派,從而爭取到同樣敵視這些組織或社群的國大黨內保守派的同情和庇護。也正因如此,1951年,當印度人民黨前身印度人民同盟的創始人希亞姆·普拉薩德·穆克吉找到戈爾瓦爾卡,表示希望借助服務團的力量另組新黨時,服務團一開始并不愿意介入。然而,鑒于穆克吉表示擁護建設印度教徒民族國家的理想,也為了避免心向政壇的年輕團員流失,“最高領袖”最終同意允許服務團“志愿者”與穆克吉黨人合作建立新黨——印度人民同盟。
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在積極支持印度人民同盟—印人黨政治活動的同時,服務團自身一直不參與選舉,而是不斷發展基層組織,逐步建立起以“團宣傳員”為核心骨干的外圍組織,這其中包括1948年建立的全印學生會、1955年建立的印度工人同盟、1964年建立的世界印度教大會和1979年建立的印度農民同盟等。這些以“團宣傳員”為骨干的右翼組織共同構成了被稱為“團家族”(Sangh Parivar)的組織網絡。這些組織與印人黨并無隸屬關系,但在核心意識形態問題上與印人黨相互呼應,有力地支持了印人黨的競選和施政。
20世紀90年代,在成功圍繞阿約提亞寺廟之爭等問題開展大規模政治動員之后,印人黨躋身全國大黨之列,并把握住了國大黨獨大格局土崩瓦解的歷史機遇異軍突起。然而,直到21世紀初,服務團一直保持低姿態,堅持自身“社會文化組織”定位,除了意識形態領導,為各外圍組織輸送后備干部,協助政黨開展選舉和施政活動外,服務團領導人鮮少拋頭露面。低調的服務團和高調的印人黨“一靜一動”,形成了一種戈爾瓦爾卡確立的“王師模式”下的微妙平衡。也正是在服務團的全力扶持下,發跡于古吉拉特邦的莫迪領銜的印人黨在2014年大選中一舉拿下過半議席,并在2019年大選后進一步鞏固優勢,塑造了今天的印人黨獨大格局。
高調服務團領袖與強勢總理并立
2009年,在服務團內根基深厚的莫漢·巴格瓦特就任服務團“最高領袖”后,服務團逐漸改變了以往低調的作風。2014年大選前,印人黨元老阿德瓦尼本欲再次披掛上陣,但在黨內卻不如代表新生代的莫迪呼聲更高。阿德瓦尼一度憤而退黨,最終還是巴格瓦特打破靜默的傳統,以“最高領袖”的身份出面協調才避免了印人黨分裂,進而成就了印人黨的獨大局面和莫迪國家領袖地位的形成。巴格瓦特也一改“最高領袖”一直以來的“隱士”作風,既不避諱公開會見國內財團代表,更是時常“公開議政”。2020年10月25日,在歡慶大神斬妖除魔的十勝節慶典上,巴格瓦特以“最高領袖”身份公開發表講話。他在講話中充分肯定了印度政府在廢除《憲法》第370條、重建羅摩神廟、強推《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等服務團所關心的重大議題上所取得的進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將印度面臨挑戰的根源指向了中國,不僅暗示中國應對疫情“負責”,更直接批評中國在邊境地區“侵略”印度,還力挺在印度國內也存在爭議的“排華”經濟政策。可以說,“十勝節講話”標志著服務團不再隱遁幕后,而是直接登上前臺指點江山。

就任國民志愿服務團“最高領袖”以來,莫漢·巴格瓦特(中)時常公開議政。圖為2020年2月15日他出席在古吉拉特邦的一場集會。
2014年大選勝利之后,憑借著龐大的人口規模和“電話入黨”等變通方式,印人黨一躍成為黨員人數最多的“全球第一大黨”。但是,這種“注水”數據之下松散的黨組織顯然無法與服務團的百年基業相提并論。在中央層面,現在的印度內閣各級部長中有超過半數為服務團成員,議會印人黨籍議員中亦有近半數為服務團成員。在基層,印人黨組織的人事權也依然掌控在“團宣傳員”出身的各級“組織部長”手中。這種服務團成員從中央到地方的全面把控的局面決定了政黨領袖很難在脫離服務團支持的情況下維持領導力。從歷史經驗來看,盡管印人黨是由服務團干部一手建立起來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服務團會永遠無條件支持印人黨。自從1951年間接參與政治活動以來,服務團就對“政客”為了現實利益不惜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妥協的實用主義作風不滿,斥之為“腐化”,并不吝采取實際行動“敲打”印人黨。
不過,莫迪今天在印度享有的個人影響力和“精神光環”對一貫“重組織輕個人”的服務團和團家族來說也是前所未有的現象,這也增強了印人黨相對于服務團的力量。如果說,“最高領袖”巴格瓦特公開議政已經打破了服務團在暗處、印人黨在明處的“團靜黨動”傳統,那總理莫迪的獨特影響力也部分改變了印人黨完全被各級服務團組織支配的“團強黨弱”的狀況。考慮到莫迪與巴格瓦特家族的淵源,很難想象在“巴格瓦特—莫迪”這一對“團黨雙星”在位期間,印度會發生土耳其那種昔日盟友正義與發展黨與“居倫運動”分道揚鑣的情況。但是,舊日平衡的打破還是為黨團關系的未來發展投下了陰影。
當然,印度的現行制度并沒有限制總理任期屆數,從理論上來說,莫迪可以像尼赫魯那樣成為事實上的終身總理。另一方面,服務團“最高領袖”也實行終身制。這也就意味著,即使一時無法產生受到各派支持的“莫迪繼承人”,現行政治印度教的“團黨雙星”依然可以維持秩序。但是,如果印人黨遲遲無法有效提升民眾福祉,那么這種看似穩定的格局終將透支民眾對“服務團—印人黨”組合以及整套政治印度教理念的信任,進而引發黨團關系的新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