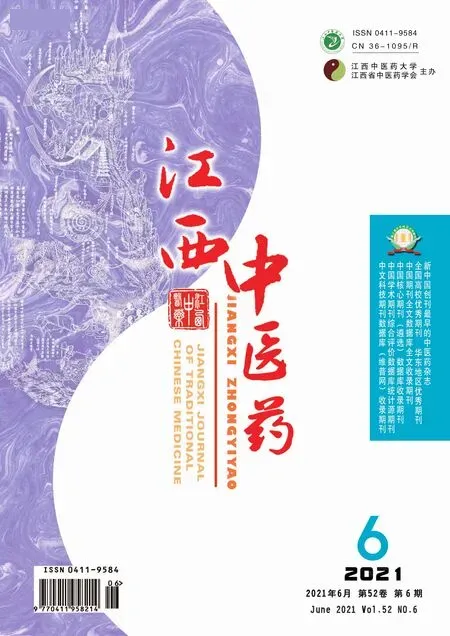方祝元應用寒溫并用法治療心系疾病經驗探析
★ 吳子嶼 方祝元(.南京中醫藥大學 南京 009;.江蘇省中醫院 南京 009)
心系疾病包含心悸、胸痹心痛、心衰、不寐等。目前中醫論治心系疾病多以氣血為綱,然臨床實際中亦有兼夾寒熱而發病者,證情復雜,易兼有他臟同病。方祝元教授歸納出以“寒溫并用法”治療“寒熱錯雜”類心系疾病的規律。靈活配伍寒涼藥與溫熱藥,以期達到藥物間的相輔相成、相反相成或去性存用的目的,取得了較好臨床療效。
1 “寒熱錯雜”類心系疾病的特點
心系疾病包含心悸、胸痹心痛、心衰、不寐等,主要表現為血脈運行的障礙和情志思維活動的異常。心居胸中,主神明,藏血脈。心氣心陽推動氣血運行,心陰心血濡養心神。故傳統辨證多以“氣血”“陰陽”為綱,區別氣、血、陰、陽之偏虛而施治。但因當代飲食結構、社會環境、致病因素的變化,使得“寒熱錯雜”類心系疾病頻見,僅用氣血辨證法已不能滿足當今臨床辨治之需。現代醫家多遵循“氣血失調”為其主要病機而進行論治,往往忽視以“寒熱”論治“寒溫失調”類心系疾病的重要性。
“寒熱”類心系疾病的特點:一以寒熱征象交雜為特征,臨床表現為寒熱征象交雜,或寒多熱少、熱多寒少、寒熱各半,或部位上表現為內外寒熱、上下寒熱、寒熱中阻等,病程表現為反復難愈;二除心系主癥外,常合并中焦脾胃癥狀,中焦為氣機樞紐,脾胃失調,易生寒熱,寒熱交結,上擾心神。故當患者以寒熱征象交雜、兼夾脾胃為病者,即可從“寒熱錯雜”之病機出發,以“寒熱并用”為治療大法,輔以“調氣和血”治之,可期良效。
2 寒溫并用法
2.1 寒溫并用法的涵義 “寒溫并用法”指組方靈活伍以寒涼藥與溫熱藥,以期達到兼顧寒熱的作用。臨床運用時包括相輔相成、相反相成、去性存用三層含義。“相輔相成”者如上熱下寒之腹痛欲嘔者投以黃連湯,中焦寒熱之痞滿者施以瀉心湯類,以期寒溫并治[1];“相反相成”者如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在大量溫熱藥中反佐以少許苦寒的豬膽汁,以期從陰引陽,使溫熱藥性得入陰寒之病所[2];“去性取用”者如麻杏石甘湯中以大寒之石膏制約麻黃辛溫之性,僅保留平喘功效,治療熱邪壅肺之咳喘[3]。總而言之,“寒溫并用法”可充分發揮不同藥物之藥性,最終達到扶正祛邪、平調寒熱、調和陰陽的治療目的[4]。
2.2 寒溫并用法的理論淵源 “寒溫并用法”的理論基礎源自《內經》,經云:“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風淫于內,治以辛涼,佐以苦……陽明之復,治以辛溫,佐以苦甘”,其依據四時之氣的不同,提出“寒溫并用”的治療大法[5]。張仲景進一步發掘“寒溫”之意,以六經為綱,細分為表里寒熱證、上熱下寒證、中焦寒熱證、少陽寒熱證、少陰寒熱證、厥陰寒熱證等不同證型。遣方用藥方面,《傷寒論》共113方,其中寒溫并用法53方,《金匱要略》共205方,其中寒溫并用法98方,足見仲景對“寒溫并用法”之重視[6]。《傷寒雜病論》中以黃連湯清上溫下、小柴胡湯和解少陽、瀉心湯辛開苦降等均體現了張仲景重視“寒溫并用”的思想[7]。“寒溫并用法”在后世醫家手中不斷發展,如孫思邈在《千金方》中以溫脾湯溫通寒積以振脾陽,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以左金丸清瀉肝火治療肝火犯胃之嘈雜吞酸等[8-9]。“寒溫并用法”經過眾多醫家的完善與發展,其內涵與應用范圍得到了不斷的豐富。
2.3 現代臨床研究及藥理學研究 現代臨床及藥理學研究也揭示出“寒溫并用”類經方的獨特功效。在“交泰丸”的藥理學研究方面,證實了黃連的主要成分小檗堿和肉桂所含的桂皮醛都具有顯著抗炎作用[10-11],且若將二者配伍后,其鎮靜催眠的效果明顯強于單藥應用,這與交泰丸“寒溫并用”治療“不寐”的理念完全吻合[12]。在“胸痹”的臨床研究中,謝相智等[13]以烏梅丸治療穩定性勞力性心絞痛患者4周后,治療組患者的臨床癥狀的緩解程度及生活質量的改善程度明顯優于對照組,且具有統計學意義。在“心癉”的動物實驗研究方面,段豪[14]通過構建FM1流感病毒誘導Balb/c小鼠病毒性心肌炎模型,并以低、中、高劑量的柴胡桂枝湯合銀翹散復方對小鼠灌胃14天。對比病毒唑組及模型組,低、中、高劑量中藥復方組均能提高感染小鼠生存率、保護小鼠心肌細胞并降低小鼠血清中N0、TNF-α含量及心肌組織中FM1、TNF-α基因相對表達量。此外,在呼吸系統疾病的治療上,劉建華等[15]發現麻杏石甘湯對治療急性肺炎,并降低血清C反應蛋白具有顯著療效。消化系統疾病的臨床研究也表明,柴胡桂枝湯在治療膽汁反流性胃炎及慢性膽囊炎方面具備顯著療效[16-17]。
3 方祝元針對寒熱錯雜心系疾病治療的臨床經驗
3.1 “寒熱中阻”之心悸病 臨床表現以乏力畏寒等心陽氣不足的心悸病,兼胃脘嘈雜、膈上有熱之癥,或兼有情緒不暢、納呆泄瀉等肝氣不疏、肝陽不足之癥者,可投以烏梅丸。吳鞠通云:“烏梅丸為寒熱剛柔同用,為治厥陰、防少陽、護陽明全劑。”方師認為烏梅丸組方以溫臟寒、清郁火為特點,不只拘泥于蛔厥、臟厥,但凡臟有虛寒、寒火郁于內者,皆可主之。方中烏梅味酸以斂陽,入厥陰可補厥陰之體、調理厥陰樞機,清上溫下,除熱安心;附子、細辛、干姜溫熱之品可溫中臟虛寒;連、柏可清上熱;同時還當以大劑量黃芪、黨參溫補心氣。根據寒熱偏盛不同,烏梅可用至30 g,寒熱藥量均宜量小平調,附子 6~10 g、細辛 3~5 g、干姜 3~10 g、黃連3~6 g,黃柏5~10 g。同時方師強調,仲景所處年代病機往往較為單一,隨著社會、飲食、氣候等變化,現代患者發病多病情復雜,兼夾臟腑為病,此時若以數方合用,效果顯著。
3.2 “心脾同病”之不寐病 臨床表現以心火亢盛為特征的不寐患者,很多伴有脾虛。表現為不易入睡、多夢多醒、食少便溏腹脹。若單用清瀉心火的藥物,則脾虛更甚,若健補脾胃則心火益盛。方師從“胃不和則臥不安”出發,化裁《韓氏醫通》之交泰丸,改肉桂為龍眼肉入心脾二經以益氣血,伍以黃連入心經以清心火,可以清而不瀉,溫而不燥。根據心火亢盛、脾陽不足的程度,黃連與龍眼肉多以3∶5、5∶5、8∶8配伍。用藥雖少,但對寒熱所處臟腑及寒熱多少的把握,選擇不同的藥物及配伍比,可效如桴鼓。同時配伍靈芝、酸棗仁、柏子仁、遠志、珍珠粉、茯神等寧心安神,療效顯著。方師認為失眠治療當注重未病先防,《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當囑患者食飲有節、寒熱避之有時,則利于避免“寒熱錯雜”等復雜病證的形成。
4 案例分析
4.1 心悸病 患者沈某,1月前每日凌晨1~2點發作心慌,全身汗出,心前區尤甚,汗后全身乏力、四肢冰冷,伴心下、脅下脹,嘈雜似饑,打嗝明顯,打嗝后上述癥狀稍有緩解,腸鳴頻繁,矢氣多,瀉下清冷,午后諸癥狀可稍有緩解,納可,寐差,二便調。舌暗紅,苔薄白,脈弦弱。既往“陣發性房顫”病史2年,“非萎縮性胃炎、膽囊炎”病史數年。心電圖示:房性早搏。診斷為:心悸病(寒熱錯雜證)。方選:烏梅丸合益氣養陰方加減。方藥:醋烏梅30 g、干姜5 g、花椒6 g、肉桂4 g、細辛3 g、制附子6 g、黃連5 g、黃柏10 g、黨參30 g、全當歸10 g、麥冬12 g、醋五味子6 g、生黃芪15 g、炙黃芪15 g、玉竹12 g、百合15 g、醋莪術6 g、丹皮6 g、丹參15 g、刺五加12 g、紅景天15 g、絞股藍15 g、法半夏8 g、陳皮6 g。日1劑,水煎早晚分服。
14劑后復診癥平,自覺噯氣較頻、寐仍差,加炒白術10 g、蘇梗10 g健脾理氣,酸棗仁30 g、首烏藤15 g、合歡皮15 g養心安神,繼服7劑后夜間心慌未做,夜寐較前好轉。
按:《傷寒論》原文記載:“蛔厥者,烏梅丸主之,又主久痢”,故烏梅丸之證,不拘于安蛔,應本于病機,陰氣漸消,陰盡陽生,若陽氣虛衰,則陰陽之氣不相順接而發為本病[18]。方祝元教授認為厥陰病者,陰陽之交互也,寒熱之所在也,烏梅丸主之。本案中患者有心悸、汗出乏力等心陽虛表現,又具脅下脹、打嗝、腸鳴矢氣、瀉下清冷等腸胃虛寒的表現。心膈有熱,故見嘈雜若饑。寒熱交錯,病程綿長。子時陰盡生陽,屬厥陰之時,患者胸陽虛衰,胸中陰陽之氣不相順接,故子時心悸癥狀加重。故本病屬烏梅丸主證。選方以烏梅丸攻補并用,酸苦辛并進,酸可澀腸,溫可補虛。又以炙黃芪、黨參溫陽益氣,百合、玉竹、麥冬滋陰斂氣,醋莪術、丹皮、丹參奏補血、行血、養血之功,法半夏、陳皮化痰理氣。藥后夜間心慌未做,便溏好轉。
4.2 不寐病 患者殷某,失眠20余年,寐短易醒,長期服用鎮靜安眠藥,效果不顯。患者頭暈頭脹反復發作,時有心煩易怒,伴惡心欲吐,全身乏力,不思飲食,少食即脹,大便偏干,日行1次,小便調。舌尖紅,苔薄白,脈細弦。診斷為:不寐病(寒熱錯雜證)。方藥:川黃連3 g、龍眼肉5 g、柏子仁20 g、酸棗仁30 g、靈芝15 g、紅景天15 g、茯苓25 g、茯神25 g、珍珠粉1.2 g。日1劑,水煎早晚分服。
14劑后復診,睡眠時長較前增加,頭脹痛尚未緩解,川黃連、龍眼肉各加至10 g、加用夏枯草15 g、丹皮10 g、丹參15 g、合歡皮15 g、首烏藤15 g、百合15 g。繼服14劑后患者寐漸安,睡眠效果及時長滿意,頭脹痛未做,守方繼續治療。
按:本案中,患者失眠、頭暈易怒、大便時干為心火旺盛的表現,惡心欲吐,全身乏力,納差,不思飲食易胃脹為脾虛之相,舌苔脈像均為佐證。選方取交泰丸之意,以黃連入心經,配伍紅景天清瀉過亢之心火,龍眼肉入心脾二經補益氣血,配伍靈芝溫補脾腎,并予酸棗仁、柏子仁、遠志、珍珠粉、茯苓神等寧心安神。復診頭暈頭脹未減,以夏枯草、百合、首烏藤、合歡皮清肝瀉火。藥后患者睡眠質量好轉,頭暈頭脹未發。
5 總結
方祝元教授臨床辨治心系疾病時,謹守病機,病證結合,準確辨證,對于“寒熱錯雜”類心系疾病,注重經方的使用,重視寒溫并用、五臟同調,同時加強對患者的健康宣教,防患于未然,取得了顯著的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