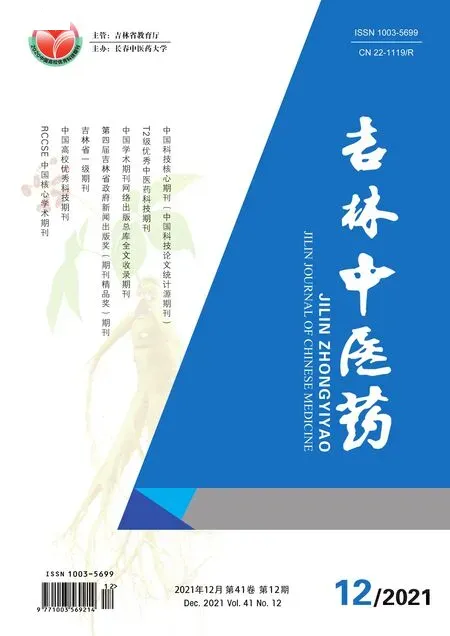基于中醫“治未病”理論試析乳腺癌的中醫診療特點
吳曉晴,崔永佳,盧雯平
(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北京 100053)
“治未病”思想證明中醫早在先秦至漢代就意識到預防疾病發生的重要性。治有治療、醫治、治病;管理、處理[1]的意思,未病可概括為三層意思:1)未患病的健康狀態;2)伏邪未發的狀態;3)疾病進程中將要累及的狀態[2-3]。結合乳腺癌的疾病特點,“未病”的概念可擴充為:1)患病高風險,但還未患病的狀態;2)經歷過現代醫學規范化治療的無瘤狀態;3)乳腺癌復發、轉移后,生命體征穩定的帶瘤狀態。治未病的思想時時蘊含并應用在乳腺癌治療的各個階段之中,與西醫規范化治療相配合,與手術、化療協同作用[4]。根據患者的預后,不同強度(劑量、劑型、用藥周期等)的干預也是治療的一部分。
1 未病先防
中醫認為體質偏頗、陰陽失衡是腫瘤發生的內在原因之一[5],未病先防主要體現在以平和質為目標,糾正偏頗體質,調整陰陽平衡。《靈樞·論勇》中記載:“有人于此,并行而立,其年之少長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闡明了體質與疾病易感性、傾向性的關系。體質是在人的生命過程中,在先天的基礎上形成的,在形態結構、生理功能和心理狀態等方面具有的綜合性、相對穩定的內在特征[6]。在乳腺癌的中醫診療中,以體質為基礎,以病證為標準,辨證論治貫穿于整個過程。《景岳全書》言:“當識因人因證之辨。蓋人者,本也;證者,標也。證隨人見,成敗所由。故當以因人為先,因證次之。”徐大椿在《醫學源流論》中提到:“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則效,治彼則不效,……則以病同而人異也。”任應秋先生說:“異病之所以同治,同病之所以異治,雖云決定于證,但就證的本質而言,仍關系于體質之有所不同。”可以說證具有體質的一部分特征,體質是內在的源頭,證是疾病外在某一時間段的呈現,司外揣內,臨床通過生活習慣、飲食偏嗜、生活環境、性格愛好結合證型來窺探體質的類型,治療時也會通過調整體質來達到減輕病理證候的目的。體質決定了證的形成和從化趨勢,例如素體陽虛,感受外邪后易從寒化;素體陰虛,外邪易化熱,素體陰津不足,外邪易燥化,所以糾正體質偏頗是“未病先防”的重要依據。
明確患乳腺癌的高危體質,是“未病先防”的基礎。《外科正宗》云:“憂郁傷肝,思慮傷脾,積想在心,所愿不得志者,致經絡痞澀,聚結成核,名曰乳巖”;《醫學入門》中有云:“郁怒有傷肝脾……名曰乳巖”;《醫宗金鑒》云:“乳癌由肝脾兩傷,氣郁凝滯而成”。王琦教授提出了現代的9 種體質的基本分型,并提出了“體病相關學說”,即具有某些體質的人對某些疾病具有更高的易感性。前期臨床研究發現,乳腺癌的易感體質類型有:氣郁質、血瘀質、痰濕質[7]。人長期處于抑郁、焦慮狀態,或長期久坐,缺乏運動,導致三焦氣機不暢,臟腑氣機逆亂,氣不行則血瘀,氣不布津則痰凝,與多種外來病理因素雜糅搏結而成癌毒,進一步交結而成有形之物,完成從無形之邪至有形之物,從功能失調至器質性損傷的病理過程。治療時,對氣郁質、血瘀質人群,在疏肝理氣,活血化瘀的同時要多給予心理疏導,氣郁質用逍遙蔞貝散加減疏肝理氣,化瘀散結,血瘀質用桃紅四物湯加減活血化瘀,扶正祛邪;痰濕質人群,治以化痰除濕,并對其進行健康宣教,加強體育鍛煉,控制體重,用六君子湯合蜂穿不留湯加減健脾化濕,化痰散結。
基于中醫體質學說,尋找中醫體質類型和乳腺癌發病的關系,篩選出乳腺癌的高發人群,提早干預,從而進行個體化的治療并給予生活建議,是對中醫“治未病”理論的應用方式之一。
2 瘥后防復,鞏固治療
盡管我國醫療水平不斷提高,乳腺癌術后復發轉移發生率仍在15%~35%[8]。有研究表明,惡性腫瘤的轉移在早期即發生異常細胞游離[9],這就強調了“瘥后防復”的重要性。此階段總體的治則為防復發轉移、“先安為受邪之地”。
2.1 循因預防 現代醫學規范化治療后,很多患者達到了“無瘤狀態”,若致病因素仍然存在,則會引起乳腺癌的復發轉移。
乳腺癌的發病與肝郁脾虛,沖任失調相關。乳房屬胃,乳頭屬肝,任脈上通膻中,沖脈為五臟六腑之海,與足厥陰肝經、足少陰腎經、足太陰脾經相互溝通,共同主管乳房的生長發育。《靈樞·經脈第十》中曾說“肝足厥陰之脈,……上貫膈,布脅肋”“胃足陽明之脈,……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朱丹溪認為乳房屬胃,乳頭屬肝;傅青主認為“乳巖乃性情每多疑忌,失于調理,忿怒所釀,憂郁所積,濃味釀成,以致厥陰之氣不行,陽明之血騰沸,孔竅不通,結成堅核,形如棋子”。故乳腺癌的病因預防應從肝、脾入手,又因沖任系于肝腎,思慮傷脾,惱怒傷肝,導致沖任脈中之氣血運行不暢,累及先天之本,沖任失調,故治療中應以疏肝益腎,調理沖任為法,在此基礎上根據辨證調整用藥。
2.2 清除余毒 患者經歷了手術、放化療后邪氣大傷,卻仍有余毒未清,或伏之未發,伺機而動,或旁竄他處。伏邪遇內在或外來病理因素引動,也易致疾病復發或傳舍他臟。正邪交爭,余毒邪氣與臟腑正氣的強弱決定了腫瘤的轉移與否,與現代醫學備加關注的腫瘤微環境學說不謀而合。《靈樞·百病始生篇》中云:“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膚,……留而不去,則傳舍于絡脈,……留而不去,傳舍于經,……留而不去,傳舍于輸,……留而不去,傳舍于伏沖之脈,……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之外,募原之間。留著于脈,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描述了腫瘤由原發病灶至他臟的轉移過程。《瘟疫論》中說:“若無故自發者,以伏邪未盡。”此時的病機主要為正氣虧虛,余毒未清。癌毒隱匿,毒性猛烈,易走竄,且易致虛致瘀致痰[10-11]。余毒的致病能力部分決定了其能否旁竄他處,使用清熱解毒、抗癌散結中藥,如白花蛇舌草、鮮龍葵果、紅豆杉、山慈菇、半枝蓮等清解余毒,達到瘥后防復的目的。
2.3 先安未受邪之地 現代醫學研究表明,研究表明,腫瘤微環境對腫瘤細胞在特定器官的生長和轉移具有重要作用[12],這就提示我們不僅要預防余毒增長和癌毒四處走竄,更要顧護轉移部位的正氣,“先安為受邪之地”。
不同病理分型乳腺癌的預后以及易轉移部位不同,利用現代醫學的研究結果指導中醫遣方用藥不可或缺。三陰乳腺癌預后較差,最容易轉移的部位是肺、腦、肝和骨,轉移到肺的風險是40%,轉移到腦的風險為30%,轉移到肝的風險為20%,轉移到骨的風險為10%[13]。所以,對于三陰乳腺癌患者患病后的前3 年,以預防復發轉移為主。用藥在顧護正氣的同時,采用補肺透腦清肝的藥物,如沙參、麥冬、魚腥草、川貝母、百部等滋陰潤燥,桔梗、杏仁引藥入肺;枸杞子、生地黃補益肝腎,滋養腦髓,菊花、天麻引藥上浮入腦;為防止肝轉移,常用艾草、龍葵、八角蓮、甲蟲、穿山甲等清熱利濕,選用入肝經之藥。Luminnal A 型易發生骨轉移,內臟轉移發生率較低[14],預后相對較好,用藥應酌加骨碎補、桑寄生、透骨草、川續斷、牛膝、威靈仙補益肝腎,強筋健骨。有研究表明淋巴結轉移可能與肝經相關[15],故可加貓爪草、橘核、白僵蠶等歸屬肝經之藥,且能化痰散結。骨轉移易發生在Luminnal B 型和HER-2 過表達型乳腺癌中,骨轉移、腦轉移較易發生在HER-2 過表達型乳腺癌中,且轉移率均高于Luminnal A 型[16-17],重在抗癌解毒、補肝腎強筋骨,HER-2 過表達型加用入腦絡、滋養腦髓藥物。
3 既病防變,帶瘤生存
晚期乳腺癌很難治愈,但可以治療,通過辨病灶,控制腫瘤進展,延長患者生存期,提高生活質量[18-20]。“治未病”的理論在這一階段體現在預防病邪深入,改善轉移器官功能,盡力使患者“帶疾而終天”。
3.1 扶正祛邪是關鍵 正邪交爭的過程始終存在于腫瘤發生、發展過程中,通過辨正邪關系強弱,予以扶正、祛邪或扶正祛邪并用,使患者處于“正邪交爭,邪難勝正”的特殊階段,是實現“帶瘤生存”的關鍵。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提到:“至虛之處,便是留邪之地。”《諸病源候論·石癰候》云:“有下于乳者,其經虛,為風寒邪氣客之,則血澀結成癰腫,但結核如石,謂之石癰。”復發轉移的患者多存在正氣虛損,《黃帝內經》有云:“大積大聚不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過則死,此治積聚之法也。”此時患者正氣已虛,不宜過于攻伐,而應保持正邪之間的平衡。脾胃為先天之本,水谷精微化生之源,為人體正氣的產生提供物質基礎,“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因此在治療過程中應時時顧護脾胃,健脾和胃,調暢中焦。
3.2 改善轉移器官功能 晚期乳腺癌出現遠端轉移時,常出現很多兼癥,預防因轉移器官衰竭而引起的死亡或生活質量下降,是此階段的目標之一。晚期出現骨轉移時,可能會出現病理性骨折、劇烈骨痛,中藥中加骨碎補、補骨脂強筋健骨,預防病理性骨折,透骨草、鹿銜草、威靈仙、枸杞子補腎活血止痛;出現肺或胸膜轉移,見咳嗽、胸悶,予葶藶子、萊菔子瀉肺平喘,杏仁、桔梗引藥入肺;出現肝轉移,惡心厭油,食欲差,加茵陳、垂盆草、田基黃、熟大黃利濕退黃;出現腦轉移時加全蝎、冰片、石菖蒲豁痰開竅,天麻、鉤藤引藥上行。
中醫“治未病”思想與現代醫學“三級預防”的內涵不謀而合,是中醫預防醫學的精髓,在乳腺癌各階段治療中應時刻謹記“治未病”的思想內涵。“治未病”思想在乳腺癌中的應用可簡單地概括為未病先防、瘥后防復、既病防變。對于乳腺癌高危人群、規范治療后鞏固治療人群和晚期復發轉移人群,治療目標不同,重點不同,靈活辨證,與辨體、辨病相結合。
4 病案舉例
張某,女,64 歲,2019 年1 月來診。患者于2018年8 月行右乳改良根治術,術后病理:浸潤性導管癌,高分化,病灶1 直徑為0.7 cm,病灶2 直徑為1 cm,前哨淋巴結(0/4)。IHC:ER(+,70%),PR(+,40%),HER-2(0),Ki67(50%)。術后環磷酰胺、多西他賽化療8 周期,現口服阿那曲唑片1 mg,每日1 次。2019 年1 月24 日乳腺超聲結果顯示:左乳實性結節,BI-RADS 3—4a 類,大小0.5 cm×0.3 cm,呈分葉狀,CDFI:點狀血流。同日胸片顯示:肺部小結節,傾向良性。來診時癥見:性情急躁,腹脹,食后脹甚,食欲可,入睡困難,大便不成形,每日1 次,小便調。舌淡苔薄白,脈弦。中醫診斷:乳巖,肝郁脾虛證;現代醫學診斷:乳腺癌 Luminnal B 型。辨體質為氣郁證。口服中藥湯劑:山慈菇12 g,皂角刺12 g,白花蛇舌草15 g,重樓9 g,橘核12 g,烏藥9 g,川楝子9 g,青皮9 g,肉桂6 g,澤瀉30 g,川芎9 g,莪術9 g,紫草12 g,黃芪30 g,茯苓15 g,法半夏9 g,黃連6 g,炒萊菔子15 g,炒杏仁9 g,骨碎補15 g,炒酸棗仁30 g。10 劑,水煎服,日1 劑。
藥后諸癥減輕,效不更方,交替使用抗癌中藥,隨患者癥狀加減中藥緩解患者癥狀。患者食后腹脹緩解,睡眠可,大便每日1 次,成形。復查左乳腺結節、肺部小結節無明顯變化。隨訪至2020 年2 月,患者無復發轉移傾向,生活質量明顯改善。
按:患者中老年女性,平素性情急躁,易多愁善感,舌淡苔薄白,脈弦,根據中醫體質量表判定為氣郁質。《金匱翼·積聚統論》云:“凡憂思郁怒,久不得解者,多成此疾。”氣郁則臟腑氣機不利,氣機不利易導致血瘀、痰凝的發生,氣、瘀、痰相互膠著,留滯不去,乃成積聚,若聚而成毒或與病理因素雜糅,則易發生惡性腫瘤。盡管該患者左乳腺結節、肺小結節尚可觀察、隨診,但是足以說明患者體質偏頗,易產生積聚,因此此次診療的目的為調整患者氣郁質體質,預防復發轉移和發生對側乳腺原發乳腺癌。方中橘核、烏藥、川楝子、青皮理氣不傷氣,為主藥,橘核、烏藥疏肝理氣散結,力度和緩,川楝子、青皮疏肝行氣,散結破堅,藥力較為峻烈,四藥配伍理氣消脹,驅邪而不傷正,目的在于緩解患者的一派氣郁之象。山慈菇、皂角刺、白花蛇舌草、重樓針對患者原發病辨病治療,防止乳腺癌的復發、轉移,考慮到Luminnal B 型乳腺癌易轉移至骨、肺[15],結合患者體質,選用萊菔子、炒杏仁宣降肺氣,骨碎補強筋健骨,“先安為受邪之地”。氣郁則血瘀,氣滯則痰凝,故加用川芎、莪術、紫草以活血通絡,茯苓、法半夏助津液輸布,既治療患者大便溏的癥狀,又防止津液輸布障礙而致成濕、成痰,從積聚的病理因素出發,逐個擊破。唯恐活血化瘀藥加速癌癥轉移,加用大劑量黃芪扶助正氣,做到攻邪不傷正,扶正不助邪。肉桂、澤瀉引邪氣下行,給邪氣以出路,緩解患者的腹脹癥狀。炒酸棗仁養心安神,保證睡眠,有利于患者條暢情緒。全方攻補兼施,相互協同,相互制約,共奏扶正固本、祛邪解毒之效,高度體現了“治未病”的中醫思想,不僅踐行了“瘥后防復”的思想,在遣方用藥上更是以中醫基礎理論為指導,根據病邪的傳變、生克特點,提前預防病邪入里或侵及他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