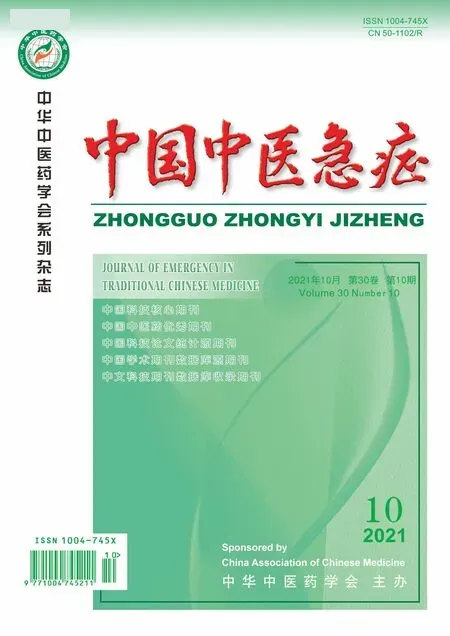從“心受氣于脾”防治心力衰竭探析*
周 穎 江慧楠 蔣衛民
(1.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江蘇 南京 210029;2.江蘇省中醫院,江蘇 南京 210029)
在發達國家心力衰竭的患病率一般估計為普通成年人口的1%~2%[1],我國由于人口老齡化加劇,冠心病、高血壓病、糖尿病、肥胖等慢性病的發病率增加,導致心衰患病率呈持續升高趨勢[2]。盡管近年來心衰的存活率有所上升,但5年生存率仍僅約50%[1],而心衰4個階段5年存活率分別為97%、96%、75%和20%[3],2013ACCF/AHA心衰管理指南建議早期識別心衰危險因素,通過控制心衰危險因素、抑制心肌重構等,以延緩或預防心衰的發生[3]。本文結合中醫“治未病”思想與現代醫學對心衰轉歸的認識,從“心受氣于脾”理論出發,探討心衰前期階段的共同病因病機及治療方法,早期干預心衰前期危險因素,拮抗心肌重構,以期通過預防性治療降低心衰發病率、患病率。
1 治未病思想與心力衰竭的防治
“治未病”思想是中醫基礎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概括未病先防、既病防變、病后防瘥3個方面。《黃帝內經》時期已經形成基本理論框架,其核心內涵是“未病先防”,并提出很多養生防病措施。東漢時期張仲景《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后病脈證》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通過“治肝補脾”之例強調了“既病防變”對于疾病發展及預后的重要性。唐代孫思邈認為“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將疾病總結為“未病”“欲病”“已病”3個階段。當代國醫大師周仲瑛認為“治未病”的理念在防治疾病于未生、未成、未發、未傳和未變等5方面[4],提出“五治”臨床思維模式。目前中醫治未病與現代醫學結合的健康管理模式已成為適合中國國情又獨具特色的中西醫結合健康保障系統[5]。
中醫學無心力衰竭病名,根據其癥狀表現歸為心痹、心水、水腫、喘證、支飲等范疇。古代醫家總結出心衰的癥狀特點:心悸、短氣、氣喘、水腫等。目前多認為心衰病位在心,可累及肺肝脾腎,病機屬本虛標實,以心氣陽虛為本,血瘀、水飲、痰濁為標,治療以益氣溫陽、活血利水為主。不難看出,中醫對于心衰的診斷建立在以胸悶、心慌、氣短、咳喘、水腫為主的癥狀群的基礎上,出現明顯的癥狀和體征時才啟動治療,對于心衰的預防性治療存在忽視。《黃帝內經》認為“有諸內者必形諸外”“視其外應,則知其病所”,根據疾病外在表現以辨病辨證,心力衰竭前期階段并無明顯的臨床表現,結合中醫“治未病”思想,在心衰已有潛在的危險因素和一定發病基礎的階段,治其未成,治其未發,防止疾病傳變。高血壓病、冠心病、糖尿病、肥胖、心肌重構雖為不同的病證,其病機不外乎“虛、痰、瘀”,從“心受氣于脾”理論,運用益氣健脾、化濁祛瘀方法使得心氣充足,心脈通暢,延緩心力衰竭癥狀或體征的出現。
2 基于“心受氣于脾”探討心力衰竭發病機制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心受氣于脾,傳之于肺,氣舍于肝,至腎而死”。五臟臟氣相通,傳變有次,受病氣于其所生之臟。脾胃屬土,心屬火,心臟所受病氣來自所生之脾臟,子病及母,為脾病逆行傳變至心臟。“心受氣于脾”理論從母子相及解釋“脾病及心”的病機,為中醫防治心力衰竭提供了理論依據。《素問·經脈別論》云“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于脈”。心脾二臟火土相依,氣血互濟,心主血脈,脾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運化水谷精微可以營養心臟,充盈血脈。子不扶母,必致心病。恣食膏粱厚味,勞逸不當,憂思傷脾,或素體脾胃虛弱,功能失常,氣血乏源,心失所養,血脈澀滯,或脾失健運,散精障礙,生痰致瘀,心脾同病,皆可導致血壓升高,糖脂代謝紊亂,動脈粥樣硬化,肥胖等病證,最終發展為心力衰竭。
2.1 從危險因素探討脾虛病機 心衰危險因素常見有高血壓病、冠心病、糖尿病、肥胖等,不患有高血壓、糖尿病、肥胖的人群發生心力衰竭的風險明顯降低,流行病學數據表明預防中年期心衰危險因素能夠顯著降低心力衰竭的發病率和患病率[6]。血壓升高可以引起左心室壓力負荷增加,心肌梗死后引起神經體液系統過度激活、炎癥反應增加,嚴重的肥胖可以直接改變血流動力學指標,增加循環總血量及每搏輸出量,糖尿病患者胰島素抵抗或高胰島素血癥狀態下心臟能量代謝紊亂等等,均可致心臟形態和功能的改變,進而導致心力衰竭的發生[7-8]。這類病證中醫分別屬于“眩暈病”“胸痹”“消渴病”“肥胖病”范疇,病理性質皆為本虛標實,脾虛為本,痰瘀為標。脾虛為高血壓的基本病機,脾虛則無以制約肝土,肝氣橫逆則肝陽上亢;脾氣虛弱,脾失健運,氣血津液運化失司,化生無源,痰濕內阻,或陰精不足。脾虛是胸痹心痛的發病基礎,一為氣血乏源,心脈失養,二為瘀血、痰濁聚生而痹阻心脈,導致胸痛發生。糖尿病和肥胖病因分為內外二因:過食和脾虛,膏粱厚味壅滯脾胃,樞機不利,清濁不分,堆積血脈則致血脂、血糖代謝紊亂,堆積體內則為脂肪。
2.2 從心肌重構探討脾虛病機 無癥狀器質性心臟病的患病人群為左心室肥厚、陳舊性心肌梗死、無癥狀的心臟瓣膜病等,其病理生理基礎為心肌重構,最初可以對心功能產生代償作用,但隨著心肌重構的加劇,逐漸由代償向失代償轉變,出現明顯的癥狀和體征。脾胃后天之本,心主血脈,以氣為用,心氣依賴于脾胃化生,心肌細胞依賴于脾胃充養。脾虛失運,子病及母,以致心氣虧虛,“氣虛為陽虛之漸”,心氣陽虛則無以推動血液運行,瘀血、痰濁此類病理產物凝聚于心,與現代醫學認為的神經體液、細胞因子、炎癥因子過度激活導致的心肌纖維化、間質膠原沉積等機制相符。此外,脾主肌肉,黃元御《四圣心源》曰“肌肉者,脾土之所生也,脾氣盛則肌肉豐滿而充實”。脾氣健運,則肌肉豐盈,強力收縮,若脾病則肌肉無氣以生,心肌萎弱不用,舒縮功能異常,終致結構性改變。
2.3 從腸道菌群探討脾虛病機 現代研究表明,腸道菌群在心血管疾病的發生和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主要包括三甲胺(TMA)-三甲胺氮氧化物(TMAO)途徑、短鏈脂肪酸(SCFA)途徑和膽汁酸途徑等[9]。高脂肪飲食富含的膽堿和肉堿是三甲胺代謝底物,經肝酶轉化為TMAO,導致血小板高反應性,促進動脈粥樣硬化及血栓形成[9-10]。高血壓前期及高血壓患者腸道菌群多樣性明顯低于正常人群[11]。糖尿病患者有益菌群減少,SCFA可以抑制胰島素抵抗、增加胰島素敏感性,產生有益代謝效應[12]。腸道菌群失調對人體炎癥反應和致病毒素產生影響,與心力衰竭的病理生理過程又密切相關[13]。
飲食物的消化和營養物質的吸收、轉輸,是由脾胃、肝膽、大小腸等多個臟腑共同參與完成,其中脾起主導作用。中醫“脾”對維持腸道菌群的穩定發揮著重要作用,脾胃功能失調會影響腸道菌群的平衡狀態,脾虛患者的腸道有益菌數量明顯減少而致病菌過盛[14]。心脾經脈相連,脾失健運,痰濁邪氣進入血脈,痰瘀互結,心脈痹阻,與腸道菌群參與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形成并促成冠心病相一致。糖脂乃水谷精微所化,脾虛精微不得布散,濁氣堆積,腸道菌群參與糖脂代謝,健脾益氣中藥可促進脾虛患者腸道有益菌增長,治療糖脂代謝相關疾病[15-16]。由此可知腸道菌群在心力衰竭前期階段發揮重要作用,“心-脾-腸”臟腑相關,健脾益氣療法可以通過調整腸道微生態,早期干預動脈粥樣硬化、糖脂代謝紊亂等,積極治療心衰危險因素,預防心力衰竭的發生發展。
3 基于“心受氣于脾”理論防治心力衰竭
心力衰竭前期階段常常不伴有臨床癥狀,中醫似乎無證可辨,基于“心受氣于脾”理論,其病機可以歸納為心脾本虛、痰瘀內生。唐代孫思邈認為“心勞甚者,補脾氣以益之,脾旺則感之于心矣”。元代李杲提出“勞倦傷脾,脾胃虛……當先于心分補脾之源”,主張補脾以治心病。現代國醫大師鄧鐵濤認為在心衰的病理演變中,五臟以脾與心的關系最為密切,并創立調脾護心法[17]。故防治心力衰竭當以益氣健脾、化濁祛瘀為治療大法,以調理后天之本為要。黃芪味甘性溫,善入脾胃,為益氣健脾要藥,又能利水消腫,臨證時常芪參并用,增強補氣之效,黃芪可隨病情進展而增加,脾運得健,氣陽充沛,推動氣血津液運行,瘀血、痰飲等陰邪自散;與白術、茯苓、薏苡仁合用,健脾化痰滲濕。溫陽可增強心臟功能,減輕心肌細胞負荷,預防心功能向失代償轉變,常用淫羊藿、杜仲、巴戟天等平和之品,以微微少火恢復陽氣,少用附子、肉桂等溫燥之品;謹慎藥性溫燥傷陽,故少伍麥冬、黃精、女貞子等藥性薄潤之品,平補心陰,少用熟地黃等滋膩易生水濕之品。心主血脈,需加用活血化瘀藥,維持心臟生理功能,如當歸、莪術;利水藥可減輕心臟負荷,可選水紅花子、路路通等。此外,可結合現代藥理學依據,優選具有降壓、調脂、降糖作用的中藥,如高血壓加用天麻、鉤藤、玉米須、鬼針草,冠心病、肥胖加用生山楂、澤瀉、絞股藍,糖尿病加用桑葉、葛根。在臨床實踐中,汪磊等基于“心脾相關理論”發現調脾護心方可以降低半乳糖凝集素-3和基質金屬蛋白酶-9(MMP-9)水平,抑制促炎因子白細胞介素-17(IL-17)、白細胞介素-6(IL-6)和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的表達,抑制心肌纖維化,改善心肌重構[18]。王萍發現芪藶苓桂術甘湯可以降低C反應蛋白(CRP)、IL-6、TNF-α和白細胞介素-8(IL-8)等炎性因子水平,抑制冠心病心衰患者的心室重構[19]。
4 病案舉隅
患某,女性,47歲,于2019年12月4日初診。患者2年前體檢查心臟彩超提示左心室擴大(左室舒張末內徑56 mm),射血分數正常,心電圖正常。予琥珀酸美托洛爾緩釋片23.75 mg口服,每日1次,病程中無胸悶氣喘,無下肢水腫,活動不受限。2019年9月4日復查心臟超聲,左室內徑無明顯變化。為求進一步診治,遂于門診就診。就診時,患者無特殊不適,平素倦怠乏力,納寐可,小便調,大便質軟。否認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病史,否認家族類似疾病史。查體:血壓120/80 mmHg(1 mmHg≈0.133 kPa),心率70次/min。形體偏胖,舌淡邊有齒印,苔薄白,脈細。中醫診斷:心衰病-氣陽不足證。西醫診斷:擴張型心肌病。處方:生黃芪20 g,炙黃芪20 g,黨參20 g,炒白術10 g,茯苓10 g,炒薏仁20 g,杜仲10 g,淫羊藿10 g,女貞子15 g,當歸10 g,莪術10 g,水紅花子15 g,黃連3 g。水煎服,每天2次,口服28劑。琥珀酸美托洛爾緩釋片71.25 mg,培哚普利4 mg,口服,每日1次。監測血壓、心率。后患者定期復診,中藥按原法繼進,逐漸加倍美托洛爾和培哚普利的劑量,病程中患者無胸悶、心慌、直立性低血壓癥狀等不適,自測血壓100/65 mmHg,心率60次/min。2020年7月1日復查心臟超聲:左室舒張末內徑53 mm,射血分數正常。
按:本案患者中年發病,先天稟賦不足,脾胃素虛,又飲食不節,脾胃運化失常,心失所養,心氣不足,雖自覺無明顯癥狀,心臟彩超提示左心室擴大,心功能尚可,心陽虛不甚。氣陽不足則血行無力,津液輸布受累,瘀血、痰濁漸積,合而為病。方中重用黃芪、黨參大補心脾之氣,脾旺則心中氣陽充沛,推動氣血津液運行,瘀血、痰濁自消;炒白術、茯苓、炒薏仁增強健脾之功,助化痰滲濕;杜仲、淫羊藿溫陽以助心行血,女貞子滋陰以補益心體,陰陽并補,體用兼顧;佐用當歸、莪術活血,水紅花子利水,使陰邪得散;少許黃連防溫燥耗傷氣陰。全方共奏益氣健脾、化濁祛瘀之功。
5 結 語
綜上所述,心衰前期階段的早期干預對于心力衰竭的防治至關重要,結合中醫“治未病”思想,從“心受氣于脾”理論出發,在心衰已有潛在的危險因素和一定發病基礎的階段,治其未成,治其未發,尤其重視調理后天之本,益氣健脾,化濁祛瘀,使得心氣充足,心脈通暢,延緩心力衰竭的發生與發展,充分發揮中醫治未病的理論優勢與實踐指導價值,為中醫藥防治心力衰竭提供新的診治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