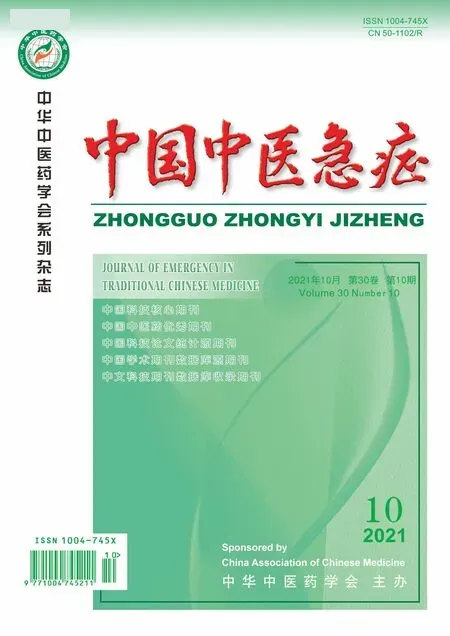撳針治療過敏性鼻炎的研究進展*
韓名媛 孫忠人 尹洪娜 馮秋菊 曹 燚 呂曉琳△
(1.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2.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0)
過敏性鼻炎(AR)又稱變應性鼻炎,是指機體暴露于變應原后由免疫球蛋白E(IgE)參與介導的鼻黏膜非感染性慢性炎性疾病,臨床以陣發性噴嚏、清水樣涕、鼻癢、鼻塞為典型表現,常伴有眼癢、流淚和灼熱感等眼部癥狀,為臨床常見耳鼻咽喉科疾病之一。隨著環境變化,AR發病率呈逐年上升趨勢,人口統計學顯示,AR在我國大陸地區患病率為4%~38%,嚴重影響患病人群的生活質量,加重心理及經濟負擔[1]。現代醫學主要應用糖皮質激素、抗組胺藥、白三烯受體拮抗劑等藥物治療本病,但長期應用局部不良反應較多,常伴有反跳性加重;變應原特異性免疫治療雖為指南中推薦治療方案,也存在變應原疫苗未規范化、標準化等問題,尚不能廣泛應用于臨床。因此,從中醫學角度挖掘新的治療思路及診療方案至關重要。縱觀近十年相關文獻,撳針療法已被廣泛應用于多種疾病的治療[2],應用撳針療法治療AR的相關研究也逐年增加,成效顯著,現綜述如下。
1 病因病機
1.1 AR的病因病機 AR在中醫學中可歸屬于“鼻鼽”范疇。中醫關于AR的記載最早見于西周《禮記·月令》“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秧敗,民多孰嚏”。本病屬本虛標實證,與肺、脾、腎三臟虛損關系密切,中醫辨證主要以肺氣虛寒、脾氣虛弱和腎陽虧虛為主[3]。經絡學說認為,AR與陽經經脈關系密切,故針刺治療本病多取督脈、足太陽膀胱經及手足陽明經穴位[4]。督脈為陽脈之海,統一身之陽氣,可條暢氣機增強正氣以抵御外邪;足太陽膀胱經主一身之表,可充分激發經氣,調整臟腑功能[5]。手陽明大腸經“上夾鼻孔”,足陽明胃經“起于鼻”,長于治療鼻部疾病;同時陽明經為多氣多血之經,肺與大腸相表里,均可調節經絡氣血、平衡陰陽[6]。從現代醫學角度分析,其病理變化主要以鼻黏膜變應性炎癥為特征,其中嗜酸性粒細胞、肥大細胞及T淋巴細胞在整個過程中起到較為明顯的作用[7],神經源性炎癥也是重要致病因素之一[8-9],治療關鍵在于抑制炎性黏液分泌增加和炎性細胞浸潤,穩定和抑制炎性介質的合成釋放,降低炎性神經肽水平[10]。
1.2 撳針治療AR的作用機制 撳針療法主要基于“十二皮部”理論而創立,可通過淺刺皮部長時間留針給予機體刺激,激發循于體表剽悍之衛氣以護衛肌表,抵御外邪。《靈樞·海論》有言“夫十二經脈者,內藏于腹藏”,十二皮部也可通過經脈的傳輸作用于相應臟腑,以疏通經絡、調和氣血。撳針療法淺刺微痛,作用較為溫和,彌補了毫針針刺時間短、針刺過深傷及皮膚血管和穴位埋線較為煩瑣的缺陷,因此,撳針療法治療AR具有獨特優勢[11]。撳針刺入體內時針體腐蝕并釋放出微量元素,在體內產生微電流,刺入皮膚時產生的微電流可改變局部電位差,直接刺激神經末梢感受器抑制病理興奮,緩解病灶部位痙攣,改善局部血液循環,同時刺激表皮細胞參與機體免疫調節,起到治療作用[12-13]。
2 撳針治療AR的臨床療效
2.1 撳針單一療法 AR主要由于臟器虛損,正氣不足,復感風寒濕邪所致,治療多標本兼治,臨床多局部結合辨證取穴,常選擇迎香、印堂、合谷、足三里、風池、鼻通、肺俞、脾俞、百會、大椎等穴位協同治療,以疏通局部氣血,補益臟腑[14]。安榮榮[6]取印堂、雙側迎香、風池、肺俞、合谷,對比觀察撳針與西藥鹽酸西替利嗪的療效,治療4周后發現撳針對中重度AR療效更明顯,對患者鼻塞、鼻癢、流涕等臨床癥狀均有改善,且隨訪發現治療結束后仍可發揮一定的后續效應。陳妙情[15]評估撳針治療AR的療效,認為撳針可通過刺激抑制組胺的合成及釋放,減少炎性分泌緩解癥狀以實現療效。石磊等[16]發現AR患兒多病程較長,久病入絡導致臟腑虛損,津液代謝異常,故基于絡病理論對60例AR患兒進行臨床治療,撳針印堂及雙側迎香穴,結果表明兩組鼻部癥狀評分均顯著下降,且撳針組更為顯著。
2.2 撳針聯合中藥復方制劑 現代藥理研究顯示一些中草藥具有降低炎性反應及抗過敏的作用,對改善AR的鼻部癥狀安全有效,臨床多將此類藥物配伍以固表實衛、益氣溫陽,達到治療AR的目的[17]。郝蕊[18]針藥并施,將撳針與自擬中藥方鼻炎1號(黨參30 g,黃芪25 g,白術、茯苓、訶子、五味子各20 g,荊芥、防風、辛夷花、枸杞子、女貞子各15 g,蒼耳子、甘草各10 g,細辛5 g)合用,穴位取雙側迎香及足三里,溫肺健脾、通竅固表以治療AR。觀察發現撳針結合中藥組在改善AR患者食少納呆、氣短懶言等次癥方面療效顯著,為臨床治療提供可靠依據。佟曉英[19]選取“鼻三穴”印堂、鼻通、迎香及手太陰、陽明經的合谷、曲池、少商、孔最穴施以撳針,聯合清肺止鼽湯治療AR,清肺通竅、通經活絡,明顯改善患者鼻塞、流涕、煩熱等癥狀,療效確切。實驗研究發現,攝涕止鼽湯在不同劑量下均可降低AR大鼠血液里白細胞介素-5(IL-5)與嗜酸細胞陽離子蛋白(ECP)含量,調節Th1/Th2細胞失衡狀態發揮療效[20]。許多證據表明,除Th1/Th2細胞分化失衡外,Th17/Treg細胞分化失衡也參與了AR的發生發展[21]。洪冬冬等[22]應用撳針聯合攝涕止鼽湯辨證加減治療AR(肺氣虛寒證),將撳針貼埋于印堂及雙側迎香、風池、肺俞、足三里穴,留針3 d后取出,聯合攝涕止鼽湯(黃芪25 g,生白術、防風、肉桂、黃精各15 g,地龍、干姜各10 g,細辛3 g)治療,治療周期為4周,并觀察患者血清Th17和Treg相關細胞因子水平變化情況,結果顯示治療后聯合組血清白細胞介素-17(IL-17)、白細胞介素-10(IL-10)和轉化生長因子-β1(TGF-β 1)的表達水平均有改變,各項癥狀評分和總分均顯著降低,療效優于單純攝涕止鼽湯或西藥治療,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3 撳針聯合西藥 中西醫結合治療疾病,二者互為補充,不僅能協同增效,也能通過減少西藥用量,控制不良反應的發生。牟月[23]采用撳針聯合孟魯司特鈉對90例持續性變應性鼻炎患兒的臨床療效及生活質量進行分析。針刺印堂、左側合谷、雙側迎香、肺俞、足三里穴治療,每周2次,每次留針3 d,配合口服孟魯司特鈉。治療4周后觀察組患者鼻塞、流涕癥狀明顯好轉,遠期療效相較于假針聯合藥物更突出。張福蓉等[24]應用撳針埋于印堂及雙側迎香、足三里、肺俞穴,同時聯合口服氯雷他定片治療AR。隨訪發現撳針聯合口服氯雷他定片的復發率為41.7%,明顯低于單純撳針與假針組,對患者的臨床癥狀及生活質量方面均有明顯改善,具有臨床優勢。吳凌云等[25]認為,AR主要由于鼻部毛細血管擴張、腺體分泌增多所致,故取穴印堂、雙側迎香、足三里、肺俞施以撳針,配合布地奈德吸入劑聯合治療。囑患者每間隔2~3 h按壓1次撳針穴位,持續1 min,共治療6次。結果顯示鼻腔容積、鼻纖毛傳輸時間及黏膜纖毛清除率均有顯著改善。
2.4 撳針聯合耳穴療法 《靈樞·口問》指出“耳者,宗脈之所聚也”。《靈樞·邪氣臟腑病形》云“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于面而走空竅,其精陽之氣上走于目而為精,其別氣走于耳而為聽”。上述經文均闡述了耳與臟腑經絡的密切聯系。現代研究證實,刺激耳郭相應穴位,可提高內源性腎上腺皮質激素含量,收縮毛細血管,調節免疫功能,增強機體對過敏物質的耐受程度[26]。于洋[27]發現耳穴貼壓對IgE、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和白細胞介素-8(IL-8)等炎性因子的表達水平均有調節作用。林永青等[28]取胃、神門、風溪、腎、脾、肺、氣管、外鼻穴艾灸聯合撳針治療AR患者1例,療效肯定。
2.5 撳針聯合輔助療法 超激光治療儀具有直線偏振光的功能,可產生熱輻射效應,照射局部可改善血管壁通透性,減緩炎性滲出及充血、水腫情況,抑制神經興奮,調節自主神經功能,改善過敏區域神經對外界各種刺激的高反應狀態[29]。岳延榮[30]觀察證明,撳針聯合超激光可調節鼻黏膜感覺、交感及交感神經興奮性,抑制相關神經肽分泌,減輕鼻腔黏膜血管擴張,起到協同增效的作用。取上星、印堂及雙側鼻通、迎香、列缺、合谷、肺俞穴給予撳針埋針,配合采用超激光疼痛治療儀按順序照射兩側星狀神經節、鼻腔、迎香穴各5 min,每日1次,共治療20次。經治療,33例患者中顯效9例,有效17例,無效7例,總有效率為78.8%。
3 討論與展望
撳針又稱“撳釘型皮內針”,是指將針體刺入并固定于腧穴部位皮內或皮下進行較長時間留針,通過刺激量長時間累積達到治療疾病目的的方式。《素問·離合真邪論》中記載“靜以久留”,撳針療法是久留針的發展演變[31]。《針灸大成》云“病滯則久留針”,撳針療法通過對穴位的持續刺激,以時效積累量效,可促進經絡氣血運行、激發正氣,對慢性疾病的治療具有一定優勢。撳針留針埋于皮下,痛感微弱,不影響患者的日常活動,且適用范圍廣泛,操作簡便、經濟安全,易于被廣大患者及醫療工作者接受、選擇[32]。
隨著臨床治療及機制研究的不斷深入,撳針治療AR已不僅僅局限于單一療法,逐漸采取多種治療手段協同配合,其有效性不可忽視,但撳針治療AR仍存在一些不足。1)研究方法上,撳針治療AR缺少規范化、系統化的診療標準,療效評估多以AR相關量表為主,缺乏客觀指標;不同治療方案中選穴位置、治療時間、治療周期等不統一,很多臨床研究缺少遠期隨訪;臨床相關研究匱乏,文獻質量較低,根據臨床經驗針對個案治療的臨床研究相對較多,可信度不高,論據欠缺說服力。2)治療手段上,除撳針單一療法外,臨床上也結合西藥、中藥復方制劑、超激光輔助等治療方案,但結合推拿、艾灸等相關臨床研究鮮有報道,缺少橫向比較,治療方案有待多樣化;撳針留針時間長短不一,AR分期辨證與撳針介入時期、留針時長的相關性研究尚不深入。3)研究方向上,撳針治療AR的相關機制和深層次的研究較為缺乏,缺少基礎研究支持;AR可誘發支氣管哮喘、變應性結膜炎、鼻竇炎、中耳炎等疾病,常影響患者的睡眠質量,且多伴有情志異常[33],對于此類轉變,我們應進一步探討。
綜上所述,筆者針對以上問題提出建議。1)制定標準化治療方案,規范診斷與療效評價標準,積極開展大樣本、多中心的循證醫學研究。2)建立較為完善的遠期隨訪體系,明確撳針治療AR的遠期療效,增加嚴謹性與可信性。3)應重點著眼于撳針治療AR的相關理論實驗研究,針對其復雜的發病機制及經穴的非線性、動態性、特異性特征,多靶點、多途徑、多層次調節,為臨床提供指導。4)基于中醫整體觀念加強對AR患者負性情緒的調控,從單一模式向多維度模式轉變,全面調節患者身心健康,促進患者早日康復。5)AR與體質關系密切[34],可將中醫未病防治的思想應用于AR的治療,通過撳針早期干預,針對不同AR患者進行個體化治療,為撳針的臨床應用與推廣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