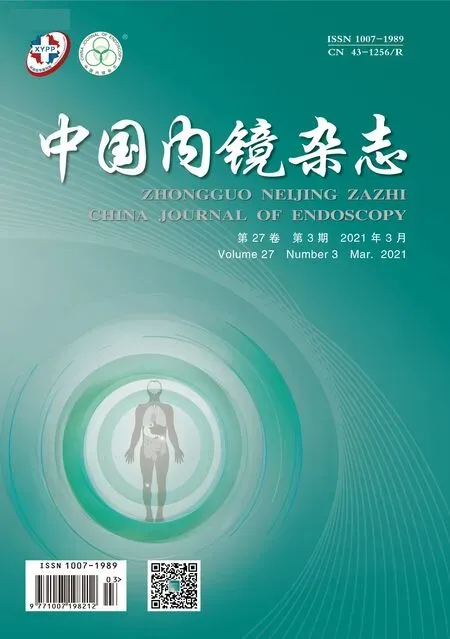關節鏡輔助下治療復雜脛骨平臺骨折的療效分析
余金勝,方文廣,冼樹強
(廣東省惠州市第六人民醫院 骨科,廣東 惠州516211)
脛骨平臺骨折是臨床中最常見的膝關節創傷之一,約占全身骨折的1.00%,占小腿部所有骨折的5.00%~8.00%[1-2]。臨床中對于脛骨平臺骨折的分類方法有Schatzker 分型、AO 分型和Hohl and Moore 分型,其中Schatzker分型是應用較多的方法。Schatzker分型中,Ⅴ型和Ⅵ型脛骨平臺骨折是因高能量暴力創傷導致的雙髁骨折和伴有干骺端與骨干分離的平臺骨折[3]。所有的脛骨平臺骨折都需要手術治療,在手術治療過程中,醫師根據X 線、CT 掃描等術前檢查結果來判斷骨折的部位及關節面的塌陷情況,從而決定手術入路,但任何入路均不能在完全直視下進行關節面復位,有時需要在半月板與關節囊之間做切口,不但觀察困難、準確度低,還增加損傷,骨折復位效果也難以保證,最終使得患者愈合效果較差[4]。
目前,關節鏡輔助下治療脛骨平臺骨折是臨床中探索的方向之一[5-7]。關節鏡不僅可以解決關節面復位困難的問題,還可以縮小手術切口、輔助微創置入內固定,并提高手術效果。而關于關節鏡輔助治療脛骨平臺骨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脛骨平臺SchatzkerⅠ型~Ⅳ型骨折,對于Schatzker Ⅴ型和Ⅵ型骨折較少涉及。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我院2017年1月-2018年12月收治的復雜脛骨平臺骨折患者的臨床資料,探討關節鏡輔助下治療復雜脛骨平臺骨折的臨床療效。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7年1月-2018年12月我院骨科收治的51 例復雜脛骨平臺骨折患者的臨床資料,根據手術術式分為關節鏡組(24 例)和常規組(27例)。納入標準:①經兩名主治以上影像科醫師和兩名主治及以上骨科醫師確診為復雜脛骨平臺骨折;②Schatzker分型為Ⅴ型和Ⅵ型;③單側、新鮮、閉合脛骨平臺骨折。排除標準:①合并同側肢體其他部位骨折;②創傷側肢體存在嚴重血管、神經損傷;③小兒骨折;④陳舊骨折畸形愈合或病理性骨折;⑤患者合并嚴重基礎疾病;⑥病歷資料不完整。本研究經我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患者均為新鮮、閉合脛骨平臺Schatzker Ⅴ型和Ⅵ型骨折。兩組患者年齡、性別、受傷部位、受創因素、受創后至手術時間、Schatzker分型和隨訪時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1.2 方法
1.2.1 急診處理所有患者入院后評估患肢軟組織創傷程度,患肢行跟骨牽引術、膝關節冰敷和下肢踝泵、等長舒縮等功能鍛煉,待腫脹消退、皮膚出現褶皺后行手術治療。關節鏡組受創至手術時間3~8 d,平均(5.60±2.40)d;常規組受創至手術時間4~9 d,平均(6.71±3.70)d。
1.2.2 術前處理所有患者術前患側肢體均行X線正、側位檢查和CT 掃描;給予止痛、低分子肝素等藥物治療,預防下肢深靜脈血栓。
1.2.3 手術方法兩組手術均由同一組高年資骨科醫師完成。腰硬聯合麻醉成功后,取平臥位,患肢大腿根部扎氣囊止血帶,術區常規消毒、鋪單。驅血帶驅血,止血帶壓力控制在45 kPa,患肢屈膝75°~90°。①關節鏡組:取膝關節前內、外側標準入路進入關節腔,沖洗關節腔,待術野清晰后檢查整個關節腔塌陷程度及半月板、韌帶損傷程度,修復損傷的半月板,二期重建完全斷裂的交叉韌帶;在關節鏡監視下,明確關節面的塌陷程度、范圍及骨折線的位置,撬撥復位關節面及骨折塊,評估復位效果,如撬撥復位困難,則做小切口切開復位,但不經半月板下方即可直接顯露關節面,減少二次創傷,對于缺損較大的骨折部位,選擇同側髂骨取骨植骨,復位滿意后微創置入鋼板及螺釘內固定,先沖洗再留置引流縫合切口;②常規組:在切開直視下,通過牽引、撬撥和頂棒抬高等方法將塌陷骨折塊復位,術中C 型臂透視復位滿意,再置入鋼板及螺釘內固定,沖洗后留置引流并縫合切口。兩組患者術后均常規使用抗生素24 h 預防感染。
1.3 術后處理及隨訪
1.3.1 功能恢復術后切口出現紅腫或患有糖尿病等基礎疾病的患者,抗生素可使用至術后2 或3 d。術后第3天鼓勵兩組患者開始膝關節功能訓練,以股四頭肌收縮鍛煉和直腿抬高鍛煉為主。術后2 d 拔除引流管后復查膝關節X 線。術后1、2、3、6、9、12和15個月復查膝關節正、側位X線。
1.3.2 觀察指標記錄兩組患者手術切口總長度(含內、外、后切口)、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后引流量、住院時間、骨折愈合時間、完全負重時間和并發癥情況。術后近期并發癥:植入物排斥反應、切口感染、關節腔感染;術后遠期并發癥:延遲愈合、螺釘松動、內固定斷裂、關節僵硬、創傷性關節炎。
1.3.3 膝關節功能評分末次隨訪時,采用膝關節損傷和骨關節炎評分(the knee injury and osteoarthritis score,KOOS)及Rasmussen 影像學評分對膝關節功能情況進行評估。KOOS評分:包括疼痛、癥狀、日常生活能力、運動及娛樂5項,每項有數量和內容不同的若干問題,每個問題的答案可獲得0~4 分;將每項得分根據百分制轉換后即為最終得分,分數越高,表示膝關節功能恢復越好,滿分為正常膝關節。Rasmussen 影像學評分:包括成角畸形、髁部變寬、關節面塌陷3項評分,每項滿分6分,分數越高,代表骨折復位效果越好。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4.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分析,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手術情況比較
關節鏡組患者手術切口長度短于常規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關節鏡組患者術中出血量、住院時間、骨折愈合時間、完全負重時間明顯少于常規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手術時間和術后引流量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術中術后情況比較 (±s)Table 2 Comparison of intra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condi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

表2 兩組患者術中術后情況比較 (±s)Table 2 Comparison of intra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condi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
組別手術時間/min 術中出血量/mL 術后引流量/mL 住院時間/d關節鏡組(n=24)切口總長度/cm 5.96±1.22 102.10±15.06 223.00±38.06 130.10±26.06 10.10±2.06骨折愈合時間/月3.70±1.06完全負重時間/月4.20±0.60常規組(n=27)t值P值10.70±3.21 2.37 0.014 110.70±35.21 1.42 0.567 358.00±25.00 2.26 0.012 142.70±35.21 1.49 0.075 13.50±4.56 2.18 0.022 4.01±1.21 1.56 0.042 4.70±0.21 1.61 0.046
2.2 兩組患者并發癥比較
術后近期并發癥:關節鏡組患者有2例切口出現紅腫等感染癥狀,抗感染治療后好轉;常規組有6例切口出現紅腫等感染癥狀,抗感染治療后好轉,3例關節腔感染,行二次手術治療。術后遠期并發癥:關節鏡組患者有3例關節僵硬;常規組有4例延遲愈合、3例螺釘松動、3例關節僵硬和3例創傷性關節炎。關節鏡組近期和遠期并發癥發生率明顯低于常規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術后近期和遠期并發癥發生率比較Table 3 Comparison of incidence of short-term and long-term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2.3 兩組患者膝關節功能評分
末次隨訪時,關節鏡組KOOS 評分中,疼痛和癥狀評分明顯高于常規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日常生活能力、運動和娛樂評分與常規組相比,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Rasmussen 影像學評分中,關節鏡組成角畸形、髁部變寬、關節面塌陷評分明顯高于常規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關節鏡組患者優良率79.16%明顯高于常規組的51.8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55,P=0.006)。見表4和5。
表4 兩組患者術后KOOS評分比較 (分,±s)Table 4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KOOS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core,±s)

表4 兩組患者術后KOOS評分比較 (分,±s)Table 4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KOOS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core,±s)
組別關節鏡組(n=24)疼痛80.15±10.22癥狀82.96±8.22日常生活能力81.07±11.22運動64.96±12.02娛樂75.96±1.22常規組(n=27)t值P值70.70±8.21 2.57 0.008 74.60±3.21 2.75 0.003 80.50±10.01 0.86 0.151 59.40±13.21 1.03 0.146 70.30±3.21 4.33 0.96
表5 兩組患者術后Rasmussen影像學評分比較 (分,±s)Table 5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Rasmussen imaging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core,±s)

表5 兩組患者術后Rasmussen影像學評分比較 (分,±s)Table 5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Rasmussen imaging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core,±s)
組別關節鏡組(n=24)成角畸形5.46±0.12髁部變寬5.42±0.31關節面塌陷4.90±0.23常規組(n=27)t值P值4.70±0.71 3.26 0.001 4.28±1.25 1.72 0.032 3.72±1.11 2.87 0.004
3 討論
3.1 脛骨平臺骨折
脛骨平臺是人體主要的負重關節,其成分主要為松質骨,脛骨平臺骨折多由車禍傷、高墜傷等高能量損傷導致,且常伴有關節面塌陷、移位和平臺劈裂。因此,在X線片上,脛骨平臺骨折常呈爆裂樣改變[8]。當脛骨平臺塌陷深度超過3 mm 時,關節腔內壓力就會增高,此時需盡快行手術治療,恢復關節面的解剖結構和功能[9]。手術的關鍵在于恢復關節面的平整、糾正下肢的立線和穩定性。脛骨平臺骨折治療原則應遵循:①最大可能做到解剖復位、堅強固定和恢復塌陷關節面;②糾正骨干部分的旋轉和成角畸形,力求恢復下肢立線;③盡早開始術后功能鍛煉和康復治療;④盡可能保留軟組織的功能。
其中,關節面的復位是治療成敗的關鍵之一,復位不當容易造成創傷性關節炎和遠期關節功能恢復不良。特別是Schatzker Ⅴ型和Ⅵ型的復雜脛骨平臺骨折,損傷程度大,骨折塊粉碎、移位明顯,且多合并膝關節周圍軟組織損傷,而手術入路的選擇、骨折塊的復位和內固定的置入對臨床醫師是一個極大的挑戰[10]。在以往的手術中,通過大切口直視下復位骨折,手術視野有限,不但觀察困難、不準確,還增加損傷的風險,骨折復位效果也難以保證,最終使得患者愈合效果較差。
隨著手術方式的改進,影像技術特別是CT 掃描和三維重建的廣泛應用,脛骨平臺骨折手術的治療滿意率大幅度提高。但是,大量研究[11-14]表明,在脛骨平臺骨折治療中,畸形愈合和創傷性關節炎仍是術后主要并發癥。發生并發癥的主要原因在于:醫師對骨折類型理解不深、關節面復位不良、重要骨折塊內固定不夠穩固和下肢力線恢復不到位等。
3.2 關節鏡技術的應用
隨著骨科手術微創理念不斷得到認可和微創技術的發展,關節鏡技術在脛骨平臺骨折治療中應用逐漸增多[15]。傳統的手術方式需要做大切口來暴露骨折斷端,有時需要切開關節囊,對膝關節周圍軟組織損傷較大,且術后瘢痕組織容易影響膝關節功能[16]。1985年JENNINGS[17]首次將關節鏡技術應用于輔助治療脛骨平臺骨折,該技術在脛骨平臺骨折中用于監視關節面塌陷的恢復情況,可降低對膝關節周圍軟組織的損傷風險,在小切口修復半月板與交叉韌帶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臨床效果[18]。研究[19]顯示,關節鏡技術在脛骨平臺骨折治療中的最大優勢便是微創,既可以在不打開關節囊的前提下清除關節腔內壞死組織,又可以在直視下觀察到關節面的復位情況,減少了手術對關節周圍軟組織的創傷,給骨折復位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但是,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簡單的脛骨平臺骨折,而對于復雜的脛骨平臺骨折,如脛骨平臺Schatzker Ⅴ型和Ⅵ型骨折等,研究相對較少。
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51 例復雜脛骨平臺骨折的(Schatzker Ⅴ型和Ⅵ型)治療效果。其中,實驗組采用關節鏡下輔助糾正關節面塌陷,并根據鏡下所見選擇微創入路置入內固定,對照組采用傳統切開直視下復位并置入內固定。本研究顯示,實驗組手術切口總長度(含內、外、后切口)平均為(5.96±1.22)cm,對照組為(10.70±3.21)cm,實驗組明顯短于對照組(P<0.05);實驗組術中出血量(223.00±38.06)mL、住院時間(10.10±2.06)d、骨折愈合時間(3.70±1.06)個月、完全負重時間(4.20±0.60)個月,對照組術中出血量(358.00±25.00) mL、住院時間(13.50±4.56)d、骨折愈合時間(4.01±1.21)個月、完全負重時間(4.70±0.21)個月,上述實驗組手術效果及術后恢復效果均明顯優于對照組(P<0.05)。關節鏡組膝關節KOOS 評分中疼痛和癥狀評分、Rasmussen 影像學評分的成角畸形、髁部變寬和關節面塌陷評分明顯高于常規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實驗組患者近期和遠期并發癥發生率也明顯低于對照組,且實驗組優良率79.16%明顯高于對照組的51.8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綜上所述,關節鏡輔助下治療復雜脛骨平臺骨折與常規切開內固定治療相比,切口小、住院時間、骨折愈合時間及完全負重時間短、術中出血量少、術后癥狀改善明顯,膝關節功能恢復良好,可作為復雜脛骨平臺骨折的常規治療方法。本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未對手術入路的選擇、內固定植入物的數量和大小進行研究探討,且納入的病例數量較少、隨訪時間相對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