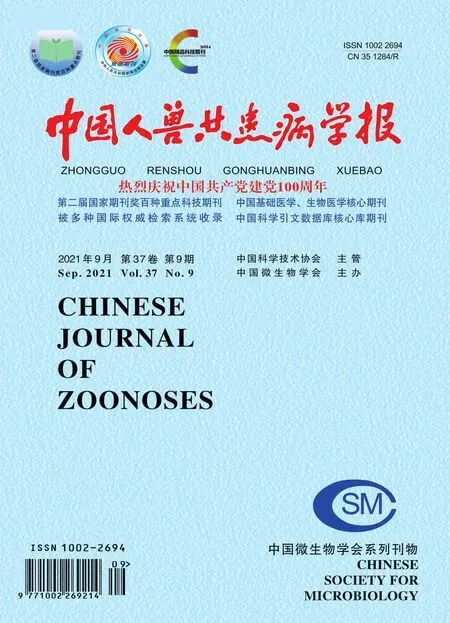艱難梭菌感染與腸道微生態的研究進展
王曉亞,安彥波,戴敏高,趙麗娜,劉軍肖,牛占叢
1 艱難梭菌與腸道微生態概述
艱難梭菌(Clostridiumdifficile)是一種嚴格厭氧的革蘭陽性芽孢桿菌[1],但它可以在有氧環境中存活。艱難梭菌定植于3%的健康成人和近80%的健康新生兒及嬰兒的腸道中,它屬于條件致病菌, 正常腸道菌群可以抵抗艱難梭菌的定殖和過度生長,而在長期大量使用抗生素的患者或其他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中,艱難梭菌會過度增殖并釋放毒素,引起以腸道病理損傷為主的感染性疾病,即艱難梭菌感染(Clostridiumdifficileinfection,CDI)[2]。艱難梭菌是引起抗生素相關腹瀉的最主要病原菌,可引起一系列疾病,如腹瀉、暴發性結腸炎、假膜性結腸炎、中毒性巨結腸、腸穿孔、膿毒癥和多器官功能障礙,是醫院內獲得性細菌感染及胃腸炎癥相關死因的首要原因,嚴重威脅住院患者的健康[3-4],據報道,艱難梭菌感染病死率可高達6.9%~16.7%[5]。高毒力的艱難梭菌菌株(BI/NAP1/027型)[6]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問題,使得艱難梭菌感染引起了更多的關注,該型菌株可引起暴發型結腸炎,病情進展迅速,病死率高,預后差。在過去的十年中,由于與艱難梭菌感染相關的發病率、死亡率和醫療費用的增加,艱難梭菌受到了新的關注[7]。
腸道微生態包含腸道微生物及其代謝產物。人體內的微生物數量至少和人體細胞的數量一樣多[8],這些微生物可存在于人體所有的粘膜部位。腸道是微生物數量最豐富的器官,由1 000多個不同的細菌種類組成,其編碼的基因數量是人體自身基因數量的數百倍,腸道菌群的總質量可達1.5 kg[9-10]。腸道微生物分布廣泛、數量龐大,人體腸道內定居著約一百萬億個微生物,并且其基因組含有參與膽汁酸代謝、碳水化合物發酵、氨基酸代謝等基因,在人體作用機制復雜,參與人體的多種生理及病理過程。腸道微生物與多種代謝、內分泌、自身免疫和炎癥性疾病有關,并參與物質代謝和營養合成[9-13]。了解腸道微生態的改變與艱難梭菌之間的聯系有望確定新的治療策略和生物標志物,從而預測治療結果并提高診斷水平。
2 艱難梭菌致病機制
艱難梭菌在人體腸道內定植主要分為產毒型菌株和非產毒型菌株,而產生致病作用的主要是產毒型菌株。艱難梭菌在腸道內增殖并分泌毒素A(toxin A,TcdA)和毒素B(toxin B,TcdB)兩種毒素,TcdA是一種腸毒素,也有一定的細胞毒性作用,TcdB是一種細胞毒素,毒素B的毒力較毒素A強10倍[14-16],毒素激活腸道宿主免疫,使中性粒細胞增加,并產生殺菌活性氧中間體、防御素、促炎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17],導致強烈的炎癥反應。這些毒素還通過多種通路與腸道上皮細胞表面受體結合,轉運到胞漿,然后修飾Rho、Ras和Rap亞家族的小分子GTP酶,通過這一作用破壞腸道上皮肌動蛋白骨架和緊密連接[18],使真核細胞骨架崩潰,并對腸上皮細胞產生細胞毒作用,引起結腸炎癥等一系列病變。有些毒株還會產生由染色體上致病性決定區外的基因cdt A、cdt B編碼的二元毒素[19],從而使艱難梭菌毒力進一步增強。CDI 發病率和嚴重程度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一種新的艱難梭菌毒株的出現,即 BI/NAP1/027[20],該菌株中TcdA和TcdB的產生增加,存在二元毒素,同時發現一種重要毒素產生下調基因 tcd C的缺失,可能有助于艱難梭菌毒性增加[6]。
腸道微生態紊亂是艱難梭菌致病的另一個潛在因素。腸道微生態紊亂可能通過膽汁酸代謝、氨基酸代謝、碳水化合物發酵物等代謝物來增加艱難梭菌的致病性。腸道微生物對膳食纖維進行厭氧發酵會產生短鏈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s),當SCFAs濃度下降時,pH升高,從而產生有利于艱難梭菌生長的環境[21]。初級膽汁酸可以促使艱難梭菌芽孢萌發[22]。另外一些研究表明,艱難梭菌的非毒素分子,特別是S層蛋白 (S-layer protein, SLP),具有免疫調節作用。研究表明艱難梭菌外蛋白質組組成與艱難梭菌基因型相關,某些菌株分泌的特定蛋白質可能與TcdA和TcdB的毒力增效有協同作用,生化分析表明,一種基因型為ST54_NAPCR1的菌株分泌的S層蛋白A(S-layer proteinA, SlpA)比其他菌株多,此外,ST54_NAPCR1菌株的SLpA具有較強的促炎活性[23-24]。
3 艱難梭菌感染的高危因素
多種危險因素可以導致CDI,關于CDI的危險因素的研究日益增多,但結論不盡相同,主要包括長時間住院、年齡大于65歲、免疫功能低下、使用抗生素治療和應用質子泵抑制劑等[23,25]。CDI的危險因素與腸道微生態的改變有關。
3.1 抗生素 艱難梭菌感染通常與抗生素引起的正常腸道微生物區系多樣性喪失有關。正常情況下,腸道微生態在維持健康人體新陳代謝,免疫防御方面起重要作用[26]。引起艱難梭菌感染的抗生素,幾乎涵蓋了所有的種類,尤以第三代頭孢菌素、廣譜青霉素、碳青霉烯類等廣譜抗生素居多[27-29]。同時,CDI 的發生風險取決于抗生素使用的頻率、持續時間、抗生素的給藥方式和使用藥物的劑型[30]。不同種抗生素產生了獨特的腸道微生物群落,增加一些促進艱難梭菌生長底物的濃度,例如初級膽汁酸以及生長所需的甘露醇、果糖、山梨醇、棉子糖和水蘇糖等碳源使艱難梭菌得以定植[22, 31-32]。與健康人相比,接受抗生素治療的人的腸道微生物態顯示出微生物多樣性、均勻性和豐富度降低。抗生素會改變腸道菌群的組成,包括腸桿菌科豐度增加和毛螺菌科、瘤胃球菌科、雙歧桿菌豐度的降低,影響微生物代謝,使艱難梭菌等增加[33]。另外,抗生素的使用會改變微生物的結構和膽汁酸的代謝,進一步啟動艱難梭菌芽孢的萌發。此外,免疫系統和腸道微生物群之間信號通路的改變也可能導致抗生素暴露后對CDI的易感性增加。
3.2 年齡 腸道正常菌群是一種重要的天然防御機制,可抑制艱難梭菌的生長。多項臨床數據分析提示年齡是CDI的獨立危險因素[34-35]。老年人常合并基礎疾病、既往抗菌藥物史、自身免疫力和抵抗力降低等,故抵抗 CDI 的能力也明顯下降。年齡大于65歲的老年人,尤其是既往長期住院或長期處于療養院等醫療機構的老年人應該高度警惕CDI的發生。
3.3 質子泵抑制劑 使用藥物(質子泵抑制劑,PPIs)抑制胃酸的產生也會增加艱難梭菌感染的風險。PPIs可以抑制胃酸的分泌,導致胃內pH升高、胃酸保護屏障破壞,引起胃腸道系統的各類不良反應,更加有利于艱難梭菌的定植。多系統評價表明,PPI的大量使用可以引起腸道微生態紊亂,誘發艱難梭菌感染[27, 36-37]。并且研究表明CDI的風險具有劑量依賴性[37]。因此,臨床上應該注意PPIs的適應癥和使用劑量,以降低CDI風險。
4 腸道微生態的定植抗性
腸道微生態失調會導致機體抵抗艱難梭菌感染的屏障被破壞,同時艱難梭菌感染也會導致腸道微生態紊亂,進而使腸道屏障功能下降甚至喪失,在腸道菌群被抑制的人群中細菌很容易定居并繁殖成為優勢菌群。腸道菌群主要分為4個菌門:厚壁菌門、擬桿菌門、變形菌門和放線菌門,健康的腸道微生物群主要以厚壁菌門及擬桿菌門為優勢菌門。艱難梭菌感染等因素可以破壞宿主腸道屏障和腸道菌群結構,尤其是降低厚壁菌門和擬桿菌門的豐度。基因組分析顯示,艱難梭菌感染后腸道微生態發生改變,表現為物種多樣性和豐富度顯著下降,主要是擬桿菌門的擬桿菌科和厚壁菌門(Firmicutes)的瘤胃球菌科(Ruminococcaceae)、毛螺菌科(Lachnospiraceae)減少[38]。腸道中可用于艱難梭菌萌發和生長的代謝物,主要受到厚壁菌門和擬桿菌門兩個優勢門的強烈影響[22]。
腸道微生態的平衡和穩態有助于宿主抵抗細菌、病毒和真菌感染,即定植抗性。腸道微生態定植抗性的機制主要包括以下4個方面。一是腸道菌群與病原體營養和空間競爭:細菌等病原體為了在腸道中定居,必須與高度適應腸道環境的腸道微生物群爭奪相同的營養源。腸道微生物競爭性消耗和利用某些單糖等營養物質,從而抑制艱難梭菌等病原體的繁殖。二是腸道微生物分泌抑菌或殺菌的小分子從而抑制致病菌定植:腸道微生物群某些菌株可以產生和分泌具有抑菌或殺菌活性的小分子,如內源性抗菌肽類物質、細菌素和溶菌酶等[39]。當艱難梭菌進入人體后,腸道內的抗菌肽類物質發揮抗菌作用。但同時,一些病原菌也可以通過此種方式影響腸道菌群從而在腸道內定植。三是腸道微生物產生代謝產物抑制病原體的生長:如次級膽汁酸、SCFAs、氨基酸等代謝產物[40-42]。SCFAs可以通過影響細胞內的pH和代謝功能來抵抗病原菌的生長,且短鏈脂肪酸的濃度與腸道pH值呈負相關,另外,SCFAs等代謝副產物激活免疫反應,從而影響全身免疫應答[9]。琥珀酸是腸道微生物碳水化合物發酵產生的有機酸,是腸道中的一種重要中間代謝物,可促進體內艱難梭菌的感染[43-44]。在健康的腸道微生態中,初級膽汁酸鵝脫氧膽酸、次級膽汁酸脫氧膽酸和石膽酸能抑制艱難梭菌在大腸內的孢子萌發和生長。然而,抗生素的使用會改變微生物的結構和膽汁酸的代謝。一項在小鼠腸道進行抗生素誘導的實驗表明,抗生素誘導后引起小鼠腸道微生物群和代謝組的改變,腸道內初級膽汁酸在腸道微生物產物作用下脫羥基轉化為次級膽汁酸[45],從而有利于艱難梭菌的生長,同時促進艱難梭菌孢子的萌發,增加了CDI的易感性。甘氨酸與某些膽汁酸結合可促進艱難梭菌的萌發。組氨酸含量的增加與艱難梭菌陽性的患者樣本有關,此外,抗生素敏感小鼠盲腸內容物中N-乙酰化甲硫氨酸、亮氨酸和異亮氨酸增加,而N-乙酰化天冬氨酸減少[46]。四是腸道微生物可增強免疫應答抵抗病原菌定植:腸道微生物對于多種免疫細胞的發育和功能是必不可少的,腸道微生物群可以對腸道免疫細胞群產生局部和全身性影響,包括影響固有淋巴細胞(innate lymphoid cells,ILCs)和Th17(T helper 17 cells)產生細胞因子、調節性T細胞(Tregs)的分化、激活中性粒細胞、誘導IgG反應等[10, 47-48]。Chen等實驗展示了由γδT細胞產生的IL-17A在抵抗艱難梭菌感染的宿主防御中的重要作用[49]。動物實驗證實給小鼠直腸注射純化蛋白SlpA可引起全身性和局部性體液免疫反應,產生IgG和IgA抗體,能減少艱難梭菌在小鼠腸道中定植[50]。
5 艱難梭菌感染的治療
大多數的艱難梭菌感染是由使用抗菌藥物后健康的腸道菌群紊亂引起的,CDI 治療的首要原則是盡早停止目前正在使用的的抗菌藥物,其次是口服有效治療藥物。目前臨床上用于治療 CDI 的藥物主要包括甲硝唑、萬古霉素、非達霉素等。CDI治療的基石最近由甲硝唑和萬古霉素改為萬古霉素和非達霉素。
有研究表明益生菌在預防原發性CDI方面有積極作用。然而,這些研究在益生菌的劑量和類型、艱難梭菌菌株、抗生素的劑量和類型以及治療的時機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歐洲[51]和美國[52]的CDI防治指南均建議對于復發性和難治性CDI,經常規治療無效后可以考慮糞便菌群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治療,以恢復患者腸道菌群穩態,減少艱難梭菌定植。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的一篇文章報道了與接受萬古霉素治療相比,經十二指腸FMT治療復發性CDI的成功率為80%[53]。FMT是治療CDI的一種高效方法[54],已被證明能誘導微生物區系恢復。移植的正常的腸道菌群可以競爭性抑制艱難梭菌的生長,同時產生氨基酸、SCFAs、次級膽汁酸等代謝物,從而抑制艱難梭菌的定植和生長。研究證明FMT后丁酸、乙酸和丙酸等短鏈脂肪酸的水平持續升高,脫氧膽酸和石膽酸等次級膽汁酸隨時間變化有不同的恢復。這些增加的代謝物與毛螺菌科、瘤胃菌科和未分類的梭菌屬的細菌有關,而初級膽汁酸與這些菌群呈負相關[55]。Weingarden等描述了糞便膽汁酸成分調節CDI的有力證據,患者進行FMT前的樣本中缺乏石膽酸、脫氧膽酸等次級膽汁酸,而進行FMT后捐贈者的樣本中膽酸和鵝脫氧膽酸等初級膽汁酸顯著減少[56]。類似地,Allegretti等研究發現,與來自健康對照組的樣本相比,初發和復發CDI患者的樣本中初級膽汁酸水平顯著升高,次級膽汁酸水平顯著降低。他們還指出,與初發CDI患者的樣本相比,復發病例的樣本中初級膽汁酸顯著升高[57]。FMT已被證明是治療復發性CDI最有效的方法。然而,由于受實際情況及道德倫理影響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可以進行FMT治療。
6 艱難梭菌感染的預防
艱難梭菌通過糞-口途徑傳播,通常住院患者艱難梭菌的攜帶率為7%~11%。許多艱難梭菌感染患者在治療成功后成為無癥狀攜帶者,并通過孢子在宿主之間傳播[58],預防CDI最重要的是合理的使用抗生素和控制感染途徑[59]。特別是在艱難梭菌感染暴發期間,減少艱難梭菌的傳播需要嚴格遵守接觸預防措施,原因不明的腹瀉患者需要進行隔離。醫護人員都應采取手部衛生和物理防護措施,包括戴手套和穿防護服。艱難梭菌芽孢對消毒劑如乙醇、高溫、紫外線等有較強的抵抗性,酒精不能殺死艱難梭菌的孢子[60],可以在物體表面存在數月到數年,從而在人群中傳播。用肥皂水洗手比使用酒精擦手更有效地清除艱難梭菌。因此,建議先用肥皂和水洗手,然后用含酒精的洗手液消毒,使用具有滅孢子功能的產品進行環境消毒,例如稀釋次氯酸鈉(家用漂白劑)[52]。
一些研究提出益生菌可作為艱難梭菌高危人群預防性治療[61-62],但目前的研究仍存在爭議,沒有足夠的數據,建議在臨床實驗之外使用益生菌作為CDI的預防。在益生菌被納入預防措施之前,迫切需要專門研究確定益生菌是否有效,以及確定哪種類型的細菌、劑量和服藥時間可以降低CDI的風險。因此,關于艱難梭菌的防治指南中并未明確將益生菌作為預防感染的方法。益生元可以被腸道微生物選擇性利用,產生對人體有益的物質,降低艱難梭菌在腸道的定植。動物實驗研究發現水蘇糖能夠改善腸道微生物豐富度,多形擬桿菌回復部分膽汁酸水平,兩者選擇性地改變了某些菌種的相對豐度[63]。隨著人們對腸道微生態研究的進一步認識,未來腸道微生態及其代謝物和免疫因子可能會成為預防CDI的突破口。
7 結 語
艱難梭菌感染與腸道微生態紊亂互為因果,正常的腸道菌群是機體抵抗艱難梭菌的主要保護屏障。艱難梭菌感染嚴重威脅患者健康,臨床上控制艱難梭菌感染途徑和合理應用藥物對于防治艱難梭菌感染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