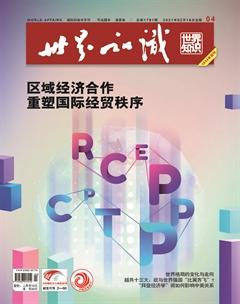治理社交網絡亂象,應尋求全球共識
譚笑間

2021年1月6日,大批示威者沖擊美國國會,導致嚴重騷亂,社交媒體被認為在這起暴力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月6日,大批示威者闖入美國國會,導致嚴重騷亂,社交媒體被認為在這起暴力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月8日,臉書公司宣布將無限期凍結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臉書和Instagram賬號,隨后推特公司以“存在進一步煽動暴力行為的風險”為由宣布對特朗普賬號進行永久封禁,并關閉了上千個被認為是“右翼宣傳平臺”的賬號。隨后,美國右翼群體轉戰其他社交媒體平臺,Parler等部分非主流平臺流量和注冊量激增。1月12日,美互聯網巨頭亞馬遜宣布將停止Parler平臺賴以運營的云服務,導致Parler幾乎所有代碼、數據等數字資產和數千萬用戶賬號一夜之間灰飛煙滅,引發軒然大波。社交網絡平臺是否有權封禁國家領導人言論?是否有權破壞和沒收數字資產?這些問題引發廣泛爭議。
美互聯網平臺獨大引發各國擔憂
對于此次封禁在任國家領導人賬號的行為,推特與臉書等平臺稱其主要依據為在推特與臉書等平臺注冊賬號時的平臺用戶規則,其中明確規定不得利用有關平臺“煽動暴力”。用戶在注冊賬號時點擊同意,即代表用戶應遵守該條款,無論其是否為國家領導人。雖然這一說辭得到了歐美主流媒體的認可,但仍舊引發了多方質疑。
1月11日,德國總理默克爾的發言人表示,“言論自由是重要的基本權利,這項基本權利可以通過法律和立法機構進行限制,而不應受到社交媒體平臺的影響。”法國財長勒梅爾同一天在接受采訪時亦聲稱:“監管數字空間是應該的,但不應由互聯網巨頭來做。”多國領導人對美國互聯網平臺的擔憂,折射出了美互聯網平臺在全世界“獨大”的影響力。像臉書、推特等已經成為在全球擁有20多億用戶的超級大平臺,各國在獲得社交網絡便利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社交網絡除了社交功能外還發揮著公共辯論“場所”的職能,若這一場所為其他國家或機構所掌控,其后果不言而喻。
實際上,臉書、推特等美國社交網絡巨頭掌握的巨大政治影響力早已引起世界各國的警惕。2016年,“劍橋分析”丑聞引發全球輿論嘩然。據媒體爆料,政治咨詢公司“劍橋分析”自1994年起便藉由互聯網干預他國選舉獲取巨額利潤,涉及全球30多個國家。可以說,這一事件直接推動歐洲出臺史上最嚴格的《一般數據保護條例》,也使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國開始重視互聯網企業“反壟斷”問題。
帶來社會治理難題
除了干預政治以外,當下社交網絡生態亦帶來了公共意見的分裂和網絡極端思想的泛濫。尤其是社交網絡群組引發的“回聲室效應”以及由網絡推送規則導致的“信息繭房”,進一步加劇了人們意見的分裂。
“回聲室效應”是指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一些意見相近的聲音以夸張甚至扭曲的方式不斷重復,令處于相對封閉環境中的人們認為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實的全部。“信息繭房”則是指人們關注的信息領域會習慣性地被自己的興趣所引導,致使自己的思想像被蠶繭包裹似地束縛起來,并反映到言論與行為的方方面面。由于社交網絡具有建立群組的功能,使得許多人依照興趣和觀點在社交媒體上形成群組,平臺也設計了基于興趣進行推送的算法機制。此類功能本意在于促進興趣交流和信息獲取,但是若涉及政治、族群等領域,就會帶來政治與社會問題。
非主流社交媒體平臺的發展,使得社交網絡生態固有的“回聲室效應”與“信息繭房”問題更加凸顯。在過去十年里,非主流的社交網絡平臺持續發展,它們多標榜自己為主流社交網絡平臺的替代者,如Parler、NewsMax、Gab、Minds、Signal、MeWe、DLive、4Chan等。縱觀這些網站平臺,其大多觀點偏激,如“白人至上”、“新納粹”、氣候變化懷疑論與極端環保主義、針對不同宗教與種族民族群體的極端排外主義等。一方面,通過加劇社會群體的意見分歧,社交網絡平臺能夠獲得不斷增長的流量,從而得到資本青睞。另一方面,各種懷有極端思想的人以這些平臺為“基地”聚集在一起,可以藉此擴大影響力。這就導致非主流社交媒體平臺與極端思想之間出現了“共生共榮”和“相互促進”關系,其影響力也迅速向主流社交網絡平臺擴散。
社交網絡的“部落化”與非主流社交媒體的發展也給許多國家的政治生態帶來了重大影響,使得部分國家的政黨與政治勢力開始通過迎合和利用這些網絡群體的意見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2018年巴西總統大選期間,許多巴西右翼政治網頁因違反網站仇恨言論規則而被封禁。為了繼續進行政治宣傳,這些網站的管理員開始推廣Gab和Parler作為替代平臺,以至于巴西人成為Gab和Parler用戶的第二大群體。而英國脫歐、美國右翼政治的興起,以及多國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風潮,背后可以說都有社交網絡的推波助瀾。
社交網絡上極端思想的泛濫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后果。近年美國、新西蘭等地針對猶太人、穆斯林乃至華人的槍擊案、“獨狼”襲擊、殺人案與傷害事件等愈演愈烈,其背后多有社交網絡上各種陰謀論推波助瀾。在網絡生態治理方面,中國已取得了長足進步,但這并不代表相關問題與中國無關,中國亦是國外社交媒體平臺上陰謀論和污蔑言論的受害者。由于長期以來西方媒體的對華意識形態偏見,國外一些群體所認知的中國與現實中的中國之間產生了巨大的“認知鴻溝”,社交媒體無序發展的弊端更加劇了這些群體對中國的偏見。
當下,國外主流社交網絡平臺迫于現實政治壓力,不得不開始頻繁采取“刪帖”等輿論控制措施,試圖控制極端言論,如啟動事實核查程序、從算法推薦中刪除違反規范的群組、使用機器學習系統來加強內容審核力度從而更迅速地檢測仇恨言論和其他惡意內容等。一些新興社交網絡平臺如Discord等還提出要建立“投票刪帖”功能,將審核極端言論的權力交還給用戶。美主流社交網絡在監管方面的轉變恰恰說明,其之前采取的過于寬松乃至無邊界的“言論自由”政策是不可取的,只能帶來分裂與動蕩。
疫情暴發以來,全球各地對于網絡社交的需求激增,使得社交網絡幾乎成為跨國、跨地區交流的“必需品”。在這一背景下,社交媒體無序發展帶來的少數平臺獨大、數據過度集中問題,以及“回聲室效應”等也引起了普遍關注。如何平衡互聯網平臺的商業屬性和社交網絡的政治與公益屬性,對極端和有害言論進行治理,已經成為各國共同關心的話題。對此,國際社會應充分認識到社交網絡上偏激言論的有害性,在多邊主義與相關治理機制的框架下,摒棄政治偏見,一視同仁地進行社交網絡的規范與治理,維護各國社會的長治久安及國際社會的團結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