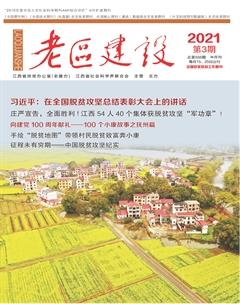跨越千年,從刀耕火種到全面小康
張勇



家,太冷了!一間間杈杈房漏風(fēng)又漏雨。
地,太瘦了!一片片荒坡收獲玉米一籮筐。
路,太遠(yuǎn)了!一條條回家山路攀爬一晌午。
多年前,從滇西北到滇西南,千里邊疆萬(wàn)道山,在云南直過(guò)民族地區(qū)隨處可見(jiàn)這樣的場(chǎng)景。
近幾年,在黨中央、國(guó)務(wù)院的關(guān)心和社會(huì)各界的支持下,云南省把直過(guò)民族聚居區(qū)作為全省脫貧攻堅(jiān)的重點(diǎn),一族一策、一族一幫。最近,云南省88個(gè)貧困縣全部退出貧困縣序列,獨(dú)龍族、德昂族、基諾族、佤族、普米族、阿昌族、拉祜族、布朗族、景頗族、怒族和傈僳族11個(gè)直過(guò)民族和人口較少民族實(shí)現(xiàn)整族脫貧,歷史性告別絕對(duì)貧困。
幾個(gè)月來(lái),記者走過(guò)滇西千里邊疆,從怒江峽谷到阿佤山,探訪了直過(guò)民族從刀耕火種到脫貧奔小康的千年跨越之路。
村里有讓我暖心的鮮花小院
怒江州蘭坪縣位于怒江東岸碧羅雪山背后的瀾滄江河谷,是全國(guó)唯一的白族普米族自治縣。2020年9月,記者走進(jìn)普米族占七成的蘭坪縣金頂鎮(zhèn)干竹河村上干竹村小組,公路邊的一個(gè)開(kāi)滿鮮花的小院引人矚目,這是普米族老人和家鳳、和富俊夫婦的家。
白墻青瓦,寬敞的庭院一側(cè)是繪有山水畫的照壁,庭院中間晾曬著三簸箕碩大的野生雞樅。身穿普米族服裝的和家鳳笑哈哈地說(shuō):“我家有5朵金花,4個(gè)出嫁,小女兒在縣城當(dāng)幼師。我們老兩口的收入靠種大蒜和養(yǎng)蜂,養(yǎng)40多箱蜂一年收入1萬(wàn)多元。”“我們村449戶靠種養(yǎng)殖和務(wù)工,全部脫貧了,通過(guò)農(nóng)村危房改造和三峽集團(tuán)幫扶,解決了安居房問(wèn)題。”干竹河村黨總支第一書(shū)記徐瑜梅介紹。“現(xiàn)在政策好,我們普米族的日子越過(guò)越好了!”67歲的和家鳳說(shuō)。
江邊有讓我安心的溫暖家園
近年來(lái),怒江州建設(shè)了67個(gè)易地扶貧搬遷集中安置點(diǎn),10.2萬(wàn)名群眾搬下高山,他們多數(shù)是傈僳族、怒族等直過(guò)民族。直過(guò)民族群眾搬遷后收入怎么樣?上學(xué)看病怎么辦?能否摘掉窮帽?帶著這些問(wèn)題,記者走訪了怒江兩岸移民新村。
在怒江畔福貢縣鹿馬登鄉(xiāng)阿路底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diǎn),60歲的傈僳族村民鄧存早請(qǐng)記者到家里做客,2室1廳的新家門上貼著“脫貧光榮戶”的紅字。鄧存早指著屋內(nèi)一幅竹篾房照片說(shuō):“這是我家在山上的老房子,現(xiàn)在搬到安置點(diǎn),好住多了。”
20年前,鄧存早唯一的兒子在家生病去世,兒媳婦在家難產(chǎn)去世,因?yàn)榧依镫x鄉(xiāng)衛(wèi)生院太遠(yuǎn),兒子兒媳生前都沒(méi)有到醫(yī)院看病。搬下山后,村里就有衛(wèi)生室,鄉(xiāng)衛(wèi)生院和縣醫(yī)院也不遠(yuǎn),老兩口看病很方便。“我種了5畝草果、4畝茶園,脫貧后,村里讓我當(dāng)護(hù)林員,還幫我申請(qǐng)養(yǎng)老保險(xiǎn)。日子好多了。”鄧存早說(shuō)。
和鄧存早一樣,從山上搬到阿路底安置點(diǎn)的71戶傈僳族貧困群眾在2018年1月住進(jìn)了新樓房,村里有小學(xué)、衛(wèi)生室,公路就在村旁,住房、醫(yī)療、上學(xué)、交通都不愁了。
許多搬遷群眾會(huì)為一件事發(fā)愁:過(guò)去在老家種菜吃,搬遷后只能買菜吃,生活成本較高。但在福貢縣匹河鄉(xiāng)沙瓦村指揮田安置點(diǎn)的319戶怒族群眾卻不用買蔬菜。安置點(diǎn)整合閑置土地15畝,劃分成330塊微菜園,廉價(jià)租給搬遷群眾種菜。“微菜園解決了搬遷戶吃菜難的問(wèn)題,還拓寬了群眾增收渠道。”沙瓦村黨總支書(shū)記斯春梅說(shuō)。指揮田安置點(diǎn)還以“黨支部+合作社+建檔立卡戶”的模式,讓所有搬遷戶都加入各種合作社,數(shù)千畝核桃、草果、茶葉提質(zhì)增效,并發(fā)展中蜂、土雞養(yǎng)殖等產(chǎn)業(yè),人均增收1000元左右。
在許多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diǎn),還有讓搬遷群眾就業(yè)的各種扶貧車間,搬遷群眾在家門口就可以就業(yè)。在指揮田安置點(diǎn)有廣東珠海幫扶建立的棒球加工車間和民族服裝加工車間。在阿路底安置點(diǎn),非遺扶貧就業(yè)工坊設(shè)計(jì)生產(chǎn)出深受當(dāng)?shù)厝罕娤矏?ài)的民族服飾,帶動(dòng)脫貧218戶412人,2020年又帶動(dòng)脫貧200人,走出了非遺扶貧的新路子。
田間有讓我驕傲的美麗村寨
搬遷的移民新村生機(jī)勃勃,更多沒(méi)有搬遷的直過(guò)民族村寨是什么面貌?在德宏州隴川縣戶撒阿昌族鄉(xiāng)戶早村,展現(xiàn)在眼前的是青磚青瓦的村莊,村前是一片片綠油油的水稻,村后是森林茂密蔥郁的山崗,家家戶戶都是新房新院子。村里看不到牛和牛糞,各家各戶的牛都集中在村后的養(yǎng)殖點(diǎn)飼養(yǎng)。60歲的馮李板正在收拾新房子的雜物,她家在村口的舊房已經(jīng)居住了4代人,平層新房由政府和云南省煙草公司補(bǔ)助修建。“這幾年省煙草公司幫扶我們村脫貧,村里的變化越來(lái)越大,原來(lái)的土基房變成了磚瓦房,土路變成了水泥路,村民家里第一次有了水沖廁所,村民們學(xué)會(huì)了種烤煙,現(xiàn)在人均純收入達(dá)10920元。”村委會(huì)副主任趙永存描述著村里的變化。村第一書(shū)記楊濤補(bǔ)充說(shuō),省煙草公司在德宏州阿昌族聚集區(qū)累計(jì)投入項(xiàng)目資金12.46億元,幫助阿昌族實(shí)現(xiàn)整族脫貧致富,戶早村310名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摘帽,同時(shí)投資780萬(wàn)元新建了戶早幸福小學(xué),讓阿昌族的孩子們也能享受標(biāo)準(zhǔn)化的校舍。臨滄市耿馬縣班幸村大灣塘自然村是個(gè)以德昂族為主的村寨,鄰近中緬邊境的國(guó)家一類口岸清水河口岸,村里的獨(dú)樹(shù)成林景觀樹(shù)至今是東南亞最大的細(xì)葉榕樹(shù)。走進(jìn)大灣塘村,只見(jiàn)藍(lán)色房頂?shù)男路垮e(cuò)落有致。班幸村委會(huì)黨總支第一書(shū)記李向松介紹,在沿邊小康村建設(shè)過(guò)程中,大灣塘村開(kāi)展以甘蔗、橡膠等生產(chǎn)加工為主的邊境貿(mào)易,打造邊境特色旅游型村莊,2019年共接待游客4.69萬(wàn)人次,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dá)15600元。
山中有我脫貧奔小康的希望
直過(guò)民族往往居住在云霧繚繞的高山上,移民搬遷下山只是部分貧困戶,更多的鄉(xiāng)親們?cè)谏缴峡渴裁疵撠氈赂荒兀坑浾吲郎显贫松系拇逭ぴL鄉(xiāng)親們的脫貧增收之路。在怒江東岸碧羅雪山上有一個(gè)美麗的怒族村寨,因?yàn)闈庥舻呐逦幕挚尚蕾p怒江大峽谷和皇冠山風(fēng)景,近年來(lái)成為自駕族們的網(wǎng)紅打卡地。這,就是福貢縣匹河鄉(xiāng)老姆登村。2000年,從上海打工回來(lái)的怒族小伙子郁伍林創(chuàng)辦了老姆登村第一家客棧。在他的帶動(dòng)下,村民們辦了20家客棧,旅游收入成為村民們的重要收入。一車車茶葉拉進(jìn)茶廠,一袋袋茶葉在秤上堆成了小山,村民笑著將茶葉抬進(jìn)生產(chǎn)車間,車間里CTC生產(chǎn)線正在流水線生產(chǎn)紅碎茶。這是記者在臨滄滄源佤族自治縣糯良鄉(xiāng)賀嶺村公播村小組佤山茶廠看到的場(chǎng)景。公播村鄰近中緬邊境,是個(gè)有著127戶的佤族村落,全村種茶1650畝。過(guò)去村民主要賣春茶,夏茶、秋茶品質(zhì)低、收入少。為此,糯良鄉(xiāng)引進(jìn)的佤山茶廠CTC生產(chǎn)線落戶公播,實(shí)施“黨組織+合作社+企業(yè)+茶農(nóng)”的模式,覆蓋全鄉(xiāng)18個(gè)茶葉合作社,幫助兩萬(wàn)多畝茶園提質(zhì)增效,人工采茶變成機(jī)器收割,春茶夏茶秋茶產(chǎn)量大幅提高,畝產(chǎn)值從五六百元增至近2000元。帕秋村茶葉合作社負(fù)責(zé)人李賽饒告訴記者:“全村有2000畝茶園,2019年只賣得56萬(wàn)元,現(xiàn)在有CTC茶廠收購(gòu),全村至2020年9月底就賣了60多萬(wàn)元。”“我們阿佤山變化很大,賀嶺村20世紀(jì)80年代人均收入500多元,2000年才1000多元,到2019年就有11355元。2012年以前全部消滅了茅草房、杈杈房,這兩年農(nóng)村危房改造消滅了危房。我們依靠綠水青山搞綠色產(chǎn)業(yè)脫貧致富,今后要打造集茶文化展示、茶園休閑、采摘為一體的生態(tài)觀光茶園游。”賀嶺村黨總支第一書(shū)記范澤輝講述了全村30多年的大變化。在怒江大峽谷,直過(guò)民族群眾搬到山下,但山上老家的草果還是他們的重要收入來(lái)源。每年9月,許多搬遷群眾都會(huì)回山上采收草果。目前怒江州草果種植面積已達(dá)111萬(wàn)畝,受益群眾達(dá)16.5萬(wàn)人。賀嶺村、老姆登村、戶早村、干竹河村……一個(gè)個(gè)直過(guò)民族村寨的巨變,是直過(guò)民族地區(qū)歷史變遷的縮影。近幾年來(lái),云南省在直過(guò)民族聚居區(qū)投入343.9億元,實(shí)施了提升能力素質(zhì)等六大工程,水、電、路、通信及互聯(lián)網(wǎng)等基礎(chǔ)設(shè)施有了顯著改善,對(duì)27822戶貧困戶實(shí)施易地扶貧搬遷,實(shí)現(xiàn)貧困家庭學(xué)生有學(xué)上、上得好學(xué),最大限度保障貧困群眾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直過(guò)民族一個(gè)民族一個(gè)對(duì)口幫扶單位,教育部牽頭組織40余所部屬高校和10個(gè)東部職教集團(tuán)對(duì)口幫扶,三峽、華能、大唐等企業(yè)集團(tuán)幫助8個(gè)直過(guò)民族和人口較少民族聚居區(qū)脫貧攻堅(jiān)。
(來(lái)源:光明日?qǐng)?b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