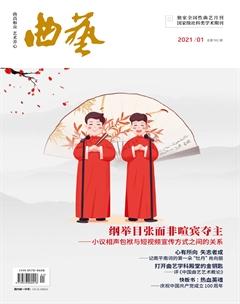短視頻語境下再論“萬象歸春”
樓一宸
“萬象歸春”①,是相聲愛好者較為熟悉的藝諺,它“可以理解為生活中的萬事萬物都能作為相聲的題材而加以反映”②,在一定程度上點出了相聲的本體特征,也蘊含著曲藝藝術的一種藝術規律。
時至當下,互聯網、新媒體帶來了新的傳播方式和平臺。相聲也與短視頻等傳播方式融合,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在這樣的背景下,“萬象歸春”的內涵和外延也有了新的深化和延展。
一、萬象——相聲內容的新拓展和傳播載體的新開發
相聲也稱為“春口”。從業者們常說“天上飛的、水里鳧的、草窠兒里蹦的”“大小買賣兒吆喝”等世間萬象都可以被融入相聲之中。另一方面,許多門生意、行當也都離不開插科打諢、逗笑取樂,在自覺不自覺中使用了某些相聲技巧。所以“萬象歸春”中“萬象”之本意,首在于相聲藝術對豐富內容的不懈追求。
如何創作好作品是當前曲藝界共同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但相聲因表演的靈活性等特殊原因,腳本多由演員自身完成,專職的相聲創作者至今仍屈指可數。這就導致相聲產量與受眾需求長期達不到動態平衡,進而不利于相聲在新時代進一步展現藝術魅力。所以找尋新素材探索新路徑就成了一大要務。當前,短視頻已經成為群眾日常娛樂消遣的重要內容,也為相聲創作提供了新的窗口。
短視頻的內容豐富多樣,表達方式也較靈活,其中三觀正確且熱度較高者更有著巨大的潛在附加值——通過閱讀相對應的評論,可以有效了解受眾對某一事件的傾向與看法。比如快手上的視頻號“警花說”,聚集了天南海北多位女警,在幾十秒幾分鐘內普及防詐反騙、交通安全、出境事項等知識,受到觀眾的喜愛,也反映出當前受眾在某些方面的“法律焦慮”。不論是以視頻本身為參考,還是以受眾評論為出發點,此類相聲都會產生很好的效果。
短視頻擁有大量用戶,每天產生的內容涵蓋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不乏超出個體認知界限者。作為創作者,相聲從業者若能夠用心感受,也會獲得很多自身生活圈以外的靈感和啟發。
除了相聲從業者,還有許多專業或半專業的喜劇內容創作者也通過短視頻迅速火了起來。如脫口秀,它比起相聲少了許多的程式,更能適應短視頻的快節奏。脫口秀演員本身也擁有較強的創作能力,對時事和社會熱點較為敏感,這使得他們也能迅速收獲大量粉絲。除此之外,不少笑話創演者也有不少頗讓人眼前一亮的技巧。這些都可以用來豐富相聲的創作。
當然,互聯網時代的信息洪流泥沙俱下,金鐵珠石紛雜,相聲從業者也要做好對短視頻內容的篩選和鑒別,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將“萬象”全部歸入相聲中,這可能對相聲形成“倒灌”,稀釋甚至淹沒相聲的藝術本體。此外,如果一味趕時髦,什么流行說什么,短視頻有什么我也要有什么,那受眾只會覺得生硬和重復。短視頻海量的內容,必須進行相聲特質的內化和轉化,才能化為供相聲所用的“萬象”。
要有效提升藝術影響力,一方面要練“內功”,有效增加內容的豐度;一方面要練好“外功”,積極尋求更有效的傳播方式。就此而論,“萬象歸春”的在傳播層面的意義,當可理解為不同傳播業態對相聲擴散藝術影響力都會起到相當的作用。
這是對現象的提煉,也是對規律的總結。縱觀相聲史,傳播層面的“萬象歸春”貫穿著相聲的發展。早些時候,藝人們用白沙灑字、唱太平歌詞等方式吸引顧客,節目也時常溢出曲藝范疇,化用戲曲、音樂等藝術形式,所以才有了“相聲藝人的肚是雜貨鋪”的說法。隨著商業電臺的興起和唱片錄制技術的日趨成熟,相聲從業者的聲音借著唱片、乘著電波走遍大江南北。電視的普及進一步增強了相聲的音相復合形象,也讓相聲成為了文藝晚會和電視晚會不可或缺的“主餐”和標配,一批相聲演員和笑星應運而生,至今仍有廣泛的影響。互聯網興起后,相聲的傳播手段更趨多元化,與線下的重新興起的小劇場一起,逐步構建起了一個層次多樣的相聲傳播體系。
就此而論,相聲和短視頻及直播的“聯姻”看似是新鮮事物,實際上承接的是相聲自誕生以來與不同媒介融合發展的傳統,是相聲在互聯網不斷發展大前提下的新產物。當然,新事物總要在經受考驗后才能分清理濁,確定利弊,“震驚!相聲從業者在借機圈錢!”“是融合還是侵蝕?‘相聲+短視頻究竟是什么?”等,這都是UC震驚部應該操心的事,抱著平和的態度,積極探索在保證相聲藝術本真基礎上的融合發展路徑方是正理,至于成敗利鈍,且聽下回分解就可。
二、歸春——本體意識下的守正創新
當前的短視頻平臺,具有較強娛樂性質的搞笑內容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不少相聲演員,尤其是青年相聲演員在短視頻平臺開通了個人賬戶,積攢了不少人氣。平心而論,擁有較強語言表達能力并對喜感有較準確把握的相聲演員在短視頻平臺確實具有先天優勢,很容易脫穎而出,對此我們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持肯定態度。
通過短視頻平臺提高知名度無可厚非,但相聲從業者也需要清醒地意識到相聲與短視頻之間的關系。“萬象歸春”,“春”是韻腳,更是題眼,一個“歸”字清晰表達出了一個觀念:不論如何融合新內容,借助新傳播方式,相聲的本質不能變。
從內容上看,短視頻里的笑話段子并不完全等于相聲段子,笑料不完全等于包袱。各類短視頻的共同點就在于要在短時間內出效果,具體到搞笑短視頻,便是要用三言兩語讓受眾發笑。這其實和相聲講求的“鋪平墊穩”和“三番四抖”等技巧相背而馳。相比起電視、廣播、晚會等平臺和媒介對相聲時長的要求,短視頻的時限更為嚴苛,相聲很難組織出完整的包袱,打造出完整的結構。
從形式上看,“相聲+短視頻”還未成為成熟的形式,也沒形成具有一定共識的通用模式。如此一來,相聲從業者就勢必要考慮一系列問題:短視頻是要遷就大多數受眾還是要堅守相聲藝術規律,是要向“笑果”傾斜還是持續關注藝術效果,是自身的“錢途”重要還是藝術的前途關鍵。更嚴重者,如果“相聲+短視頻”真正形成規模,相聲是否會從一種藝術形式退化為純粹的視頻腳本提供者。
相聲歸根結底是語言藝術,需要運用具體的言語與受眾進行信息交流。短視頻則是視聽兼備,而視覺語言又先于聽覺語言。如若不能清晰地認識二者在本質上的區別,則可能影響相聲從業者對相聲本體的認知,將兩種形態的喜劇手法混為一談。以短視頻方式說的相聲,必然也是缺少了相聲味的相聲。曾經以網絡段子拼湊的相聲作品遭到了詬病,這是“相聲+短視頻”模式的前車之鑒。
短視頻也好、直播也罷,相聲在不斷嘗試著新的可能。科技在革新,時代在前進。度過互聯網2.0時代,或許還會有3.0、4.0,又或許5G的全面普及會帶來全新的信息交互方式。而相聲從業者要做的,就是遵循相聲自身的藝術規律,利用媒介和平臺的變化推動相聲在新時代獲得新的發展,不斷講述“萬象歸春”的新故事。
注釋:
①“萬象歸春”有時也被寫作“萬相歸春”,本文采用學術領域較為通行的前者。
②參見《相聲大詞典》“萬象歸春”詞條。
參考文獻:
[1]侯寶林、薛寶琨、汪景壽、李萬鵬:《相聲溯源》,中華書局,2011年出版。
[2]吳文科:《相聲考論》,中國文聯出版社,2018年出版。
[3]蔣慧明:《“云端”上下,相聲何為?》,《人民日報》,2020年9月23日。
[4]王松:《想起“萬相歸春”》,《小說月報》,2019年第8期。
(責任編輯/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