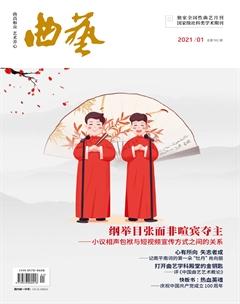一粒米
陳靈犀 饒一塵
一粒米,啥稀奇,
一粒米哪亨好算大事體。
大不可小算要曉得,
一粒米當中有大道理。
奈勿要看輕一粒米,
何妨拿把算盤來算仔細。
有一位老貧農想出一個好主意,
為了使年輕一代珍惜一粒米,
俚拿出一兩米叫小孫子一粒粒數仔細。
共總是一千八百三十七粒半,
一數數出仔個大問題。
如果全國人民每人每天節約一粒米,
或者每人每天浪費一粒米,
一進一出數目大得邪邪氣。
我伲全國人口六億五千萬,
如果每人每天節約一粒米,
一日天就是三萬六千四百零三斤;
一年算起來一千二百九十六萬多斤米。
撥勒五千人格工廠當口糧吃,
吃仔七年還多-些些。
撥勒農村里一個生產小隊當口糧吃,
阿要幾化日腳可以吃完俚?
好吃一百六十年。
阿爹吃到孫子手里,
還勿曾吃完一粒米。
奈說阿稀奇來勿稀奇。
如果折合人民幣拿來賣機器,
一粒米好換四十多部小型拖拉機,
奈說阿稀奇來勿稀奇。
一滴一滴水匯成東海闊,
一粒一粒沙堆得泰山齊。
如果每人每天節約一粒米,
可以堆得倉庫高來白云低。
勞動人民愛的是勤儉恨的是浪費,
深曉得一粒米來之勿容易。
搶收搶種多辛苦,
車水耘耥勤積肥。
滴滴汗珠粒粒米,
故而珍惜用糧是大事體。
我伲厲行節約從小處來著手,
勤儉建國勿要忘記,
請大家切莫看輕一粒米。
賞析:
蘇州彈詞擁有20余種流派唱腔,其中嚴雪亭的嚴調自20世紀40年代中期創立以來,一直深受廣大評彈愛好者的喜愛。其學生和再傳弟子在業內亦人才輩出,嚴調藝術至今傳唱不衰,流傳甚廣。嚴雪亭的代表作——長篇彈詞《楊乃武》《三笑》《十五貫》等早已風靡書壇,進入新社會后,他加入了上海人民評彈團(現為上海評彈團),在表演和唱腔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先后編演了《情探》《白毛女》《風暴》等作品。他在20世紀60年代所演唱的彈詞開篇《一粒米》是嚴調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成為了蘇州彈詞白話開篇中的代表性作品。
彈詞開篇《一粒米》創作于1964年左右,作者是當時上海人民評彈團的資深評彈作家陳靈犀和青年編劇饒一塵。陳靈犀先生是廣東潮州人,創辦過報紙,做過編輯,文筆甚好,1949年后成為了一名專職的評彈作家。不容易的是,他的母語是廣東潮州話,上海話雖也流利,但蘇州話要靠學。當時陳靈犀已年過半百,但他和評彈藝人吃住在一起,下農村、去海島,成為“評彈一支筆”,他的一生創作和改編了很多經典評彈作品,評彈界尊稱他為“犀老”。
20世紀60年代,經歷了3年自然災害之后,國家號召厲行節約,人們對糧食愈加珍惜和愛護。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陳靈犀參與創作了這首彈詞開篇。雖然他的古文底蘊深厚,平仄格律十分講究,所編的唱詞文采好,詞句雋永,但是在這首《一粒米》初創時也碰到了困境。饒一塵先生生前曾說過自己參與這個開篇創作的經歷,據他回憶:當時犀老在寫完這個開篇之后,自覺不甚滿意,他覺得還不夠生動,缺乏說服力,有些句子比較教條,組織上就讓已由演員轉為編劇的饒一塵和他一起再進行修改。好的曲藝演員往往都能夠自己進行創作,會根據自己的舞臺實踐經驗對作品做生動的提亮。針對評彈作品以往存在的問題,兩個人在構思這篇作品時,從小小的一粒米開始展開想象:如果全國每人每天節約一粒米,可以省下多少斤糧食,繼而又從人的口糧量來算,算出節約這一粒米可以讓三代人吃多少年,又算出將這些量轉化為人民幣能購買多少臺工農業生產機器。他們希望通過這個開篇來鼓勵人們節約每一粒糧食。因為作品是用數字說話,所以特別有說服力,比一般的說教要來得更有力。
評彈中的彈詞開篇用中州韻咬字的比較多,《一粒米》是典型的非中州韻演唱的白話類開篇,而且用的音韻是蘇州彈詞中較少用到的冷僻韻腳——“雞棲韻”,這個韻腳可供選擇的字較少,故作者在寫作唱詞時大多不會使用,但是兩位作者卻用這個“不太受歡迎”的韻腳寫出了一首膾炙人口、影響深遠、至今還在廣泛傳唱的好作品。
嚴雪亭先生生于1913年,是徐云志的大弟子,在徐調和小陽調的基礎上形成了獨樹一幟的嚴調。嚴調唱腔的特點是親切、明快、樸素、流暢,情感真切,貼近觀眾。白話文演唱是彈詞演唱的一大亮點,嚴調尤其擅長此類演唱,比如,作品中有多處蘇州方言的運用讓觀眾覺得親切樸實,如“哪亨”(怎么)、“數出仔個”(數出了)、“邪邪氣”(很多)、“拔勒”(給)、“阿要幾化日腳”(要多少日子)、“我伲”(我們)等。另外,這個開篇中有不少數字要唱出來,從唱腔的編排來看是比較難的,因為沒有了彈詞唱詞中固定的“二五句”或“四三句”的分割法,對此,嚴雪亭的處理十分高明,既流暢分明有重點,又符合音韻平仄的聽覺感受。在咬字和節奏上,他也動了很多腦筋,比如開頭和最后的3個字都是“一粒米”,他在演唱時,開頭過門彈完后,沒有直接按節奏唱出“一粒米”3個字,而是略有停頓后,集中口勁和力度,把這3個字送到了聽眾的耳中和心里。最后結尾的這3個字,他將字與字之間進行了分隔,更強調了一粒米的來之不易,讓人聽完這個開篇后還久久沉浸在他的內容中。白話開篇中,一般唱腔都比較簡單,內行講就是不太容易做腔,但是嚴雪亭在設計唱腔時,卻也注重旋律的豐富,如“可以堆的倉庫高來白云低”這句,充分體現了嚴調唱腔的風格。這首開篇的生動之處就在于有祖孫兩個人物做底襯,演員可以充分利用評彈“跳進跳出”的表演特色來演唱,嚴雪亭又是單檔表演的大師級藝術家,所以使整個開篇更添活力和親和力。他演唱了這首開篇之后,在江南的農村鄉鎮引起了熱烈的反響,每到一地演出,只要有嚴雪亭出場,農民們都爭相觀看,都說這位說書先生唱出了我們農民的心聲。
雖然這首彈詞開篇創作演唱于20世紀60年代,但對今天的我們仍然具有積極的作用。“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在當下物質生活日益豐富的時代,我們還是要珍惜每一粒糧食,杜絕舌尖上的浪費,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所以,我再次重溫嚴雪亭先生的彈詞開篇《一粒米》時,還是覺得這個作品深入人心,很有必要讓大家再聽一聽。
(賞析人:上海評彈團團長、國家一級演員 高博文)
(責任編輯/朱庭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