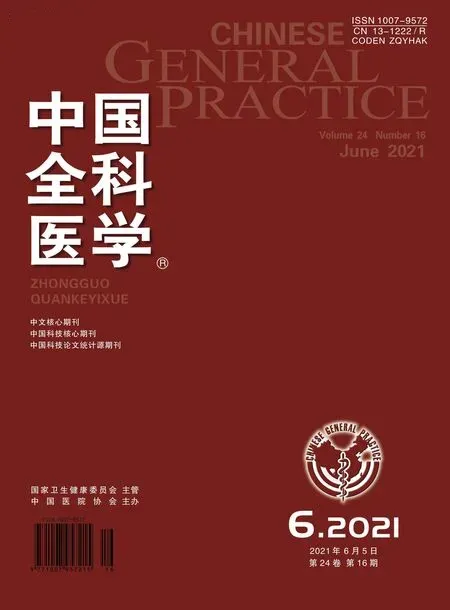我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政策進展及實踐
秦江梅,王芳,林春梅,張艷春,張麗芳
2020年8月,國家衛生健康委、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印發《關于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的指導意見(試行)》(國衛辦基層發〔2020〕9號,《指導意見》)[1],拉開了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國家監測、省級考核的序幕。我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從2010年“兩衛”實施績效工資開始,已經走過10年之路,績效考核指標體系不斷完善,對考核作用認識不斷深化,考慮到全國層面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數量眾多,不同經濟地區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設施設備、人力資源和服務能力差異較大,基層績效考核工作由國家提出指導意見,省級衛生健康行政部門、中醫藥主管部門科學合理設置指標權重和評分標準,縣級衛生健康行政部門會同中醫藥主管部門具體組織實施。為了指導各地完善考核方案、確定標準值、細化評分標準,本文通過對績效考核理論與方法介紹、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政策梳理、對各地績效考核實踐總結,針對我國基層績效考核實施層面關鍵和難點提出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1 績效考核理論與方法
1.1 績效概念及內涵 績效(performance)也稱業績、效績、成效等,反映的是機構或個人從事某一活動所產生的成效和成果。關于績效的定義主要有3種觀點:一種認為績效是行為,一種認為績效是產出(結果),還有一種將績效看作素質或勝任特征。(1)績效是行為:代表人物是坎貝爾(Campbell,1990年),認為“績效是員工在完成工作過程中表現的一系列行為特征,是員工自己能夠控制的與組織(機構)目標相關的行為,如工作能力、責任心、工作態度和協作意識等”。(2)績效是產出(結果):代表人物是伯納丁(Bernadin,1995年),認為“績效是員工最終行為的結果,是員工行為過程的產出,一項工作績效在總體上相當于某一關鍵職能或基本工作職能績效的總和,結果績效可以用如產出、指標、任務、目標等詞表示”。(3)績效作為素質:代表人物是伯姆瑞(Brumbrach,1998年),該觀點強調員工潛能與績效的關系,更關注員工的素質,關注未來發展[2],可通過測量個體的勝任力來說明個體的績效。近年來,人們趨向于認為:績效是指具有一定素質的員工圍繞職位的應負責任所達到的階段性結果,以及在進行過程中的行為表現,即績效包括整個過程和結果[3]。
1.2 績效考核概念及內涵 從不同來源的定義看,績效考核、績效評估和績效評價概念內涵無太大的區別,只是側重點不同,績效考核和績效評估側重對人員,績效評價側重對單位和地區,也包括人員。根據評價主客體的不同,西方績效考核理論的研究對象主要包括兩方面,即組織(機構)績效評價和個人績效評價。組織(機構)績效評價:通常由出資人或者該組織的上級管理者作為考核主體,按照組織績效考核評價模式和指標體系,考核組織的運營狀況,及時發現存在的問題,落實組織的戰略目標,提高組織的績效,考核結果是對組織進行薪酬總量兌現和對最高層領導者的薪酬兌現,以及作為其職務任免的重要依據[4]。個人績效評價:是指考評主體對照工作目標或績效標準,采用科學的考評方法,評定員工的工作任務完成情況、工作職責履行程度及發展情況,并將評定結果反饋給員工的過程。績效評價(考核)一般包括4個環節:(1)選擇考核對象,確立考核目標;(2)建立考核系統,確定考核主體、考核指標、考核標準及考核方法;(3)收集相關信息;(4)形成價值判斷。對醫療衛生機構而言,績效考核可以分為3個層次:一是以醫療衛生機構為對象的績效考核;二是以科室為對象的績效考核;三是以員工為對象的績效考核。
1.3 績效考核(評價)相關理論 (1)績效管理理論。完整的績效管理應該是一個循環流程,包括績效目標制定、績效輔導、績效考核及績效激勵等內容。從過程看,績效考核是績效管理的一個環節,績效管理是一個完整且連續不斷進行循環的管理過程;從時間看,績效考核指特定時期(年底),績效管理伴隨績效活動的全過程;從重點看,績效考核側重對機構(員工)績效的判斷和評價,績效管理注重管理部門(人員)和機構(員工)持續的溝通及機構(員工)績效的提高;從方式看,績效考核是事后的評價,績效管理是事先的溝通和承諾;兩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績效考核是在年底對過去績效情況的回顧,而績效管理則是向前看,側重過程。(2)績效工資理論。績效工資是在績效考核的基礎上,根據工作業績和貢獻而計付的除基本工資之外的一種分配形式,是對過去工作行為和已取得成就的認可。績效工資的前身是計件工資,最早出現于美國19世紀晚期的米德沃爾鋼鐵公司,其是由“科學管理”之父泰勒發明差別工資制后逐漸發展起來的。績效工資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工資與產品數量掛鉤的工資形式,而是在科學的工資標準和管理程序基礎上的工資體系,指依據個人或組織工作績效發放工資的一種工資制度。其建立在對員工進行有效績效評估的基礎上,關注重點為工作“產出”,如銷售量、產量、質量、利潤額及實際工作效果等。
1.4 常用績效考核方法 常用的績效考核方法包括目標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MBO)、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KPI)、平衡計分卡(balance score card,BSC)、360度績效考核法(360 degree performance appraisal)等。(1)目標管理法是由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在《管理實踐》中最早提出目標管理思想,把目標分解為一個個小目標。目標管理的核心是將組織的整體目標逐級分解直至個人目標,最后根據被考核人完成工作目標情況來進行考核。(2)關鍵績效指標的核心是根據二八原理將考核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關鍵的結果和關鍵的過程上。(3)平衡計分卡是哈佛大學羅伯特-卡普蘭教授和復興全球戰略集團總裁大衛-諾頓1996年提出,包括財務維度、顧客維度、內部業務維度及學習與成長維度。(4)360度績效考核法是愛德華和埃文等于20世紀80年代提出,后經1993年美國《華爾街時報》與《財富》雜志引用后,開始得到廣泛關注與應用,其核心是由被考核者的上級、同級、下級及客戶綜合評價,同時結合自我評價綜合而成。在設計一個科學合理的績效評估指標體系時,首先應基于一個科學適用的績效指標模型框架。由于醫療行業的特殊性,不像一般的企業那樣具有普遍性的評估尺度,在具體實施考核時,必然是多種方法的結合應用,有時并未具體應用到某一種方法,但卻應用了該種方法的思路。在制定各種考核方案時,一定要有此種開闊的思維,這樣考核出的結果才能客觀、準確、全面。
《關于加強公立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評價的指導意見》(國衛人發〔2015〕94號)和《關于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的指導意見(試行)》(國衛辦基層發〔2020〕9號)分別構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評價指標體系(試行)》(2015年)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指標體系(試行)》(2020年)。《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評價指標體系(試行)》(2015年)一級指標包括社會效益、服務提供、綜合管理、可持續發展,《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指標體系(試行)》(2020年)一級指標包括服務提供、綜合管理、可持續發展、滿意度評價,均是按照“平衡計分卡”基本原理將一級指標分為4個維度;在二、三級指標構建過程中采用的是“關鍵績效指標”方法確定核心和關鍵績效指標;社會效益中的患者和職工滿意度評價遵循的是“360度績效考核法”;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多數指標都有目標導向,如《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指標體系(試行)》(2020年)中10個國家監測指標醫師日均擔負診療人次、病床使用率、門診次均費用、住院次均費用等均可以分解為對省級、縣級、機構、科室及對職工的考核。
2 我國績效考核政策文件進展
2.1 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的提出 2009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中發〔2009〕6號)明確提出建立高效規范的醫藥衛生機構運行機制,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公共衛生機構及公立醫院的績效考核。要求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加強和完善內部管理,建立以服務質量為核心、以崗位責任和績效為基礎的考核與激勵制度,形成保障公平效率的長效機制[5]。《“十二五”期間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暨實施方案》(國發〔2012〕11號)進一步強調建立科學的醫療機構分類評價體系[6]。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加快公立醫院改革、落實政府責任、建立科學的醫療績效評價機制做出部署[7]。
2.2 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政策 為配合公共衛生與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實施績效工資政策,原衛生部人事司于2010年制定出臺《關于衛生事業單位實施績效考核的指導意見》(衛人發〔2010〕98號),該文件分別對公共衛生機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公立醫院3類衛生事業單位提出不同的績效考核內容。其中,針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績效考核提出應體現履行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與基本醫療服務職能、綜合管理和服務對象滿意度等方面情況。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職能具體考核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開展數量、質量等;基本醫療服務職能具體考核醫療工作效率、醫療質量、合理用藥及醫療費用控制等[8]。2010年以后,原衛生部各業務司局制定了鄉鎮衛生院、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婦幼保健機構、衛生監督、院前急救、采供血機構等各類機構的績效考核文件。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均屬于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因隸屬不同業務司局,相應業務司局分別出臺了《關于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實施績效考核工作的意見》(衛辦農衛發〔2011〕34號)、《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績效考核辦法(試行)》(衛辦婦社發〔2011〕83號),兩類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文件的主要原則、考核內容、指標體系等均有所不同,具體異同點不再贅述。2015年12月,原國家衛生計生委出臺《關于加強公立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評價的指導意見》(國衛人發〔2015〕94號),該文件分別構建了公立醫院、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專業公共衛生機構及衛生計生監督執法機構的績效考核指標體系,4類機構均以社會效益、服務提供、綜合管理、可持續發展為一級指標,分別下設二級指標和三級參考指標。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指標包括4個方面:(1)社會效益指標,重點評價公眾滿意、健康素養提高等情況。(2)服務提供指標,重點評價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和醫療服務提供情況。其中,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包括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開展數量、質量等;醫療服務包括醫療服務數量和效率、醫療質量和安全、醫療費用控制,以及中醫藥、康復、計劃生育技術等服務開展情況,通過評價促進醫療機構合理、規范診療。(3)綜合管理指標,重點評價財務資產管理、藥品管理、服務模式、信息管理,以及黨建工作、行風建設等情況。(4)可持續發展指標,重點評價人才隊伍建設等情況[9]。
2.3 近期出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文件2020年8月印發的《指導意見》,目的是通過建立健全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機制,推動其持續提升服務能力、改進服務質量,努力為人民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經濟的醫療衛生服務。該文件從服務提供、綜合管理、可持續發展、滿意度評價4個維度構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指標體系:(1)服務提供,重點評價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功能定位、服務效率、醫療質量與安全;(2)綜合管理,重點評價經濟管理、信息管理、協同服務;(3)可持續發展,重點評價人力配置和人員結構;(4)滿意度評價,重點評價患者滿意度和醫務人員滿意度[1]。
3 我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實踐
在原衛生部制定出臺《關于衛生事業單位實施績效考核的指導意見》及業務司局制定鄉鎮衛生院、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績效考核文件后,我國各地相繼出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實施辦法與工作細則,河北省、山西省、內蒙古自治區、吉林省、浙江省、江西省、安徽省、山東省、河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四川省、陜西省、甘肅省及青海省14個省份以“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為名出臺績效考核辦法,廣東省、海南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黑龍江省分別出臺了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和鄉鎮衛生院績效考核文件,上海市、江蘇省出臺以“公共衛生與基層醫療衛生事業單位”為名的績效考核文件,各地出臺文件與國家出臺文件內容類似,沒有太多創新和突破。北京市在全市范圍內建立市-區縣-機構三級考核制度;天津市建立市區(縣)衛生行政部門對轄區衛生事業單位、事業單位對工作人員的兩級考核體系;山西省加強績效考核,縣級對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每半年考核一次;內蒙古自治區完善了以服務數量、質量、效率和綜合滿意度為重點的自治區、盟市、旗縣三級考核制度和獎優罰劣制度;吉林省建立了以醫療服務任務完成情況、群眾滿意度等為指標的綜合性指標考核體系,實行縣(市、區)政府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年度目標考核制度;江蘇省、安徽省等地建立了“雙考核、雙掛鉤”機制,把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考核結果與經費補助掛鉤,對基層醫務人員的考核結果與個人收入掛鉤;浙江省全面建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工資制度和績效考核辦法,獎勵性績效工資占比在50%以上;重慶市建立“三級管理,分類考核,量化分配”的基層醫療衛生績效管工作模式。各地進行了大量的探索與實踐,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普遍開展績效考核工作。2001年上海市出臺《上海市公共衛生和基層醫療衛生事業單位績效考核指導意見》(滬衛人事〔2011〕59號),要求績效考核在注重績效的同時,突出職業道德、服務質量及服務對象滿意度,嚴禁將績效考核結果直接與經濟創收指標掛鉤[10]。以上海市長寧區為例,長寧區衛生健康委成立由委主要負責人擔任組長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績效考核小組,建立多維度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從功能任務、基本醫療、公共衛生、業務管理、綜合管理五大板塊進行績效考核,考核結果作為機構年度等級評定、基本公共衛生經費、家庭醫生簽約費撥付的重要依據。2019年長寧區90%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達到國家社區衛生服務能力推薦標準,2020年簽約覆蓋率達到44.9%,重點人群簽約覆蓋率達到66.4%,有效簽約比例達到74.1%[11]。2010年北京市出臺《北京市社區衛生服務崗位績效考核指導方案》,近年來不斷加大對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及人員績效考核的力度,在全市范圍內建立三級考核制度(市-區縣-機構),加強日常監督管理與考核。以北京市東城區為例,2008年以來東城區對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考核、機構對職工考核均包括服務數量、服務質量、社會評價3個維度,2017年組建“東城區社區衛生服務質量管理專家技術指導組”,每年對社區衛生工作質量進行2次全面考核,加大績效考評系統中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工作的分值權重,并且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績效考核內容和方法與時俱進,利用強大的社區衛生信息化管理平臺直接抓取數據,實現了考核結果自動生成[12]。2017年浙江省為配合全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財政補償機制改革,制定《浙江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補償機制改革試點基本服務項目標化工作當量參考標準》(浙財社〔2017〕63號)》。以浙江省江山市為例,江山市按“2+3”模式搭建三級績效評估體系,即醫共體牽頭醫院績效考評細則、醫共體分院績效考評細則、分院內部績效考核方案,績效評估指標包括行政管理、能力建設、業務管理、分配激勵、服務滿意度5個方面,對醫共體牽頭醫院的評估側重行政管理、能力建設,對衛生院分院的評估側重業務開展、分配激勵等,衛生院分院內部評估側重業務開展和服務滿意度等。在績效評估中充分發揮大數據管理優勢,衛生健康行政部門、醫共體牽頭醫院、衛生院分院均可通過績效考評系統直接抓取數據,做到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每個崗位、每個人的實時績效評估,助推當量購買明細延伸到醫生個人[13]。從全國層面來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制度尚不完善,存在考核結果應用與財政補助和醫保支付不緊密、第三方參與考核不夠等突出問題。
4 討論與政策建議
4.1 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文件的考核內容一脈相承,指標體系逐步完善 2010年《關于衛生事業單位實施績效考核的指導意見》提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考核要履行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職能(數量和質量)、基本醫療服務職能(醫療工作效率、醫療質量、合理用藥及醫療費用控制)、綜合管理和服務對象滿意度;2015年《關于加強公立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評價的指導意見》提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要重點考核社會效益(重點評價公眾滿意、健康素養提高等)、服務提供(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開展數量和質量,醫療服務數量和效率、醫療質量和安全、醫療費用控制,以及中醫藥、康復、計劃生育技術等)、綜合管理(財務資產管理、藥品管理、服務模式、信息管理,以及黨建工作、行風建設等)、可持續發展(人才隊伍建設等);2020年《指導意見》提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要重點考核服務提供(功能定位、服務效率、醫療質量與安全)、綜合管理(經濟管理、信息管理、協同服務)、可持續發展(人力配置、人員結構等)、滿意度評價(患者滿意度、醫務人員滿意度等)。不同時期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文件的績效考核框架均包括服務提供(功能定位或者職責)、綜合管理及滿意度,2015年《關于加強公立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評價的指導意見》中績效考核增加了1個維度,即可持續發展(人才隊伍建設),2020年《指導意見》中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指標體系進一步完善和優化。
4.2 2020年《指導意見》強化指標可操作性,關注經濟運行和信息化 (1)《指導意見》在指導性和可操作性上進一步加強。考慮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數量眾多,不同地區發展水平差異較大,考核工作由國家層面給出指導意見,省級層面結合實際情況進行細化完善,縣級衛生健康行政部門和中醫藥主管部門具體組織實施,同時,確定國家監測指標10項。《指導意見》中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以定量客觀指標為主,定量指標占88.1%(37/42),并且多數指標可從衛生健康統計年報、衛生財務年報、中醫醫療管理統計年報中獲取,加強了績效考核的可操作性,降低了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工作壓力。(2)考核指標多維度,關注經濟運行和分配激勵。《指導意見》的績效考核指標體系從服務提供、綜合管理、可持續發展、滿意度評價方面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綜合績效進行多層面、多角度的分析和評判,在重視公平的同時,進一步關注運行效率,如醫師日均擔負診療人次、醫師日均擔負住院床日、病床使用率、平均住院日等指標引導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提高管理能力。在保持公益性前提下,兼顧經濟效益和分配激勵。將醫療收入變化情況、醫療服務收入占比(不含藥品、耗材、檢查檢驗收入)、收支結余和人員支出占業務支出比例納入考核指標,落實“兩個允許”,必須有結余,并且明確基層人員支出占比,才能保障醫務人員工資水平。(3)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以信息化為支撐。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指標數據多來源于現有相關年報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信息系統,能夠實現實時抓取,強調要加強大數據處理技術、統計分析技術、互聯網技術等現代信息技術在績效考核中的應用。
4.3 對開展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的建議 績效考核作為一種管理手段,目的是更好地調動廣大醫護人員的積極性、創造性,為患者提供良好的醫療衛生服務。各地應借助2020年發布的《指導意見》,從以下幾方面著手,積極推動本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工作。(1)在省級層面完善指標體系,明確各指標標準值并細化評分方法。從完善指標體系方面看,各地應根據當地基層工作重點,有的放矢增減指標,如浙江省在國家42個指標基礎上,增加10個與標準化工作當量相關指標。從各指標標準值設定方面看,各地確定時應主要參考國家已出臺的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能力基本標準和推薦標準、醫療質量安全標準、臨床診治指南、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規范、重大疾病防治工作規范、重大公共衛生服務評價項目實施方案等方面的規范性文件和衛生標準值;部分沒有明確標準值的,應結合各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發展情況確定,如診療人次數、住院人數等重點是考核與上年相比變化情況,增長幅度確定要適宜,可用全省(區、市)平均增長幅度(或平均增長幅度的3/4等)作為標準值,也可以按照不同經濟發展區域的平均增長幅度分別確定。如醫師日均擔負診療人次、醫師日均擔負住院床日、病床使用率等指標標準值,在按照全省平均水平(或3/4等)確定標準值的同時,也應將指標變動幅度作為評分維度,只要指標值較上年增長,沒有達到確定的標準值也應得分。(2)指標值和評分方法要利用歷史數據模擬,并且持續完善和優化。各指標標準值和評分方法應該利用往年相關數據進行模擬,經反復驗證后確定適宜的標準值和評分辦法。指標體系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指導意見》及各省(區、市)確定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指標體系需要在實踐和實施中不斷完善和持續優化,以達到評判結果符合預期、接近實際情況。(3)明確省級監測指標,加強分級考核,重視績效考核結果應用。《指導意見》從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指標體系確定了診療人次數、出院人數等10個指標作為國家監測指標。省級相關部門也應從本省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指標中明確省級監測指標,建立不同層面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指標體系,加強省對地市、對縣(區)和對縣域醫共體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結果的應用如果做得不到位,會讓考核工作“含金量”打折扣,各地縣市衛生健康行政部門要高度重視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結果應用,發揮好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指揮棒”作用,引導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經濟良性運行、提高效率,促進可持續發展。(4)依靠信息化平臺和信息化技術,量化指標直接抓取,為基層減負。目前國家層面已經建立“基層醫療衛生服務及績效考核評價”子系統,省級層面應建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信息系統,對于能夠從各類年報數據獲取的定量指標數據,應建立數據對接接口,采取數據直接抓取,加強對指標統計分析,確保績效考核信息互聯互通,為省級層面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順利實施保駕護航,為基層減負。
作者貢獻:秦江梅負責論文撰寫;王芳負責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績效考核實踐整理,對文章整體負責;林春梅、張艷春、張麗芳參與資料收集。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