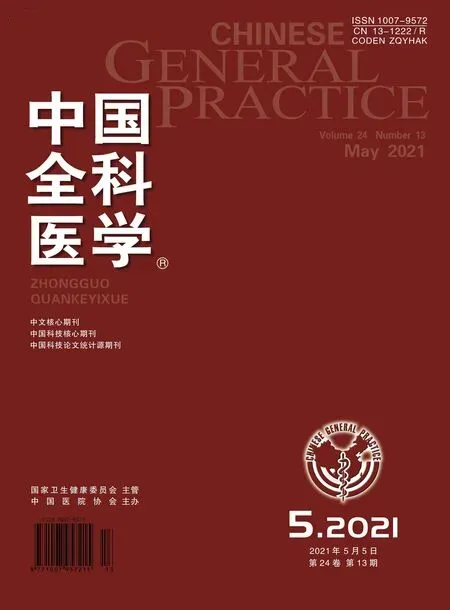大流行的盤點: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的對比
Leon Piterman,Marika Vicziany,林楚玲(譯),黃文靜(譯),楊輝(譯)
正如我們如下所要辯論的,在西班牙流感(1918年)大流行與當下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之間,進行有科學意義的對比,其結果是令人擔憂的。
最樂觀地講,我們至少希望從過去曾經的大流行或流行病,如重癥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或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中汲取相關經驗,并可將這些經驗轉化為未來緊要關頭的戰略規劃和行動。然而可悲的是,大流行很可能卷土重來。歷史已經給我們上過慘痛的課。我們生活在一個復雜的生態系統中,與那些不友好的、一直在伺機襲擊我們的致病生物,共棲共存。在與致病生物的較量中,人類不會常勝。盡管醫學知識有了重大的進展,然而在沒有疫苗和缺乏治療措施的情況下,我們經常還是要祭出歷史悠久的抵擋策略。我們現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采用的隔離措施,也是當年防御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時的措施。
雖然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所造成的影響,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造成的影響,有一些相似之處,但兩者之間也有明顯不同。1918年,世界人口約為25億,估計當時有5億人受到感染,占世界人口的20%;多達5 000萬人死亡,占感染人數的10%,且罹患和死亡者以20~40歲的年輕人居多。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中,世界人口已達80億,感染者超過2 700萬,死亡率則以老年人最高[1]。考慮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時,老年人可能因為過去接觸過其他的流感毒株而獲得了部分免疫力。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中,澳大利亞的情況貌似比現在這個大流行中的其他國家要好。然而,1919年大流行的第二波和第三波所造成的損失,遠大于第一波的破壞性。我們必須認識到,當目前澳大利亞大多數州正在從第一波中恢復的時候,維多利亞州可能正在經歷第二波疫情。當西班牙流感在澳大利亞暴發時,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才剛成立18年。就像現在各州的做法一樣,當時大多數州在實施政策與行動方面是各自為政的。那個時候“江湖庸醫”大行其道,包括吸入硫酸鋅蒸汽、接種幾種細菌菌株混制的疫苗,這些做法也許能預防細菌性肺炎,但對病毒感染無效[1]。直到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10年之后,我們才分離出致病的病原體,即H1N1流感病毒;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才對這個病毒進行基因測序,并發現H1N1的禽流感變種[2]。相比之下,2020年初,研究人員只用了幾周的時間就完成了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測序。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有關的正確信息和錯誤信息傳播速度遠遠超過當時西班牙流感的信息傳播速度。我們現在生活在數字時代,數字時代有利于可靠信息的傳播,但也往往阻礙正確信息的傳播,從而創造了一個像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時那樣的消息跳蚤市場。有人鼓動大家使用鋅含片和維生素D,說這樣可以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然而幾乎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些做法的臨床功效。鋅和維生素D這些藥劑畢竟還是相對無害的,但是我們不能說羥氯喹無害,因其的確存在引起心律失常和致死的風險。1919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時,澳大利亞基本上還是單一文化的國家,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是當時的主流。現在,澳大利亞25%的人口在海外出生,50%有家人在海外出生。人們把他們自己的健康信仰,帶入了臨床服務的環境。他們的信息源不僅局限于澳大利亞的媒體,更依賴于從他們的祖國傳遞過來的消息,通過各種媒介可以輕易獲得這些信息。考慮到各人群間健康素養方面的差異,我們的衛生主管部門發布的信息要更加準確,而且要有多種語言的翻譯。這些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時期出現的挑戰,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時并沒有這個問題。從正反兩方面看,信息時代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期間,可能有利于遏制病毒傳播以減少死亡人數;然而,沉重的信息超載和偽劣信息散播,可能會導致推高焦慮程度的后果。
這兩次大流行的控制傳染方法是相似的,除了依賴于古老的原則如檢疫、隔離、保持社交距離外,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防疫還新加了“封鎖”這一項。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和1918—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致病的病毒都是新出現的,而且都源于另一物種:流感病毒H1N1是禽類,新型冠狀病毒可能是蝙蝠或其他動物。西班牙流感始發于1918年8月,于1919年1月傳入澳大利亞。病例的傳入是通過越洋船只運載自歐洲回國的被感染士兵,途中經歷了4~6周后抵達澳大利亞。而現代旅行方式(航空)能以更快的速度將新型冠狀病毒帶入我們的國家。不過就像其他地區的情況一樣,豪華游輪的航運形式,也對新型冠狀病毒在澳大利亞的傳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這兩次大流行中,檢疫措施都是捉襟見肘。1919年從歐洲返回的戰士被安置在一個特定的檢驗場所,但是戰士逃跑時有發生,從檢疫場所逃逸的人將病毒傳播到了居民社區。2020年的新型冠狀病毒檢疫也是問題百出:海外回國者被安排在沒有準備好的酒店里,招聘缺乏培訓的保安人員提供服務,海外返回的感染者把病毒傳染給保安,保安再把病毒帶回社區的家中。
1 大流行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必須認識到,當醫務人員在處理危及生命的危險時,我們往往忽視對因大流行造成的心理健康問題的管理。對西班牙流感大流行造成心理問題的文獻廖廖無幾,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造成心理問題的相關研究,也大多是應景的、描述的和預測的。沒有人通過臨床試驗研究探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期間和之后某個特定心理干預措施的效果。因此,盡管全球在過去6個月出版了5萬多篇關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論文,但其中涉及心理健康問題的研究少之甚少。
由于缺乏可靠的數據,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與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心理健康問題進行比較,是非常困難的。澳大利亞護理人員曾報告流感大流行期間一線醫生的絕望感受。挪威的一項研究表明,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間自殺率比大流行之前和之后高出7倍。還有一些證據表明西班牙流感導致了神經精神方面的臨床表現。流感在急性期對腦的結構性損傷可表現為急性的或潛伏性的精神癥狀,如意識混亂、譫妄和認知紊亂。西班牙流感患者中有100萬病例出現了嗜睡性腦炎,導致困倦、運動障礙和意識混亂。大流行數年后發現,大量的帕金森病例與西班牙流感有關,因此提出西班牙流感可能是帕金森病的病因之一[3]。
為了做出西班牙流感對心理健康影響的有根據的估計,我們可以借鑒2003年SARS和2009年的豬流感H1N1的研究。在SARS大流行期間,美國36%的住院患者出現了精神疾病癥狀[4]。由于西班牙流感的嚴重程度及高死亡率,那些在家、在醫院或其他照護機構臥床的患者中,可能會出現相同比例的心理問題。將這個估算用在目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上,那么目前在澳大利亞有超過3 000例患者需要精神病學服務。在美國,這個估計數字可能超過100萬。HAWRYLUCK等[4]也在SARS流行期間對加拿大129例患者進行了隔離對心理影響的研究,發現28.9%的患者符合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的診斷標準,31.2%符合具有臨床意義的抑郁診斷標準。健康工作者,尤其是在醫療第一線的醫護人員的心理健康問題,引起了人們的擔憂。GRACE等[5]發現,那些曾照料過SARS患者的醫生中,有45.7%存在心理困擾,而那些沒有照料過SARS患者的醫生中,這個比例只有12.5%。
1919年的時候,精神病學作為一個臨床學科仍處在襁褓階段,并且這個階段持續了40年之久。1867—1916年,在維多利亞州的亞拉臘、比奇沃斯、基烏(威爾斯梅爾)和皇家公園等地方,開設了精神疾病收容所。不過1912年才發現苯巴比妥類藥物,所以精神疾病類藥物療法僅限于巴比妥。1919年,幾乎沒有任何精神療法或以社區為基礎的治療的證據。直到20世紀70年代,心理健康的治療方法才有了發展。在西班牙流感暴發期間及之后,那些患有抑郁、焦慮或PTSD者,很可能沒有得到任何正式的治療。除非其精神疾患非常嚴重,只能關進精神病收容所,而在收容所里,主要的治療方法就是束縛和隔離。
澳大利亞與其他國家一樣,也很難將西班牙流感造成的精神疾病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精神疾病區分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于1918年,其給人類留下的是精神疾病的“余孽”,其中包括現在稱之為PTSD的“炮彈休克”。澳大利亞大概有1.5萬人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中失去生命,有超過6萬人犧牲在一戰前線,還有30萬人飽受軀體和心理上的創傷,對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只有用喝酒來療傷。家庭暴力普遍存在,因此家庭中的心理問題往往是混合的。在當時醫學知識不足的時代背景下,有些臨床醫生把“炮彈休克”看成是個人軟弱的表現,正如帕特·巴克的三部曲小說之一《再生》中所描述的那樣。雖然西班牙流感大流行10年后才出現世界經濟大蕭條,但是1917年澳大利亞大罷工之后出現了就業的不安全感,其是造成緊張和心理疾病的另一個原因。
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時的某些特征,與澳大利亞目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是一樣的,如經濟的大衰退已經造成了異常的失業狀態,尤其是年輕人的失業問題。幸運的是,2020年時的心理健康服務已經得到了很好的發展。當然,即便是當前最好的心理健康服務狀態,資源仍然是緊缺的,特別是農村及偏遠地區仍不容易獲得心理健康服務。隨著失業加劇和經濟發展舉步維艱,預計服務提供會變得越來越差。根據超越抑郁(Beyond Blue,澳大利亞提供社區心理健康支持的組織)的報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期間打心理熱線電話尋求心理幫助的數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了40%。即便是沒有任何疾病大流行,在以往的經濟衰退中,失業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系已經得到了很好的證實。考慮到現今澳大利亞工作的不穩定性,即便是在“正常時期”,害怕失業也是焦慮的來源之一[6-9]。
2 2020年大流行的演變
要想理解現在大流行背景下的心理問題的演變過程,我們需要劃分出3個階段:大流行前期、大流行急性期、大流行急性后期。
2.1 大流行前期 1月中旬至下旬,晚間新聞反復出現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相關報道,人們對新聞報道的反應各異,從一開始的否認,到不斷升級的害怕與警覺。3月前,出現了恐慌式搶購,報道稱有人在超市因衛生紙和其他物品而發生爭斗。囤積生活必需品,特別是消毒液及食品的現象開始變得普遍,這使得恐慌在墨爾本和悉尼的各郊區蔓延開來[10]。就像SARS時發生的一樣,人們對被感染病毒的焦慮日漸增長,這導致了人們對亞洲面孔人群的歧視。那時,新型冠狀病毒有時也被稱作“中國病毒”“武漢病毒”或者是“新黃禍”[11]。
2.2 大流行急性期 由于度假者及其他人陸續回國,新型冠狀病毒開始緩慢地滲入澳大利亞的社區,急性大流行階段開始于實行檢疫、保持社交距離和身體距離等政策。到3月中旬,澳大利亞各州實行了多種形式的封鎖。人們被要求留在家中,除了需要醫學治療、鍛煉身體、購買生活必需品或藥品,或者不可能在家工作而必須外出的情況,禁止人們離家。不允許人們去學校、健身房、公共場所、餐廳,也不允許在家庭內和戶外舉行大型聚會。根據數學模型的演算,預計將檢測出13萬個病例。據此政府制定了應對大流行的充分計劃,包括準備大宗的個人防護設備以保障醫務人員的安全,并采購7 500臺呼吸機以提供給病情最危重者使用。
晚間電視新聞一直在播放總理和首席醫務官的每日疫情簡報。突然之間,人們感到疫情結束是遙遙無期了,失業人數不斷攀升,經濟衰退貌似不可避免。人們眼前一片迷茫[12],這些不確定性加劇了害怕、焦慮、失眠,并最終導致抑郁和PTSD。對那些原本就有心理健康問題,特別是廣泛性焦慮障礙的人來說,這種情形無疑是雪上加霜,對他們的影響更為嚴重。在2009年H1N1大流行期間,社區中25%~33%的人經歷過高度的壓力和焦慮[13]。因此我們意識到,要對某些高危群體給予特別關注,包括醫務人員、在檢疫過程中處于完全隔離的人、現有的和新出現的失業者、無家可歸的人,以及與外界隔離的老人。
雖然還沒有確鑿的數據,但是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期間的隔離措施造成的影響,我們是有理由擔心的。這些影響包括酒精濫用、家庭暴力,以及因為學校關閉后孩子只能居家學習,可能存在的兒童虐待問題[14]。維多利亞州警方也傳出非正式消息,說因家庭暴力而請求出警的次數增加了。因為家庭暴力受害者不太可能在施暴者在場的情況下給警察打電話求助,所以真實的家庭暴力發生率可能永遠無法得知。
因住院治療而造成的心理影響也是所知甚少。這些影響范圍很大,從急性的低氧狀態和新陳代謝改變,到有可能直面死亡的住院經歷所帶來的長期和創傷性的心理影響。與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一樣,PTSD無疑會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之后持續很多年。因此除了管理患者身體方面的恢復外,還應采取相應措施去緩解PTSD和抑郁。這些壓力源會隨著封閉時間的延長和經濟損失的加重變得越來越惡劣[15-16]。
2.3 大流行急性后期 伴隨著對社交活動限制的放松,學校、酒吧和餐廳的開放,以及對旅行和職業競技體育活動限制的減少,大流行的第二波或后繼波的威脅也隨之到來。這是目前正發生在維多利亞州的情況。
從澳大利亞的患病和死亡數據上,我們看到了與瑞典、英國和美國等的明顯不同,那些國家幾乎沒有限制政策,或者防控措施遲滯。相比而言,有些國家或地區如中國臺灣、韓國和澳大利亞,則采取了及時和嚴格的限制措施。在我們面前還有新加坡這樣發人深省的例子,新加坡經歷了第二波疫情,一周內新增病例超過7 000例。發生第二波疫情的可能性,加上隨后漫長的隔離期,會生成更多的不確定性、害怕、顧慮、焦慮及擔心。人們擔心的是可以打疫苗之前(如果有疫苗的話)是不是還要再采取嚴厲的限制措施,以遏制一波又一波的疫情。澳大利亞仍然要求人們保持社交和身體距離、使用消毒劑、洗手、盡可能在家工作。最近在墨爾本,開始要求人們如果出家門后不能保證與別人保持1.5 m的距離,則必須佩戴口罩。在這段時間,我們將目睹更多有心理疾患的人出現。這包括仍在飽受第一波大流行疫情痛苦的人們,再加上那些樂觀情緒被消磨殆盡的人們,他們面前是不確定的未來,害怕的是長期的經濟衰退。
3 結論
雖然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兩者所造成的傷害都是巨大的,但是有關這兩次大流行對心理健康影響的數據是普遍缺失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小心謹慎地進行兩者的對比。雖然2003年的SARS大流行給我們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經驗教訓,不過遺憾的是,在當前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中,除了中國臺灣和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小部分國家和地區外,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并未汲取上次大流行的經驗教訓。截至2020-07-09,擁有2 400萬人口的中國臺灣只有448個病例和7個死亡病例,而擁有3億人口的美國卻有300萬個病例及132 310個死亡病例。關于這種新型冠狀病毒的性質我們已經了解了不少,但是關于其對全球社區的社會心理方面的影響,以及即將到來的經濟衰退對當代和后代人身體和心理健康的影響,還需要有更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