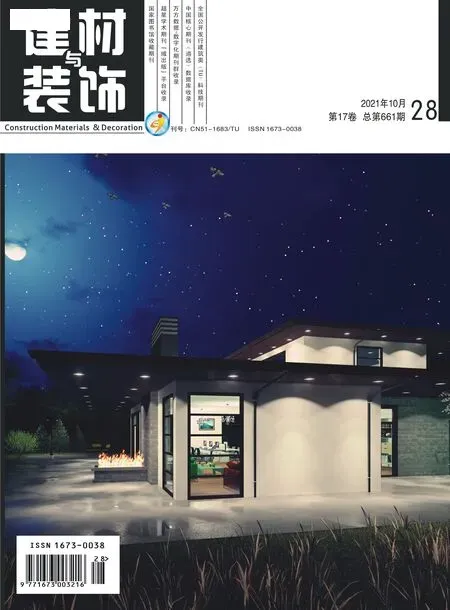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非毗鄰地區合作路徑研究
董楠婭
(重慶國際投資咨詢集團有限公司,重慶 400067)
0 引言
2020 年12 月29 日,重慶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發布關于《關于同意設立川渝高竹新區的批復》,川渝高竹新區率先正式設立,為兩省毗鄰區市縣的合作落地與掛牌吹響了沖鋒號。與毗鄰區市縣熱鬧非凡的合作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非毗鄰區市縣雖然有參與合作的強烈意愿,但在模式和機制上缺乏抓手,尚未廣泛開展起有效的合作。在成渝兩地全方位、多層次開展雙層經濟圈建設的大背景下,非毗鄰地區要搶抓戰略機遇,找準切入點和著力點,強化協同聯動發展。本文以跨區域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與深化區域合作為理論,結合非毗鄰地區的產業合作分析非毗鄰地區合作的主要類型,提出推動成渝非毗鄰地區協同聯動發展的合作路徑,提高各非毗鄰區縣的經濟實力、促進經濟發展,建立各個非毗鄰區縣間的合作渠道,實現長期合作模式穩定發展,助力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
1 我國區域合作的現狀與形勢
1.1 區域合作相關方積極性差異大
區域合作成員之間的積極性,是區域合作的關鍵點,我國區域合作的現狀是:經濟發展較落后的地區為加速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改善經濟狀況,從而大力開展并且積極響應與其他地區進行區域合作。而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對此并不積極,兩則之間的積極性截然相反,主要是因為發達地區在會承擔較高合作成本的同時,資源的投入與合作的收益卻不成正比。同時,各地政府與當地民間組織、企業對區域合作的積極性同樣是一高一低,此現狀主要有兩個原因:①因為企業、民間組織未意識到自身在區域合作發展中的重要性,未能通過加強自身能力,整合與優化區域內各種生產要素,來提高區域內的經濟水平;②政府沒有強調各企業與組織在區域合作中的主體地位與基礎作用,并且未能規范保護企業在區域合作中的合法權益。
1.2 區域內產業結構趨同程度加強
我國西部的成渝經濟作為典型案例,許多城市在自然資源環境與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都具有相似性,而城市化與工業化現狀都處于同一階段,導致其產業結構的同質化。此情況易導致區域內各地區之間的惡性競爭,導致各城市難以共同發展,這樣的結果不利于整個區域的經濟協調發展。
1.3 區域內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矛盾凸顯
以西部為例,從人口角度來分析,留守在農村的勞動力因為第一產業的飽和則面臨著向第二與第三產業轉型的壓力,選擇進入城市的部分農村勞動力也面臨著社會保障等問題;從基礎設施建設來看,不但農村各個方面的設施(交通、教育、醫療等)都遠遠落后于城市,并且進入城市的勞動力也因各種原因無法享受到當地的一些基礎設施,尤其是子女教育與個人醫療方面。因資本的趨利性,不發達的地區各大資本和社會生產要素不斷流向較發達地區的現象已成為常態,形成經濟上的虹吸效應。大城市進一步擴張,小城市則繼續萎縮,城市貧富分化嚴重[1]。這些現象不僅不利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同時也會影響社會安定[2]。
2 國內非毗鄰地區合作案例
目前,國內非毗鄰地區合作案例主要有:“秦皇島分園”“G60科創走廊沿線”“長三角文旅產業聯盟”三個比較有代表性的,所以我國已有非毗鄰地區區域合作的成功案例,并且合作類型具有多樣性,不管是北京海淀與河北秦皇島的點狀合作、G60 科創走廊的建設的帶狀合作、還是長三角文旅產業聯盟的網狀合作,都結合了自身地區特點,整合了優勢資源,與其他地區達成高效的區域合作,并為我國其他面臨此問題的地區提供借鑒意義。
3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非毗鄰區縣的現狀分析
3.1 面臨的問題
3.1.1 政府支持力度不夠
自從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提出以來,川渝兩地協同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成果初現,兩省市共同謀劃實施的31個重大項目。川渝兩地將未來的地區經濟發展戰略中心與重心都落于此處,在推進毗鄰地區融合發展方面,重慶印發《關于推動毗鄰四川的區縣加快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川渝毗鄰地區合作共建區域發展功能平臺推進方案》,因地制宜提出10 個合作平臺,服務川渝毗鄰的13 個區縣和6 個地市融合發展。
由此可看出,川渝兩地舉全省市之力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兩地大力開展與積極響應區域經濟合作,并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與物力資源。但不管是各大政策的發布還是眾多項目的落地,都有一個共同點與關鍵詞,就是“毗鄰地區”。而與此詞相反的就是“非毗鄰地區”,目前關于非毗鄰地區合作發展的文件與政策可以說是極少的,因此川渝兩地政府對非毗鄰地區合作的支持與指導力度還欠佳。
3.1.2 合作方式存在局限性
2020 年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從某種意義上被定位為經濟第四級,地位更高,使命更緊迫,成渝地區迎來歷史發展的窗口期。回望成渝城市群過去的發展,雖然雙方簽署了一系列合作協議,但總體而言,成渝雙城競爭更加激烈。成渝雙城在產業、文化等多個領域上展開了激烈的交鋒。例如,成都近年來全力孵化汽車產業發展,向東設立工業區(今龍泉驛區經開區),如今龍泉驛汽車產業已形成近5 千億的產業集群。而汽車產業一直以來也是重慶的強項,雙方的產業競爭的態勢十分明顯。而汽車的競爭也只是產業競爭的冰山一角。四川與重慶的優勢產業呈現出一個“高度重疊”的狀態,這就產生了一個“同質化”的競爭,存在資源錯配的問題。
3.2 合作機制與政策協同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戰略正式提出以來,川渝合作創造多項“第一”,正在告別曾經的“瑜亮之爭”,兩地在合作機制上不斷完善,在政府政策上更是大力支持,兩地政府聯合發布《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放管服”改革2021 年重點任務清單》《川渝通辦事項清單(第二批)》等相關的政策出臺和調整,不但方便了兩地人民的日常生活,更是推動了兩地產業的協同發展。
4 推動成渝地區非毗鄰地區合作發展的具體模式
4.1 根據共同發展需求加強“一對一”點狀合作
(1)合作共建產業園區。常見的合作共建園區模式有:股份合作模式、“總部+基地”“研發+生產”模式、品牌和管理輸出模式。川渝非毗鄰地區有關區市縣可根據自身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等,在學習借鑒先行地區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積極探索符合雙方共同利益的合作模式,共建跨區域合作產業園區,形成使命共擔、協同共建、開放共贏的發展格局。
(2)發展科創研發聯盟。依托非毗鄰兩個區市縣的科創研發和產業創新資源,可共同構建產業研究院和技術研發中心等,構建完善的創新鏈條。
(3)深化企地、校地合作。成渝地區擁有眾多高校院所,各行業也有不少優勢企業,蘊藏著巨大的合作空間,非毗鄰區縣應積極發揮自身比較優勢,主動加強對接,進一步深化企地、校地合作,實現共同發展。
4.2 以大江大河和重要交通干線為紐帶打造沿江沿線經濟走廊
4.2.1 長江上游綠色發展走廊
充分發揮長江黃金水道的自身優勢,共同推進長江航道整治和沿江高鐵建設,加強港口分工協作,推動港口聯動發展,促進瀘州、宜賓、涪陵、長壽、萬州等地產業園區圍繞延鏈、補鏈、強鏈開展深度合作,構建完善的跨區域上下游產業鏈,打造特色優勢產業集群。
4.2.2 嘉陵江流域生態經濟走廊
嘉陵江流域覆蓋重慶合川、北碚、渝北、江北、沙坪壩、渝中等區縣和四川廣元、南充、綿陽、德陽、遂寧、廣安等市,近年來在文化旅游合作和嘉陵江流域國家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建設等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效,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建立嘉陵江流域綜合保護開發協同聯動機制,加強流域內生態文化旅游資源整合和產業鏈上下游合作,推動產業的加快發展,打造嘉陵江流域生態經濟合作區。
4.2.3 成渝科創走廊
此方案可借鑒G60 科創走廊模式,以(重慶)科學城和(成都)科學城作為“兩極”,再以成渝高速和成遂渝高速作為發展主軸,沿線各區市縣共建成渝科創走廊,同時依托成綿高速延伸至德陽、綿陽,依托長江延伸至宜賓,共建共享科技創新平臺資源,探索建立科技創新協同合作機制,增強協同創新和高質量的科技成果轉化能力,推動建設具有全國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
4.3 依靠共同資源稟賦組建跨區域合作聯盟
(1)文旅合作聯盟。巴蜀文化與景觀的名聲一直以來全國皆知,其文化旅游資源非常豐富,為兩地合作提供了廣闊舞臺。如重慶梁平、北碚、銅梁和四川長寧、青神、大竹等區縣可依托豐富的竹資源,組建竹海文旅聯盟,共同開發竹海旅游。可構建景區門票互免、游客互送、文化互動、品牌互育和優勢互補的緊密合作關系。
(2)頁巖氣產業合作聯盟。四川和重慶頁巖氣資源量分別居全國第一位和第三位,全國頁巖氣資源總量的30%來源于此。長寧—威遠區與涪陵區均為國家級頁巖氣示范區,四川的自貢、瀘州、內江、宜賓和重慶的榮昌、永川、大足、璧山、潼南、酉陽、黔江、城口、秀山等地均是頁巖氣資源有利成礦區。上述區市縣可共同組建頁巖氣產業合作聯盟,抱團與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合作,建立相關合作機制,推動央地共同發展。
(3)商貿物流聯盟。萬州、涪陵、江津、永川、綿陽、達州、南充、宜賓、自貢等依托物流樞紐節點地位,共同組建商貿物流聯盟,打造西南地區國家級物流樞紐網。
5 結語
隨著我國再一次全面深化成渝雙城經濟圈的建設與規劃,川渝相毗鄰區縣合作如火如荼。在此大背景下,川渝非毗鄰區縣如何開展有效合作,如何積極參與并努力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是一個值得研究課題。同時也要多方面綜合各種因素,從而確保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非毗鄰地區合作路徑取得顯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