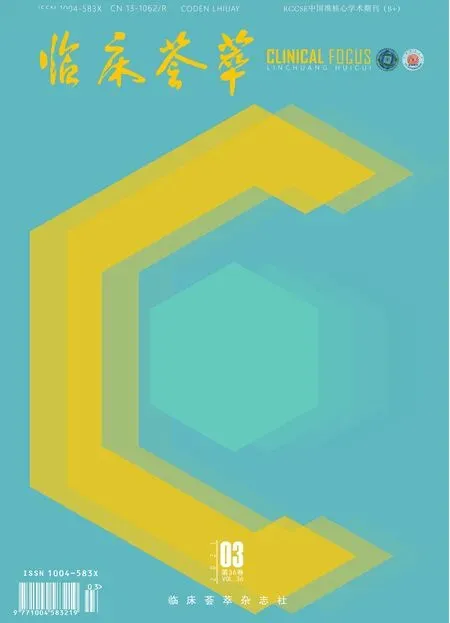序貫化療系統性免疫球蛋白輕鏈型淀粉樣變性腎病1例
高興連,童宗武,楊崇猛,趙艷紅,盧永新,丁 蓉
(昆明醫科大學第六附屬醫院 腎內科,云南 玉溪 653100)
系統性免疫球蛋白輕鏈(AL)型淀粉樣變性是由單克隆免疫球蛋白輕鏈錯誤折疊形成淀粉樣蛋白,并沉積于組織器官,造成組織結構破壞、器官功能障礙并進行性進展的疾病,主要與克隆性漿細胞異常增殖有關,少部分與淋巴細胞增殖性疾病有關,病因及發病機制仍在不斷探索中,遺傳因素的作用尚不確切。臨床表現為多系統受累,腎臟主要以腎病綜合征多見,循環系統主要為低血壓,心臟肥厚等,部分可有肝、脾、舌等腫大。該病診斷主要依賴腎活檢、血清蛋白電泳、骨髓穿刺、肝穿刺病理檢查等,對于分類困難的患者,可行基因檢查協助診治[1]。我國AL型淀粉樣變性的發病率也呈現出逐年升高的趨勢[2]。過去此病生存率低,患者在確診12個月內的病死率在30%~40%,而腎淀粉樣變性病是系統性淀粉樣變性病患者發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現為腎病綜合征(尿蛋白定量>3.5 g/24 h),部分伴有腎功能不全[3]。此病治療主要為抑制單克隆免疫球蛋白合成,但尚缺乏統一的治療方案,現將我院1例AL型淀粉樣變性腎病的診療過程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患者,男, 42歲, 2020-04-25 10:00因“雙下肢水腫4天”入院。既往體健。患者4天前無誘因出現雙下肢水腫,伴尿量減少,晝尿1~2次,夜尿0~1次,每次尿量250 ml,略感惡心、臍周隱痛、腹脹,伴腹瀉,每天解稀便2~3次,當地衛生院予“利尿劑及消食片(具體不詳)”治療,癥狀無好轉,至某縣醫院就診,查“尿蛋白3+、血清白蛋白(ALB)24.80 g/L、甘油三酯(TG)4.59 mmol/L”,即到我院診治,診斷 “腎病綜合征”收住。入院時查體:血壓110/70 mmHg(1 mmHg=0.133 kPa);皮膚、黏膜無蒼白;眼瞼無水腫;雙肺呼吸音清晰,未聞及干濕性啰音;心界無擴大,心率105次/min,無雜音;腹軟,下腹部輕壓痛,無反跳痛,肝脾未觸及,雙腎區無叩擊痛,移動性濁音陽性;雙下肢膝關節以下輕度凹陷性水腫。2020-4-25在縣醫院肝功能:總蛋白(TP)54 g/L、ALB 24.80 g/L;血脂:總膽固醇(TC)17.1 mmol/L、TG 4.59 mmol/L、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11.44 mmol/L;尿常規:蛋白質(3+);腎功能正常。入院診斷:腎病綜合征。
入院后輔助檢查 ①血液檢查:凝血4項, 血栓三項:活化部分凝血激酶時間(APTT)44 s、凝血酶時間(TT)22.2 s、D-二聚體(D-Di)1.29 μg/ml;血沉36 mm/1 h;肝功能:血清TP 40.3 g/L、ALB 18.9 g/L、ALB與球蛋白比值(A/G)0.88、前白蛋白(PA)131 mg/L、天冬氨酸轉氨酶(AST)56 IU/L、堿性磷酸酶(ALP)204 IU/L、γ-谷氨酰轉移酶(GGT)289 IU/L、巖藻糖苷酶(AFU)72 IU/L;腎功能:肌酐(CREA)85 μmol/L、尿酸(UA)440 μmol/L、肌酐清除率(Ccr)79.23 ml/min。血脂:TC 11.29 mmol/L、TG 3.23 mmol/L、LDL-C 9.1 mmol/L、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0.39 mmol/L;電解質、感染性標志物、血常規、糖三聯、類風濕性標志物、常規心肌標志物、心力衰竭標志物示正常;輸血三項、抗HIV抗體陰性;甲狀腺功能8項:三碘甲狀腺原氨酸(T3)0.54 μg/L、人促甲狀腺素(H-TSH)7.497 mIU/L;腫瘤標志物A組:鐵蛋白857 μg/L、糖類抗原(CA125)214 kU/L;抗核抗體譜18項、血管炎(ANCA)8項、抗磷脂譜8項均陰性;血清免疫固定電泳:未發現異常單克隆條帶;血清蛋白電泳:未發現M蛋白。②尿液檢查:尿液及尿沉渣定量分析:蛋白(4+)、白細胞4~6、紅細胞0~1;尿本周蛋白定性試驗陰性;早期靈敏腎功能:β2-微球蛋白1.27 mg/L、免疫球蛋白 >200 mg/L、尿微量白蛋白 >500 mg/L;24小時尿蛋白定量:尿蛋白34 398 mg/L、尿蛋白定量17 199 mg/24 h。③影像學檢查:腹部彩色超聲:肝內中強回聲結節(不除外血管瘤);膽囊壁水腫、增厚;腹腔積液;雙腎形態、大小正常。頸部血管彩色超聲未見異常。心臟彩色超聲檢查:二維超聲心動圖及彩色血流檢查正常(超聲提示左側胸腔積液)。全腹CT檢查:腹盆腔散在積液;肝膽胰脾右腎及膀胱平掃未見異常;掃描范圍內雙肺下葉炎癥并雙側胸膜腔少量積液。X線檢查:骨盆骨質未見異常,頭顱骨質未見明確異常,提示寰枕及頸2、3椎融合。心電圖:竇性心律,正常范圍心電圖。④骨髓活檢:表現有核細胞增生明顯活躍,以粒系增生明顯且伴有退行性改變。
腎臟病理報告:送檢腎穿刺組織常規做蘇木精伊紅(HE)、PAS、PASM、Masson染色,主要為腎皮質,可見54個腎小球,其中3個腎小球球性硬化。其余腎小球系膜區有大量粉染的均質無結構物質沉積,使部分腎小球系膜區增寬,腎小球基底膜出現節段性睫毛樣變化,毛細血管襻受壓,系膜區、上皮下、內皮下無明顯嗜復紅蛋白沉積,壁層上皮細胞無增生,未見新月體形成。腎小管上皮細胞空泡及顆粒變性,個別腎小管萎縮,腎間質散在炎癥細胞浸潤,無明顯纖維化,小動脈管壁增厚,可見粉染的蛋白樣物沉積,官腔狹窄。特殊染色:剛果紅染色+,氧化剛果紅+。免疫熒光:IgG(-)、IgM(+)、C3(-)、C1q(-)、Fib(-)、AlB(-)、Kappa(+)、Lamda(-)、AA(-)、IgG1(-)、IgG2(-)、IgG3(-)、IgG4(-)、PLA2R(-)、TSHD7A(-);沉積部位及方式:ALB 腎小管可見重吸收小滴、血管Kappa(+)、Lamda(-)、AA(-)。電鏡:腎小球:鏡下檢到2個腎小球。毛細血管內皮細胞明顯空泡變性,個別管腔內可見紅細胞,無明顯內皮細胞增生,毛細血管襻部分受壓,腎小囊壁層增厚、分層,壁層細胞空泡變性,無明顯增生。基底膜:節段性增厚,厚度約250~600 nm。臟層上皮細胞:上皮細胞腫脹、空泡變性;足突剝脫。系膜區:系膜細胞和基質增生,未見電子致密物沉積。系膜區和基底膜內可見大量纖維樣物質沉積,直徑約8~12 nm, 僵硬無分支,排列雜亂。腎小管-間質:腎小管上皮細胞空泡變性,腎間質無特殊改變。腎間質血管:毛細血管腔內見紅細胞簇集。見圖1~3。

圖1 組織學檢查

圖2 免疫熒光染色

圖3 電鏡觀察
腎臟病理診斷:腎淀粉樣變性腎病,AL型。最終診斷 AL型淀粉樣變性腎病。住院期間予保腎、降脂、補充ALB、利尿、抑酸護胃等治療,期間并發“呼吸道感染、菌血癥”,予抗感染治療。化療:2020-05-13、20、27及06-03行環磷酰胺、硼替佐米、地塞米松(CBD)化療方案[環磷酰胺0.48 g(0.1 g/kg)、硼替佐米2 mg、地塞米松40 mg]治療,共完成1個療程。并于06-10開始環磷酰胺、沙利度胺、地塞米松(TCD)化療方案(連續服用沙利度胺75 mg/晚,環磷酰胺480 mg、地塞米松40 mg 靜脈滴注,每月1次)。
經過長達約5月的隨診治療,患者雙下肢水腫已基本消退,腹腔積液明顯減少,腹脹已基本緩解,肝臟回縮至肋緣以內,尿蛋白定量降至1 g/24 h,尿量增加至2000 ml/d。整個病程,患者病情相關指標變化,見圖4。

圖4 病情相關指標變化
2 討 論
本病的致病物質-淀粉樣物質來源不同,包括非正常蛋白產物、野生型蛋白的分泌增多或減少或遺傳性蛋白變性,但是所有的纖維類型實質上有相似的超微結構,其β-片層結構在特定的空間有結合剛果紅染料的能力,這是診斷的一項依據。組織學染色、免疫熒光或免疫組織化學可用來分型,不能確定的可通過激光纖維切割聯合以蛋白質組學為基礎的液相質譜分析(LMD/MS)進行確定[4]。該例患者為中年男性,診斷除了根據病史及臨床癥狀及體征,依靠腎穿刺病理活檢已確診。因部分多發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 MM)可表現為淀粉樣變,又稱MM相關淀粉樣變,最常見為輕鏈型淀粉樣變,是否合并MM或原發病因為MM將影響患者的治療策略及預后[5-6],本例患者骨髓活檢、尿本周蛋白檢查均陰性,亦無溶骨性病變、高鈣血癥等臨床表現,但未做多部位骨髓穿刺,仍需繼續密切觀察隨訪,如出現骨痛、骨折、高鈣血癥、貧血等,可再次行骨髓穿刺檢查等警惕多發性骨髓瘤。
該病目前尚無最佳治療方案,在過去,治療方案主要為以馬法蘭為主的綜合方案,而近30年來,隨著新藥的不斷出現,研究證據的不斷更迭,已逐漸變化為“硼替佐米+環磷酰胺+地塞米松、沙利度胺+環磷酰胺+地塞米松”等化療方案,取得了比較好的療效,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我國的臨床指南也推薦上述方案為一線用藥[7]。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據已證明硼替佐米、沙利度胺為基礎的化療在AL型淀粉樣變性病中的療效,黃湘華[8]的研究共納入72例診斷AL型淀粉樣變性患者,所有患者均腎臟受累,接受中位2個療程的硼替佐米聯合地塞米松(BD)治療,總體血液學緩解率為75%,完全緩解率45%,2年腎臟反應率為60%,2年總體生存率76%,認為BD方案有較好的臨床緩解率和遠期生存率,可考慮作為臨床一線治療方案。2020年Milani等[9]納入153例患者的研究表明,對于難治性、復發性AL型淀粉樣變性病,波馬利度聯合地塞米松可取得較為快速的血液學反應。另外,自體干細胞移植(ACST)也取得了較好療效[10-11]。但是,在2020年林澤宇等[12]總結近10余年來系統型淀粉樣變性腎病的國內外治療方案,其中提出,對于初治患者,ACST為首選方案,對于不能進行ACST的初治患者,“硼替佐米+美法侖+地塞米松”方案較“沙利度胺+環磷酰胺+地塞米松”可取得更高的緩解率,但患者總生存時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降低淀粉樣蛋白生成前體的供應或將其穩定在非淀粉樣蛋白生成狀態,從而干擾淀粉樣蛋白形成和毒性的初始階段的治療藥物如抗淀粉樣蛋白抗體、新興靶點治療藥物正在積極研究開發中[13-14],這些新藥可能為患者的生存甚至治愈帶來曙光和希望。
本例患者經濟困難、居住山村、交通不便,根據目前文獻及研究結果,原本擬對患者行ACST治療,但患者及家屬拒絕,則為其選擇CBD方案誘導緩解,此方案亦需住院輸液、費用較高,所以完成一個療程后予TCD方案維持,此類治療方案尚未檢索到臨床報道,現在該病例取得了部分緩解(very good partial response, VGPR)的臨床療效,且尚未觀察到器官反應,但需要繼續密切隨訪診治,若治療成功,可能為AL型淀粉樣腎病患者的治療提供較為新穎的研究思路。
對于評估療效,主要通過血液學、尿液學檢查及患者全身狀態的評估,即使成功地進行了血液學治療(CR/VGPR),淀粉樣沉積物仍然存在于腎臟中,并且不可能區分新淀粉樣沉積物還是舊淀粉樣沉積物,這使得在大多數情況下無需進行重復腎臟活檢[15]。本例患者仍在繼續隨訪治療中,若病情再發加重或者出現腎功進行性衰竭等,則必要時行重復腎穿刺及其他相應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