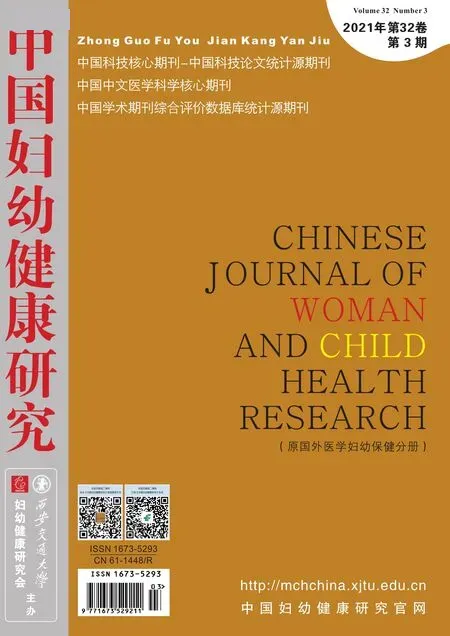GCH1基因剪切突變致多巴反應性肌張力障礙1例
董 暢,任淑紅,張曉燕
(保定市兒童醫院神經內科,河北 保定 071000)
多巴反應性肌張力障礙(dopa-responsive dystonia,DRD)是一組基因相關的遺傳性疾病,與左旋多巴胺合成代謝通路上的酶活性缺陷有關,進而出現進行性肌張力障礙。本病患病率較低,以女性多見,女性為男性的2~4倍。DRD主要是由于三磷酸鳥苷環化水解酶1(guanosine triphosphate cyclohydrolase 1,GCH1)基因和酪氨酸羥化酶(tyrosine hydroxylase,TH)基因突變所致,不同基因缺陷所致臨床表現具有明顯異質性,故該病的診斷存在較多困難。本文報道1例GCH1基因內含子突變所致DRD,從而進一步探討GCH1基因對該病的影響。
1臨床資料
患兒,女,5歲,主因走路姿勢異常、易摔跤3年余,于2017年2月就診于我院。患兒自1歲3個月開始學步走路后,無明顯誘因出現走路姿勢異常,動作笨拙,步態不穩,易摔跤,行走速度慢,可自行上下樓梯,不會雙足及單足跳,家長未予特殊治療,上述癥狀進行性加重,似有晨輕暮重的特點,患兒語言及智力發育正常,無肢體疼痛、無力,無感覺異常及尿便障礙。自發病以來,患兒精神狀態良好,體力情況良好,食欲食量良好,睡眠情況良好。既往史無特殊,否認傳染病接觸史,本患兒為第2胎,足月剖宮產,圍產期(-),生長發育史同正常幼兒,否認家族遺傳史。查體:體重27.00kg,神志清,精神反應可,計算力、理解力、記憶力正常,定向力正常,可正常對答,對答切題,吐字清晰,角膜K-F環(-),顱神經查體陰性,四肢肌力正常,肌張力正常,雙側膝腱反射活躍,踝陣攣(+),巴氏征(+),Gower征(-),其余神經系統查體(-)。門診輔助檢查:血常規、肝腎功能、心肌酶、電解質、血沉、抗核抗體譜、葉酸、維生素B12、血尿篩查、肌電圖均正常。骨盆正位片、頸腰椎核磁、頭顱CT及核磁均未見明顯異常。異常輔檢:乳酸3.10mmol/L,血氨111.56μmol/L,呈升高,復查后恢復正常。雙側髖膝關節彩超示雙側股骨頸前間隙增寬并伴積液。骨密度檢測示中低水平。2017年2月該患兒及家屬完善家系基因檢測(見表1及圖1),受檢者及其父親均發現GCH1基因c.542-2A>T(編碼區第542號核苷酸前內含子中倒數第2位核苷酸由A變為T)的雜合核苷酸變異,其母親、大姐和弟弟未發現變異。
患兒及其父親發現的GCH1基因c.542-2A>T屬于剪切變異,與該變異同一位點的c.542-2A>C的致病性已經有文獻報道[1],且與DRD相關,該變異不屬于多態性變化,在人群中發生的頻率極低。該基因突變經MutationTaster軟件預測蛋白功能損傷為可能致病,變異分級評分為可能致病,且該變異與疾病的相關性在HGMD數據庫中有收錄[1]。患兒予以美多芭31.25mg/次,2次/日,口服治療后,用藥1周患兒動作笨拙較前緩解,2個月后走路姿勢逐漸正常,4個月后可雙足跳,無智力及生長發育落后表現。患兒目前體重32.00kg,美多芭用量為62.50mg,2次/日,可以雙足跳,不會單足跳,至今未出現癥狀反復或不良反應。

表1 患兒家系GCH1基因變異及類型

圖1 患兒及父親GCH1基因突變位點
2討論
2.1多巴反應性肌張力障礙的臨床特點
DRD屬于一種遺傳性錐體外系疾病,是由于多巴胺合成不足導致紋狀體功能障礙[2],絕大多數在兒童及青年期起病,具有不完全外顯率和高變異性的特點。通常的表型為早發孤立性肌張力障礙,主要發生在下肢,癥狀具有晝夜波動性,對低劑量左旋多巴反應劇烈而持續[3],亦稱Segawa病。典型的臨床表現為雙下肢姿勢異常,會出現尖足行走或馬蹄內翻足。疾病癥狀的波動性除晨輕暮重表現,有些在疲勞或感染情況下加重,在休息或睡眠后減輕或消失。非典型臨床特征包括步態蹣跚、全身性肌張力減退和近端肢體無力。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焦慮、抑郁及強迫癥等非運動癥狀也應歸為GCH1缺乏引起的臨床表現,因其缺乏導致四氫生物碟呤(BH4)合成不足及5-羥色胺低水平,引起相關精神癥狀[4]。治療方面,外國一項研究將DRD患者步態、姿勢等參數量化,根據參數定量分析左旋多巴治療后效果,結果顯示下肢運動參數幾乎全部得到明顯改善,提示左旋多巴劑量個體化治療效果顯著[5]。據統計,DRD在國內外發病率不高,約為5/1000萬,因常有報道如腱反射亢進、踝關節陣攣等患者被誤認為腦癱,故其患病率高于發病率,需注意鑒別。本病例為學齡前期患兒,以雙下肢走路姿勢異常起病,表現為步態不穩、動作笨拙,癥狀有晨輕暮重特點,患兒病史偏長,但予以美多芭治療后臨床癥狀很快恢復且無運動并發癥,符合經典型DRD的表現。
2.2 GCH1基因突變形式
GCH1基因位于人類第14號染色體上(14q22.1-22.2),包含6個外顯子及2個內含子。DRD遺傳方式分為常染色體隱性遺傳(AR-DRD)和常染色體顯性遺傳(AD-DRD)兩種。常染色體顯性遺傳DRD主要由三磷酸鳥苷環化水解酶1基因缺陷引起,為臨床典型病例的50%~60%,而隱性遺傳主要由酪氨酸羥化酶(TH)基因缺陷引起[6]。GCH1基因編碼的三磷酸鳥苷環化水解酶1是參與BH4合成的關鍵酶,而BH4是參與多巴胺合成過程中的限速酶,BH4的減少最終會導致多巴胺等神經遞質的減少甚至缺乏,進而出現一系列臨床癥狀。目前根據國內外文獻描述,共發現GCH1基因編碼區的228種突變[7],且其突變率會逐漸升高。DRD的GCH1基因異常包括錯義突變、無義突變、移碼突變和剪切突變。約15%的GCH1基因檢測陰性的患者可能存在深部內含子突變異常,或尚未明確的基因突變形式[8]。既往研究報道顯示,大部分GCH1基因突變集中于編碼蛋白質的外顯子區域,本研究中患兒GCH1基因c.542-2A>T屬于內含子部位的剪切變異,該變異評級為可能致病,目前該位點國外文獻已有收錄,但國內尚未出現相同位點突變報道。
2.3臨床遺傳異質性
有研究表明男性可能在同家系中僅表現為異常基因的攜帶者,而女性則可出現DRD臨床癥狀[9]。國外研究發現通常無癥狀攜帶者GCH1的活性下降至30%~40%,當GCH1的活性下降到正常水平的20%以下會出現相應臨床癥狀。本例患兒及其父親均為GCH1基因內含子相同部位的剪切突變,而家族中其他人員未檢測到基因突變,父親無該病臨床表現,符合該病臨床表現外顯率可能受到性別或年齡的影響[10]。患兒經美多芭治療后臨床癥狀有所好轉,可間接證明其致病性,據ACMG指南關于變異分級評分為可能致病性變異,結合患兒的臨床表現,支持致病證據,推測內含子剪切位點突變導致成熟RNA發生變異致翻譯的多肽鏈結構異常而致病。總之,DRD患兒的臨床表現復雜多樣,在診斷不明的前提下盡早完善基因檢測,可以有效避免漏診誤診,或可檢測GCH1的活性判斷干預時間及治療效果,有效改善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