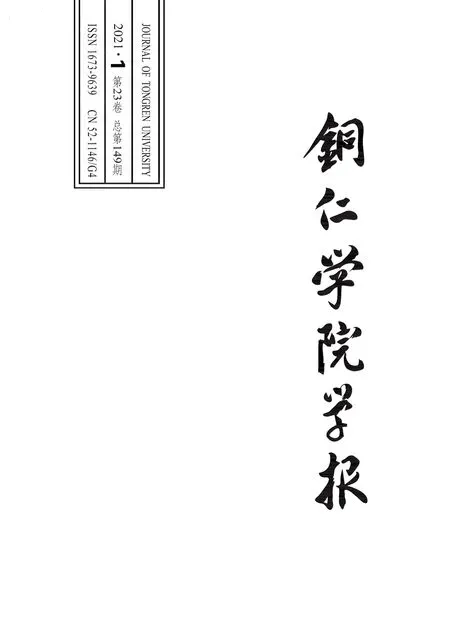胡聲與漢韻——音樂史視域下的中古琵琶文學
吳夢雅
(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文學系,北京 102488 )
琵琶興盛于隋唐,其時有四弦琵琶、五弦琵琶、直項琵琶、曲項琵琶等多種樣式。在此之前,魏晉南北朝是琵琶定型的關鍵時期,此時琵琶的音箱、形制還沒有完全固定下來,面板的大小、音箱的厚度和形狀,琵琶頸的長度和寬度,琵琶項的曲直、出音孔的數目和形狀等等,都是比較自由的。據《中國古代琵琶的“相”與“品”》一文統計,其音箱形狀主要有大梨形、小梨形、瘦梨形等等[1],琵琶弦數目有四弦和五弦,琵琶項有曲項和直項。這也說明,早期“琵琶”是某一大類樂器的統稱,而非特指一種樂器。以地域劃分,當時的琵琶主要有北朝琵琶和南朝琵琶。
北朝的琵琶的主要特點是:梨形或近梨形的音箱(見圖 1)、四弦或五弦、曲項或直項不定,它是在戰火中進入到北朝的。據史料記載,北魏滅北燕馮氏政權后,西域諸國樂器進入北魏的宮廷,成為北魏樂署的重要成員。由于當時戰爭頻繁,北魏宮廷又缺乏音樂專才,琵琶進入北魏樂署后,并沒有立即綻放異彩。
與之相對,南朝也有頗為流行的彈撥樂器——阮咸琵琶。南朝士大夫們優游卒歲,沉浸在與山水相伴的文藝生活中。這種生活自然不會缺少音樂的點綴。善彈琵琶的士大夫們被時人視為文藝兼修的通才。但細究形制,流行于南朝貴族之間的阮咸琵琶,與北朝的琵琶大相徑庭。到了唐代,為了便于區分兩者,唐人將北朝琵琶仍稱琵琶,將南朝琵琶改稱“阮”,或“阮咸”:
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弦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2]
阮咸的外形雖與唐琵琶相似,但其音箱為圓形,音色清亮高雅。南朝的琵琶與北朝的琵琶在形制、音色方面如此不同,卻都被叫作琵琶,是因為其演奏手法的相似。琵琶在劉熙《釋名》中被解釋為“推手前曰枇,引手卻曰杷”,[3](現代琵琶的演奏手型,仍然是以“枇”“杷”為基礎,即以食指彈、大指挑為右手的基本手型。)

圖1 伎樂天,北魏,麥積山石窟七八窟,《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18
南朝琵琶與北朝琵琶雖然演奏手法相似,其樂器特點、音樂功能都是極不相同的。具體而言,南朝琵琶(阮)的出現較早于北朝琵琶;南朝琵琶更多與箏、笛等配合,北朝琵琶更喜好與鼓、鈸等樂器配合;南朝琵琶音色亮雅,而北朝琵琶鏗鏘有力;更重要的是,從樂器的功能來說,南朝琵琶多為歌唱伴奏,北朝琵琶多為舞容伴奏,下面將分條論述。
一、出現時間與音樂風格的不同
南朝琵琶(阮)出現在秦漢時期,但以此演奏魏晉時期的新音樂,是在曹魏時期。并且,因為“新聲”的出現,南朝琵琶開始嶄露頭角,《晉書》記載:“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為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為十三曲。”[4]716漢代舊曲已經初具規模了,不但有相和的絲竹,亦有掌管節奏的樂工,并由掌節奏者歌唱。樂工們一面整理漢代舊曲,一面造新聲:“案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
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4]716(魏晉新聲較漢代舊曲,樂隊分工更加科學。漢代舊曲“執節者歌”,而魏晉新聲“擊節”者只是唱和,“清歌”另有專人負責,主唱者不主節奏。)包含琵琶樂的魏晉新聲涵蓋了三個層面:一是新的曲調,二是新的歌辭,三是新的律呂。
新的曲調自不必說,這里的器樂都是為徒歌伴奏的,徒歌來自民間的口耳相傳,新曲調的產生,是自然的事情。而新的歌辭,乃是由于曹氏父子對音樂的重視,于是文士們跟隨其后,創作出許多可伴管弦的歌辭。“及削平劉表,始獲杜夔,揚鼙總干,式遵前紀。三祖紛綸,咸工篇什,聲歌雖有損益,愛玩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詠神靈,贊揚來饗。”[4]676
新的律呂,不是指新音階或新調式的產生,是指重新校定十二律的音高。這部分工作主要是由荀勖完成的。武帝泰始九年,荀勖發現由于歷史的遷變,當時的度量工具與古代所用的不同,如此勢必造成音高上的誤差,于是荀勖依《周禮》記載重造度量工具,并以此造新的定音工具:銅鐘。“荀勖造新鐘律,與古器諧韻,時人稱其精密。”[4]491在這樣濃厚的音樂氛圍下,阮可以演奏的曲調更多,其音律更加準確,在樂隊中的分工也更加明確,因此漸漸流行開來,并在其后的南朝,成為士大夫們標示風骨的樂器。
北朝的琵琶,是由西域諸國傳進來的樂器。其傳播的渠道有兩種:一種是和平的方式,如聯姻、貿易等等,如北周迎娶皇后阿史那氏,隨行有蘇祗婆這樣的琵琶樂手;一種是戰爭的方式,“世祖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擇而存之。后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于樂署。”[5]2828在這兩種力量的助益下,北魏的樂舞景象為之豐富。然而,北魏雖然得到了許多樂器、各地曲調,距離融合各地音樂、形成新音樂仍然有很長的一段路。北魏的音樂制度建立緩慢,主要是因為帝王們忙于征戰,政治局面并不安定。“既初撥亂,未遑創改,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5]2827同時,北魏初期的帝王們大多缺少對音樂的興趣:“諸帝意在經營,不以聲律為務,古樂音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5]2828并且,撥亂時期的北魏也缺少音樂人才:“時司樂上書,典章有闕,求集中秘群官議定其事,并訪吏民,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修廣器數,甄立名品,以諧八音。詔‘可’。雖經眾議,于時卒無洞曉聲律者,樂部不能立,其事彌缺。”[5]2828這些因素都使得北魏音樂制度一直沒有完備。即便如此,北魏樂署仍舊擁有著來自多民族的、各個地域的音樂,其中,來自西域的琵琶數量最多,有七十余件。說明北魏對西域音樂,尤其是琵琶,是完全接納并欣賞的,“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樂。金石羽旄之飾,為壯麗于往時矣。”[5]2828-2829這為后來北朝琵琶音樂的發展定下了基調。
北周時,樂工蘇祗婆入周武帝宮廷,以高超的琵琶演奏技巧為周武帝賞識。北周亡后,蘇祗婆入隋,更以龜茲調式為異域新聲:
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祗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商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鐘、太簇、林鐘、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捻琵琶,弦柱相飲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6]345-346
與南朝荀勖所作的音律改革不同,蘇祗婆引入了新的音階。此時的中原音樂已經有雅樂音階和清樂音階,蘇祗婆的新音調帶來了新的調式和新的音樂風格。①于是,北朝琵琶開始有了系統的音樂理論基礎。與以往僅存其器的狀況相比,這時候的北朝琵琶才開始了樂理與樂曲并行的局面。而更多的曲調的出現,則有待于其后的唐代樂師們。
就演奏風格而言,南朝琵琶與北朝琵琶有明顯的差異。根據《隋書·音樂志》的記載,南朝琵琶是用于演奏絲竹之樂的,因此與之搭配演奏的樂器都是箏、笛等;而北朝琵琶是多與鼓、鈸等打擊樂器配合。就音色而言,南朝琵琶清澈圓潤,而北朝琵琶聲音高亢、穿透力強。唐時,南朝琵琶已經更名為阮,白居易曾形容阮的音色:
掩抑復凄清,非琴不是箏。還彈樂府曲,別占阮家名。古調何人識,初聞滿座驚。落盤珠歷歷,搖珮玉琤琤。似勸杯中物,如含林下情。時移音律改,豈是昔時聲。(《和令狐仆射〈小飲聽阮咸〉》)[7]
“落盤珠歷歷”是撥片快速彈挑帶來的聽覺感受,“搖珮玉琤琤”說明阮的音色清澈溫潤,而北朝梨形音箱的琵琶音色則激烈得多。唐人詩云:
渾成紫檀金屑文,作得琵琶聲入云。胡地迢迢三萬里,那堪馬上送明君。(《涼州詞》)[8]
“聲入云”說明其聲高亢、穿透力強,這正是北朝琵琶的音色。
二、音樂功能不同:為歌唱伴奏和為舞容伴奏
(一)南朝琵琶的音樂功能:為詩即興吟唱伴奏
除了音樂風格的不同,南朝琵琶和北朝琵琶的功能也有很大區別。南朝琵琶經常是為聲樂伴奏的,聲樂的音樂部分即魏晉時代開始出現的“新聲”,聲樂的文字部分多是流行于民間的曲辭,或是文人創作的歌詩。在南朝,能為琵琶彈奏“新聲”,是彰明才藝而又不失身份的事情,劉宋時代的范曄因為有這項才藝,被宋文帝屢屢暗示,希望他彈奏一曲:“(范曄)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偽若不曉,終不肯為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止弦。”[9]從這段史料可以看出,南朝琵琶是歌唱時絕佳的伴奏樂器,而范曄無視宋文帝的暗示,姿態倨傲,而“上歌既畢,曄亦止弦”,說明歌止弦亦止的伴奏法是反常的,是范曄為不愿配合伴奏的姿態,正常的伴奏應當是歌唱結束后,琵琶的樂音在其后慢慢結束。
那么,魏晉南北朝的士大夫,是以怎樣的曲譜來唱著詩作、并以琵琶伴奏的?何以后世并不聞其譜呢?筆者認為,與民族音樂中以骨譜記音的習慣有關。骨譜的特點是不完全呈現完整的曲調,只記載其中的主要音符,更多的細節音符和演奏技巧,在于樂工的口傳心授,這是中國民族音樂的一個特點,好處是可以由演奏者或演唱者自由發揮②,弊端是過于依賴面對面的傳授,曲調難以廣泛流傳。當時有樂工間流傳的譜子,應當是在演奏中總結出來的、較為簡潔的骨譜。既然譜子不必示于大眾,只在樂工之間流傳,當時的記譜一定是極其簡略、隨意的。再加上戰火,當時譜子便難以流傳至今了。
骨譜是在演奏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業已成熟的曲調,筆者認為,當時還有一種器樂伴奏方式——無譜即興伴奏,上文所引范曄為宋文帝歌唱伴奏,即是一例。即興伴奏,是指按照歌者的即興演唱,以琵琶伴奏。筆者大膽設想,當時人們的即興演唱,是根據朗誦聲調的高低變化,形成一種介于吟誦和歌唱之間的方式——吟唱。若以現代普通話衡量,平上去入四聲調自然沒有多少變化,念出來難以形成復雜的曲調,但中古音聲調繁多,從誦讀過渡到吟唱,是可以形成較動聽的旋律的。這一猜想并不是憑空的,現今仍舊有以方言吟唱詩的習慣,趙元任先生曾就家鄉常州孩童的吟唱,整理出了若干譜子。[10]當然,這只能說明吟唱的存在,并不能說明南朝有以琵琶為詩歌吟唱伴奏的現象。筆者的這一猜想,當需要更多的歷史文本的佐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于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11]700
《世說新語》言王敦“語音亦楚”(余嘉錫先生認為,此處“楚”語指的是齊魯間的地方語言),“語音亦楚”一方面陳述了王敦的口音,另一方面,也與下文所說的不擅長“伎藝事”有因果聯系:當時朝臣都懂得一些樂器,而王敦由于口音仍舊是齊魯間的方音,才使得他不會演奏流行的絲竹樂器,由此可見,絲竹之樂與方音,是有一定關系的。不過,既然齊魯之音被譏為“楚”音,那么,正音應當是哪一種呢?《晉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袁宏字彥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勖,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淸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郞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4]2391
謝尚對袁宏的吟誦極為贊賞,不僅僅是因為他的辭藻,更因其誦念清會動聽。袁宏是陳郡陽夏人,父親為臨汝令,屬吳地。袁宏所念,當是洛陽音與吳語的結合,可見,在南朝,洛陽音與吳語的結合體正是當時所尊的口音。袁宏尚未將吟詠發展到歌唱,就已經如此動聽,吸引了愛好音律的謝尚駐足良久,可知吟詠已經具備了基本的旋律性,可以作為唱的基礎。
如果說以上兩則材料還不夠明確,那么《舊唐書》中一段記載則可以說明南朝音樂與說話聲調的密切聯系:
自長安已后,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轉缺,能合于管弦者,唯《明君》《楊伴》(《通典》作?《楊叛》?)《驍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等八曲。舊樂章多或數百言,武太后時,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傳二十六言,就之訛失,與吳音轉遠。劉貺以為宜取吳人使之傳習。以問歌工李郎子,李郎子北人,聲調已失,云學于俞才生。才生,江都人也。今郎子逃,清樂之歌闕焉。[12]
由于樂工不能正確掌握歌辭念法,使得舊的樂章歌曲大都不傳,而要解決這一問題,惟有讓樂工學習吳音。這就很能說明,歌辭的口音與聲調對歌曲的旋律是有決定的意義的,正由于此,唯一掌握聲調口吻的李郎子出逃后,清樂歌曲再不能演奏了。
宋文帝欣賞范曄的音樂才能,而范曄卻不情愿為宋文帝伴奏,這說明對士族而言,擅彈琵琶是可以自矜自許的一項重要才能,其演奏姿態可以彰示士人的風骨,而不僅僅是炫耀技法。《世說新語》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腳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11]734
這段記載有另一種版本:“堅石挈腳枕琵琶,有天際想。”[11]734關于“企腳”“挈腳”的具體動作,諸家解釋不一。一種意見認為是垂足而坐的姿態。但是,垂足而坐應當是有胡床等坐具,胡床在當時是新式坐具,如有使用,一般會點明(如下引謝尚在市中佛國門樓上彈琵琶時,便點明其坐具為胡床),而這里并沒有說明謝尚所坐的是胡床,故垂足而坐的解釋不取;筆者傾向于將“企腳”“挈腳”解釋為翹起足尖。從“挈腳枕琵琶”的文本來看,“枕琵琶”似乎以琵琶為枕,但首先,謝尚作為愛音樂之人,很難想象他會將脆弱的樂器當做枕頭,另外,提起腳枕著樂器躺著的姿態,實在怪模怪樣,難以稱作“有天際想”。因此,“枕琵琶”應當是以彈奏者身體的某個部位,為琵琶作枕。此處以琵琶模擬人,人類的頸部既然需要枕頭為支撐,琵琶長頸,亦需要“枕”。以彈奏姿態而言,琵琶頸部枕于左腿,是需要左腿稍微高于右腿的,在席地而坐的姿勢中,為了使左腿側起,需要一個支撐點,這個支撐點就是后腳跟,而當后腳跟發力支撐時,腳尖會不自覺翹起,形成“挈腳”“企腳”的樣子。
但是,謝尚為何要將琵琶頸部枕于腿上呢?正常的盤腿姿態不能滿足演奏么?這就涉及到了左右手演奏的問題。魏晉時候的阮,還不是豎直著演奏的,而是橫抱或者斜抱在懷中的(見圖 2),右手彈奏,左手按弦,但由于是橫(斜)抱,左手既承擔著按弦、換音位的職責,又要承擔一部分樂器的重量,并不輕松。謝尚的“企腳”“挈腳”,以演奏姿態來說,應當是右腿仍處于盤的姿勢,左腿側起,將琵琶頸部置于左腿膝蓋前后的位置上,此時以左腳后跟發力以掌控平衡,左腳后跟翹起。這一演奏姿勢將左手解放出來,更加自如地演奏。這才有了“天際真人”的自由揮灑狀態。

圖2 《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圖》之《阮咸圖》,南京西善橋劉宋大墓壁畫
關于謝尚的琵琶演奏,《樂府詩集》中還有一段記載:“謝尚為鎮西將軍,嘗著紫羅襦,據胡床,在市中佛國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市人不知其三公也。”[13]這里謝尚不再是盤腿而坐了,應當是垂足坐,如果依舊橫抱琵琶,琵琶頸部就失去了力度支撐,因此,筆者推測,謝尚已經開始嘗試了豎抱彈奏姿態了。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首先,南朝琵琶的音樂功能之一是為詩的即興吟唱伴奏,這一吟唱,是從南朝所用語言的聲調添加音符、形成簡單旋律而來的。由于這是依據說話聲調的即興吟唱行為,因此不需要曲譜,但需要琵琶伴奏者具有聽音、找音能力。好的琵琶伴奏,可以為詩歌吟唱定節奏、旋律,是伴奏者音樂才華的體現,因此,南朝士大夫以善彈琵琶為傲;其次,南朝琵琶的彈奏姿態,仍然是橫抱或斜抱姿態,這一姿態不利于解放左手,但當時的演奏者已經開始探索解放左手的方式,如謝尚以側起的左腿為支撐,將琵琶頸部枕于膝蓋附近,使左手免于承擔一部分樂器的重量,便于彈奏。并且,由于胡床的使用,南朝時可能已經開始嘗試阮咸琵琶的豎抱彈奏。
(二)北朝琵琶的音樂功能:為騰躍旋轉的舞蹈伴奏
北朝則多以琵琶為舞蹈作伴奏,音樂的首要作用就是為舞蹈提供恰當的音調和節奏。《魏書·樂志》說:“凡音樂以舞為主,故干戈羽籥,禮亦無別,但依舊為文舞、武舞而已。”[5]2842因此,北朝吸收了大量的其他民族的舞蹈。如天竺樂與康國樂:
天竺(樂)者,起自張重華據有涼州,重四譯來貢男伎,《天竺》即其樂焉。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6]379
康國(樂),起自周武帝娉北狄為后,得其所獲西戎伎,因其聲。歌曲有《戢殿農和正》,舞曲有《賀蘭缽鼻始》《末奚波地》《農惠缽鼻始》《前拔地惠地》等四曲。[6]379
北朝琵琶是為了適應舞蹈而演奏的,北朝舞蹈,既有本族的舞蹈,更多是外來舞蹈:西域諸國如龜茲、安國、康國、疏勒而來的舞蹈,扶南、天竺等南方國家而來的舞蹈。以龜茲舞蹈為例,其舞容生動而明快,頭部動作有撼頭、弄目,手部動作有彈指、抃等等,其腳步動作有快速騰躍、旋轉,為了適應多樣的舞蹈動作和快速的舞蹈節奏,舞蹈的伴奏音樂也須是“急管繁弦”式的。唐詩中對西域舞蹈的描述是:
胡騰身是涼州兒,肌膚如玉鼻如錐。桐布輕衫前后卷,葡萄長帶一邊垂。帳前跪作本音語,拾襟攪袖為君舞。安西舊牧收淚看,洛下詞人抄曲與。揚眉動目踏花氈,紅汗交流珠帽偏。醉卻東傾又西倒,雙靴柔弱滿燈前。環行急蹴皆應節,反手叉腰如卻月。絲桐忽奏一曲終,嗚嗚畫角城頭發。胡騰兒,胡騰兒,故鄉路斷知不知。[14]
從此詩來看,舞曲節奏明快,結束時亦有突然收煞之感,以西方樂理言,其曲調當多有八分音符乃至十六分音符、三十二分音符,可見北朝琵琶音樂多是此類快節奏的舞曲,但是,其演奏之快,并不為了炫耀技術,而是為了與花樣繁多、騰躍優美的舞蹈相合。
三、南北朝的琵琶交流
(一)南朝琵琶進入北朝
南朝琵琶與北朝琵琶,因南朝與北朝的對峙,以及兩地審美的差異等因素,在南北朝時期一直是各自為政的。不過,史書亦記載了幾次南北朝的琵琶交流,最著名的一次,是北魏太武帝于兩軍陣前向南朝借樂器,太武帝率軍于戲馬臺,對南朝形成軍事上的威脅,在此次對峙中,南北朝交換了許多特產名物,北朝向南朝送了各類鹽、胡鼓,南朝則向北朝送了酒、柑橘及各色樂器,“太武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箏、笛等器及棋子。”[15]太武帝就南朝借樂器,說明北魏帝王雖然對音樂不大感興趣,但希望以更多的樂器、樂工充實樂署。這不僅是由于音樂的娛情功能,也是因為音樂所具有的政治意義:中原雅樂代表的是正統皇權,北魏志在一統,必然會對中原雅樂感興趣。因此,北魏帝王們在征戰過程中,總是注意帶回當地的音樂:“初,高祖討淮、漢,世宗定壽春,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荊楚四聲,總謂《清商》。至于殿庭饗宴兼奏之。”[5]2843“自中原喪亂,晉室播蕩,永嘉已后,舊章湮沒。太武皇帝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相傳,間有施用。”[5]2841
(二)北朝琵琶進入南朝
北朝的琵琶亦曾經進入南朝宮廷演奏,如前所述,北朝琵琶形制尚未統一,出現在北朝壁畫、石刻中的琵琶,音箱形狀、琵琶頸的長度等等,并不一致。其中有一種曲項琵琶,亦是從西域諸國傳入的,與直項琵琶相比,曲項琵琶的弦的張力更強,因此,惟有將項彎曲,才不至于發生跳軸的現象。③曲項琵琶進入南朝,正逢蕭梁王朝政治動蕩,梁武帝在侯景之亂中已崩于凈居殿,簡文帝在風雨飄搖中登上帝位,然亦時時在侯景的威脅下為政,終于被侯景殺害,正是在此時,曲項琵琶出現在了蕭梁的宮廷中:“于是并赍酒肴、曲項琵琶,與帝飲。帝知不免,乃盡酣,曰:‘不圖為樂一至于斯!’”[16]曲項琵琶在此處的功能是助酒興。由于曲項琵琶的音色是鏗鏘而壯麗的,詩歌風格“輕艷”的簡文帝不大可能喜好這種音樂風格,“不圖為樂一至于斯”不是贊嘆而是嘲諷:此時的宮廷已經不是自家的天下,助酒興的樂器與演奏的曲調風格,都是自己無法選擇的,正如身世命運落入他人之手,榮辱被他人操縱著。北朝琵琶在簡文帝的悲涼際遇中,代表著來自北方的侯景的權力,也在無意中宣示著,北朝琵琶正式進入南朝士族的音樂視野中。
四、唐琵琶的出現
南朝琵琶與北朝琵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曾共用一名,到了唐代,南朝琵琶短暫消失了一段時間后重新問世,更名為阮,北朝琵琶則進一步成為唐琵琶,在唐代音樂、舞蹈領域都發揮著主要作用,這是就形制而言。具體到曲調,由于唐琵琶的形制與史料記載的以及石窟藝術中的北朝琵琶形制更為接近,容易產生唐琵琶樂即是北朝琵琶樂的延伸與發展的印象。任中敏指出,這種“琵琶所到,必為胡聲”的觀點是有違音樂發展歷史的客觀事實的,“惟琵琶之傳入中國,早在漢代,向來廣泛使用,初不以奏胡樂為限;久之,琵琶遂有胡制、漢制及二者兼制之分。無論純粹胡樂或半胡化之西涼樂,或摻雜若干胡樂成分之法曲,甚至全無胡樂成分之清商樂內,皆可用琵琶伴奏。……近人以為琵琶所到,必為胡聲,殊非事實,不可不辨。”[17]30
產生“琵琶所到,必為胡聲”這一刻板印象的原因,一是唐代琵琶的形制承北朝琵琶而來,二是唐人琵琶詩往往強調琵琶渾厚有力的演奏和異域音樂風格,這更加給人以唐琵琶樂完全承襲自北朝琵琶樂的印象了。比如:
彎彎月出掛城頭,城頭月出照涼州。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琵琶一曲腸堪斷,風蕭蕭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別來三五春。花門樓前見秋草,豈能貧賤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幾回,斗酒相逢須醉倒。(《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18]1220
黃云隴底白雪飛,未得報恩不能歸。遼東小婦年十五,慣彈琵琶解歌舞。今為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古意》)[18]602
平明船載管兒行,盡日聽彈無限曲。曲名?無限?知者鮮,霓裳羽衣偏宛轉。涼州大遍最豪嘈,六幺散序多籠撚。(《琵琶歌》)[18]3066
琵琶聲在異域的廣闊中響起,放眼望去,天地之間不見街市繁華,只見行旅之人匆匆和戍守邊關將士們的冷清壓抑,琵琶高亢的聲響與原本黃云白雪的寂寞構成沖突,形成獨有的壯闊凄清之美,這正是唐詩魅力的來源。正因為唐詩中的琵琶多以演奏胡地音聲的形象出現,人們容易產生“琵琶聲中盡是胡聲”的印象。任半塘先生在《教坊記箋訂》中多次辨明這一點:“本編對于諸曲所以分判清、胡之意,……而衹在于著明歷史事實,示與風行之胡樂同時,固有所謂‘華夏正聲’者,依然存在于唐代朝野之間,殊不應掩沒耳。”[19]14“龜茲樂與中國樂,必有一甚長時間并存并行于中國。”[19]151任半塘先生此論,根據的是音樂流變的規律:胡音聲不可能完全取代古代中國的本土音樂,唐代琵琶樂,應當既演奏北朝琵琶樂,也演奏南朝琵琶樂,既有外來曲調,亦有古代中國本土的曲調。從音樂文獻中亦可以找到印證此論點的內容。北魏舞蹈《火鳳辭》入唐后為胡部音樂,多用琵琶、箏彈奏。“胡樂及道曲皆有《火鳳》。分屬林鐘羽、黃鐘羽、黃鐘宮三音調。促拍者名《急火鳳》,多入琵琶與箏,初唐用琵琶尤盛。盛唐《火鳳》在胡部中甚突出。”[17]155其辭有“佳人靚晚妝,清唱動蘭房。影入含風扇,聲飛照日梁。嬌嚬眉際斂,逸韻口中香。自有橫陳分,應憐秋夜長。”[17]155這是唐琵琶樂中來自北朝琵琶樂的部分,而來自南朝琵琶樂的曲調,亦有相當的文獻佐證,《樂府詩集》記載:“后豫章王北宅后堂集會,文季與淵并(喜)〔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為《明君曲》。”(《王昭君》曲名版本眾多,有《昭君怨》《明君詞》等。)[20]776其曲辭有琴曲、石崇所作等版本,《玉臺新詠》載石崇所作:“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后世人,遠嫁難為情。”[21]唐以琵琶或五弦琵琶演奏,其辭有“玉關春色晚,金河路幾千。琴悲桂條上,笛怨柳花前。霧掩臨妝月,風驚入鬢蟬。緘書待還使,淚盡白云天。”[17]144-145因此,雖然從形制角度來說,唐琵琶更接近于北朝琵琶,但就樂調和歌辭而言,唐代琵琶樂所承襲的,是南朝琵琶樂與北朝琵琶樂兩者之結合,而非北朝琵琶樂一種。
注釋:
① 這并不是說在龜茲樂或蘇祗婆新調式傳入以前,中原音樂的調式乏味難陳,如此又過分夸大了二者對中國琵琶樂的影響了。林謙三就誤以為龜茲樂入中原以前,“中國古時一均之中之七音,其宮聲以外者不以為調首,因而調與宮調不外是同意語,但其后宮聲以外的六聲都可以為調首而成為調了。那種思想之被涵養了出來的,當是龜茲樂輸入的影響。”丘瓊蓀在《燕樂探微》中則駁斥了林謙三的這一觀點:“在文獻上證明,歷代所用的調絕對不止一調,自漢至隋凡七百年,都有五引,晉、宋、齊三朝反而闕失了宮引。”
② 骨譜在現在的民族器樂和聲樂中,仍有體現,傳統民樂《夕陽簫鼓》,都有多種版本,其曲調、指法都存在一定的差異,其原因在于大致相同的曲調,在不同的樂人手中有不同的演繹方式;以聲樂來說,昆曲所記譜子與昆曲演員實際演唱的曲調相比,常常少很多音符,究其原因,是譜子只記載一些骨干音,演唱者可以在兩個音符之間加上數個墊音,以使唱腔更加圓潤、自然。見孫寶:《何承天〈鼓吹鐃歌〉十五首作年考論》,《歷史文獻研究》2012年第4期。下文所引孫先生的觀點都出自這篇論文,不贅。
③ 詳見丘瓊蓀:《燕樂探微·琵琶·曲項的物理作用》,《燕樂三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3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