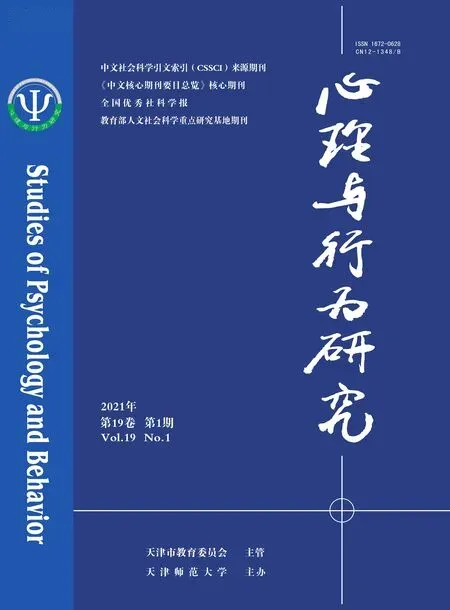母親受教育水平和青少年學業自尊的關系:母親教養方式的中介作用和性別的調節作用 *
劉嘯蒔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心理學系,北京 100084)
1 引言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國家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國國民受教育程度在過去幾十年里得到了顯著提升,尤其是女性的受教育水平(郝娟,2018)。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不僅惠及自身,還可能惠及下一代的成長(林策, 2019; 莊平,1996)。國內研究顯示,兒童的智力(張朝, 于宗富, 2002)、語言(王娟, 鮑玲, 楊洋, 2017)、健康(魯婧頡, 臧旭恒, 2011)都會不同程度地受到母親受教育水平的影響。子女的學業表現更與母親受教育水平有著密切的關聯。諸多研究發現,母親受教育程度對孩子的學業成就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Magnuson, 2007; Tan, Zhou, & Li, 2020; Torvik et al., 2020)。
然而,除了提升客觀的學業成績,青少年時期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建立良好的學業自尊(Fu,Lee, Chen, & Wang, 2020; Pullmann & Allik, 2008)。學業自尊是指個體在學業領域形成的有關自我價值的判斷(丁雪辰, 劉俊升, 李丹, 桑標, 2014)。研究發現,學業自尊與客觀的學習成績存在十分密切的關聯,二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Fu et al.,2020; von Soest, Wichstr?m, & Kvalem, 2016; Zheng,Atherton, Trzesniewski, & Robins, 2020)。形成積極的學業自我評價對于青少年形成良好的學校表現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Fu et al., 2020; Rosenberg,Schooler, Schoenbach, & Rosenberg, 1995)。
那么,母親受教育水平除了可以促進孩子客觀的學業成就外,對孩子主觀的學業自我評價,即學業自尊是否也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最近一項研究發現,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與青少年整體自尊以及其他具體領域性的自尊(如身體、社交自尊)的高低沒有關聯,但父母受教育水平能非常顯著地預測青少年的學業自尊(von Soest et al.,2016)。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聚焦母親受教育水平與青少年學業自尊關系的研究還十分有限,尤其是關于二者關系的具體機制以及不同性別青少年受益于母親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是否不同,鮮有研究見諸報告。因此,本研究擬對上述關系做進一步探究,以豐富母親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如何促進兒童青少年學業發展的研究。
1.1 母親教養方式的中介作用
作為家庭背景特征,母親受教育水平可能并非直接作用于孩子的學業自尊,而是通過某些中介變量起作用。根據Conger 和Donnellan(2007)的家庭投資模型(family investment model),研究者認為較高的受教育水平增強了父母將優質資源投資于子女的能力,而良好的家庭教養方式就是其中一種重要的投資方式(畢馨文, 魏星, 王美萍,陳亮, 張文新, 2018; Harding, Morris, & Hughes,2015)。研究發現,父母受教育水平與其采取何種教養行為有密切關聯,受教育水平較高的父母更傾向于采用溫暖關愛的方式(劉琴, 周世杰, 楊紅君, 楚艷民, 劉利, 2009),積極參與子女的生活(畢馨文等, 2018),更少采取控制的交流方式(Harvey et al., 2016)。而受教育水平較低的父母所擁有的經濟、社會和認知等資源都比較有限,這些均不利于其采取積極的教養行為,他們可能更多采取懲罰的方式去阻止孩子的不良行為,更常拒絕孩子的需要(曹薇, 2012; 林青, 2009)。
在我國文化背景下,學校、家庭教育的核心目標往往包括學習知識,獲得良好學業表現(Liu,Bullock, & Coplan, 2014; Phillipson & Phillipson,2007)。同時,母親在孩子的教育上往往承擔著主要責任(楊小梅, 2019; 鄒盛奇, 伍新春, 黃彬彬, 劉暢, 2019)。因此,假若母親以溫暖接納的方式和孩子互動,有意無意地傳遞相關的教育期望;當青少年體驗到來自母親的關愛后,繼而感知到自我價值被肯定,他們就會更好地內化母親的學業期待,從而形成積極的學業自我評價。已有研究發現,父母積極的教養方式有利于青少年建立學業自尊(周麗芳, 2014; von Soest et al., 2016),而消極的教養方式則會破壞青少年的學業自尊(周麗芳, 2014)。本研究假設,母親積極或消極教養方式在母親受教育水平與學業自尊之間起中介作用;教育水平高可以顯著提升母親積極教養方式,顯著降低母親消極教養方式,進而促進個體的學業自尊。
1.2 性別的調節作用
在個體社會化的過程中,男孩和女孩會發展出與性別規范相適應的行為;受到性別刻板印象和性別角色期望的影響,男孩從小被鼓勵獨立、要有主見、學會自我探索,女孩則被教導要順從、敏感,建立親密、依賴的人際關系(Bem,1981;Milfont & Sibley, 2016)。對于女孩來說,性別角色期待讓女孩比男孩更注重關系和情感體驗。研究發現,一方面,父母的懲罰(Xing, Wang,Zhang, He, & Zhang, 2011)和子女間沖突(Davies &Lindsay, 2004)能夠預測女生而非男生的問題行為。另一方面,良好的親子關系、友誼質量對于女生幸福感的保護性作用也更強(柴喚友, 孫曉軍,牛更楓, 崔曦曦, 連帥磊, 2016)。此外,考慮到中國學校和家庭教育氛圍都非常強調學業成就的重要性(Liu et al., 2014; Phillipson & Phillipson,2007),由此,本研究假設:由于女生更注重關系,情感體驗更為敏感,積極教養方式對女生的學業自尊有更強的正向預測,而消極教養方式對女生有更強的負向預測;也就是說,相比男生,無論是母親積極教養方式,還是母親消極教養方式均可能對女生的學業自尊影響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個體升學進入初中后,學業難度陡增,青少年在這一階段開始面臨明顯的學業競爭與挑戰(潘斌, 張良, 張文新, 紀林芹, 2016;Dotterer, McHale, & Crouter, 2009)。因此,本研究擬以初中生為被試,以便更好地分析影響青少年學業自尊的因素。綜上,本研究建構了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將聚焦母親受教育水平與青少年學業自尊的關系,以及母親教養方式的中介作用和性別的調節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采取方便取樣的方式,從河北廊坊地區選取三所初中,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團體施測。共發放問卷880 份,回收845 份,去掉人口學信息填寫不完整、所選答案有明顯規律可循以及剔除連續5 題及以上未作答的問卷后,最終獲得有效問卷715 份。其中男生350 名(48.95%),女生365 名(51.05%);初一320 名,初二252 名,初三143 名。被試平均年齡為13.75±0.76 歲。
2.2 研究工具
2.2.1 母親受教育水平
由初中生來報告母親的文化程度。參考以往研究(畢馨文等, 2018; 張朝, 于宗富, 2002),采用4 點計分,1 為小學及以下,2 為初中,3 為高中(包括中專及職校),4 為本科(包括大專及以上)。
2.2.2 母親教養方式
教養方式調查采用了由岳冬梅、李鳴杲、金魁和和丁寶坤(1993)修訂的父母養育方式調查問卷,共66 題,采用4 點計分。其中母親教養方式的測量共五個維度:母親情感溫暖、理解(以下簡稱“母親情感溫暖”),母親過分干涉、過分保護(以下簡稱“母親過分干涉和保護”),母親拒絕、否認(以下簡稱“母親拒絕”),母親懲罰、嚴厲(以下簡稱“母親懲罰”),以及母親對被試的偏愛程度(由于研究對象多為獨生子女,故偏愛維度在本研究中不作考慮)。各維度得分越高,表示相應的教養方式越強。本研究中,前四個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為0.90、0.70、0.81、0.86。
2.2.3 學業自尊
兒童自尊量表由魏運華(1997)編制而成。測量對象為10 到15 歲的少年兒童。根據本研究實際需要,采用成就感維度測量被試的學業自尊水平。該維度共4 個題目,例如“每次作業我都能出色地完成”、“我對自己的功課感到自豪”。采用5 點計分,所有項目得分加總后的平均分代表個體學業自尊水平,分數越高則學業自尊越高。以往研究表明該量表具有較好的信效度(孫鳳華, 高凌飚, 2007; 徐鳳嬌, 袁群, 鄧瑞姣, 2010)。本研究中,該維度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66。
2.3 數據處理
采用SPSS20.0 對數據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相關分析和有調節的中介分析。在進行統計分析之前,使用Harman 單因素檢驗法對研究問卷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如果得到多個因子,且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沒有超過40%,則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問題不嚴重。統計結果發現,特征值大于1 的公因子有12 個,且第一個因子只解釋了方差的21%。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3 結果
3.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以性別為自變量,各研究變量為因變量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表明(見表1),母親受教育水平、母親情感溫暖、學業自尊不存在性別差異。母親過分干涉和保護、母親拒絕、母親懲罰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均表現為男生顯著高于女生。
相關分析結果見表2。從表中可以看出,母親受教育水平與母親情感溫暖存在顯著正相關;母親受教育水平與母親拒絕、母親懲罰存在顯著負相關;母親受教育水平與學業自尊存在顯著正相關。青少年的學業自尊與母親情感溫暖存在顯著正相關,與母親拒絕和母親懲罰存在顯著負相關。由于母親過分干涉和保護與母親受教育水平和學業自尊的相關均不顯著,所以不再進行后續分析。

表 2 各變量之間的相關
3.2 母親受教育水平與青少年學業自尊: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參照溫忠麟和葉寶娟(2014)提出的檢驗方法,考察母親教養方式在母親受教育水平與青少年學業自尊的關系中的中介效應,以及性別對該中介作用的調節效應。首先,將除性別外的所有變量進行標準化處理,以檢驗母親受教育水平對青少年學業自尊(Y)的直接效應。檢驗的回歸方程為Y=c0+c1母親受教育水平+e1(方程一)。結果顯示,母親受教育水平對兒童學業自尊的效應顯著,β=0.19,t=5.05,95% 置信區間為[0.11,0.26],p<0.001。
接下來,分別考察三種母親教養方式(M)的中介作用和性別的調節作用。檢驗方程分別為:M=a0+a1母親受教育水平+e2(方程二)和Y=c0’+c1’母親受教育水平+b1M+b2性別+b3M性別+e3(方程三)。方程二的檢驗結果表明,母親受教育水平對母親溫暖的教養方式效應顯著,β=0.21,t=5.76,95% 置信區間為[0.14, 0.28],p<0.001。此外,母親受教育水平對母親拒絕的教養方式效應顯著,β=-0.08,t=-2.08,95%置信區間為[-0.15, -0.01],p<0.05。母親受教育水平還對母親懲罰的教養方式效應顯著,β=-0.08,t=-2.20,95%置信區間為[-0.15, -0.01],p<0.05。方程三的檢驗結果表明,母親溫暖的教養方式對青少年學業自尊的效應顯著,β=0.40,t=8.42,95%置信區間為[0.30, 0.49],p<0.001;母親溫暖的教養方式與孩子性別的交互作用項對青少年學業自尊的效應顯著,β=-0.16,t=-2.25,95%置信區間為[-0.29, -0.02],p<0.05,此時母親受教育程度對學業自尊的效應仍顯著,β=0.12,t=3.34,95%置信區間為[0.05, 0.19],p<0.01。母親拒絕教養方式對青少年學業自尊的效應顯著,β=-0.28,t=-5.62,95%置信區間為[-0.38, -0.18],p<0.001;母親拒絕的教養方式與孩子性別的交互作用項對青少年學業自尊的效應顯著,β=0.18,t=2.51,95%置信區間為[0.04, 0.32],p<0.05,此時母親受教育程度對學業自尊的效應仍顯著,β=0.17,t=4.75,95%置信區間為[0.10, 0.24],p<0.001。母親懲罰的教養方式對青少年學業自尊的效應顯著,β=-0.26,t=-4.68,95%置信區間為[-0.37, -0.15],p<0.001;母親懲罰的教養方式與孩子性別的交互作用項對青少年學業自尊的效應顯著,β=0.16,t=2.07,95% 置信區間為[0.01, 0.30],p<0.05,此時母親受教育程度對學業自尊的效應仍顯著,β=0.17,t=4.62,95%置信區間為[0.10, 0.24],p<0.001。綜合以上結果,本研究提出的有調節的中介模型得到支持(溫忠麟, 葉寶娟, 2014)。母親受教育水平不僅對青少年學業自尊有直接預測作用,同時還通過母親教養方式的中介作用預測學業自尊,且該中介作用的后半路徑受到性別的調節。
為了進一步理解調節作用的本質,采用Aiken 和West(1991)的作法,分別考察針對男孩和女孩不同的教養方式對學業自尊的預測效應。簡單斜率分析的結果如圖1、圖2、圖3所示。結果發現,相比男孩(β=0.27,t=5.24,p<0.001),母親溫暖對學業自尊的正向預測作用在女孩(β=0.42,t=8.94,p<0.001)中更強;相比男孩(β=-0.11,t=-2.18,p<0.05),母親拒絕對學業自尊的負向預測作用在女孩(β=-0.30,t=-5.82,p<0.001)中更強;相比男孩(β=-0.12,t=-2.40,p<0.05),母親懲罰對學業自尊的負向預測作用在女孩(β=-0.28,t=-4.93,p<0.001)中更強。

圖 1 性別對母親溫暖和學業自尊的調節作用

圖 2 性別對母親拒絕和學業自尊的調節作用

圖 3 性別對母親懲罰和學業自尊的調節作用
4 討論
4.1 母親受教育水平與青少年學業自尊的關系
Conger 和Donnellan(2007)提出的家庭投資模型認為社會經濟地位主要通過父母對孩子的投資,從而影響兒童的發展。然而,它是一個相對宏觀的理論,模型中每一個要素的內涵都非常豐富,需要研究者細致檢驗每一個關鍵要素之間的關系。而本研究聚焦家庭投資模型中的一個關鍵要素—母親受教育水平對青少年學業自尊的影響。
與以往研究類似(von Soest et al., 2016),本研究發現,母親受教育水平可以更好地促進孩子在學業方面形成主觀積極的自我評價。這可能是由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母親,可能對孩子有更高的教育期望(Augustine, 2017),會更愿意對子女進行更多的教育投資(Harding et al., 2015)。此外,由于受教育水平高的母親相比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個體可能掌握更多問題解決的技能,在幫助孩子面對學業問題時,可以給予更好的建議,這些都會促進孩子的學校表現和學業自我評價。同時,家長對于青少年的心理行為有著重要的榜樣示范作用(寇彧, 王磊, 2003;蘆詠莉, 董奇, 鄒泓,1998)。在教育上取得成功的母親,很可能成為孩子追求成就的榜樣,他們會更認同學習的價值,有更高的成就目標,從而進一步體現在對自身學業的積極評價上。這一結果啟示,應重視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制定保護女性平等接受教育的措施。這不僅有益于女性整體社會地位的提升,還將提升下一代的學業適應,進一步使整體國民素質得到提升。
4.2 母親教養方式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母親溫暖、拒絕、懲罰的教養方式在母親受教育水平和學業自尊之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首先,與以往研究一致(畢馨文等, 2018;Harding et al., 2015),母親受教育水平越高,則積極教養方式越多,消極教養方式越少。通過接受教育,父母可能會學習到更多有利于實施積極教養行為的知識和技能(Harding et al., 2015)。受教育水平高的父母,可能秉持更好的教育理念,以更溫和接納的方式(畢馨文等, 2018),而非嚴厲的懲罰或否定批評的方式(曹薇, 2012;林青,2009)來促進孩子的發展。其次,本研究結果顯示,母親積極溫暖的教養方式會促進孩子形成良好的學業自尊;母親消極的教養方式會破壞學業自尊。這些發現也與以往研究相一致(周麗芳,2014;von Soest et al., 2016)。由于中國父母一般對孩子的學業成就有較高期望(Liu et al., 2014;Phillipson & Phillipson, 2007),溫暖接納的母親可能更傾向給予孩子更多的個人空間,鼓勵其自由探索,并將一些積極的社會目標以平等協商而非強制的方式傳遞給孩子,使孩子在潛移默化中內化家長的學業期望,從而更好地促進孩子形成積極的學業自我評價。而母親拒絕、懲罰等消極教養方式,可能會阻礙交流,造成孩子的逆反,破壞青少年對學業成就的追求,從而形成不良的學業自我評價。
4.3 性別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還檢驗了母親受教育水平通過母親教養方式影響青少年學業自尊的中介過程,是否受到青少年性別的調節。結果表明,性別對于中介作用后半路徑的調節作用顯著。相比男孩,母親積極的教養方式(溫暖接納)對女孩學業自尊的促進作用更大;同時,母親的消極教養方式(拒絕、懲罰)對女孩的破壞作用也更大。這可能是由于,社會對兩性的性別角色期望不同,人們會希望男孩更獨立、有主見,女孩則需要順從、敏感、依賴他人(Bem, 1981;Milfont & Sibley,2016),因而女生對關系中的情緒信息反應也更為敏感。同時,由于母女之間往往有更密切的情感聯結(Diener, Isabella, Behunin, & Wong, 2008),加之母親常會卷入對孩子的教育中(劉春雷, 霍珍珍,梁鑫, 2018)。當母親以積極溫暖方式和女孩交流,相比男孩,女孩更容易感受到母親的引導、贊揚和對她們學業理想的支持,從而對其產生更大的激勵作用。但另一方面,當母親以消極的方式和女孩交流,相比男孩,女孩更容易感受到母親的拒絕和否定,對她們學業成就的不認可更易誘發無能感,從而對其學業自我評價產生更大的破壞作用。
5 結論
(1)母親受教育水平對青少年的學業自尊具有正向預測作用。(2)母親教養方式在母親受教育水平與青少年學業自尊間具有中介作用。(3)性別調節母親教養方式對母親受教育水平與青少年學業自尊中介過程的后半段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