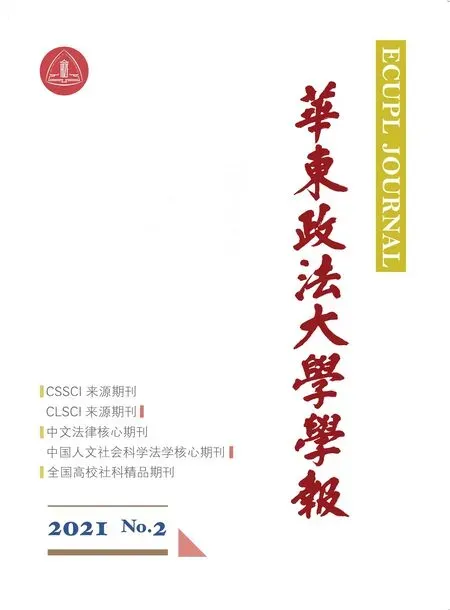盜竊罪量刑規范化問題實證研究
彭文華
一、量刑規范化需要進行階段性分析和效果評估
2014 年1 月1 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頒布實施。《指導意見》對量刑的指導原則、基本方法、常見量刑情節的適用,以及十五種常見罪名的量刑作了具體規定,其目的在于“增強量刑的公開性,實現量刑公正”。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二)(試行)》(以下簡稱“《指導意見(二)》”),又增加了八種常見犯罪的量刑規定。《指導意見》與《指導意見(二)》的出臺,是我國量刑規范化改革的階段性成果。客觀地說,從其淵源來看,《指導意見》與《指導意見(二)》的出臺,在某些方面是受《美國聯邦量刑指南》影響的。
眾所周知,量刑是極其復雜的司法活動,非定罪所能比擬。要想實現量刑公正,離不開專門的量刑機構發揮作用。當初,以弗蘭克爾為代表的美國量刑改革派,在構建量刑改革法案的同時,還提出要設立專職的量刑改革機構,即量刑委員會。量刑委員會與量刑改革法案,是20 世紀中后期美國量刑改革的兩大核心內容。由此,《美國聯邦量刑指南》所確立的量刑模式,又被稱為量刑委員會模式(sentencing commission model)。量刑委員會之所以不可缺少,是因為它具有機構能力,可以制定比任何立法機構都更加精細和具體的經過微調的量刑標準。〔1〕See Michael H. Tonry., Sentencing Reform Impacts, Chapter 5: The Sentencing Commission, 1987, p.46.量刑委員會還行使重要的量刑權力,如為所有非金錢量刑的替代方案包括社區監督、定期監禁、分判和持續監禁制定指南,通過制定量刑準則處理監禁和社區監督之間的選擇,以及對每項判決的推定長度的決定,等等。〔2〕See Marvin E. Frankel & Leonard Orland, “Sentencing Commissions and Guidelines”, 73 Georgetown Law Journal 225, 228(1984).此外,量刑委員會每年至少向國會提交一份指南實施情況的分析報告,并對指南的應用發表一般性政策聲明,還必須要充分理解關于指南的評論和批評,至少需要對它們如何工作有初步的了解。〔3〕See Stephen Breyer, “The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and the Key Compromises Upon Which They Rest”, 17 Hofstra Law Review 1, 6(1988).其中,量刑指南實施的年度報告是對其實踐效果的評估,對于實現量刑均衡與一致以及量刑公正,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我國,傳統上重定罪而輕量刑是有目共睹的。“無論在刑法學習過程中,或在刑法實務上,一向重犯罪論而輕刑罰論的法事實,在司法官考試的試題中,大多以定罪的問題為重點,而甚少涉及科刑的問題,也就難怪在法學教育和法官的司法專業培育中刑罰制裁普遍受到忽視,而虛有其表。”〔4〕林山田:《刑法通論》(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版,第363 頁。我國推進量刑規范化改革,便是突破傳統觀念、重視量刑的體現。然而,由于我國在推進量刑規范化改革時始終未設立專門量刑機構,導致在《指導意見》與《指導意見(二)》頒行后,沒有專門機構就實施情況作出分析和評估,也就無法動態評估兩個指導意見的實踐效果。同時,學界對此也顯然缺乏深入研究。可以說,在量刑規范化改革上,我們還有很多工作需要進一步展開。
盜竊罪是司法實踐中最常見的犯罪之一。《指導意見》對盜竊罪的不同法定刑幅度的量刑起點以及基準刑的確定、親屬相盜的基準刑減輕等作了具體規定。本文無意對盜竊罪的量刑規范化展開全面研究,而是擬對量刑規范化改革最核心的任務之一,即實現量刑均衡與一致加以深入研究。由于不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治安形勢的變化,要想對不同司法管轄區進行量刑均衡與一致的比較,相對來說是比較難的。不過,《指導意見》規定:“對于同一地區同一時期、案情相似的案件,所判處的刑罰應當基本均衡。”這說明對同一地區同一時期、案情相似的案件,還是可以進行比較分析的。本文通過對特定地區一定時期的盜竊罪的裁判文書進行研究,旨在客觀評估《指導意見》頒行后的實踐效果,并對《指導意見》的規定以及刑罰裁量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加以深入分析。
二、樣本概況與相關法律規定
本文的案例樣本來自中國裁判文書網。這些判例的主要法律依據是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指導意見》,以及甲省高級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實施細則》(以下簡稱“《實施細則》”)。由于量刑情節屬于一般性規定,故關于盜竊罪的量刑規定主要涉及量刑起點和基準刑。
(一)樣本概況及其類型化說明
本文以東部某省(以下簡稱“甲省”)某縣級市(以下簡稱“乙市”)人民法院有關盜竊罪的一審判決書為樣本,〔5〕該市經濟較發達,法治意識強,法官隊伍具有一定規模,法律素養整體比較高,故選擇該市法院的判例進行分析較具代表性。樣本覆蓋的是入門級犯罪的量刑情節,不包括數額巨大或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加重量刑情節,即主要以在基礎法定刑幅度內的盜竊罪量刑為研究對象。本文所選擇判例樣本的裁判時間乃2014 年1 月1 日至2020 年8 月27 日期間,乙市人民法院裁定的有關盜竊罪的一審判決書,共檢索到2833 份。其中,盜竊數額巨大(50000 元以上)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判例共97 份,占比約3.42%。基本量刑情節(含數額較大、入戶盜竊、多次盜竊、攜帶兇器盜竊和扒竊)的判例共2736 份,占比約96.58%。從所檢索的案例來看,影響盜竊罪量刑的因素較其他犯罪往往要復雜,主要因為法定的入罪要素較多,給樣本模型帶來多樣化,致使量化分析更為復雜。不過,從量刑均衡與一致的角度來看,選擇量刑情節相同或者相近的犯罪進行比較,還是有其合理性的。
根據刑法規定,盜竊罪的入罪要素包括數額、多次、入戶、攜帶兇器、扒竊。從所檢索的案例來看,攜帶兇器的盜竊相對少見,但其他類型的盜竊均很常見。影響盜竊罪的量刑情節主要表現為自首、立功、坦白、認罪認罰、累犯、前科、取得(被害人)諒解、退賠、達成和解協議、未遂等。在所檢索的判例中,以包括入罪要素在內的所有影響量刑的情節為基礎,按照量刑情節的不同進行劃分,共有70 余種不同量刑情節的判例。其中,數額作為評價盜竊罪定罪與量刑的首要因素,幾乎所有判例都有涉及(只是存在數額多少之別)。分析發現,除了超限的入罪情節(如超過入罪數額、超過入罪次數)外,一般盜竊罪也多少存在犯罪事實外的其他量刑情節。發案率相對較高的盜竊罪,主要集中在數額型盜竊罪、入戶型盜竊罪以及多次型盜竊罪中。
刑法對盜竊罪規定了三個量刑幅度。受定罪情節與量刑情節雙重多樣化影響,盜竊罪相同或相似情節的樣本類型較多,要想將每一種盜竊罪的量刑進行比較分析其實難度是很大的。因此,對本文選擇的判例類型,筆者特做以下說明:(1)本文所選取的有關盜竊罪的判例,均為基礎量刑幅度內的犯罪,即處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的犯罪;(2)本文所選取的盜竊罪判例的類型,涉案數額均在10000 元以下,主要考慮到這類判例占大多數,能為類型化提供足夠的樣本數量;(3)為了減少量刑的影響因素,本文沒有將未成年人犯罪、未遂犯以及共同犯罪等判例納入分析。理由在于,未成年人的不同年齡、未遂中是部分未遂還是全部未遂等,對量刑有不同影響,判例通常對此未加說明,無法進行相對客觀、確切的比較;(4)本文所選擇樣本不完全以數量多少論,而是立足于量刑均衡與一致、量刑公正的比較,選擇具有代表性的樣本類型進行分析,具體包括:①具有坦白情節的數額型盜竊罪;②具有坦白、認罪認罰情節的數額型盜竊罪;③具有坦白、認罪認罰情節的入戶型盜竊罪;④具有坦白、認罪認罰和累犯情節的數額型盜竊罪。需要說明的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2018年以后全面推行,且在刑事訴訟法中得以規定,因而該制度主要體現在2018 年以后的判例中,屬于新近判例。
(二)有關盜竊罪量刑的規定
包括司法解釋和地方司法機關的規定在內,應當說有關量刑及其內容的規定還是不少的。但是,就影響量刑偏差的情況來看,主要涉及的是量刑起點和基準刑。因此,這里主要介紹司法解釋和地方司法機關有關量刑起點和基準刑的規定。
《指導意見》規定:“構成盜竊罪的,可以根據下列不同情形在相應的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1)達到數額較大起點的,兩年內三次盜竊的,入戶盜竊的,攜帶兇器盜竊的,或者扒竊的,可以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指導意見》還規定:“多次盜竊,數額達到較大以上的,以盜竊數額確定量刑起點,盜竊次數可作為調節基準刑的量刑情節;數額未達到較大的,以盜竊次數確定量刑起點,超過三次的次數作為增加刑罰量的事實。”根據甲省高級人民法院出臺的《實施細則》規定,盜竊數額和相關情節應在下列對應的刑罰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其一,入戶盜竊、多次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量刑起點為拘役3 個月;每增加一次作案或者一種情形,增加一個月刑期確定基準刑。其二,盜竊數額達2000 元以上不滿1 萬元的,量刑起點為拘役3 個月。其三,盜竊數額達1000 元,不滿2000 元,并具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二條第(一)至(八)項規定情形之一的,量刑起點為拘役3 個月。根據相關司法解釋以及甲省司法機關的有關規定,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標準,是人民幣2 千元以上不滿5 萬元。
關于基準刑的確定,《指導意見》規定:“在量刑起點的基礎上,可以根據盜竊數額、次數、手段等其他影響犯罪構成的犯罪事實增加刑罰量,確定基準刑。”《指導意見》還具體規定了調節基準刑的方法,以及調整基準刑的14 種具體量刑情節。《實施細則》則對此進行了細化,如規定盜竊數額達到較大金額以上,并具有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或者扒竊等數種情形的,以盜竊數額確定量刑起點,可增加基準刑的20%以下。《實施細則》還對因生活、治病急需而盜竊等情形,規定減少一定比例的基準刑。
三、樣本類型化分析與主要研究發現
(一)樣本類型化分析
1.具有坦白情節的數額型盜竊罪量刑
檢索數額型盜竊罪具有坦白情節的判例共69 份,裁判日期主要在2014—2016 年間。其中,單處罰金的判例27 份,判處拘役的判例29 份,判處拘役緩期執行的13 份。判處拘役以及拘役緩期執行的,均有并處罰金的處罰。具體情況分為三種。(1)在單處罰金的27 份判例中,罰金的數額為1000~2000 元不等,數額最低與最高的分別為2080 元和7780 元。值得注意的是,諸如涉案數額為2080 元等較低的,罰金數額卻為2000 元。(2)在判處拘役的29 份判例中,刑期為2~5 個月不等,并處罰金的數額均為1000 元。(3)在判處拘役緩期執行的13 份判例中,刑期為2~5 個月不等,緩刑考驗期為3~6 個月不等,并處罰金的數額均為1000 元。(參見表1)

表1 具有坦白情節的數額型盜竊罪量刑
2.具有坦白、認罪認罰情節的數額型盜竊罪量刑
檢索數額型盜竊罪具有坦白、認罪認罰情節的判例共47 份,數額最低的為2000 余元,數額最高的為9000 余元。這類判例所判處的刑罰相較具有坦白情節的數額型盜竊罪更為多樣化。其中,單處罰金的判例2 份,判處拘役的判例14 份,判處拘役緩期執行的18 份,判處有期徒刑的10 份,判處有期徒刑緩刑的3 份。判處拘役以及拘役緩期執行、有期徒刑以及有期徒刑緩期執行的,均有并處罰金的處罰。具體情況有四種。(1)單處罰金的2 份判例涉案數額分別為2960 元和3600 元,罰金數額分別為2000 元、1000 元;(2)在判處拘役的14 份判例中,刑期為2~6 個月,并處罰金的數額為1000~2000 元。(3)在判處拘役緩期執行的18 份判例中,刑期為2~5 個月,緩刑考驗期3~6 個月,并處罰金的數額均為1000 元。(4)在判處有期徒刑的10 份判例中,刑期6~8 個月,并處罰金1000~2000 元。(5)在判處有期徒刑緩期執行的3 份判例中,涉案金額分別為6000 元、6000 元和6299 元,刑期分別為7 個月、8 個月、6 個月,緩刑考驗期均為1 年。(參見表2)

表2 具有坦白、認罪認罰情節的數額型盜竊罪量刑表
3.具有坦白、認罪認罰情節的入戶型盜竊罪量刑
入戶型盜竊罪的量刑較為特別。從理論上來看,只要入戶盜竊,通常就成立犯罪,可不受數額限制。根據《指導意見》規定,當盜竊數額未達到較大時,其量刑起點與普通盜竊達到數額較大時一樣。但是,當入戶盜竊達到數額較大時,則要以數額較大作為量刑起點。《實施細則》規定,盜竊數額達到較大以上,以盜竊數額確定量刑起點,并具有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或者扒竊等情形的,可增加基準刑的20%以下。可見,具有坦白、認罪認罰情節的入戶型盜竊罪的量刑,與上述數額型盜竊罪有所不同,需要區分未達到數額較大與達到數額較大兩種不同情形。檢索入戶型盜竊罪具有坦白、認罪認罰情節的判例共20 份。其中,11 份判例的涉案數額在2000 元以下,9 份判例的涉案數額在2000 元以上。在11 份涉案數額在2000 元以下的判例中,5 份判例判處拘役,刑期為2~4 個月,均并處罰金1000 元;6 份判例判處有期徒刑,刑期為6~8 個月,均并處罰金1000 元。在9 份涉案數額在2000元以上的判例中,判處拘役的有2份,刑期分別為3個月和5個月;判處拘役緩期執行的有3份,刑期為4~5 個月,緩刑考驗期為5~6 個月;判處有期徒刑的4 份,刑期為6~8 個月。并處罰金數額為1000~2000 元。(參見表3 和表4)

表3 具有坦白、認罪認罰情節的入戶型盜竊罪涉案數額2000 元以下的量刑

表4 具有坦白、認罪認罰情節的入戶型盜竊罪涉案數額2000 元以上的量刑
4.具有坦白、認罪認罰和累犯情節的數額型盜竊罪
根據《解釋》規定,曾因盜竊受過刑事處罰,“數額較大”的標準可以按照刑法規定的“數額較大”標準的50%確定。這意味著具有累犯情節,盜竊的入罪數額標準可以按照1000 元確定。根據《實施細則》規定,盜竊數額達1000 元,不滿2000 元,并具有《解釋》第二條第(一)至(八)項規定情形之一的,量刑起點為拘役3 個月。同時,《實施細則》規定,數額達到2000 元以上的,則應該以數額較大作為確定量刑起點的依據,其他量刑情節屬于調節基準刑的依據。檢索具有坦白、認罪認罰和累犯情節的數額型盜竊罪判例共16 份。其中,9 份判例的涉案數額在1000~2000 元以下,均判處有期徒刑,刑期為7~9 個月不等,均并處罰金且其數額均為1000 元。7 份判例的涉案數額在2000 元以上,均判處有期徒刑,刑期為7~9 個月不等,均并處罰金且其數額為1000~2000 元不等。(參見表5)

表5 具有坦白、認罪認罰和累犯情節的數額型盜竊罪量刑
(二)主要研究發現
1.多刑種的量刑起點確定問題
根據《刑法》第264 條規定:“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該規定具體涉及四個刑種: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以及罰金。《指導意見》 規定,可以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實施細則》則規定量刑起點為拘役3 個月。問題在于,如果以拘役3 個月為100%的話,那么要想判處管制或者罰金,理論上需要減少基準刑100%以上。這是一個什么概念呢?根據《指導意見》規定,自首可以減少基準刑的40%以下,當庭認罪可以減少基準刑的10%以下,一般立功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取得被害人諒解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換句話說,如果行為人具有自首、當庭認罪、立功和取得被害人諒解四個從輕處罰情節,仍然要判處拘役,不足以判處管制和罰金。這無論如何也是不合理的。可以說,這等于在某種程度上導致管制和罰金兩種刑罰被虛置。可見,在同一法定刑幅度內存在多刑種情形下,如何確定量刑起點對不同刑種適用具有直接影響。
如表1 所示,對于盜竊數額較大并有坦白情節的,不少判例最后判處罰金。如此判罰顯然不符合《指導意見》和《實施細則》的規定。因為,《指導意見》規定在1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拘役中確定量刑起點,《實施細則》則將量刑起點進一步確定為3 個月拘役。雖然有坦白情節,根據《指導意見》可減少基準刑20%以下,很難得出判處罰金的結論。這是否意味著起點刑為罰金就不合理呢?顯然不是的。需要提出的是,《指導意見》和《實施細則》所確定的量刑起點依據是什么?是否科學、合理?為什么量刑起點不能是管制或者罰金?如果在管制或者罰金中確定量刑起點,在具有坦白情節的情形下,判處罰金也就在情理之中。可見,判處罰金盡管不符合《指導意見》和《實施細則》規定,但未必就完全不合理。在罰金也能作為量刑起點的場合,判處罰金就在情理之中。看來,在同一法定刑幅度內存在多刑種,如何確定量刑起點無疑值得探討。
2.關于基準刑的確定與調節問題
分析發現,各地司法機關對《指導意見》規定的基準刑,可能存在理解不確切的現象。根據《指導意見》規定:“根據其他影響犯罪構成的犯罪數額、犯罪次數、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實,在量刑起點的基礎上增加刑罰量確定基準刑”,“根據量刑情節調節基準刑,并綜合考慮全案情況,依法確定宣告刑”。由此可知,基準刑是以量刑起點為基礎,根據犯罪事實來確定的。其實質在于,當基本犯罪事實達到犯罪臨界點的基礎上,通過過限的基本犯罪事實(入罪事實),如超過基本入罪要求的數額、次數、后果等來確定基準刑。可見,基準刑永遠是在量刑起點的基礎上,通過基本犯罪構成事實過限而作增量來確定的。在確定基準刑后,再根據調節基準刑的量刑情節決定宣告刑。因此,基本犯罪事實之內影響量刑的情節,屬于基準刑確定情節;基本犯罪事實之外影響量刑的情節,屬于基準刑調節情節,以及所謂的量刑情節(狹義的)。
然而,《實施細則》似乎對《指導意見》的上述規定未充分理解,乃至于在規定具體的基準刑調節情節時,將確定基準刑的基本犯罪事實情節與調節基準刑的量刑情節混為一談。例如,《實施意見》規定了十種可調節基準刑的情節,如多次盜竊、因盜竊造成嚴重后果、采取破壞性手段盜竊造成公私財產損失等,將之作為調節基準刑的情節。事實上,根據《指導意見》規定,這些情節屬于犯罪構成事實要素,是據以確定基準刑的,而非調節基準刑的量刑情節。將多次盜竊、因盜竊造成嚴重后果等作為調節基準刑的情節,等于將基本犯罪事實之內的影響量刑的情節,與基本犯罪事實之外的影響量刑的情節相混淆,這是不符合《指導意見》規定的。事實上,《實施細則》的規定應當說并無不可,只是在表述上存在一定的問題,從而導致將確定基準刑的情節與調節基準刑的情節混淆。正確的表述應該是:“在確定基準刑時,有下列情節之一的,可以在量刑起點的基礎上增加20%以下……”將基本犯罪事實之內的影響量刑的情節,與基本犯罪事實之外的影響量刑的情節相混淆,會直接影響司法實踐對基準刑的確定和調節,最終影響宣告刑。
3.司法機關對《指導意見》與《實施細則》的貫徹問題
《指導意見》與《實施細則》對量刑起點、基準刑調整、量刑步驟和方法等,都作了具體規定。不過,從司法實踐中的情況來看,司法機關對這些規定似乎貫徹的并不徹底,甚至可以說并沒有較好地遵循《指導意見》與《實施細則》的規定。因為,從所檢索的判例來看,裁判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充分體現《指導意見》與《實施細則》的有關規定。
如前所述,關于盜竊數額較大的量刑起點,《指導意見》規定:“可以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2014 年實施的《實施細則》進一步明確了盜竊數額達2000 元以上不滿1 萬元的,量刑起點為拘役3 個月。入戶盜竊、多次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量刑起點為拘役3 個月。從所檢索的數額型盜竊罪中具有坦白情節的69 份判例來看,有27 份判處罰金,占比約39.13%。如前所述,在量刑起點為3 個月拘役,具有坦白情節并可減少基準刑20%以下的情況下,很難得出判處罰金的結論。在數額型盜竊罪具有坦白、認罪認罰情節的47 份判例中,判處有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緩刑的判例分別為10 份和3 份,占比約27.66%。在量刑起點為3 個月拘役,具有坦白和認罪認罰情節,并可減少基準刑30%以下(根據《指導意見》規定,認罪認罰可減少基準刑10%以下)的情況下,判處3 個月拘役都很難想象,更別提判處有期徒刑。同樣,涉案數額在2000 元以下的入戶型盜竊罪,在具有坦白、認罪認罰情節的情況下,判處有期徒刑也是讓人費解的。涉案數額在2000 元以上的入戶型盜竊罪,入戶作為增加基準刑20%以下的情節,充其量與坦白情節相抵消,在具有認罪認罰情節的情況下,判處有期徒刑也是不可能的。在具有累犯、坦白和認罪認罰情節、數額在2000 元以下的盜竊罪中,判處有期徒刑也是難以讓人置信的。在盜竊數額不足2000 元的情形下,累犯屬于定罪情節,不應二次評價再影響量刑。根據《實施細則》規定,其量刑起點應為拘役3 個月。以拘役3 個月為量刑起點,坦白、認罪認罰作為調節基準刑的情節,應在拘役3 個月的基礎上減少30%以下的刑罰。如此一來,不可能會得出判處有期徒刑的量刑結論。
另外,從相關對比中也可以發現問題所在。例如,涉案數額在2000 元以下,具有坦白、認罪認罰的入戶型盜竊罪中,入戶作為入罪依據,根據規定其量刑起點應為3 個月拘役,坦白和認罪認罰為調整基準刑的情節。涉案數額在2000 元以上,具有坦白、認罪認罰的入戶型盜竊罪中,根據規定,數額在2000 元以上作為入罪依據,其量刑起點為3 個月拘役,入戶、坦白、認罪認罰為調整基準刑情節。就具有坦白、認罪認罰的入戶型盜竊罪而言,將涉案數額在2000 元以下和2000 元以上的案件進行對比,就會發現后者實質上多了入戶情節,刑罰應當更重。但是,通過比較不難發現,后者的刑罰并不比前者重,甚至可以說要相對輕些。且不說后者3 份判例判處拘役緩刑,即便是判處有期徒刑的比率,前者約54.55%,后者約44.44%,前者要略高于后者。在多了一個增加基準刑情節的基礎上,量刑反而偏輕,這只能說明《指導意見》與《實施細則》的規定沒有得到充分遵循。
總之,通過上述分析可知,在很多情形下,司法機關對被告人判處的刑罰要重于根據《指導意見》和《實施細則》規定判處的刑罰。過重的刑罰表明,司法機關在量刑時,許多時候并未以《指導意見》和《實施細則》為基礎,至少沒有充分貫徹《指導意見》和《實施細則》所規定的在確定量刑起點和基準刑的基礎上,通過量刑情節合理調整基準刑。
4.關于重增量情節而輕減量情節的問題
從所檢索的判例來看,司法機關對增加刑罰量的量刑情節,似乎更加關注。在存在增量情節的情形下,量刑相對來說偏重。比較典型的是具有累犯、坦白和認罪認罰情節的盜竊罪。如表5 所示,對于具有累犯、坦白和認罪認罰情節的盜竊罪,無論涉案數額在2000 元以上還是在2000 元以下,一律判處有期徒刑。倘若以拘役3 個月為量刑起點,等于在處罰上提升了一個刑種等級。事實上,即便是涉案數額在2000 元以上,從《指導意見》的規定來看,遠遠達不到這樣的程度。如前所述,坦白、認罪認罰可減少基準刑30%以下,根據《指導意見》規定累犯可增加基準刑10%~40%,綜合三者充其量只能增加基準刑10%以下。以拘役3 個月為量刑起點,很難得出判處有期徒刑的結論。這似乎表明,司法機關更重視增量情節對量刑的加功作用。
比較而言,減量情節對量刑的加功作用不明顯。從表2 的情況來看,坦白、認罪認罰等減量情節對量刑的影響相對有限。在表3 中,當涉案數額在2000 元以下時,坦白、認罪認罰對量刑的加功作用基本上可以忽略,因為有超過一半的判決判處有期徒刑。在判處拘役的5 份判例中,只有一份判處拘役2 個月,其余均判處拘役3 個月以上。本來,當涉案數額在2000 元以下時,入罪是由入戶這一情節決定的,根據規定其量刑起點為拘役3 個月。在11 份判例中有10 份的量刑均在拘役3 個月以上,足以說明坦白、認罪認罰對量刑的加功作用基本上被忽略。
5.關于酌定量刑情節適用問題
在不同犯罪中,影響量刑的因素千變萬化,其中絕大多數屬于酌定量刑情節,法律所能規定的量刑情節只是極少數,謂之滄海一粟也不為過。自美國聯邦量刑指南頒行以來,連年不斷的修正及篇幅、內容的擴張,也證明了酌定量刑情節的復雜化與多樣化。“經歷了過去的15 年后,當前版本的量刑指南有500 多頁,修正案超過600 個。指南包含冗長而復雜的規定,反映了量刑委員會試圖涵蓋每一個法官在對刑事被告人量刑時可能考慮到的、與加重和減輕處罰有關的因素。”〔6〕Kirby D. Behre & A. Jeff Ifrah, “You Be the Judge: the Success of Fifteen Years of Sentencing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Guidelines”, 40 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 5, 5-6 (2003).因此,量刑時充分考慮酌定量刑情節是非常必要的。
遺憾的是,司法實踐對酌定量刑情節的考慮少之又少,甚至可以說到了可有可無的地步。從所檢索的判例來看,量刑情節基本上限定在《指導意見》規定的14 種情節之內,很少考慮酌定量刑情節。雖然有少數判例會提及“偶犯”“初犯”,也基本上是作為附隨情節。例如,在表述被告人存在坦白等情節可以從輕處罰的基礎上,再提及被告人系“偶犯”“初犯”,作為“從輕處罰”的強化情節,并非獨立的從輕處罰情節。另外,雖然《實施細則》規定因生活、治病急需而盜竊的,可減少一定比例的基準刑,但鮮有判例提及。究竟是被告人不存在生活、治病急需情形,還是存在而未考慮,不得而知。總之,《指導意見》雖然規范化了量刑情節,卻在一定程度上拘束了量刑情節,無形中使重法定量刑情節而輕酌定量刑情節的導向性更為明顯。
6.關于量刑說理問題
量刑說理,是指根據事實與法律對量刑進行學理分析與說明。“量刑缺乏說理,會為法官濫用司法自由裁量權提供極大的便利,這將嚴重影響量刑公正與司法公正。”〔7〕彭文華:《量刑說理:現實問題、邏輯進路與技術規制》,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7 年第1 期,第107 頁。最高人民法院歷來非常重視量刑說理,多次以通知、意見等形式要求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加強量刑說理。〔8〕如2010 年10 月1 日起試行的《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明確刑事裁判文書應當說明量刑理由,2013年12 月23 日下發的《關于實施量刑規范化工作的通知》 也要求各級法院裁判文書要充分說明量刑理由。值得提出的是 2015 年2月4 日頒布的《關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對包括量刑說理在內的裁判說理確定了繁簡分流原則,提出完善裁判文書說理的剛性約束機制與激勵機制和建立裁判文書說理的評價體系。然而,從所檢索的判例來說,量刑說理依舊是極為薄弱的環節。法官在進行量刑說理時,主要采取的依據是估堆式說理模式,即將各種量刑情節加以概括闡述,致使量刑說理在形式上極其籠統、模糊,缺乏應有的邏輯分析,量刑結論的推斷也相對草率。值得提出的是,不少判例將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作為量刑依據,即采取諸如“量刑建議合理”等表述,直接將量刑建議的結論作為量刑結論。但是,從司法實踐中的情況來看,量刑建議是缺乏應有的量刑說理的。建議本指針對客觀存在的人或事,提出合理的見解或意見,使其具備一定的改革和改良的條件,使其向著更加良好的、積極的方面去完善和發展。顯然,完整、充分和富有邏輯性的量刑說理,才能談得上合理的見解或意見,也才能體現向著更加良好的、積極的方面去完善和發展量刑。遺憾的是,量刑建議關于量刑說理部分,甚至較之判例還要籠統、概括,難以擔當公正量刑之建議的重任。
四、研討與結論
(一)量刑起點的確定
量刑起點是確定基準刑的依據,如前所述,《指導意見》和《實施細則》對量刑起點的規定,多少還是存在一定問題的。那么,如何確定量刑起點呢?對此,理論上存在較大分歧,具體涉及兩個問題:一是量刑起點究竟是個理論概念還是裁判概念;二是如何確定量刑起點。
在學界,有學者借鑒美國聯邦量刑指南的經驗,通過對司法實務中的判例加以專業化分析來確定量刑起點。〔9〕參見周濱:《關于在刑事審判中合理確定量刑起點量刑情節和量化幅度的調研報告——以故意傷害罪為視角》,載《武漢公安干部學院學報》2010 年第4 期,第7 頁。這種做法在白建軍教授所著《罪刑均衡實證研究》一書中亦有采用,且得到不少學者推崇。不過,在筆者看來,這種根據裁判確定量刑起點的做法,顯然誤讀了美國聯邦量刑指南關于量刑起點確定的目的和初衷。眾所周知,美國聯邦量刑指南出臺前,各州法院在確定量刑起點時基本上各執己見。制定聯邦量刑指南的目的是為了在聯邦層面出臺統一的強制性量刑規定,以實現量刑均衡與一致,減少量刑偏差等目的,這當然需要確定相對一致的量刑起點。由于美國屬于判例法國家,通過對成千上萬的判例進行分析,確定相對一致的量刑起點作為聯邦法院的量刑依據,自然在情理之中。不過,美國根據判例確定量刑起點純屬一種量刑策略和需要,并非意味著量刑起點植根于裁判之中。“為了規避尊重并使對某一判決的上訴復審成為可能,法院可以簡單地規定一種罪行類別和該罪行的‘起點’,并在原則上將量刑偏離這樣規定的類別視為一種錯誤。”〔10〕Paul Moreau, “In Defence of Starting Point Sentencing”, 63 Criminal Law Quarterly 345, 352 (2016).在美國,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從來就未有量刑起點是裁判概念之共識。
在我國,筆者認為量刑起點應為理論概念,其功能在于為司法實踐確定基準刑和宣告刑奠定基礎。在如何確定量刑起點上,學界亦有不同看法。以往,學界主要有中線論、分格論、形勢論、主要因素論、危害行為論以及分類確定論等不同觀點。〔11〕參見王恩海:《論量刑基準的確定》,載《法學》2006 年第11 期,第62-69 頁。其中,分類確定論將犯罪分為非數額型的常見犯罪、數額型的犯罪和絕對確定法定刑的犯罪,并分別確定不同的量刑起點。不少學者對該觀點表示認同。“分類確定論反映了審判人員對裁判經驗的總結,該標準兼顧了確定量刑起點的穩定性和靈活性,融合了對中線論的運用,進一步細化了適用中線論的條件,比純粹的中線論更加具有合理性。”〔12〕李彥澤:《量刑起點、基準刑及宣告刑的確定依據》,載《人民檢察》2018 年第13 期,第68 頁。近些年來,不少學者提出新的主張。如有學者提出犯罪常態論,認為量刑時應當按照犯罪的常態確定量刑起點,犯罪常態是指某種犯罪最通常的情形或者絕大多數的情形,只能根據刑法規定與統計資料予以確定。〔13〕參見張明楷:《犯罪常態與量刑起點》,載《法學評論》2015 年第2 期,第2-3 頁。另有學者提出基本犯罪構成事實既遂論。“量刑起點(也可簡稱為‘起點刑’)就是指根據具體犯罪的基本犯罪構成事實的一般既遂狀態在相應的法定刑幅度內所應判處的刑罰。”〔14〕陳學勇:《確定量刑起點的方法》,載《人民法院報》2011 年7 月13 日,第6 版。
筆者贊成基本犯罪構成事實既遂論。確定量刑起點,必須科學、合理,最好有相應的法律依據根據。“起始量刑準則必須是合理的。這是最高法院的一個提醒,起點判決絕不能淪為一個愚蠢的數字游戲。量刑起點的內容必須體現議會和判例法闡明的量刑基本原則。”〔15〕Steven Bilodeau, “Starting Point or Finish Line”, 25 LawNow 46, 48 (2001).根據《指導意見》規定:“根據基本犯罪構成事實在相應的法定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這意味著確定量刑起點是,首先要以基本犯罪構成事實為根據,其次對不同的法定刑幅度應確定不同的量刑起點。《指導意見》還規定:“根據其他影響犯罪構成的犯罪數額、犯罪次數、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實,在量刑起點的基礎上增加刑罰量確定基準刑”,這表明確定量刑起點的依據是最基本的犯罪構成事實,若在犯罪數額、犯罪次數、犯罪后果等方面過限,則成為增加基準刑的事由。這種最基本的犯罪構成事實,只能是成立既遂的基本犯罪構成事實。根據學界通說,“刑法分則的法定刑是為既遂犯設定的,未完成形態的犯罪則依此為基礎,在總則中規定責任原則。”〔16〕李潔:《犯罪既遂形態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第11 頁。刑法在總則中對犯罪預備、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的特征及處罰原則作出明確規定,而沒有對犯罪既遂的特征及處罰原則作規定,真正原因在于我國刑法分則是以犯罪既遂為模式構建的,故總則中當然無需重復規定。〔17〕參見何榮功:《關于我國刑法分則條文設立模式的解讀》,載《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5 版,第37 頁。如果刑法分則的法定型模式是既遂模式,那么該法定刑幅度內的最低刑也可以成為量刑起點。
不能將量刑起點等同于某一法定刑幅度內的法定最低刑。這是因為,即便是基本犯罪事實,也存在一定差別。例如,同樣是盜竊3000 元,盜竊對象分別是富翁和生活相對艱辛的人,其社會危害就有所不同。需要注意的是,在確定量刑起點時,應當將增加基準刑的犯罪事實與基本犯罪事實區別開來。有實務部門的同志指出,“即便是基本犯罪構成要件相同的犯罪,其具體犯罪行為也不可能完全一樣。比如,同樣是持刀致人重傷,捅刺胸部要害部位致人重傷與捅刺大小腿致人重傷的危害性是不一樣的,在確定量刑起點時就應有所區別,不能都確定法定最低刑為量刑起點。”〔18〕陳學勇:《確定量刑起點的方法》,載《人民法院報》2011 年7 月13 日,第6 版。該觀點有將增加基準刑的犯罪事實與基本犯罪事實混為一談之嫌,有所不妥。即便是重傷,根據規定也有重傷一級和重傷二級之別,重傷二級才是基本犯罪構成事實,重傷一級應為犯罪后果過限情形,屬于增加基準刑的犯罪事實,而非基本犯罪事實。從司法實踐中的情況來看,在排除增加基準刑的犯罪事實的情況下,諸如被害人為富翁和生活相對艱辛的人這樣的基本犯罪事實,其所引起的社會危害性差異顯然不應過分夸大。因此,量刑起點的確定,應以法定刑幅度內的最低刑為基礎,允許一定的幅度差,但不應過大。
法定刑幅度內的最低刑,若是同一刑種不存在問題,如有期徒刑的最低刑是6 個月。但是,若是不同刑種如何確定最低刑呢?如上所述,在盜竊罪的基礎法定刑幅度內,共包括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和罰金,如何確定最低刑呢?顯然,《指導意見》并未對這種情況加以充分考慮,而是特別規定:“綜合全案犯罪事實和量刑情節,依法應當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管制或者單處附加刑、緩刑、免刑的,應當依法適用。”問題在于,量刑是以量刑起點為基礎展開的,如何綜合全案情節判處無期徒刑、管制或者單處附加刑等,無疑讓人感到費解。筆者認為,原則上不應將附加刑作為確定最低刑的依據。“附加刑是補充主刑適用的刑罰類型。其既可以附加主刑適用,也可以獨立適用;而且,對同一犯罪人,可以同時適用多個附加刑。”〔19〕黎宏:《刑法學》(第2 版),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346 頁。既然附屬于主刑適用,且可以同時適用多個附加刑,顯然不適合作為確定最低刑的依據。因此,在法定刑幅度內確定最低刑,應當限于主刑。通常情況下,應以某一法定刑幅度內最輕的主刑的最低刑為基礎,在一定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如“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量刑起點可確定為10~11 年。若最輕刑種因性質不同難以區分,如管制和拘役,兩者性質決然不同,不能簡單地說拘役絕對重于管制,故而可分別確定最低刑。
這樣看來,《指導意見》和《實施細則》將基礎法定刑幅度內的盜竊罪量刑起點確定為“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和拘役3 個月,確實有所不妥。首先,不應將管制刑排除在確定最低刑的刑種之外。其次,《指導意見》所規定的在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與其所規定的確定量刑起點的“基本犯罪構成事實”存在不協調。因為,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是個非常寬泛的法定刑幅度,其所對應的基本犯罪事實也應當非常寬泛,這樣的犯罪事實是否是基本犯罪事實,令人生疑。這也許是間接造成上述實證分析研究所分析的,量刑存在嚴重不均衡、不一致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對于基礎法定刑幅度內的盜竊罪,應當在管制和拘役的幅度內,以各自的最低刑為基礎,在充分考慮拘役和管制的性質差異的情況下,確定相應的量刑起點。如對管制可以在3~6 個月的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拘役可在1~2 個月的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同時,考慮到基本犯罪事實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相關規定不應一刀切地明確絕對、具體的量刑起點,應由司法機關酌情確定具體的量刑起點。
(二)基準刑的確定及其調節
根據《指導意見》規定,確定基準刑需要以犯罪數額、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實為基礎,在量刑起點的基礎上增加刑罰量。理論上,根據犯罪事實內的量刑情節所確定的刑罰,通常被稱為報應刑或者責任刑。“報應是對行為人實施不法行為的意思決定的非難,刑罰的痛苦程度應與責任程度相應,故報應刑是與責任相應的刑罰。”〔20〕張明楷:《責任刑與預防刑》,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20 頁。根據犯罪事實外的量刑情節所確定的刑罰,往往被稱為功利刑或者預防刑,它是將預防犯罪作為刑罰正當化根據。
責任刑在量刑時始終處于前提和基礎地位。責任刑的優點是充分體現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要求量刑必須受到責任程度及其輕重的制約,以限制預防刑的刑度和范圍。其缺陷是具有一定的被動性與消極性。預防論則一改報應論針對已然之罪的被動、消極態度,轉而以主動、積極的態度對將來的犯罪進行干涉、預防。其積極意義在于將局限于責任報應的消極刑罰變成積極預防犯罪的舉措,以求更好地適應現實需要防衛社會。如果說責任刑是回溯性的,那么預防刑則是前瞻性的,兩者結合使刑罰兼具原則性與靈活性,有利于實現刑罰目的。
不難看出,《指導意見》明確責任刑是預防刑的前提和基礎,只有在責任刑的基礎上根據犯罪事實外的量刑情節對刑罰加以調節,才能確定預防刑。“如果處罰局限在罪責的范圍內,并受責任程度及其輕重的制約,那就只能是責任刑;如果處罰需要以責任程度及其輕重為基礎,并適當考慮預防再犯罪的可能性需要,則屬于以責任報應為基礎的預防刑。”〔21〕彭文華:《累犯認定: 現實問題、路徑選擇與技術規制》,載《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9 年第3 期,第87-88 頁。在此基礎上,《指導意見》規定:“根據量刑情節調節基準刑,并綜合考慮全案情況,依法確定宣告刑。”這意味著通過確定責任刑和預防刑,才能夠綜合考慮全案情況確定最終刑罰,即宣告刑。因此,司法機關在量刑時,應當嚴格區分根據犯罪事實內的量刑情節所確定的責任刑和根據犯罪事實外的量刑情節所確定的預防刑,確保量刑均衡與一致,以充分實現量刑公正。
(三)酌定量刑情節的適用及其規范化
一般來說,酌定量刑情節是在一定的時間和場合對法定情節的必要補充。〔22〕參見胡學相:《量刑的基本理論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第177 頁。在相對罪刑法定時代,酌定量刑情節依然擔當重要使命,它最大的理論、實踐價值在于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證個別公正,同時也可以彌補法定情節的不足。〔23〕參見房清俠:《酌定情節的學理研究》,載《法學家》2001 年第5 期,第22 頁。忽視酌定量刑情節或者將之法定化,是最終導致美國聯邦量刑指南的強制性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國聯邦量刑指南確立的量化量刑模式,試圖不斷地將酌定量刑情節法定化后加以運用,導致法官幾乎沒有機會去因地制宜地考慮他面前的被告的罪責性。〔24〕See Kate Stith & Lose A. Cabranes, Fear of Judging:Sentencing Guidelines in the Federal Cour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p.82-83.因此,重視并合理運用酌定量刑情節,對于實現量刑公正而言非常重要。遺憾的是,在司法實踐中,酌定量刑情節卻處于可有可無的境地。鑒于酌定量刑情節意義重大卻得不到應有重視,一些學者呼吁將酌定量刑情節法定化,認為這樣做符合現實需要,亦有其深厚的理論基礎,〔25〕參見肖敏:《論酌定情節法定化》,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7 年第10 期,第118 頁。而《指導意見》也有將酌定量刑情節法定化的傾向。〔26〕例如,《指導意見》就將當庭自愿認罪、退贓、退賠、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并取得諒解、達成刑事和解協議、有前科等酌定量刑情節,與法定量刑情節一道作為常見量刑情節明確其量刑尺度。
筆者認為,通過法定化來解決法官漠視酌定量刑情節問題,是不可取的。首先,酌定量刑情節復雜多樣,很難也不可能將之一一法定化。其次,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的社會經濟發展、風土人情等相差很大,同一情節在不同的地域受到的適用不具有通識性,故將之法定化以便統一適用有所不妥。再次,酌定量刑情節千變萬化,需要及時運用才能體現量刑公正,法定化總讓人感覺有滯后之嫌。最后,將酌定量刑情節法定化,只會加深法定量刑情節受重視的印象,進一步削弱酌定量刑情節的體系地位。當然,適用酌定量刑情節可能容易導致濫用司法自由裁量權,但與其在量刑中的價值相比,這無疑是次要的。事實上,司法自由裁量權濫用還是可以通過有效方式避免的。從國外的經驗來看,通過嚴格的上訴審查、規范的量刑說理等,就能有效防止司法自由裁量權濫用。要想達到這一點,離不開規范化的量刑程序。量刑程序規范化與量刑規范化,均對實現量刑公正具有重要意義,它們之間屬于一體兩翼的關系,需要同步進行。
(四)如何進行量刑說理
量刑說理以事實和法律為基礎,對如何量刑以及如何推斷量刑結論進行全面、系統的學理分析與說明,對澄清量刑事實和相關法律規定,防止司法自由裁量權被濫用,維護量刑均衡與一致,實現量刑公正,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英美法系國家,包括量刑說理在內的裁判理由,通常占據裁判文書內容的60%左右,足見對量刑說理的重視。遺憾的是,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量刑說理始終是突出的短板之一。具體地說,主要存在以下問題:一是說理方式普遍呈現固定化、格式化特征;二是主刑說理粗略,附加刑基本不說理,裁量制度說理疏漏;三是混淆處罰規范與非處罰規范,導致量刑說理缺乏邏輯性;四是說理時 “張冠李戴”,讓人難以接受;五是缺乏必要的分析和論證,導致說理缺乏信服力;六是用語生硬、刻板,影響刑事裁判的社會效果。〔27〕參見彭文華:《量刑說理:現實問題、邏輯進路與技術規制》,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7 年第1 期,第108-111 頁。從理論上來講,量刑說理是具有很強的理論性與邏輯性的,并非簡單地重復事實和法律,也不是對事實和法律的籠統、概括的評述。一般來說,量刑說理應當做到以下幾點:一是以三段論為基礎,根據不同的量刑規范命題的結構形式區別對待;二是需要論證量刑結論具有較高的可接受性, 符合語用邏輯,說理用語應具有契合性與情景感,并適當運用修辭與對話方法;三是對量刑說理需要進行適當的技術規制。如可以考慮將刑事判決書中的“量刑理由”改成“量刑說理”,實行實質說理制度,明確量刑說理繁簡分流的依據和標準,加強對量刑說理的審查和監督,構建量刑判例信息庫。〔28〕參見彭文華:《量刑說理:現實問題、邏輯進路與技術規制》,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7 年第1 期,第114-127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