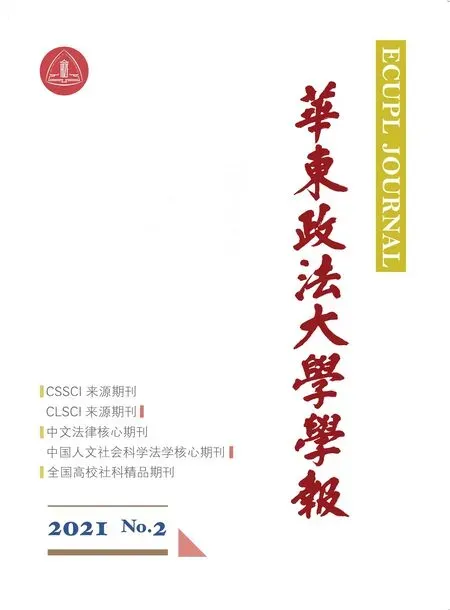我國涉外協議離婚法律適用規則的規范修正與適法邊界
許 凱
一、問題的提出:對《法律適用法》第26 條的兩種立場
協議離婚,也稱為自愿離婚,主要是指合法婚姻關系的雙方對離婚以及離婚后相關事項達成合意,并經國家法定部門認可而發生婚姻關系解除效果的離婚方式。就當代中國而言,離婚率的逐年攀升引發了重大的社會關注,而協議離婚是主流的婚姻解除方式。依據民政部的統計數據,2018 年依法辦理離婚手續的446.1 萬對夫妻中,采取協議離婚方式的為381.2 萬對,而法院判決、調解離婚的僅為64.9 萬對。〔1〕《民政部2018 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來源: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20 年6 月13 日訪問。在我國《民法典》通過之前,國內法中協議離婚的法律淵源主要是1998 年《婚姻法》第31 條的規定,〔2〕1998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31 條:“男女雙方自愿離婚的,準予離婚。雙方必須到婚姻登記機關申請離婚。婚姻登記機關查明雙方確實是自愿并對子女和財產問題已有適當處理時,發給離婚證。”至于協議離婚時需要完成的程序性規定,則主要見于2003 年《婚姻登記條例》和民政部制定的相關配套性文件。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與國際社會的開放對接,涉外婚姻的類型與數量均呈現上升態勢,而我國法院受理的涉外離婚案件也層出不窮,這種態勢直接促成了1986 年《民法通則》第147 條規定的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和外國人結婚適用婚姻締結地法律,離婚適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然而,當時該條文在涉外離婚的范疇中只包含了涉外訴訟離婚這一事項,并未涵蓋我國國內法中承認之協議離婚事項。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當時我國涉外婚姻登記的相關規定并不允許中國公民和外國人在中國的婚姻登記部門提出協議離婚的申請,故第147 條關于涉外協議離婚的缺位也看似順理成章。〔3〕1983 年民政部發布的《中國公民同外國人辦理婚姻登記的幾項規定》第6 條規定:“中國公民和外國人在華要求離婚的,應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有關規定,向該管人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要求復婚的,按結婚辦理。”同年,民政部在《關于辦理婚姻登記中幾個涉外問題處理意見的批復》第4 條中作出解釋:“《中國公民同外國人辦理婚姻登記的幾項規定》中,關于中國公民同外國人在華要求離婚的規定,是根據有的國家規定不經法院判決離婚無效的情況作出的,不論雙方自愿離婚還是一方要求離婚的,都由我國人民法院處理。這一規定是經最高人民法院統一的,應按規定執行。”學界普遍性認為,這樣規定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避免在我國獲準的涉外協議離婚,在有關國家得不到承認的情形。參見黃進、姜茹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釋義與分析》,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第136-137 頁。
時移世易,在《民法通則》實施后,國際私法學界開始逐漸關注、支持涉外協議離婚法律適用規范的制定問題。其原因有二:一是當年立法中禁止中外當事人在我國協議離婚的規定逐漸與時代脫節,因此,在2003 年《婚姻登記條例》中出現了有條件允許中外當事人在我國協議離婚的轉變;〔4〕2003 年《婚姻登記條例》對于中國公民同外國人或者內地居民同香港居民、澳門居民、臺灣居民、華僑在中國內地自愿離婚的情形,允許雙方共同到內地居民常住戶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記機關辦理離婚登記。但該條例第12 條第3 項規定了一項特別條件,即申請涉外協議離婚登記的雙方其結婚登記必須也在中國內地辦理。二是在《民法通則》實施之后的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中外當事人在外國協議離婚的效力需要我國法院予以鑒別的案件。〔5〕在1998 年上海法院受理的渡邊義睦重婚罪一案中,被告渡邊義睦(日本籍公民)與自訴人宋某(中國籍公民)于1994 年4 月在中國登記結婚,當年6 月被告向日本有關部門申請協議離婚并獲準。1995 年5 月,被告又在中國上海與他人登記結婚。1998年自訴人在上海法院提起刑事自訴,控告被告犯有重婚罪。本案的焦點問題是被告與自訴人于1994 年6 月在日本進行的協議離婚行為是否有效,但囿于當時《民法通則》第147 條未涉及涉外協議離婚的法律適用規則,因而引起學界熱議。參見左冰:《從渡邊義睦重婚罪一案看我國涉外協議離婚的法律適用》,載《法學》1999 年第8 期,第57-60 頁。有鑒于此,涉外協議離婚的法律適用應當具有獨立的沖突法意義在這一時期被學界所廣泛支持。〔6〕2000 年由中國國際私法學會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私法示范法》第132 條第2 款規定:“當事人協議離婚的,適用其以明示方式選擇的當事人任何一方或者共同的本國法、住所地法、慣常居所地法。當事人沒有選擇法律的,適用離婚登記機關或者其他主管機關所在地法。”對于這一規定,當時學界普遍認為是考慮中國實際情況所致,在涉外離婚案件中允許當事人協議離婚,并可以協商選擇所要適用的法律,反映了國際私法發展的最新方向。參見趙相林主編:《中國國際私法立法問題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年版,第409 頁。也有學者認為:“《法律適用法》對協議離婚的法律適用問題作了明確的規定,彌補了《民法通則》對涉外離婚法律適用規定不完整的缺陷。”參見喬雄兵:《涉外離婚的法律適用:傳統、變革及發展——兼評〈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有關規定》,載《江漢學術》2013 年第6 期,第46 頁。最終該種觀點為201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簡稱《法律適用法》)第26 條所體現:“協議離婚,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適用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國籍國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共同經常居所地法律;沒有共同經常居所地的,適用共同國籍國法律;沒有共同國籍的,適用辦理離婚手續機構所在地法律。”
《法律適用法》出臺之后,第26 條的實施卻并沒有像此前學界預想的那樣一帆風順,近年來對該條規定的質疑之聲似乎愈演愈烈。不少學者認為,第26 條所規范的涉外協議離婚事項并無獨立的規范意義和現實意義。因此,面對《法律適用法》實施前后兩種截然不同的立場,本文擬對質疑第26 條的主要理由進行分類分析,進而以該條沖突規范的適用范圍為中心予以剖析,最終目的在于說明《法律適用法》第26 條適用的價值和邊界。
二、質疑第26 條規范價值的理由
《法律適用法》作為現今我國在涉外法律適用領域最為重要的單行法,其對于涉外離婚法律選擇規則進行了重構,這其中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將此前立法中并無涉及的涉外協議離婚事項進行了專條規定,并在沖突規范連接點的選擇和排布方面引入了意思自治以及共同屬人法規則,這兩大“創新”幅度不可謂不大。然而從《法律適用法》實施至今,國際私法學界與實務界對于上述“創新”均有著不同的反對聲音,雖然這些質疑之聲來自于不同視角,但其共同的指向則是明確的,那便是以《法律適用法》第26 條為代表的涉外協議離婚法律適用規則不應當具有獨立的規范意義。
(一)激烈的法律沖突:涉外協議離婚是否應當承認
離婚是一項解除婚姻關系的要式法律行為,因其常與各國的公序良俗緊密關切,故經歷何種離婚形式方可為一國承認,將直接影響跨國離婚的效力判斷。相較于訴訟離婚方式,各國對待協議離婚問題上的法律沖突要激烈得多:第一,并非所有的國家都允許協議離婚這種離婚方式,一些國家僅承認判決離婚的方式,如德國、意大利、瑞典等國家;〔7〕參見齊湘泉:《〈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原理與精要》,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第222 頁。第二,在允許協議離婚的國家,協議離婚的受理機關和適用程序也有很大差異,主要區分為行政協議離婚和訴訟協議離婚。前者是由行政機關通過行政程序辦理的協議離婚,其中行政機關包括戶籍機關(如日本、蒙古)、民事機關(如墨西哥)和其他行政機關(如丹麥,協議離婚由州長處理;在挪威,協議離婚由郡都處理)。訴訟協議離婚也可分作兩種情況:一是當事人離婚須經法院審批,如法國;二是當事人的協議離婚須經法院裁決,如奧地利;〔8〕參見李雙元、溫世揚主編:《比較民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671 頁。需要說明的是,法國于2016 年11 月18日頒布了《21 世紀的司法現代化法》,該法規定從2017 年1 月1 日起,選擇協議離婚的案件不再由法官審理,離婚雙方達成的私署協議經各自律師聯署簽名后,遞交公證人審查存檔,即可完成離婚手續。參見蔡勇:《法國改革離婚制度 分流法院非訴案件》,載《人民法院報》2017 年7 月28 日,第8 版。第三,某些允許協議離婚的國家對于協議離婚的實質性條件存在特別規定,例如俄羅斯、蒙古規定雙方不得有未成年子女,不論是親生的還是收養的皆在此列。〔9〕參見萬鄂湘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條文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 年版,第192 頁。
正是由于協議離婚在各國法制中差異甚大,因而早在《法律適用法》尚處于草案時期,就有學者指出我國在涉外離婚方式上不宜采用協議離婚的方式,進而認為未來立法應取消協議離婚的法律適用規則,其主要理由在于基于協議離婚方式并未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協議離婚的效力一般不能得到外國的承認。〔10〕參見汪金蘭:《關于涉外婚姻家庭關系的法律適用立法探討——兼評〈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草案)的相關規定》,載《現代法學》2010 年第4 期,第165-166 頁。但筆者認為,協議離婚法律沖突的激烈性與《法律適用法》中涉外協議離婚法律適用規則存廢之間的關系有待討論,在當下我國《婚姻登記條例》已經有條件認可涉外協議離婚方式的前提下,即便我國婚姻登記部門作出的離婚登記不被外國所認可,但此困境的產生與《法律適用法》第26 條似無因果關系。退而言之,即便我國真的擯棄涉外協議離婚這種方式,但假如某一成立于外國的協議離婚效力需要得到我國法院認定時,似乎又存在《法律適用法》第26 條之適用余地。因此,即便協議離婚之法律沖突甚劇,其也不應成為廢棄《法律適用法》第26 條的理由。
(二)比較法上的孤立:雙軌制立法模式的并軌
就國際私法本身而言,面對涉外離婚這一個整體性的概念,在設計、編排法律適用規范時,以是否需要區分為涉外訴訟離婚和涉外協議離婚兩個部分,形成了單軌制立法與雙軌制立法兩種模式。在單軌制立法模式中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前述不承認協議離婚國家的國際私法立法,其僅僅就涉外訴訟離婚進行了規范,此非本文所涉;第二種是將協議離婚和訴訟離婚合二為一,用統一的沖突規范予以規制,這是當今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做法。
雙軌制的立法模式以我國《法律適用法》的規定為典型,即區分涉外訴訟離婚和協議離婚分而治之。針對這種雙軌制的立法模式,有學者指出:“‘協議離婚’這一規定在當今國際社會尚屬首例,從目前我國實踐中是否需要運用涉外‘協議離婚’之法律適用狀況來看,恐怕的確能算得上是超前立法。然而是否需要這樣的‘獨創’,學界也是存在爭議的。”〔11〕彭思彬:《涉外婚姻家庭關系法律適用若干爭議評析》,載《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6 期,第84 頁。反對雙軌制立法的學者進而認為:“區分協議離婚與訴訟離婚,分別適用不同的準據法,勢必造成涉外離婚準據法的不統一,使我國涉外離婚制度變得復雜。對于涉外離婚的當事人而言,這種區分模式會引導當事人根據法律適用的結果來選擇離婚的方式,在客觀上容易導致法律規避的發生。”〔12〕汪金蘭:《中歐涉外離婚法律適用法的新趨勢》,載黃進、肖永平、劉仁山主編:《中國國際私法與比較法年刊》第15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163 頁。
到底要不要順應世界立法之趨勢實現并軌?這一問題的回答應集中于《法律適用法》第27 條“訴訟離婚”的探討,即我國涉外訴訟離婚的法律選擇規則有無必要與可能引入第26 條中的意思自治與共同屬人法規則。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將兩條文合二為一便是順理成章的。但就現有立法以及既有的涉外離婚司法時間而言,訴訟離婚適用單一的法院地具有很強的支持度和操作性,因而在第25 條的連接點無法變動的情況下,雙軌制的立法模式恐怕還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予以維持。
(三)中國涉外協議離婚的司法實踐:適用范圍的有限性
除了通過比較方法質疑《法律適用法》第26 條的獨立性以外,還有不少學者通過對該條在實踐中適用范圍的分析,得出其并不存在適用空間的觀點。如有學者將第26 條的適用區分為“在我國境內的離婚”和“在我國境外的離婚”兩種情況分別探討,一方面認為第26 條無法適用于我國境內的離婚登記,原因在于在我國境內進行離婚登記要符合我國法律規定的條件;另一方面指出在我國境外的離婚協議如未取得離婚登記或判決,這一協議原則上不會被我國所承認,因此,第26 條的規定與我國現行實踐相背離。〔13〕參見杜濤:《〈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釋評》,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 年版,第215-216 頁。筆者贊同這種分類探討的方式,但上述觀點似乎對“在我國境內的離婚”并未區分協議離婚的實體問題和程序問題,而對“在我國境外的離婚”僅注意了判決承認問題而遺漏了在具體案件中可能以協議離婚作為先決問題的情形,有待于下文詳述。
另一種證明《法律適用法》第26 條適用范圍有限的方式來自對我國涉外審判實踐的檢索與統計,比如有學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查詢自2011 年4 月至2015 年10 月適用《法律適用法》第26 條的案例,得出的結果僅有兩件。〔14〕兩件案例分別為:福建省福州市晉安區人民法院(2014)晉民初字第641 號民事判決書與遼寧省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大民一終字第354 號民事裁定書。參見戴霞:《論涉外協議離婚的法律適用 ——以〈法律適用法〉第二十六條為中心》,來源:http://www.sohu.com/a/197319639_725762,2019 年12 月10 日訪問。也有專業法官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以及其他渠道,對截至2017 年9月適用《法律適用法》第26 條的案例進行檢索,得到的結果是五件相關案例。〔15〕五件案例分別為:福建省福州市晉安區人民法院(2014)晉民初字第641 號民事判決書、遼寧省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大民一終字第354 號民事裁定書、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2016)京0108 民初38611 號民事判決書、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4012 號民事判決書和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粵06 民終876 號民事判決書。參見王姝:《意思自治原則在涉外婚姻司法實踐中的困境與出路——兼評〈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 24、26 條》,載《法律適用》2017年第23 期,第113 頁。筆者自己也曾嘗試對2019 年12 月10 日之前的相關案例進行檢索,得出十四件相關案例,其中還存在錯誤援引以及法律事實與爭議同一的情況。〔16〕十四件案例分別為: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7)京01 民終字5355 號民事判決書、遼寧省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大民一終字第354 號民事裁定書、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粵06 民終876 號特殊程序民事判決書(法條援引錯誤)、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法院 (2015)佛順法民一初字第391 號民事判決書、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法院(2015)佛順法行初字第75 號行政判決書及該案再審審查和審判監督案件、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粵行申1469 號行政裁定書、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4012 號民事判決書、福建省福州市晉安區人民法院(2014)晉民初字第641 號民事判決書、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2015)普民四(民)初字第2925、2926 號民事判決書及兩案的二審案件、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2017)滬02 民終11336、11339 號民事判決書、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2015)普民四(民)初字第4142 號民事判決書及該案的二審案件、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2017)滬02 民終10660 號民事判決書。但假如僅因為援引第26 條的案件數量稀少就否定其存在意義,不免有些本末倒置。事實上,涉外離婚本身的特點必然導致其涉訴性的減弱,而前述適用第26 條案件的存在正好說明了其在司法實踐中具有一定的“用武之地”,因而,正確的做法應是在這些案件中通過歸類、排除等方法尋找適用第26 條的案件類型。
三、第26 條的規范分析與修正
《法律適用法》第26 條作為涉外協議離婚的法律適用規則,不能僅因為協議離婚法律沖突的激烈、雙軌制立法的弊端以及實踐中適用數量的稀少就對其獨立性進行否定。筆者認為,判斷該條存廢的前提應從該條沖突規范的范圍入手,厘清該條調整的“涉外協議離婚”是否具有理論與實務中的獨立存在必要?其結論是應當將第26 條的范圍修正為“離婚協議”,即第26 條規定的協議離婚的法律適用,應僅是指協議離婚實質要件的準據法的確定規則。〔17〕參見黃進、姜茹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釋義與分析》,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第135 頁。而就協議離婚的形式要件而言,未來修法時應當明確為適用“辦理離婚手續機構所在地法”,而不再適用第26 條的現有選法規則。
(一)涉外協議離婚的構成要件分析
由于協議離婚乃要式的身份性法律行為,因此如果以我國國內協議離婚為對象,那么自然可以得出“協議離婚=離婚協議+登記”的公式。但如前所述,在涉外協議離婚領域,雖然承認協議離婚這種方式的國家或地區均認同其要式法律行為的性質,但究竟是否為登記這一要式行為?如果需要登記,當事人應向何種登記機關登記?這些問題的回答均有所差異。因而,對于涉外協議離婚的構成要件應當予以適度擴展,即“涉外協議離婚=離婚協議+要式方式”。
在明確了第26 條的范圍“涉外協議離婚”的兩項構成要件后,依據第26 條現有之系屬,其至少說明兩點:其一是,“涉外協議離婚”允許當事人意思自治選法,其二是,案件可能適用外國法作為準據法。從邏輯上講,這兩項特點自然也就應當一體適用于“離婚協議”和“要式方式”兩個構成要件。在一個涉外協議離婚的案件中,當事人在離婚協議中進行法律選擇,甚至選擇適用法院地以外的外國法均為合理,因為其純屬私權之處分。但是,后一個要件即“要式方式”可否同樣允許選法,則不得不打上問號。
試舉一例,假如一對中國籍夫婦在甲國居住期間簽訂了一份離婚協議,協議約定以“中國法”為準據法,其后雙方按照甲國當地的要式方式辦理了協議離婚手續。嗣后,一方當事人以甲國當地的要式方式與中國法中的登記方式不符為由,向我國法院提出宣告協議離婚無效之訴,我國法院應當如何適用第26 條?法院是否應當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適用中國法去判斷甲國要式行為的效力問題?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因為一國如何辦理協議離婚的手續屬于該國公法之范疇,婚姻解除的手續是法定機關代表國家依法行使職權,法定機關審查和認可協議離婚的程序和條件只能是本國的法律,此乃公法屬地性的體現。〔18〕參見萬鄂湘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條文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 年版,第194-195 頁。就我國而言,無論當事人在涉外離婚協議中作出何種選法安排,其均應當按照我國《婚姻登記條例》的規定提出離婚申請,而適格的登記機關也只能按照《婚姻登記條例》的規定進行審查。故通過以上對“涉外協議離婚”構成要件法律適用的分析,可以看到,第26 條的適用范圍僅限于“涉外離婚協議”,而不得適用于“要式方式”。
(二)涉外協議離婚類型化案件的檢視
為了檢驗上述觀點的成立,即第26 條的范圍部分是否應修改為“離婚協議”,以下以我國法院受理之實務案件進行審視。回到“涉外協議離婚=離婚協議+要式方式”的構成公式,可將實務案件分為三種類型進行探討:第一種類型是既有完整的離婚協議也完成了要式方式的案件,其典型為在我國內地辦理離婚登記后請求法院撤銷離婚登記的案件,〔19〕此類案件具有兩種訴訟路徑,其一是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9 條為依據,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變更或者撤銷財產分割協議,參見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7)京01 民終字5355 號民事判決書、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法院 (2015)佛順法民一初字第391 號民事判決書;其二為以《婚姻登記條例》等行政法規為依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判令撤銷婚姻登記機關作出的違法登記行為。參見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人民法院(2015)佛順法行初字第75 號行政判決書及該案再審審查和審判監督案件、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粵行申1469 號行政裁定書。以及請求實際履行生效離婚協議的案件。〔20〕參見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4012 號民事判決書。這兩種案件當屬第26 條調整無疑,但對于證明上述觀點并無價值。
第二種類型的案件為協議離婚的要式方式已經完成,但離婚協議的內容或效力存在爭議的案件。此類案件在我國國內法背景下幾無可能,因為我國《婚姻登記條例》明確將離婚協議書作為婚姻登記機關受理離婚申請的條件,且“離婚協議書應當載明雙方當事人自愿離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對子女撫養、財產及債務處理等事項協商一致的意見”。〔21〕《婚姻登記條例》第11、12 條規定。但在涉外協議離婚領域,由于某些國家離婚登記制度不要求全面的處置意愿,因而會產生在協議離婚時未作出約定的夫妻財產分割、子女撫養等問題的法律適用疑義。在松田浩德訴松田江美、黃淑芳確認無效合同糾紛案中即發生此種情況,該案原告與被告一均為日本籍公民,2012 年在日本登記離婚,但《日本民法》規定協議離婚無需對夫妻共同財產作出處理即可辦理離婚手續。其后,雙方對夫妻財產分割問題產生爭議,被告一出示一份沒有落款時間的《離婚協議書》以證明雙方已完成財產分割之事實,但原告對該份《離婚協議書》的真實性予以否定。就本案中雙方簽訂的《離婚協議書》的效力而言,受理案件的法院援引了《法律適用法》第26條的規定并依據當事人的合意選法最終適用《日本民法》作為準據法。〔22〕參見福建省福州市晉安區人民法院(2014)晉民初字第641 號民事判決書。這一案件的法律適用情況表明,當境外協議離婚的要式行為是否完成應尊重行為地法律的規定,而《法律適用法》第26 條的適用范圍應當為離婚協議的效力審查以及實際履行等爭議事項。
第三種類型是只有離婚協議而未完成協議離婚要式行為的案件,此類案件的爭議往往來自離婚協議是否在其后的訴訟中作為法院考慮夫妻財產分割和子女撫養問題的依據。在上海法院審理的孫某與董某離婚后財產分割的系列案件中,原被告均為中國公民,1999 年在中國登記結婚,婚后原告前往澳大利亞定居。2013 年原被告簽訂《離婚協議書》一份,約定內容為“雙方同意協議離婚,同意在澳洲離婚。”《離婚協議書》中對于離婚后財產分配和子女撫養,也做出了明確的約定。但澳大利亞的國內法中并不認可協議離婚這種方式,因此,2014 年原告向澳大利亞聯邦巡回法院提出離婚申請并獲得《離婚令》,同年《離婚令》對解除雙方婚姻關系條款的效力得到中國法院的承認。2015 年,原告向中國法院起訴請求分割雙方在中國的財產,被告主張按照雙方之間《離婚協議書》的內容進行分配,而原告則認為《離婚協議書》未發生效力。本案中《離婚協議書》效力準據法的判斷問題,一、二審法院均認為應當適用第26 條“涉外協議離婚”的規定,最終適用中國法為準據法作出了判決。〔23〕參見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2015)普民四(民)初字第2925、2926 號民事判決書及兩案的二審案件、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2017)滬02 民終11336、11339 號民事判決書、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 (2015)普民四(民)初字第4142 號民事判決書及該案的二審案件、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2017)滬02 民終10660 號民事判決書。但本案卻折射出一個問題:當事人雙方有離婚協議但沒有履行要式方式,而后又以訴訟離婚方式解除夫妻關系,其離婚效力的判斷究竟應落入《法律適用法》第26 條“協議離婚”的范疇,抑或屬于第27 條“訴訟離婚”的范疇?筆者以為,本案的爭議是《離婚協議書》有無產生法律效力的問題,因此識別為第26 條的“協議離婚”應屬當然。之所以產生上述疑問的原因正是在于第26 條現有的表述“協議離婚”范圍過廣,因而在要式行為缺失的案件中出現識別困難的“假象”。如在未來修法中將其范圍的表述修改為“離婚協議”,則自然得以修正。
四、第26 條的司法適用邊界
在明晰了第26 條的表述問題后,要論證其獨立性還需要從其在實務中的適用范圍進行分析:一方面,哪一類型的爭議應當適用該條沖突規范?另一方面,經由第26 條指引后找到的準據法,其適用范圍如何?上述問題的回答,便是第26 條得以獨立存在的司法適用邊界。
(一)訴訟離婚中的調解協議不適用第26 條
從第26 條的案件范圍來看,帶有涉外性質且符合“離婚協議+要式方式”要件的協議離婚案件,在法律適用的過程中顯然屬于該條的范疇,這些案件的類型在前文中已有分類探討,在此不贅。此處需要討論的是,某些與上述公式不盡符合的事項能否被歸入?最為典型的情況是在涉外訴訟離婚的案件里,如當事人雙方在訴訟過程中達成調解協議,能否適用第26 條?對此問題,最高人民法院的傾向性意見認為:“當事人以訴訟方式離婚,不能協議選擇適用的法律。但如果夫妻雙方在訴訟過程中達成調解協議,則可以在其中選擇協議離婚適用的法律。”〔24〕萬鄂湘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條文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 年版,第196-197 頁。學界與實務界對于這一問題也大多持支持立場,其理由主要是三點:一是可以充分體現意思自治原則在涉外離婚案件中的貫徹;二是打破“進入訴訟即為訴訟離婚”的固有認識,擴大第26 條的適用范圍;三是從實務上看,避免因婚姻登記機關只適用“公法”而導致的第26 條的適用落空。〔25〕參見戴霞:《論涉外協議離婚的法律適用 ——以〈法律適用法〉第二十六條為中心》,來源:http://www.sohu.com/a/197319639_725762,2019 年12 月10 日訪問;王姝:《意思自治原則在涉外婚姻司法實踐中的困境與出路——兼評〈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 24、26 條》,載《法律適用》2017 年第23 期,第116 頁。
但是,就上文提到的我國法院受理涉外離婚案件后當事人調解結案的情形之下是否能夠適用第26 條的問題,筆者持反對的觀點:第一,沖突規范的識別問題在我國法律中應當堅持法院地法原則,〔26〕《法律適用法》第8 條:“涉外民事關系的定性,適用法院地法律。”而在我國《婚姻法》的規定中,協議離婚與訴訟離婚的界限是涇渭分明的,只要通過法院訴訟最終以判決書或者調解書方式達成離婚法律效果的,一律認為屬于訴訟離婚范疇。上述最高院及部分學者的觀點將調解結案的協議歸于協議離婚范疇,顯然與我國作為法院地的識別標準不符,同時還會導致內外協議離婚法制不統一的結果,故非有充分之理據實不可采;第二,從學者們支持的觀點來看,似乎認為不把訴訟中調解離婚事項納入第26 條的范圍,該條就有得不到適用之虞。筆者認為,與離婚相關的訴訟案件是否均屬“訴訟離婚”案件應當從當事人的請求出發進行判斷,比如涉外案件中的當事人簽署了離婚協議,但一方因拒絕履行法定登記手續,另一方當事人請求法院判決離婚的案件應當屬于涉外訴訟離婚范疇。但假如雙方離婚協議已經登記,而一方當事人向法院起訴請求撤銷離婚協議或者請求對方當事人履行離婚協議的案件,則屬于第26 條涉外協議離婚的范疇。另依據司法實踐,以協議離婚效力作為先決問題而引發的夫妻財產分割、處分類案件也屬其中。可見,進入訴訟程序并不必然進入“訴訟離婚”的沖突規范范圍;第三,從操作性的層面來看,一件涉外離婚案件在我國法院被提起,當事人一旦達成調解協議,其后的結果無非兩種:第一是調解協議經過《民事訴訟法》中的普通程序或者特別程序,最終由法院出具有既判力的《民事調解書》,在該種情形下當事人不可能在調解協議中約定法律適用問題,即便能夠約定,這種約定面對具有既判力的司法文書又有何意義?第二是當事人達成協議后未經過司法確認而以撤訴方式結案的情形,在此情形下當事人的調解協議尚需得到登記機關的確認方得有效,故其當然屬于涉外協議離婚的范圍,而此種結果與前次法院的訴訟行為已無任何關系。因此,筆者以為從實踐操作的角度而言,討論上述問題根本不具有現實的可能性,而實踐中至今也未出現此類案件。
(二)第26 條的準據法適用范圍
在界定了《法律適用法》第26 條適用的案件類型后,假如我國法院在這些案件類型中依據第26條的指引找到應當適用的準據法,那么這一準據法的適用范圍究竟是僅限于協議離婚的效力問題,還是可以在因協議離婚而導致的夫妻財產分割、子女撫養等方面也發揮同樣的作用?
對于這一問題,我國國際私法學界和實務界存在三種看法:一是狹義說,即認為既然《法律適用法》已經就夫妻人身關系(第23 條)、夫妻財產關系(第24 條)、父母子女關系(第25 條)、涉外撫養關系(第29 條)分別作出規定,那么從邏輯上推斷,離婚的法律適用針對的僅是婚姻關系的解除,即離婚的理由;〔27〕參見汪金蘭:《中歐涉外離婚法律適用法的新趨勢》,載黃進、肖永平、劉仁山主編:《中國國際私法與比較法年刊》第15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165 頁;汪晶、劉仁山:《我國涉外離婚法律適用立法之完善——兼論〈羅馬Ⅲ〉對我國相關規定的借鑒》,載《湖南社會科學》2013 年第6 期,第92 頁。二是中義說,認為離婚的效力應包含離婚以及因離婚而引起的財產分割,其理據為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88 條的規定;〔28〕1988 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88 條規定:“我國法院受理的涉外離婚案件,離婚以及因離婚而引起的財產分割,適用我國法律。認定其婚姻是否有效,適用婚姻締結地法律。”參見劉元元:《我國涉外離婚法律適用規則的新發展及反思》,載黃進、肖永平、劉仁山主編:《中國國際私法與比較法年刊》第1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46 頁。三是廣義說,這一說法乃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見,認為第26 條適用于協議離婚的實質要件即離婚條件、財產分配、夫妻扶養及子女撫養等問題。也就是說,當事人協議離婚在條件及離婚相關事項均需符合選擇的準據法的規定。〔29〕參見萬鄂湘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條文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 年版,第194 頁。
在目前無法可依的情況下,筆者持廣義說的觀點。理由有二:一是離婚協議的性質是一項混合法律行為,在多數涉外離婚協議中,解除夫妻間婚姻關系的法律行為與后續財產分割、子女撫養的法律行為之間形成了強大的牽連關系,前者的有效成立構成后者的生效要件,故如果將其分割適用不同的沖突規范,與兩類法律行為之間牽連性的本質不符;二是協議離婚與訴訟離婚最大區別在于當事人往往對于是否離婚以及離婚后財產與人身關系的變動有著清晰的約定,且實踐中有時是否愿意離婚還會以離婚后財產與人身關系的約定作為前提和“對價”,故針對當事人整體性的意思表示應以統一適用準據法為方案。至于離婚協議未涉及的財產分割或扶養事項,則不屬于第26 條的范圍,而屬于第27 條訴訟離婚的范圍。〔30〕需要比較說明的是,對《法律適用法》第27 條“訴訟離婚”準據法的適用范圍,最高人民法院的觀點認為其也適用于離婚所產生的夫妻人身關系、財產分割、子女扶養等關系。萬鄂湘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條文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 年版,第205 頁。而按照部分實務界法官的觀點,《法律適用法》第27 條解決的是離婚后的法律關系,自然包括當事人離婚之后,再次請求財產分配的“離婚后財產糾紛”。王姝:《意思自治原則在涉外婚姻司法實踐中的困境與出路——兼評〈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 24、26 條》,載《法律適用》2017 年第23 期,第115 頁。未來應在立法或司法解釋中界定26 條準據法的范圍。
五、結論
通過以上問題的厘清,我們可以對《法律適用法》第26 條的未來發展作出一個基本的判斷:雖然協議離婚制度并未獲得各國立法的一致認可,但在我國無法解決雙軌制立法的現實背景下,第26 條具有獨立的規范價值。2020 年5 月28 日我國《民法典》正式通過,《民法典》對協議離婚制度進行了多方面的完善,其中之一便是從民事立法層面確立了“協議離婚=離婚協議+登記”的公式表達。〔31〕202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076 條:“夫妻雙方自愿離婚的,應當簽訂書面離婚協議,并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申請離婚登記。離婚協議應當載明雙方自愿離婚的意思表示和對子女撫養、財產以及債務處理等事項協商一致的意見。”因此,《民法典》的這種變動為《法律適用法》第26 條的修正提供了實體法基礎,在未來《法律適用法》的修法過程中,應當將現有第26 條范圍中“協議離婚”的措辭變更為“離婚協議”。這樣做的目的是明確區分協議離婚的實質要件(離婚協議效力)與形式要件(要式行為)兩部分,把現有第26 條的適用范圍限縮為協議離婚的實質要件,而協議離婚的形式要件則因其公法性質僅可適用“辦理離婚手續登記機構所在地法律”。順應這種修法意見,在未來涉外離婚的司法實踐領域,《法律適用法》第26 條應當適用于我國法院受理的涉外協議離婚有效性糾紛、以離婚協議的效力為先決問題的婚姻家庭糾紛以及離婚協議生效后的履行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