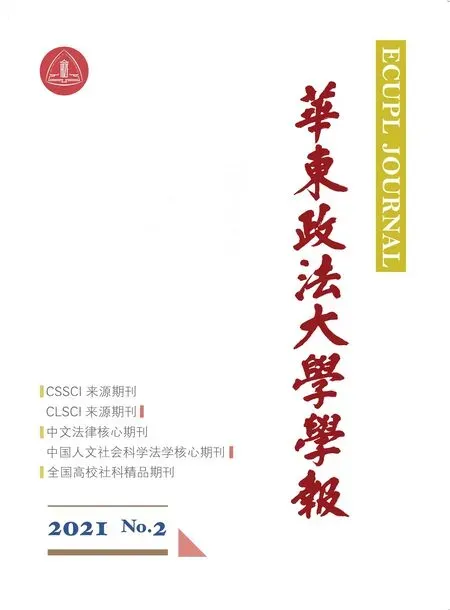維多利亞時代的困惑:領事裁判權與治外法權之惡
[英]柯安德 著屈文生 詹繼續 譯
在克里米亞戰爭行將結束之際,英法奧三國的戰略要務在于建立一道堅強的堡壘,以抵制俄羅斯在地中海的野心。1856 年3 月,強烈的結盟欲望促成了《巴黎條約》第7 條的誕生,是條的要義為奧斯曼帝國被“獲準共享歐洲公法與外交協同體(Public Law and System/Concert of Europe)的益處”。〔1〕Augustus H. Oakes and Robert B. Mowat eds., The Great European Treat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larendon Press, 1918, p.177.該俱樂部吸收非基督教國家作為其成員,尚屬首次;然而這個例外卻也暴露出19 世紀國際關系中的斷層線。既然加盟意味著享有完整的主權,那歐洲人在奧斯曼帝國卻享有治外法權(削弱了奧斯曼帝國主權)又該作何解?意識到這種曖昧后,歐洲各國駐奧斯曼帝國的全權代表們曾鄭重聲明會在君士坦丁堡就治外法權問題召開一次多邊會議。〔2〕“全權代表們一致認識到修改奧斯曼帝國讓步協定的必要性,并在議定書內將記錄了他們希望在君士坦丁堡展開磋商的愿望”。Protocols of Conferences Held at Paris Relative to the General Treaty of Peace, Foreign Office, 1856, p.59.但這場會議從未召開。與俄國發生新軍事沖突后,19世紀70 年代以降訂立的一系列條約不過強化了既有的安排,固化了奧斯曼帝國最后幾十年統治“主權未定”(hanging sovereignty)或“主權擱置”(sovereignty in abeyance)情狀而已。〔3〕Eliana Augusti, “From Capitulations to Unequal Treaties: The Matter of an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24 Journal of Civil Law Studies 286, 307(2011).
在一個以狹隘的“文明國家內核圈”為中心的全球秩序中,被“歐洲協同體”(Concert of Europe)接納只能是一場皮洛士式的勝利(pyrrhic victory)。〔4〕“內核圈”的說法是特維斯爵士對世界國家(civitas maxima)的解讀,改變了包含“所有國家”的普遍解釋,而這種說法是由沃爾夫(Christian Wolff)在十八世紀提出的。Jennifer Pitts, “Empire and Legal Universalisms”, 17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1(2012).隨著成員國遍及大西洋沿岸國家,歐洲協同體體系突破了原來的地域,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國際禮讓(Comity of Nations)框架逐漸為人所接受。〔5〕雖然“國際禮讓”這一術語可以追溯至1862 年,但其使用其實更早。Harris to Cass, 11 Sep. 1858,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Townsend Harris Collection Letter book 4, Correspondence no. 30.威斯特伐利亞主權模式(Westphalian model of sovereignty)乃歐洲人的杰作,被認為具有普適性。〔6〕威斯特法利亞主權模式意味著一個國家在其領土范圍之內享有排他性權威。Stephan Krasner,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0-25.拉丁美洲的一眾新共和國甫一成立,即被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完全接納。〔7〕Turan Kayaoglu, Legal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Extraterritoriality in Japa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7.盡管這些新共和國要么政權不穩,要么統治腐敗,但是歐洲各國認為這些新生國家對于國際法的理解同它們一致。即便是夏威夷王國(Kingdom of Hawaii),當它在1846 年同英法兩國締結條約后,也被給予了完全主權國家的地位——這個在1820 年皈依了基督教的王國,由此成為首個被納入“國際大家庭”的非歐洲原住民國家(indigenous state)。〔8〕夏威夷王國先后處于英國和美國的保護中,直到1893 年滅亡。Lorenz Gonschor,“ Ka Hoku o Osiania: Promoting the Hawaiian Kingdom as a Model for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Oceania”, in Sebastian Jobs & Gesa Mackenthun eds., Agents of Tansculturation: Border-Crossers, Mediators, Go-Betweens, Waxmann, 2013, p.159.
但是,歐洲各國與東方的非基督教國家間不存在這樣的共識。奧斯曼帝國的習俗、宗教和法律與歐洲的是如此迥異,以至于在奧斯曼帝國的威尼斯人、熱那亞人及其他歐洲商人依照所謂“單方讓步協定”(capitulations)的特許權,長久以來享有豁免權。這些協定給予在奧斯曼帝國的外國人以治外法權,將他們置于本國領事的保護之下。〔9〕這種賦予領事超出本國人的司法權力的實踐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的地中海地區。Andreas T. Muller, “Friedrich F. Martens on ‘The Office of Consul and Consular Jurisdiction in the East’”, 25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78(2014).最初,這些特權只是君主(1536 年蘇萊曼大帝曾向法國國王授予這種特權)的賞賜,在彼時這些特權則被人們看作是與生俱來的權利。〔10〕“這些特權并非利用蘇丹人的弱點并使用強力獲得的;奧斯曼家族曾經是歐洲的恐怖之源,這些特權只是那一時期的遺留問題。” “Turkey (from our correspondent)”, The Times, 3 May 1854, p.10. 正式的個人許可和讓步協定是在1740 年與法國簽署條約時被載入。孟德斯鳩等人形成了這樣一種信念:歐洲人有權免受東方暴君用以奴役歐洲各國臣民之野蠻法律的管轄。對所謂暴政和酷刑的恐懼,為西方列強與清朝(1842 年)、暹羅(1855 年)和日本(1858 年)以訂立條約的方式來獲得類似特權提供了借口。〔11〕1842 年《南京條約》并沒有出現領事裁判權的表述,第一次出現是在1843 年《虎門條約》。
治外法權由此成為19 世紀延伸至東亞的條約口岸體制中的一則關鍵問題。1843 年英國《域外管轄權法案》(Foreign Jurisdiction Act)為治外法權提供了法律依據,確認了英國域外法院依“條約、單方讓步協定、許可狀(grant)、習慣(usage)、默許(sufferance)和其他合法方式”而獲得的權力。〔12〕1843 年《域外管轄權法案》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1825 年英格蘭黎凡特公司解散后所產生的法律問題。Turan Kayaoglu, Legal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Extraterritoriality in Japa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44.然而,在《巴黎條約》簽署不久,有人對領事裁判權的道義性甚至正義性提出了質疑。1856 年10 月,它成為發生在廣州的“亞羅號”事件的核心問題,該事件導致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兩年后,《天津條約》的訂立使更多的外國租界得以在中國建立,《日英修好通商條約》中確立的類似條款將英國領事引入日本后,這種質疑變得有增無減。〔13〕盡管存在出島的荷蘭工廠廠長這樣的先例,但是“領事”在日本是一個新詞匯,領事裁判權濫觴于條約口岸的開通。See Michael Auslin, Negotiating with Imperialism: The Unequal Treaties and the Culture of Japanese Diplom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5.本文旨在分析這項爭議話題在維多利亞時代政治話語中出現的緣起。文章意在梳理英國人早在國外針對治外法權問題爆發抗議前即已產生的矛盾心理。從短期來看,隨著針對治外法權問題之辯論的徐徐展開,這些異議僅引起了政府有限的回應,其影響似乎僅限于針對英國人早先制定的某些辦法和針對混合法院做出的某些改變。但這些不同聲音最終得到更多人的關注,其影響波及的邊界并未止于國際法界,也為日本等國提出反抗領事裁判權制度的立論提供了重要啟發。
一、維多利亞時期不滿初現
在國際關系中,治外法權問題彼時出現在關于跨國流動和全球化是否有可能削弱威斯特伐利亞主權國家的辯論之中。〔14〕Teemu Ruskola, Legal Orientalis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dern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40.治外法權這一術語的不斷使用重新喚起了人們研究其歷史的興趣。〔15〕See Turan Kayaoglu, Legal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Extraterritoriality in Japa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r Kristoffer Cassel, Grounds of Judgment: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但是,法學界對于治外法權的研究從未真正停下來過。例如,1943 年《中美新約》或許已經廢除了治外法權,但是一則新的補充協議馬上為美國軍人在全球軍事基地確立了“徹底免受當地法律管轄”的法律保護框架;〔16〕Teemu Ruskola, Legal Orientalis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dern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04; Turan Kayaoglu, Legal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Extraterritoriality in Japa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88, 198.就沖繩問題論,《美日駐軍地位協定》(US-Japan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在今天仍是政治關系緊張的根源。此外,從網絡空間的增長、跨國企業的整頓到保護難民、引渡和關塔那摩監獄關押的期限等一系列問題均涉及治外法權。〔17〕See Jodie A. Kirshner, “Why is the U.S. Abdicating the Policing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o Europe? Extraterritoriality, Sovereignty, and the Alien Tort Statute”, 30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59-302(2012).
在中東和東亞的近代史上,反抗治外法權是反抗西方奴役斗爭敘事中的重要主題。早在19 世紀中期前,奧斯曼帝國已有政治家指出治外法權的影響貽害無窮。在1856 年巴黎和會上,“大維齊爾”阿里·帕夏(Grand Vizier Ali Pasha)不滿于治外法權,并稱其“在政府里另立了小政府,終于成為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礙,阻礙了所有的進步”。〔18〕Mariya T. Slys, Exporting Legality: The Rise and Fall of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China, Graduate Institute Publications, 2014, p.52.在東亞,這種意識還有待明晰,但到19 世紀70 年代,治外法權已成為日本明治政府修約運動中的主要抨擊對象。治外法權也是中華民國在1925 年向國際聯盟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訴求時的重要矛頭指向。到這一階段,隨著1894 年《日英通商航海條約》(Aoki- Kimberley Treaty)在1899 年生效,治外法權在日本得以廢除;土耳其也在1923 年的《洛桑條約》(Treaty of Lausanne)中廢除了治外法權。緊接著,波斯和泰國先后在1928 年和1938 年也廢除了治外法權,但它在中國直到1943 年才被廢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直至1949 年治外法權的實踐依然存在于埃及的混合法院,在摩洛哥的丹吉爾國際共管區(International Zone at Tangier)則直到1956 年還存在。〔19〕Jasper Brinton, The Mixed Courts of Egyp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25, 208; Teemu Ruskola, Legal Orientalis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dern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203,308-309.即使在那時,英國王室在整個波斯灣(除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對非穆斯林外國人仍行使治外管轄權;在科威特,治外法權直到1961 年才消失,在馬斯喀特(Muscat)是1967 年,在其他地方則遲至1971 年才被廢除。〔20〕William M. Ballantyne, Essays and Addresses on Arab Laws, Curzon Press, 2000, p.127.
對于治外法權制度(extraterritorial regimes)的反抗并不是一夜之間出現的。領事裁判權在日常運行過程中產生的實際問題,一直以來都是顯而易見的,但倘若沒有國際法作為底色,其理論意義就不那么明顯。不唯此,與“單方讓步協定”及其他法律多元主義傳統形式不相容的主權觀念也是到19世紀前幾十年里在國際法“實證轉向”出現后才被引入。例如,遲至18 世紀90 年代,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印度總督沃倫·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被彈劾一案中,還在為印度競合交錯的管轄體系辯護。〔21〕Jennifer Pitts, “Empire and Legal Universalisms”, 17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2 (2012).但是,隨著美國法學家亨利·惠頓(Henry Wheaton)在1836 年寫明“專屬的民事與刑事的立法權是……每一個獨立國家享有的基本權利”,一種與陳說顯然不合的觀點才逐漸形成。〔22〕Henry Wh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rey, Lea & Blanchard, 1836, p.98.依據這一架構,治外法權作為普遍規則的例外,只有通過“明示條約”方可存在。〔23〕Henry Wheaton,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rey, Lea & Blanchard, 1836, pp.109-110.
因此,在治外法權成為萬夫所指的問題之前,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從君士坦丁堡到江戶,知識精英們試圖運用本國的文化術語來消化這些外來概念。〔24〕東亞學者經常從自然法角度理解這些西方思想,而這些思想又和他們自身的儒家思想有相似之處。See Ohira Zengo, “Japan’s Reception of the Law of Nations”, 4 The Annals of the Hitotsubashi Academy 58, 62-63(1953). 實證法從未完全取代自然法,自然法仍然繼續為維多利亞時代理論家對歐洲法律的普遍主義愿望提供思想源泉。Jennifer Pitts, “Boundaries of Victorian International Law”, in Duncan Bell ed., Victorian Visions of Global Order: Empi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69.他們最初接觸的“各國律例”(Law of Nations)來自照會文件,緊接著他們有機會讀到了翻譯過來的法律文本。在奧斯曼帝國,這些西方理念孕育于1839 年坦志麥特(Tanz?mat,即重組時期)法律改革時期。此前一年,奧斯曼帝國與英國和法國簽訂了新的商業條約。在東亞,國際法理念的引入,是伴隨1864 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漢譯惠頓《萬國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以及日本首批赴歐洲學習國際法留學生的歸來而實現的。〔25〕例如,西周(Nishi Amane)于1863-1865 年在萊頓大學學習,1868 年出版了西蒙·菲塞林(Simon Vissering)所授課程的聽課筆記。福地源一郎在1865-1866 年間游歷了英國和法國,1869 年出版了卡爾·馮·馬頓斯的《外交指南》。譯者注:Guide diplomatique 于1876 年在同文館教習丁韙良的主持下翻譯并出版了中文版,名為《星軺指掌》。
在克服語言或文化障礙后,一些英國觀察家對領事裁判權表達了保留意見。例如,英國外交大臣阿伯丁勛爵(Lord Aberdeen)在評價1829 年《亞德里亞堡和約》(Treaty of Adrianople)時稱,“該條約賦予俄國臣民的商業特權和豁免權,似乎與我們對于君主和獨立王公之權威已經形成的所有觀念并不一致。”阿伯丁勛爵最關心的是俄國對于奧斯曼土耳其的侵犯,但他在解釋“土耳其政府司法的缺陷”是如何形成這種異常時,實際上背叛了他那個時代的西方文化優越論。〔26〕Aberdeen to Heytesbury, no. 22, 31 Oct. 1829, [Kew, United Kingdom National Archives, Public Record Office], F[oreign] O[ffice Records] 181/78; British Library, Aberdeen MSS, Additional MSS 43089, fo. 110.二十五年后的1854 年,當阿伯丁聯合政府發動克里米亞行動時,載有上述言論的公文在議會浮現并通過媒體傳播開來。〔27〕如《亞德里亞堡條約》,The Times, 28 June 1854, p.9; “Further English Extracts, by the Steamer Asia at this Port”, New York Daily Times, 14 July 1854, p.2.根據《泰晤士報》駐君士坦丁堡記者,“單方讓步協定制度”(the system of capitulations)成為彼時“重要的改革議題”,因為各國在奧斯曼土耳其行使管轄權的“方式與國家獨立和主權理念相抵牾”。〔28〕“Turkey (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 The Times, 3 May 1854, p.10.該記者不情愿地承認,盡管“土耳其法院的確可憎”,但是,更加應當譴責的是,“單方讓步協定之惡帶來的影響和對外國干涉的合法化,這兩大問題在帝國的各個區域和各社會階層帶來的影響,才是更應得到重視的”。〔29〕“Turkey (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 The Times, 11 Sep. 1854, p.8.
至這一時期,英國的外交官愈加懷疑俄國和法國向奧斯曼帝國內東正教和天主教教徒提供保護的動機。與此同時,英國人也開始在奧培植他們自己的被保護人(protégés),這些被保護人多來自愛奧尼亞群島或馬耳他,這兩地自1815 年即成為英國的保護領地,“更不消說還有那些以某種借口設法獲得英國護照的真正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30〕Sir Edmund Hornby, Sir Edmund Hornby: An Autobiography, Constable, 1929, p.93.正如特立獨行的英國外交官尤斯塔斯·格倫維爾-穆雷(Eustace Grenville-Murray)以“流浪的英國人”為筆名在1855 年記錄的那樣,“一個臭名昭著的事實是,賦予臣民般特權的英國護照很容易就簽發給了外國人,尤其是在黎凡特地區(the Levant)。”〔31〕Eustace Clare Grenville Murray, The Roving Englishman in Turkey: Sketches from Life(1855 年首次出版),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877, p.74; 關于格倫維爾-穆雷的波折命運,See Geoffrey R. Berridge, Diplomatic Whistleblower in the Victorian Era: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E. C. Grenville-Murray (online publication, 2nd edition: grberridge.diplomacy.edu, Dec. 2014).新近發布的“樞密院令”依據《域外管轄權法案》賦予那些生活在土耳其、中國、暹羅和日本等及中國澳門英國領事和副領事非常廣泛和特別的權力。很多時候,這些權力可使他們不受任何英國法院或治安法官管轄,其權限甚至超過了任何法院或任何一位英國殖民地總督所享有的權力,〔32〕Law Officers to Russell, 30 July 1860, FO 83/2298, fo. 70.對此,英國王室司法官也不無擔憂。此外,在整個中東,語言帶來的問題甚至迫使外交部不得不聘請當地的英國商人擔任領事職位。用當時還只是一名君士坦丁堡年輕官員的洪卑(Edmund Hornby)的話來說:“整個黎凡特地區的權力系統全已失控。”〔33〕Sir Edmund Hornby, Sir Edmund Hornby: An Autobiography, Constable, 1929, p.138.
1856 年,巴黎會議上的歐洲外交家們認定是治外法權出現了問題。如阿里·帕夏(Ali Pasha)指出的那樣,治外法權甚至還給貿易帶來障礙,而受阻的貿易正是他們擬解決的問題。〔34〕Turan Kayaoglu, Legal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Extraterritoriality in Japa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21.為了牽制俄國,他們建議改良治外法權,但改良全倚仗奧斯曼帝國的法律改革,其結果離廢除治外法權的目標還差得很遠。為了回應這些聲音,洪卑受托提交一份關于無法律教育或執業背景的英國領事行使司法權問題的報告。1857 年,樞密院在這份報告的基礎上下令建立了英國駐君士坦丁堡最高法院—— 一個由訓練有素的法官組成的全新終審法院。〔35〕Sir Edmund Hornby, Sir Edmund Hornby: An Autobiography, Constable, 1929, p.94.到1867 年,新的磋商又催生了一部新的土地法典,該法最終賦予外國人在奧斯曼帝國擁有財產的權利。巴黎會議上提出的問題并未消失,但是似乎正在得到解決。與此同時,英國政界對治外法權的視線轉向了東亞。在這里,領事裁判權似乎是引發“維多利亞女王之局部戰爭”(Queen Victoria’s Little Wars)的主要因素。〔36〕克里米亞戰爭后的十年里,英國軍隊入侵了印度、中國、沙撈越、新西蘭、黃金海岸、暹羅、日本、不丹、牙買加、阿拉伯和加拿大,See Byron Farwell, Queen Victoria’s Little Wars, Allen Lane, 1973, pp.134-137, 163.治外法權在東亞不僅是“東方問題”(Eastern Question)的構成部分,也并不僅局限于中國或日本,它充斥在針對整個英國外交政策的更多論辯之中。
二、維多利亞時期政治思想中的治外法權
早在1856 年,就在巴黎會議解決克里米亞戰爭的同時,印度總督達爾豪斯伯爵(Lord Dalhousie)宣布吞并烏德(Oudh)的消息傳了出來。印度兵變(1857—1858)、日本開放通商口岸(1859)和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1858—1860)后英國商貿向長江盆地的擴張等,進一步加劇了英國外交部的工作負荷。在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這一頂峰期,人們普遍相信英國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全球貿易帶來的是仁慈的甚至是具有教化意義的影響。但是,一些反對者的聲音表示他們并不確定英國的這種責任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他們對殖民地人民的福祉表達人道主義關切,他們的不干涉呼吁反應出對帝國過度擴張產生的越來越強烈的不安。〔37〕Gregory Claeys, “The ‘Left’ and the Critique of Empire c. 1865-1900: Three Roots of Humanitarian Foreign Policy”, in Bell ed., Victorian Visions of Global Order, pp.239-266.
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等支持自由貿易的人士對大英帝國征戰四方批判得最為激烈。盡管科布登主義者(Cobdenite),或稱曼徹斯特學派(Manchester School),并不完全反對帝國擴張,但是他們認為能夠帶來持久繁榮的道路是商業而非戰爭。東亞當時發生的涉及領事事件也引發了人們對治外法權問題的關注。在參考國際法有關文本后,政治家們使用了一種老套但卻十分奏效的修辭手段,通過假言對比,強調了歐洲對非基督教國家采取的是雙重標準。這種思路可引起人們對“文明”本質的反思。
比如說,1857 年2 月科布登在下議院對于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的譴責,對巴麥尊勛爵政府的下臺(盡管只是暫時的)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38〕巴麥尊通過大選擊敗了曼徹斯特學派重掌權力。戰爭斷斷續續地一直持續到1860 年。“China”, Commons debate, 26 Feb. 1857, Hansard, vol. 144, cols. 1391-1421.科布登譴責道:在“亞羅號”事件的處理上,英國方面于法不合。在他看來,對于廣州官兵登上中國船只逮捕疑似中國籍海盜船員的行為,英駐廣州領事巴夏禮(Harry Parkes)并無權申訴,更不消說訴諸武力。科布登對巴夏禮所謂此舉有損英國國家榮譽的說法也提出了質疑,因為他們在此過程中扯下船上懸掛的英國艦旗(British ensign)的指控從未被證實。顯然,這艘船只上懸掛的只是方便旗(flag of convenience),旗子只是這艘船只的中國船主在香港將其登記為“亞羅號”時獲得的而已,更遑論這艘船的執照實際上已經過期。〔39〕John Y. Wong, 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1860)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4-5, 44-45, 53-54, 78.科布登斷言,這起事件若發生在查爾斯頓(這里指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港口城市),英國駐華盛頓大使會令在場英國官員向南卡羅來納州的州長道歉,而絕無可能像其對待兩廣總督葉名琛那樣要求獲得賠償。他對利物浦商人呼吁的“值百抽五”進出口稅則也頗不以為然,“我倒是希望在利物浦適用的稅則是5%。”至于英國人將所有中國沿海沿江口岸向英國船只開放的要求,他質問道,如果俄羅斯沙皇向土耳其宣布類似的計劃,英國人該做何反應?科布登問,“如果俄國向我們下達了要求開放所有口岸的沙皇敕令(ukase),這件事的嚴重程度只會比在利物浦發生爆炸事件更甚,你能想象還有什么事比此更加令人驚訝的嗎?”〔40〕在俄語里,“ukase”是指帝國政令。“China”, Commons debate, 26 Feb. 1857, Hansard, vol. 144, col. 1410.
1858 年,在《天津條約》中止了軍事行動后,治外法權問題在上議院再度遭受抨擊。英國人此時在整個中國都享有特權,但作為前殖民地大臣和早期自由貿易的倡導者,亨利·格雷(Henry Grey)對中英和平關系前景表示擔憂。他發現,即便在現有的條約口岸,領事不得不疲于應付“看管與審查在其監督之下所有英國商人的行為。”格雷認為,那些選擇在中國營利的商人應當自擔風險,因為“在沒有英國警察、英國法院及維持秩序與和平之手段對他們約束的情況下,只是接受英國法律的審判,法律不被其濫用是完全不可能的。”〔41〕“China-Address for Papers”, Lords debate, 19 Feb. 1861, Hansard, vol. 161, cols. 550, 581.
盡管格雷只是持此觀點的少數派,但并非只有他一人為英國在亞洲的擴張而感到擔憂。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作為東印度公司的前雇員,也對即將出現的統治(Raj)持保留態度。〔42〕Jennifer Pitts, “Empire and Legal Universalisms”, 17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7(2012).類似的,高產作家弗朗西斯·威廉·紐曼(Francis William Newman)也將印度兵變(Sepoy Rebellion)后的動亂歸責于達爾豪斯所持的那個頗有爭議的“無嗣便失權原則”(doctrine of lapse)——這一原則一直用作攫取領地的“正當機會”。紐曼在《威斯敏斯特評論》(Westminster Review)發表的文章認為,英國在1858 年仍然有義務與新并入的印度各邦維持“國際”關系,并指責達爾豪斯采取的手段是英國整個國家外交政策的表癥。紐曼解釋說,“英國政治家對亞洲人(Asiatics)所說的正義(just)這個詞,指的是‘根據條約’,但他們全然不顧該條約是不是通過不合理的暴力手段而訂立(正如我們與印度土邦烏德訂立的所有條約),也不關心條約一方是否擁有任何法律或道德上的訂約權。”〔43〕Francis William Newman, “Our Relation to the Princes of India”, 69 Westminster Review 463 (1858).
例如新訂《天津條約》〔44〕譯者注:《天津條約》內該款原文為:“兩國交涉事件,彼此均須會同公平審斷,以昭允當”,實際上誤譯,因為原文并不含“會同”之意,而該譯文為英國取得案件的“會審權”埋下了伏筆。1844 年中美《望廈條約》第二十一款的譯文“須兩得其平,秉公斷結,不得各存偏護,致啟爭端”是正確的。和《江戶條約》(即《日本國美利堅合眾國修好通商條約》)均規定“Justice shall be equitably and impartially administered on both sides(司法案件須兩得其平,秉公斷結,不得各存偏護)”。〔45〕Hertslet’s Commercial Treaties (31 vols.,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840-25), xi. 90, 398.但就中國而言,這款明顯是戰爭強加的;英國與日本簽署的該條約,則似乎堪稱“和”(peaceable)約。然而,英國駐日公使阿禮國(Sir Rutherford Alcock)在其1863 年出版的兩卷本回憶錄《大君之都》(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中記載稱,美國駐日公使湯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正是借助英國軍事力量才促成了這一里程碑條約的訂立。〔46〕Sir Rutherford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 Residence in Japan (2 Vols.), Longman, Green, Longman, Roberts & Green, 1863, Vol. 1, pp.199-200.哈里斯1857 年在江戶城堡(Edo Castle)接受采訪時,無疑夸大了香港總督包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致其若干信函的重要性——哈里斯警告日本“英國政府……準備好了同日本交戰”。〔47〕William G. Beasley ed.,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853-186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161.是故,格雷在上議院報告時稱,所有這些條約“都是城下之盟”。〔48〕“Japan-Resolutions”, Lords debate, 1 July 1864, Hansard, vol. 176, col. 574.根據哈里斯的說法,額爾金“告訴日本專員,如果他們延遲履行條約,他將立即離開,并且很快會帶領一支50 艘船組成的艦隊返回。”Harris to Cass, 11 Sep. 1858, THC, Letterbox 4, Correspondence no. 30. 給哈里斯傳達信息的是他的翻譯Henry Heusken,額爾金曾在會談時向哈里斯借過這名翻譯,但是額爾金的這種威脅并沒有出現在Laurence Oliphant 所記載的那些友好會談的記錄中,See Narrative of the Earl of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in the Years 1857,’58,’59, William Blackwood & Sons, 1859.
格雷很快就成為“治外法權這一以惡名著稱之條款”(筆者不清楚誰發明了這一說法)最有力的批判者。〔49〕“Japan-Address for Papers”, Lords debate, 10 July 1863. Hansard, vol. 172, col. 524.在刻畫條約口岸處于一種近似無政府狀態時,他的觀點透出他對海外商人群體的一絲成見。來自威斯敏斯特的觀點,也反映出英國外交家對在日英商持有偏見。〔50〕Yuki A. Honjo, Japan’s Early Experience of Contract Management in the Treaty Ports, Japan Library, 2003, p.34.格雷在解讀阿禮國之記載時認為,“在世上任何別的國家中都找不到如此眾多膽大妄為、無法無天之人”。〔51〕“Japan-Address for papers”, Lords debate, 10 July 1863. Hansard, vol. 172, cols. 524-525. 阿禮國這樣寫道:沒有更大規模的人群涌入,有的只是來自世界各地無法無天的浪蕩淘金客。Sir Rutherford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 Residence in Japan, Longman, Green, Longman, Roberts & Green, 1863, Vol. 2, p.33.類似地,在1860年一次訪日途中,維多利亞教區主教施美夫(George Smith,bishop of Victoria)發現橫濱到處都是“無法無天的加利福尼亞冒險分子、葡萄牙亡命之徒、逃亡的水手、逍遙法外的海盜及歐洲各國道德淪喪的廢物。”〔52〕George Smith, Bishop of Victoria (Hong Kong), Ten Weeks in Japan, Longman, Green, Longman & Roberts, 1861, p.263.可嘆的是,管理這群不羈之徒的領事們從不敢自詡接受過多少法律培訓,在這一時期的清朝和日本,所有死刑案件或上訴案件均交由香港的最高法院審理。正如格雷所說,“假如法國有權說,在英國犯罪的法國人不接受除法國當局之外做出的任何刑罰,若在法國還未在英國設立法院的情況下,我敢保證,倫敦會在24 小時內被洗劫一空。”〔53〕“Japan-Address for papers”, Lords debate, 10 July 1863. Hansard, vol. 172, col. 531.
即便沒有憤懣的日本武士潛伏在周圍,僅有人們對于治外特權的疑惑,也足以令在橫濱的外國人群體處于不安之中。商人并不樂見自己被喚作“歐洲的渣滓”,在阿禮國離開日本之前,就連英國外交官也不被允許進入橫濱俱樂部。〔54〕Francis C. Jones, Extraterritoriality in Japa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1, p.54.邁克·莫斯案(case of Michael Moss)的發生構成事件的轉折點。邁克·莫斯是一名年輕商人,1860 年11 月,他因違反禁獵規定及在距離江戶城25 英里范圍內不得使用火器的法律而拒捕時,有意射擊并重傷了一位日本護衛。法國《祖國》(La Patrie)雜志當時的評論是,“外國人膽敢在溫莎森林(Windsor forest)或在法國的森林里開槍的,會發現他們會立刻受到法律的懲處”。〔55〕Henry E. J. Stanley ed., The East and the West: Our Dealings with our Neighbours, Hatchard & Co., 1865, p.12.莫斯在當地監獄僅被關了數個鐘頭后,便被英國領事保了出來,領事法院對他處以罰金和驅逐出境的處罰。然而,橫濱當地的英國人竟組織了募捐活動以籌措這筆罰金,就連阿禮國試圖再關其三個月禁閉的判決也被香港最高法院推翻。阿禮國被英國商人在保衛莫斯時所展示出的恫嚇所刺痛,遂下令對領事裁判制度作出切實改革。他主張宜在香港任命訓練有素的法官,然后再根據實際需求,將這些法官派遣到條約口岸,如此“這些英國人就可以不再被趕鴨子上架而充當‘稚嫩的領事’(boy consul)和‘外行的法官’(lay justice)”。〔56〕Sir Rutherford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 Residence in Japan, Longman, Green, Longman, Roberts & Green, 1863, Vol. 2, p.29.至于駐君士坦丁堡最高法院,阿禮國補充道,“黎凡特地區已經成功地推行了這種或者類似的制度。”〔57〕Sir Rutherford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 Residence in Japan, Longman, Green, Longman, Roberts & Green, 1863, Vol. 2, p.30.
到1863 年,日本日益不穩定的局勢使作戰部隊面臨著卷入到該局面的危險之中來。在格雷向上議院進言后不久,就有消息稱一支皇家海軍中隊已開向薩摩藩,為英國商人查理斯·理查森(Charles Lennox Richardson)一年前在此地被殺而討公道。1862 年9 月2 日,查理斯·理查森在靠近橫濱城騎馬時被大名對列(daimyo procession)的護衛砍死。在格雷看來,無論這場致命襲擊是不是因受害人挑釁而起,都是外國人群體失去控制的征兆。〔58〕關于理察遜的聲譽和可能犯下的不法行為,參見Mitsuru Hashimoto and Betsey Scheiner, Collision at Namamugi, Representations, no. 18, 1987, pp.76-77.這起事件無疑加深了施美夫在其見聞錄中形成的印象,“我在日本各地看到的景象是,英國人和我熟悉的其他人在村莊和城市郊區的人群中橫沖直撞,人們驚慌失措,倉皇地向兩邊躲避,好讓自己不被撞倒”。〔59〕George Smith, Bishop of Victoria (Hong Kong), Ten Weeks in Japan, Longman, Green, Longman & Roberts, 1861, p.258.
鹿兒島轟炸的報道出現后,議會爭論的焦點轉移到了海軍行動之上。科布登公開稱,“這就好比敵人一把火將布里斯托燒掉是因為有人在倫敦至布倫特福德的公路上被謀害一樣荒謬”。〔60〕“Mr. Cobden on the Japanese Question”, The Times, 10 Nov. 1863, p.6.在引用瓦特爾(Vattel)和馬騰斯(de Martens)等法學家時,查爾斯·巴克斯頓(Charles Buxton)提醒下議院“摧毀城鎮是一種可惡可憎的辦法”,并提出“攻城者只能將大炮對準防御工事”的行為準則。〔61〕“Bombardment of Kagoshima-Resolution”, Commons debate, 9 Feb. 1864, Hansard, vol. 173, col. 341.在某種程度上,巴克斯頓的聽眾在發生于1862 年11 月暹羅南部的堪與炮襲鹿兒島事件相提并論的英國炮擊登嘉樓(Tringanu)事件后已經意識到了其中牽涉的邏輯困境。在這起事件中,他們獲悉“科貝特艦長(Captain Corbett)盡力只向宮殿和工事射擊,但由于船只旋轉的緣故,若干枚炮彈落在了人口稠密的鎮上而燃起了大火。”〔62〕Sir John Hay, “The Attack on Tringanu”, Commons debate, 10 July 1863, Hansard, vol. 172, col. 587.
與此同時,在守護下關海峽(Strait of Shimonoseki)長州藩(Chōshū domain)的若干炮臺向外國船艦開火及英國經過內海的貿易被封鎖后,1864 年的日本又隱約出現了英軍報復事件。為平息長州藩的炮火,阿禮國組建了聯合中隊,他因過于好戰而走到了威斯敏斯特的聚光燈之下。有人匿名向英國議會遞交了一份《在日外交》小冊子,將矛頭直指阿禮國,其大意是:應當受到責罰的不應是在日商人而是駐日領事,尤其是阿禮國,因為他樹立了一個壞榜樣。〔63〕阿禮國因為冒險進入肥前的一座礦井而受到人們的批評,格雷也在其向議員發表的演講中提及了此事。Diplomacy in Japan: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Japan, Blackwood, 1864, p.41; Sir Rutherford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 Residence in Japan, Longman, Green, Longman, Roberts & Green, 1863, Vol. 2, p.79.但是,最應受到批評的應當是條約本身才對,因為治外法權是“允許訂立該條款之國家所做的自殺性讓步”。〔64〕Diplomacy in Japan: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Japan, Blackwood, 1864, p.8.它只會給主張特權的人帶來麻煩,“對于加諸于英商群體之上的罵名,被視作是日本所有麻煩之始作俑者的他們可援用廣州等城市的事例為自己辯護——在這些地方,貿易安穩地繁榮了一百余年,就是因為那里先前沒有治外法權條款的存在”。〔65〕Eliana Augusti, “From Capitulations to Unequal Treaties: The Matter of an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24 Journal of Civil Law Studies 286, 307(2011).這一說辭美化了廣州貿易體系(Canton System),實際上廣州貿易體系從18 世紀中期確立到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經常是中英關系緊張的源頭。〔66〕轉折點是1784 年“休斯夫人號”事件,當時一名英國炮手在鳴禮炮時意外造成一名中國人死亡而被處以死刑。這起事件使得東印度公司自此以后不再向清朝移交英國的犯罪分子,See P?rKristoffer Cassel, Grounds of Judgment: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43.此外,這種說法也暗示出治外法權的失穩效應終究為害不淺的看法,“自治外法權制度確立二十年來,為使‘西方文明’處于支配地位,已打過三場戰爭”。〔67〕Diplomacy in Japan, iii.
這也是格雷向議員給出的暗示:“宜修訂條約,修正各項條款。”在為日本列出十二條解決方案之后,格雷建議,“當務之急是要限制被稱為‘治外法權’條款的運用”。比如說,格雷驚訝于英國駐橫濱領事竟需發布告示譴責“英國人養成的在鬧市里膽大妄為地騎快馬的習慣”。目前,日本當局似乎也無力“強制英國人執行自己的良好行為規范”,因為就像格雷評論的那樣:“如果英國水手在法國勒阿弗爾或美國紐約,或者美國或法國水手在英國利物浦,享有不受當地警察干涉的豁免權,如果他們只接受本國領事的處理,那么這些城市連一天的秩序與和平都休想維持。”如果治外法權總歸要保留下來,在他看來,也“只能將其限制在盡可能小的范圍內”。〔68〕“Japan-Resolutions”, Lords debate, 1 July 1864. Hansard, vol. 176, cols. 585, 589.
格雷的動議遭到否決,但他的十二條方案全文很快就出現在了《橫濱商業新聞報》上,并隨即被翻譯成日文。〔69〕Japan Commercial News, 7 Sep. 1864, 14 Sep. 1864.橫濱歷史檔案館沒有收藏原始英文文件,在其他地方也沒有找到。箕作麟祥的日文翻譯版收藏在慶應義塾大學,并收錄于Kitane Yutaka ed., Nihon shoki shin bun zenshu (64 vols., Tokyo: Perikansha, 1987), iv. 151-153, 169-172.與此同時,在倫敦,這些決議在1865 年出版的一部名為《東方與西方:與鄰居打交道》(The East and the West: Our Dealings with Our Neighbours)的論文集中再次出現。顯然,格雷的想法與文集主編亨利·斯坦利(Henry E. J. Stanley)不謀而合,讓他回憶起了自己在奧斯曼帝國擔任外交官的經歷。格雷在該書開篇《我們的領事制度》(Our Consular System)一文中回顧了源于奧斯曼單方讓步協定之外國人特權的演化史,并強調目前的制度安排已變得極易被濫用。例如,在君士坦丁堡,曾有英國輪船不顧當地人的抗議而在皇宮附近停泊,并“將輪船所有的煙霧從船窗排了出去”。曼谷也有類似的事件發生,當地的風俗習慣完全被無視,“在暹羅的大臣或貴族走水路從木橋前經過時,歐洲人以在運河上的小木橋上駐足為樂”。〔70〕Henry E. J. Stanley ed., The East and the West: Our Dealings with our Neighbours, Hatchard & Co., 1865, pp.10-11.
吃驚于“治外法權制度造成的損害”,斯坦利認為,“格雷的方案無法行得通,僅僅因為這些內容太過于實際,對于邪惡的根源瞄得太準。”〔71〕Henry E. J. Stanley ed., The East and the West: Our Dealings with our Neighbours, Hatchard & Co., 1865, pp.25, 32, 49.將領事裁判權引入日本是個極大的錯誤,“經驗證明它無法維持社會的秩序”。隨后,斯坦利列舉了十項原因,解釋為何“在解決日本國民與英國國民間發生糾紛時寄希望于領事可以公正執法的想法是虛幻的”。他確信“這些條約幾乎不會發生作用,即便有再好的機構,也于事無補”。鑒于在南美的法國人和英國人在沒有獲得類似保護的情況下也照樣可以應付得來,將領事數量至少減少到“直至這些過時的單方讓步協定在土耳其被廢除,與其他國家的條約得以修改,不至于像現在這樣成為戰爭的緣起和犯罪免于懲罰的借口時”才是合理的。〔72〕Henry E. J. Stanley ed., The East and the West: Our Dealings with our Neighbours, Hatchard & Co., 1865, pp.29, 47-49.
斯坦利上述對于領事管轄權公然敵視的評論,在珍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看來“可視作是維多利亞時代圍繞國際法范疇之辯論的挑釁時刻”。〔73〕Jennifer Pitts, “Empire and Legal Universalism”, 17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9 (2012).斯坦利的確異于常人,1859 年他在中東旅行時皈依伊斯蘭教,進而成為英國上議院第一位穆斯林貴族。這部文集內的其他文章討論了“作為政治體制的伊斯蘭教”及“希臘與俄國的教會”。他對僑胞的不屑可從中可見一斑,他宣稱,“每個持平的、曾在海外游歷并同外國人深入交往的英國人都不會否認,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在整個世界都是極不受歡迎的”。措辭最為強烈的指控則出現在“蔑視國際法之后果”一文中,他在該文中宣稱,“在19 世紀,作為口號的‘文明’取代了‘基督教’進而成為侵略的借口”。他揭露了“文明和非文明這種臆想的區分”,諷刺了那些為治外法權辯解的說辭。〔74〕Henry E. J. Stanley ed., The East and the West: Our Dealings with our Neighbours, Hatchard & Co., 1865, pp.115, 265. 維多利亞主教在1861 年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世界各地的歐洲人……在那些完全陌生的國家,統治者也難以容忍他們,(有時候確實)被看做文明中的下等人,而這些歐洲人也以一種優越的和征服民族的語氣自我貶低,See George Smith, Bishop of Victoria (Hong Kong), Ten Weeks in Japan, Longman, Green, Longman & Roberts, 1861, p.258.
上述主題重新出現在了《國際政策》(International Policy)一書內,該書是對英帝國進行批判的早期作品,由激進思想家理查德·康格里夫(Richard Congreve)在1866 年出版,作者是英國實證主義運動的奠基人。〔75〕Gregory Claeys, “The ‘Left’ and the Critique of Empire c. 1865-1900: Three Roots of Humanitarian Foreign Policy”, in Duncan Bell ed., Victorian Visions of Global Order: Empi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40.在他看來,東西方之間的關系有賴于對“歐洲貿易呈現出的掠奪式趨勢”進行“強有力管控”。為實現上述目的,他堅信,政府應當取消“對不公商人之所有保護”,并把他們的案件交由“當前被他們掠奪的人民審理”。〔76〕Richard Congreve, “The West”, in idem ed., International Policy: Essays on Foreign Relations in England, Chapman & Hall, 1866, pp.17, 42-43.其他文章討論了英國與“法國”“大海”“印度”“中國”“日本”及“非文明社會”的關系。有關日本的那篇文章參考了阿禮國及英政府向議會提交的藍皮書,對英國采用脅迫手段強迫日本簽署條約的行徑進行了抨擊,對于“當前涌向橫濱和上海的無知冒險家”也多有指責。不過,這些結論很難說是激進的,它們不過是要求英政府對其商人和外交官施加限制,以使“日本人能夠隨著時間的推移,忘卻他們對外國人的敵意”。〔77〕Charles A. Cookson, “England and Japan”, in Richard Congreve ed., International Policy: Essays on Foreign Relations in England, Chapman & Hall, 1866, pp.512-513.
在《巴黎條約》簽訂后十年,有跡象表明政治辯論產生了作用。然而并未朝著格雷和斯坦利關于減少海外事業的呼吁邁進,變化主要在于對《域外管轄權法案》的援用和對海外英人管制的加強等方面。比如,根據1865 年樞密院令,英國在上海設立上訴法院——英國在華及在日最高法院(British Supreme Court for China and Japan,又稱大英按察使司衙門),并派洪卑(彼時已晉爵士銜)擔任巡回法官,其經驗全都來自君士坦丁堡。〔78〕Sir Edmund Hornby, Sir Edmund Hornby: An Autobiography, Constable, 1929, p.193.該法院的創建是對發生在橫濱的“審判不公”做出的實際回應。當時,一位名叫阿爾弗雷德·布朗寧(Alfred Browning)的英國商人在橫濱被控犯有謀殺罪。德川時代的法律長期禁止日本人到海外旅行,這起案件涉及“無法派遣日本證人”赴英國駐香港最高法院出庭作證的問題。〔79〕Law Officers to Russell, 25 June 1864, FO 83/2298, fo. 262.與此同時,在奧斯曼帝國,對于外國臣民的進一步規制,有助于控制持英國護照之被保護人的規模。〔80〕Sir Edmund Hornby, Sir Edmund Hornby: An Autobiography, Constable, 1929,p. 97; 同時參見Sibel Zandi-Sayek,“ Ambiguities of Sovereignty: Property Rights and Spectacles of Statehood in Tanzimat Izmir”, in Sahar Bazzaz, Yota Batsaki and DimiterAngelov eds., Imperial Geographies in Byzantine and Ottoman Space( Washington, DC, 2013),2016 年3 月15 日訪問。對于英國來說,在1864 年英國將愛奧尼亞群島割讓給希臘后,護照持有人數過多的問題得到了緩解。隨著最終確定下來的土地法于1867 年生效和在埃及建立混合法院體系草案的提出,以下印象得到了鞏固:盡管治外法權的根本問題并未真正得到解決,但這一時期在威斯敏斯特就領事及特權展開的辯論正在起著某種作用,改革已如箭在弦上。
三、混合法院:是小惡嗎?
幾個世紀以來,中東地區的單方讓步協定造成了迷宮般競合的管轄權問題,弊端顯見。正如《泰晤士報》曾刊登過一則杜撰的故事:
在《漂泊在土耳其的英國人》(The Roving Englishman in Turkey)一書中,我們讀到困惑不解的帕夏(Pasha,音譯名,也譯為巴夏,指高級領導人)的一段講述:有一次他在政府首都接見領事團成員,身著奧地利、法國、俄國和英國服飾的國賓一個一個登臺受到接見,但直到帕夏定睛一看后,才認出他們竟是偽裝在風格各異的服裝下的同一個人。〔81〕“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Times, 24 Aug. 1868, p.8. 這段敘述美化了關于科斯島上發生的事件的原始敘述。原本只是描述了這個人如何代表七名領事,但只提到他穿了法國和奧地利的服裝。Eustace Clare Grenville Murray, The Roving Englishman in Turkey: Sketches from Life,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877, p.276.
這篇1868 年的文章接著引用了一則前述《東方與西方》書中的故事:“例如,在杜姆亞特(Damietta),有黎凡特人在身份尊貴的、間接代表著十五六個國家的一位領事面前下向他彎下了腰。”〔82〕John Ninet, “Modern Christendom in the Levant”, in Stanley ed., The East and the West, p.91.這就是所謂的貿易領事,他們人品不一,靈活地游走于外交和商業間以生出“職業的”中間地帶人(borderlanders)角色。盡管他們中的許多人受到其所服務國家的贊許,但在其領事身份給予他們的豁免權和免稅等特權的些許刺激下,他們中也不乏具有多重身份的“法律變色龍”。〔83〕Ziad Fahmy, “Jurisdictional Borderlands: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Legal Chameleon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lv (55), no. 2 (2013), p.310.
就像在東亞的條約口岸一樣,僑民群體在中東的名聲也是毀譽參半。就在該文章在《泰晤士報》發表前的一個月,前英國外交部常任次官奧斯丁·亨利·萊亞德爵士(Sir Austen Henry Layard)曾對下議院提到,他在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館任職期間,有一次“為了維護英國同胞的榮譽,曾支持他們提出的虛假索賠而腆顏作證”。外相斯坦利勛爵(與前述斯坦利同名,但并非《東方與西方》一書的作者)對在愛奧尼亞島土著要求獲得特權案中英國無法忍受般地濫用被保護人之受保護權的現象也感到深惡痛絕。〔84〕“Consular Courts in Turkey and Egypt-Observations”, Commons debate, 10 July 1868, Hansard, vol. 193, cols. 1035, 1050. 亨利·斯坦利(后晉男爵銜)屬于斯坦利家族中的愛德華·斯坦利(英國外相,后為德比伯爵)這一支。在為《泰晤士報》撰稿時,安東尼奧·加侖伽(Antonio Gallenga)解釋道,“唯一能夠從這一制度獲利的,是在天黑后能讓佩拉(Pera)和加拉塔(Galata)的街道變得更不安全的那些暴徒、刺客和小偷。”〔85〕加侖伽是借用而不僅參考了斯坦利的說法。“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Times, 24 Aug. 1868, p.8.斯坦利是這樣說的:“伊奧尼亞人、馬耳他人、希臘人等經營的酒船和咖啡店都靠近警察局。而酒船是強盜、殺人犯和其他罪犯的聚集地。在這里的犯人比在阿爾塞西和薩伏伊避難所的犯人更加安全。”參見Stanley ed., The East and the West, pp.4, 36.
有關領事裁判權的辯論,是在埃及設立混合法院的新提議被提出后興起的。在這片“十七處政權執行十七種不同法典”的土地之上,“領事裁判權的變態”(1837 年美國總領事語)已經造成“司法的混亂狀態”。〔86〕美國總領事報告認為,“為了獲得副領事官職位,杜姆亞特的兩個不同派別出價1000 美元。”Ziad Fahmy, Jurisdictional Borderlands: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Legal Chameleon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lv (55), no. 2 (2013), p.315; Jasper Brinton, The Mixed Courts of Egyp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9.在洪卑擔任英國駐君士坦丁堡法院首席法官時,對于英國駐埃及領事,他只能表示同情,因為這些領事“要管理的是許多極度任性的英國臣民,此外還有生活在保護領地如馬耳他和愛奧尼亞島的那些烏合之眾。”〔87〕Sir Edmund Hornby, Sir Edmund Hornby: An Autobiography, Constable, 1929, p.172.在港口城市亞歷山大,這個問題顯得尤為突出,外國人口在新近幾十年來呈指數式增長,到19 世紀70 年代時總數已逾四萬人。〔88〕Ziad Fahmy, Jurisdictional Borderlands: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Legal Chameleon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lv (55), no. 2 (2013), p.313.
埃及新任外交部長努巴爾帕夏(Nubar Pasha)計劃說服所有十七個政權承認一個統一的混合國際法庭來審理民事案件。這一盤算較君士坦丁堡的早期計劃更加宏大——早在1820 年,君士坦丁堡就有涉外商人民事案件歸共同管理大會(jointly administered assemblies)審理的做法。自1840 年起,土耳其人和外國人之間的商事案件也開始由混合法院(tidjaret)管轄。〔89〕Jasper Brinton, The Mixed Courts of Egyp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6-8.此外,在1859 年,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亨利·布爾沃爵士(Sir Henry Bulwer)建議混合法院適用一部統一法典。這個計劃未言明的,是將地方司法權力擴張與奧斯曼帝國法律改革的希望協同推進的一項行動綱領。〔90〕Turan Kayaoglu, Legal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Extraterritoriality in Japa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23.
《巴黎條約》簽訂后,努巴爾帕夏試圖將奧斯曼帝國的混合商事法院體系引入埃及,但沒能成功。在建造蘇伊士運河的時代背景下,努巴爾的愿景似乎十分適時。然而,當他于1867 年在巴黎提出這些建議時,巴黎對此沒有多大熱情。但是,在倫敦,努巴爾發現英國外交部更加接受這個提法。當萊亞德(Layard)次年提醒下議院時,斯坦利勛爵坦然認可“當前埃及的領事裁判權制度帶來了一些惡果”的說法。〔91〕“Consular Courts in Turkey and Egypt-Observations”, Commons debate, 10 July 1868, Hansard, vol. 193, col. 1045.斯坦利本人也承認,“在治外法權的侵蝕下,當地法庭的權力在不同程度上被僭越或被擱置了”。〔92〕Stanley to Stanton, 18 Oct. 1867, FO 78/1975, Despatch no. 40 (no folio number).反對混合法院的論點于是出現在《泰晤士報》上,有一些是努巴爾撰寫的,而貝爾(Mr Bell)的一封信則對在埃及的英國人群體發表了保留意見。〔93〕Jasper Brinton, The Mixed Courts of Egyp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4.最后,在英國政府的支持下,開羅在1869 年成立了討論該方案的國際委員會,到1872 年春,一個總括協議終于得以形成。盡管遭到了法國人些許反對,混合法院于1875 年正式成立,從一開始就是“成功的”。〔94〕Jasper Brinton, The Mixed Courts of Egyp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27. 格蘭維爾認為“埃及的混合法院運行良好。”Granville to Plunkett, 11 Jan. 1884, [Kew, United Kingdom National Archives, Public Record Office], Public Record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30/29/313, Part vii, 12.
1868 年的治外法權辯論體現出維多利亞時代的政治家們為在司法中適用既定原則而做出的斗爭。自《巴黎條約》之后,斯坦利勛爵一直堅稱,“所有歐洲大國都有同一種感受:領事裁判權的適用是一種早宜袪除的反常現象”。他甚至承認,“毫無疑問,領土以外的管轄權本身是一種惡”。與此同時,他反對萊亞德將努巴爾混合法院的模式引入土耳其的建議,因為土耳其是“一個地域廣闊的帝國”,包含“文明程度不同的眾多省份”。〔95〕“Consular Courts in Turkey and Egypt-Observations”, Commons debate, 10 July 1868. Hansard, vol. 193, cols. 1050, 1052.相反,他視埃及計劃為一項實驗,如果成功,可以適用到其他地方,這種理解為英國此后多年的政策奠定了框架基礎。因此,斯坦利所有的修辭都在表達一個十分務實的觀點,他在為領事裁判權辯護,他在警示人們相較于引入一個原則性極強但卻未經檢驗的“在實際上也無法實現正義”的法院,而維持一種雖有缺陷但卻經過實踐檢驗的制度,只能算得上是“一種較小的惡”(a lesser evil)。這一謹慎的回應徹底激怒了加侖伽(Gallenga),他告訴《泰晤士報》的讀者,“最溫和的伊斯蘭司法甚至會顯得惡性更小”。〔96〕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Times, 24 Aug. 1868, p.4.一位曾在19 世紀70 年代初期隨巖倉使團(Iwakura Embassy)周游世界名叫福地源一郎(Fukuchi Gen’ichiro)的年輕外交官,曾建議將埃及混合法院模式改良后適用于明治時代的日本,大概也將其只算作是一種“較小的惡”。〔97〕Nakaoka San’eki, “Fukuchi Gen’ichiro no Ejiputokongosaibanchosa”, (32) Kokusai shokadaigakuronso 48 (1985).
相比那個時代國際法頂級學者的成果,加侖伽的國際法觀一直都被認為具有“明顯更加包容性”特點。〔98〕Jennifer Pitts, “Empire and Legal Universalism”, 17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9 (2012).他顯然并不認同斯坦利的雙重標準,他堅信“我們選擇將其他民族歸為野蠻的或半野蠻的這個簡單事實,并不能賦予我們以野蠻人一樣對待他們的權利”。在回應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在建立起橫跨亞洲的貿易體系后出現的戰爭道路所引發的焦慮時,他認為“正是基督教的偏執或虛偽,才使這些遙遠的國家看著我們不舒服,他們于是建起了那些不久就被暴力推倒的‘壁壘’以阻止同我們開展貿易”。加倫伽堅定不移地認為,“土耳其和埃及只能有一個司法權,就像在法國或英國也只有一個一樣”。〔99〕“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Times, 24 Aug. 1868, p.4.
五年之后的1873 年,君士坦丁堡舉行了一次類似會議,以管理既有的商事混合法院并使其能同埃及的新制度相協調,并最終在1875 年對其做了若干改動。然而,這些僅是實際修正,與《巴黎條約》中確定的召開治外法權會議的愿景還相去甚遠。〔100〕Eliana Augusti, “From Capitulations to Unequal Treaties: The Matter of an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24 Journal of Civil Law Studies 303 (2011).實際上,這些修正只是進一步強化了如下主流觀點:奧斯曼土耳其單方讓步協定在該國尚未達到“文明標準”或在其“文明赤字”尚未填平前依然有效。〔101〕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larendon Press, 1984, p.115; Eliana Augusti, “From Capitulations to Unequal Treaties: The Matter of an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24 Journal of Civil Law Studies 289 (2011).例如在1873 年,著名國際法學家馬騰斯曾為領事裁判權辯護,認為領事裁判權是一種加強“東方國家”法治的必要工具。他認為,應當從文明教化的角度來理解治外法權,其應更多被視作是一種責任而不是特權。〔102〕Andreas T. Muller, “Friedrich F. Martens on ‘The Office of Consul and Consular Jurisdiction in the East’”, 25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81, 882 (2014).勝任的法官管理下的領事法院因此是當地法院的楷模。1872 年,英國外相格蘭維爾勛爵(Lord Granville)在接待訪問倫敦的巖倉使團主要成員時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以斯坦利勛爵的觀點為基調,他解釋道,“在所有類似情形下,英國政府會同意當地政府對英國人具有管轄權,這與當地的啟蒙和文明進步程度精準地成正比關系”。〔103〕格蘭維爾與日本全權大使巖倉具視之間的訪談備忘錄,參見Foreign Office, 27 November 1872, FO 881/2138, 2. 1900 年埃及混合法院開始擁有對破產案件的管轄權。1930 年代前就擬定了一部刑法典以取代領事裁判權,但該法在很大程度上并沒有得以施行,參見 Jasper Brinton, The Mixed Courts of Egyp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89, 107, 192.然而,這種以科學的精確度來衡量進步的脆弱觀念只能稱得上是“不穩定的政策(conjectural policy)”。格蘭維爾的說辭給人以公平待遇的期待,但那種“穩定的文明標準(stabl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卻從未出現過。〔104〕Martti Koskenniemi, The Gentle Civilizer of Nations: 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34-135.
在東亞也是如此,英國人很早便對混合法院表現出了某種興趣。在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的1856 年,廣州被英軍占領,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安排了一位中國推事會同審判。此舉被中國人斥為“與裝飾門面無異”,有奏折描述該官員“坐位在英、佛理事官之下,雖有座位,而不準說話,不準吐痰、不準吃煙”。〔105〕P?rKristoffer Cassel, Grounds of Judgment: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58. 原文參見齊思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第3 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第378 頁。——譯者注與此同時,英國官員似乎意識到了《巴黎條約》中治外法權引發的問題,故而計劃將混合商事法院引入埃及。東亞地區除前述條約外,1858 年額爾金勛爵(Lord Elgin)在天津和江戶簽訂的條約表明,他在努力制定一種至少可在民事案件適用的會同審理爭議的辦法。〔106〕參見《天津條約》第17 條和《江戶條約》第6 條,Hertslet’s Commercial Treaties( 31 vols.,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840-25), xi. 90, 398.
1864 年,巴夏禮再次進行試驗,這次他與地方當局一道設立了上海混合法院(Shanghai Mixed Court,即上海會審公廨),審理中國人為被告的案件和沒有本國領事保護的外國人案件(即華人與無約國僑民為被告的民、刑案件)。會審公廨最早在英國領事署審理案件,與洪卑次年設立的英國駐華最高法院共存。〔107〕P?rKristoffer Cassel, Grounds of Judgment: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59, 66-67. 上海會審公廨同時審理輕微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反映了英國接受了中國人對《天津條約》有關于“會同公平審斷”的解讀。在某一個時間點上,甚至有過將這兩所法院合并的討論,盡管這引起彼時已經成為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的共鳴,但洪卑不為所動。〔108〕P?rKristoffer Cassel, Grounds of Judgment: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70.1867 年,會審公廨遷至南京路新址。在這里,作為國際混合法庭(International Mixed Tribunal)的會審公廨成為中國權力看得見的象征,將清朝的主權投射到了作為治外法權飛地的上海。但實際上,它只會帶來外國人干涉地方司法的問題,并不會侵蝕到領事裁判權。中國也試圖控制外國陪審員對于司法的干涉,比如1869 年頒布的新規定;再如1876年簽訂的《芝罘條約》試圖阻止外國陪審員對被告人為中國人的案件作出判決。盡管如此,會審公廨總是華洋沖突的原因之一。1885 年,在某英國陪審員被一位中國地方副縣官襲擊后,會審公廨甚至一度短暫關閉。會審公廨一直存在至1926 年,最終被僅受中國人控制的法院所取代。〔109〕P?rKristoffer Cassel, Grounds of Judgment: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69, 79, 82-83, 178; TeemuRuskola, Legal Orientalis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dern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85.
在日本,《江戶條約》提出采用某種聯合方法處理民事案件,但最終并未形成正式的混合法院。〔110〕Morita Tomoko, “Bakumatsuishinki no ryojisaiban to minjisoshotetsuzuki”, (604) Rekishihyoron 15 (2000).合作的情形卻是有的,例如在埃德爾曼-柴谷(Edelman-Shibaya)案中,日本被告人是在英國領事館內進行審理的,雙方均有代表在場。〔111〕Morita Tomoko, “Bakumatsuishinki no ryojisaiban to minjisoshotetsuzuki”, (604) Rekishihyoron 17-19 (2000).日本官員出席領事法庭,而英國領事也參加當地法院的審判,他們經常使用調解的方式在庭外解決爭議。〔112〕Morita Tomoko, “Bakumatsuishinki no ryojisaiban to minjisoshotetsuzuki”, (604) Rekishihyoron 21 (2000).1866 年,英國外交官薩道義(Ernest Satow)在《日本時報》上撰文并對疑難案件常被提交至海關(Customs House)處理的做法表示不滿,他說“這(指海關)是一處外國人完全未知是否可以獲得公正對待的地方”。〔113〕The Japan Times, 19 May 1866, reproduced in Grace Fox, Britain and Japan, 1858-1883, Clarendon Press, 1969, p.573.在日外國人批評最厲害的當屬日本破產法,以至于駐橫濱的英國領事要求日本成立混合法院,并在第二年提議建立聯合法院。〔114〕薩道義將第7 條有關于追回債務和懲罰欺詐性債務人的規定“是一個過于沉痛的話題以至于外國債權人不忍細說”。The Japan Times, 19 May 1866, reproduced in Grace Fox, Britain and Japan, 1858-1883, Clarendon Press, 1969, p.573; James E. Hoare, Japan’s Treaty Ports and Foreign Settlements: The Uninvited Guests, 1858-1899, Japan Library, 1994, p.62.薩道義的文章也被翻譯成了日文,當新的明治政府宣布了修約的意圖后,這個主題又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在意識到英國有支持日本修約的想法后,日本外交部在其擬定的條約草案稿中著重包含了設立混合法院的條款。在英國駐東京公使館向條約口岸領事和企業發出的通知中,也含有建立混合法院的內容。正如有人回應說,“在中國也設立的混合法院制度,可以有效地適用于日本”。〔115〕Howell & Co. to Troup, 19 Dec. 1871, FO 46/151, fos. 97-98.1872 年,格蘭維爾在倫敦接見巖倉具視時也“提到了埃及的情況,治外管轄權一度在埃及盛行,但現在正在嘗試允許讓埃及自己的法院來管轄民事案件”。〔116〕格蘭維爾接著說,“如果這一嘗試成功了,那么也可以審理刑事案件,也就沒有理由不在日本采取類似的方法”。Interview between Granville and Iwakura, 27 Nov. 1872, FO 881/2138, 2.
日本人從來沒有對上海會審公廨表現出任何興趣,但是他們很關注土耳其和埃及的混合法院。很快,在格蘭維爾接見巖倉后,福地源一郎被派往埃及和土耳其考察該式法院。〔117〕Nakaoka San’eki, Fukuchi Gen’ichiro no Ejiputokongosaibanchosa, Kokusai shokadaigakuronso, no. 32 (1985), p.52.他和一位名叫島地黙雷(Shimaji Mokurai)的佛教僧人同行。他們是最早訪問君士坦丁堡的日本人。在考察之旅結束后,福地源一郎提交了一份主張學習埃及混合法院模式的報告,后續的報告基本延續了這一觀點,盡管他在某些方面持保留意見,比如埃及和日本有些關鍵不同點。〔118〕例如,在1873 年法務省總結認為日本已經獲得了比埃及更多的權利。Naganuma Hideaki, Naigai shosokaramitanihon no saibankenmondai, Rekishihyoron, no. 604 (2000), p.37.19 世紀80 年代,井上馨(Inoue Kaoru)擔任日本外務大臣時,曾在東京召開了兩次主題為修約的多邊會議,設立混合法院議題是井上馨抑制治外法權問題戰略的重要內容。但在法國法學家保阿索納德(Gustave Boissonade)發表了一篇抨擊報告后,井上馨在1887 年放棄了該方案。面臨人們對于外國法官可能出現在日本法院前景的不滿,井上馨好不容易與列強達成的協議很快就破產了。
與此同時,在歐洲,領事裁判權和混合法院不再是英國議會“權力走廊”的辯論議題,該討論逐漸僅限于法律界。有兩個重要組織同于1873 年在比利時成立。一個是國際法研究院(Institut du Droit International);另一個是國際法改革和法典編纂協會,后改名為國際法協會(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國際法研究院在1874 年成立了專門委員會,研究“東方國家”是否可以被納入“國際法大家庭”。五年后,英國法學家屠威斯爵士(Sir Travers Twiss)向在布魯塞爾召開的第五屆大會提交了一份報告,指出這些國家同歐洲國家一樣意識到條約義務,但是摒除領事裁判權的時刻尚未到來。〔119〕Sir Travers Twiss, “Rapport”, in Annuaire de l’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879-1880) (2 vols.), Libraire C. Muquardt, 1880, Vol.1, pp.302, 304.似乎是為了強化這一結論,英國駐日法院同一年在日本設立。1878 年,在法蘭克福召開的國際法協會大會上,關于治外法權的討論也形成了類似的看法。中國和日本代表參加了本次大會,這是兩國代表第一次參加國際法學家的聚會。〔120〕Arnulf Becker Lorca, Mestizo International Law: A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中國駐英國公使郭嵩燾對目前的安排似乎表示順從,但日本駐英國公使上野景范要求明確接受“國際禮讓”的可感知規則,他“急切要求西方法學家就文明體系與東方主義體系之間的接觸點發表看法”。〔121〕“Extra-territoriality”, The Japan Weekly Mail, 19 Oct. 1878, p.1093.但是,在剛借助訂立《柏林條約》來解決俄土戰爭(Russo-Turkish War)的這一年(指1878 年),對奧斯曼單方讓步協定來一次全面修訂的希望似乎比以前更加渺茫了。在這個時刻,那些被治外法權制度所累的國家仍然反常地處于一種“永久的例外狀態”,顯然處于國際社會的邊界之外,身處于“正常”規則無法被適用到的場域。〔122〕Teemu Ruskola, Legal Orientalis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dern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41.
四、結論
不論戈壁灘的人們何時抱怨,領事只是邊笑邊說,“條約就是這么規定的”。當他們建議撤銷領事裁判權條款時,他“笑得喘不過氣來,以至于我們希望他能笑到窒息而死”。就像領事解釋的那樣,“可憐的愚蠢人,你們沒有修約的權利,只有我們有”。〔123〕Frederick Marshall, “Justice Abroad”, The Fortnightly Review, July, 1874, p.143.1874 年英國《雙周評論》(The Fortnightly Review)雜志發表的一篇名為《海外司法》的文章就講述了這個寓言故事。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馬歇爾(Frederick Marshall)的英國人,曾長期居住在法國,當時任日本駐巴黎公使館秘書,應召參與明治政府發起的修約運動。在其對英國外交政策嚴厲的控訴中,他吸引公眾形成如下輿論:“(英國外交政策是)一種比堅船利炮更為兇猛的力量”。〔124〕Frederick Marshall, “Justice Abroad”, The Fortnightly Review, July, 1874, p.145.他將治外法權描述為“那個野蠻的詞語”——呼應了十年前格雷在上議院發表的說法,這很難說是巧合。〔125〕Frederic Marshall, International Vanities, William Blackwood & Sons, 1875, p.265.
但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公眾似乎不再如從前般密切關注英國在日本的外交政策,當然也就再無前些年當沖突隨時發生、英國向橫濱派駐軍隊時甚囂塵上的爭議。當奧斯曼帝國與俄國間的戰爭陰云再度籠罩時,“東方問題”再次成為一項緊迫的議題。奧斯曼帝國軍隊屠殺保加利亞基督徒的報告在提醒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譴責土耳其人“令人無法容忍的暴行”。〔126〕William Gladstone, Bulgarian Horror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East, John Murray, 1876, p.12.二十年前在巴黎制定的有關廢止奧斯曼單方讓步協定的原則性聲明,如今似乎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在日本,治外法權成為一個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在英國,這個問題依然囿于人們熟知的討論框架。對于領事的規制加強了,新的法院也建立了,有關治外法權的整個討論于是轉移到了如何運作這些混合法院之上。
但是,這種折衷方案是一把雙刃劍;在實際中,混合法院在幫助控制領事裁判權被濫用的同時,也對所在國的主權造成了相當的侵蝕。混合法院的設立制造了改革就緒的印象,甚至是提供幫助的仁慈形象,也沒有直面《巴黎條約》所暴露出的治外法權根本斷層線。它從維多利亞時代的政治中退了出來,圍繞外國司法的公開辯論越來越轉為只限于私密的國際法圈子中的會議討論。公眾對這一議題的關注被引向了他處。在接下來的十年里,雖然曾受到日本報紙和日本本國的英文報紙發表過一些尖銳的觀點而受到些耽擱,在君士坦丁堡從未召開的會議最終還是在東京召開了。
舉凡討論反抗治外法權的,主要圍繞的是此后直至二十世紀的抵制治外法權運動,并自然地形成了一個以后幾代人都理解的反抗主題。然而,本文分析的是,早在維多利亞時代中期,英國即曾對此問題表現出過意義深遠的政治憂慮。一些批評家敏銳地意識到國際秩序中隱含的矛盾,該國際秩序有選擇性地不去承認某些特定群體具備其新成員的資格。短期內,這種異議對政策的影響力有限,主要限于對海外英國臣民的管控力度的加大和對于試驗設立混合法院的推進等兩點之上。因此,它無法做到不偏斜,無法不被吸收到根深蒂固的官方文化之中,也就總是無法與最初擬定的重新審視條約規定的司法制度的嘗試完全契合。英國外交部僅滿足于紙面上修補現有制度的裂縫,而不太愿意解決其結構性缺陷問題。但是,這種政治話語不但激起了國際法界的辯論,也啟發了受領事裁判權影響之國家的觀點。實際上,這一政治話語預示了人們會愈加意識到治外法權制度的根基并沒有其支持者所想的那般堅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