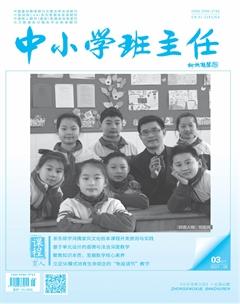延展教學主線的“植物組織培養技術”課堂實踐
周敏 王薦

[摘要] 課堂教學的有效性依賴于教學設計主線的連貫鋪陳。通過延展教學主線設計“植物組織培養技術”一課,讓學生從科學史中了解技術,自主歸納技術流程,達成課堂知識目標;從生產實踐報告中感受技術,提升差異性思維能力;到生活中運用知識,達成學科核心素養發展。
[關鍵詞] 植物組織培養技術;科學史;教學主線
高中生物選修課程有“依托拓展課程和校本課程,為學生進一步學習和職業規劃奠定基礎”[1]的作用。課堂上,教師一方面要為學生創造條件達成基本課程知識目標;另一方面要通過多種途徑為學生開闊生物科學技術視野,發展學科核心素養。本文以“發展科學史→理論基礎→技術流程→工廠實踐→優點與應用”為主線,多維度設計“植物組織培養技術”一節教學,為學生呈現完整、立體的植物組培這一現代生物技術。
一、從科學史中了解技術,自主歸納技術流程
1.教師查閱資料,編寫科學史學習材料
一部科學史就是一部思想史,亦是一部人類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史。用好生命科學史這抔土,可以開出美麗的花。通過查閱資料,教師整理植物組織培養的發展歷史。該技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細胞學說,至今一百多年的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簡化資料)。
探索階段:1839年,施萊登(M.J.Schleidon)和施旺(T.Schwann)提出細胞學說。為每個細胞可能獨立生活提供理論基礎。1902年,哈伯蘭特(Haberlandt)預言細胞“全能性”,他用了很多植物材料嘗試卻沒有成功。
奠基階段:1937年,懷特(White)配制出懷特培養基,并成功誘導番茄根尖切段長出愈傷組織。1957年,斯庫格(Skoog)和米爾(Mill)提出激素調控植物組織培養中根、芽的形成。1958年,斯圖爾德(F.C.Steward)研究植物生長調節的化學因子。他用胡蘿卜根韌皮部成熟細胞離體培養,誘導脫分化得到愈傷組織,再加入從幾千加侖椰子水中得到的提取物、液體胚乳等,成功誘導再分化成胚狀體,最終獲得完整胡蘿卜植株。這一植株能開花結果,證實了哈伯蘭特的細胞全能性預言。
發展階段:1960年,莫雷爾(Morel)獲得脫毒蘭花。1964年,庫巴(Cuba)和馬畢斯布瓦里(Mabesbwari)用毛葉曼陀羅的花藥培育出單倍體植株。1970年,斯圖爾德(Steward)懸浮培養單個胡蘿卜細胞得到可育胡蘿卜植株。1983年,贊布瑞斯基(Zambryski)獲得首例農桿菌介導轉基因植物。現今,植物組織培養技術與水稻、玉米、小麥等的轉基因技術結合,開始在生產上大面積推廣使用。
筆者在梳理植物組織培養技術發展史時遇到一個小插曲。按照習慣性思維,要了解胡蘿卜植物組織培養,就想到查閱斯圖爾德當年論文,希望看到操作流程介紹。可是查閱文獻發現斯圖爾德1959年的論文闡述的主要內容是他用新技術從幾千加侖椰子水中提取了誘導植物生長和形態發生的化學物質。他在文章一開頭提到“本文將回顧大量已被研究過的話題,將聯系整個領域已知的結論和發展趨勢,研究植物生長調節化合物”。由此可知,他不是植物組織培養研究的第一人,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找到了調節植物生長的關鍵化學因子,最終促成植物組織培養的成功。筆者順藤摸瓜,通過查閱書籍、知網、生物類雜志等途徑找到了諸多科學家參與的將近100年探究資料,將之改編成學生的閱讀資料,并注意編排的詳略,著重體現植物組織培養技術產生的細胞學理論基礎,科學家克服困難的創舉,以及突出第一位完成該技術的斯圖爾德實驗過程。
2.學生利用資料,自主生成技術流程
學生利用這些資料,學習目的有二:第一,閱讀科學史,歸納抽提構成技術的要素,用關鍵詞和箭頭的形式自主構建植物組織培養技術流程模型達成知識目標。由于科學史亦是一連串相關的科學故事,且是令學生耳目為之一新的新技術,故事讀來充滿趣味性、啟發性和探究性。圍繞著組培技術讀完科學史,學生自然而然能夠生成流程模型,從而達到闡明“植物組織培養是在一定條件下,將離體的植物器官、組織和細胞在適宜的培養條件下誘導形成愈傷組織,并重新分化,最終形成完整植株的過程”[2]這一次位概念。
第二,品味科學史,發展學生的技術思維和工程思維,實現獨特育人價值。實現植物組織培養技術是一項經歷了幾代科學家的偉大系統工程,學生能夠感受多學科交叉以及新技術應用對技術發展的推動作用,繼而認同組培技術的復雜性與系統性。梳理這段歷史,有助于學生理解科學技術的發生、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的。
二、從實踐中感受技術,提升差異性思維意識
植物組織培養技術寫進教材已十年有余,且就整個選修三教材而言,植物組織培養技術是諸多現代生物技術中不可多得的能讓學生參與體驗的技術之一。正因如此,研究者聯系了當地的公司,實地了解鐵皮石斛植物組培的工廠化生產。此次參觀更多地采訪了技術員,了解鐵皮石斛植物組培的實際生產狀況,對理論知識進行拓展。[3]研究發現:教材的植物組織培養技術編寫以揭示事物的普遍特征為主,所選案例具有普遍性。而差異性思想作為生物學的重要思想,在植物組織培養這一技術的理論與實踐中體現得尤為突出。
1.生產實踐與理論流程差異枚舉
差異1:生產上用愈傷組織簡化微繁流程。人教版教材中表述為“在一定條件下,利用它們(植物)的一片葉子、一片花瓣,甚至一粒花粉,可以得到大量的幼小植株”,即利用少量外植體材料,無限循環操作相關流程就可以實現作物大量繁殖,產量和速度相當驚人。工廠的采訪了解到這個流程還能再簡化,省去的外植體脫分化過程實際上是省去了一個比較艱難的誘導過程。所以,實際生產中通過對愈傷組織擴大培養,實現更快捷的微繁效果。
差異2:由分化培養基與繼代培養基看組培流程。課文中對“分化培養基”有所提及而并未展開講述,僅在習題答案中出現“繼代培養基”。此次采訪鐵皮石斛的工廠化生產,清楚地看到兩條生產路線:一是對愈傷組織擴大培養,愈傷組織保持原形態而不分化,采用的便是繼代培養基;二是誘導鐵皮石斛外植體長出符合生產要求的根,采用的是誘導生根的分化培養基。不同種類的培養基主要區別在于激素杠桿這根魔術棒的巧妙應用,這對學生深刻理解課文中的“植物生長調節劑在組織培養中的神奇作用”大有益處。
差異3:避光不是培養愈傷組織必要條件。課文中提到“胡蘿卜組織塊避光培養后觀察愈傷組織生長狀況”,師生常將其理解為培養愈傷組織一定需要避光條件,考題中也多次涉及需要避光培養。而工廠化生產鐵皮石斛,它的愈傷組織擴大培養卻并不避光,愈傷組織大方地呈現出綠色并不斷增殖。直接從植株附近長出的原球莖(愈傷組織的高級階段),也無須避光生長。這是鐵皮石斛愈傷組織的特殊性,而同一工廠培養的天山雪蓮、人參的愈傷組織,卻需要嚴格避光的條件。
綜上所述,植物組織培養技術并不是一個固化刻板的過程:不同目的,植物組織培養技術有差異;培養不同種類植物,組織培養技術有差異;同種植物,在不同地方操作,技術也有差異(如在激素配比方面)。
2.差異性思維與探索事物本質的統一性的辯證關系
差異性思維的引入不等于否定書本基本理論。從工廠化生產鐵皮石斛操作流程來看,這是對植物組織培養技術流程的靈活應用,基于基礎技術而靈活應用于生產實踐。正因為這種靈活性,使師生更加關注愈傷組織,產生想要對愈傷組織一探究竟的想法。為此,教學設計了植物組織培養與植物營養繁殖比較環節。學生熟知的景天科植物利用一個葉片(相當于外植體)也能產生一株新植株。對景天科植物進行植物組織培養又會怎樣?答案是外植體脫分化形成的愈傷組織能夠萌蘗出數十個芽體,進而產生數十個新植株。所以愈傷組織帶來的經濟效益是巨大的,因而得到工廠的青睞。
反復圍繞“愈傷組織”展開植物組織培養教學,在發現差異、了解差異的過程中,學生找到了萬變不離其宗的愈傷組織,使其作用得以凸顯。可見,實踐的差異并未否定理論的實質,而是突出了理論的核心。
3.學生基于證據,理性思考,表達自己
目前普通高中并不完全具備讓學生體驗植物組織培養操作的條件,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對于問題的探究、討論。上文所做的工作是引導學生討論由生物技術引發的問題,是一種基于工廠生產證據的討論,有助于了解技術的規范性和標準性,有助于發展思維的嚴謹性——這是對組培技術流程刻板記憶教學所不能媲美的。
教學如果只圍繞課本展開而不加拓展,容易將學生帶入思維定式的誤區。教師應當在充分利用課本資源的基礎上,通過多種途徑為學生開闊生物科學技術視野,引導學生基于事實證據、運用科學概念論證客觀事物的本質,養成優秀的思維習慣和品質。
三、到生活中應用技術,達成知識深度體驗
當學生了解了植物組織培養技術的發展史、感受工廠化生產過程后,就能夠知道該技術在哪些方面可以應用,存在怎樣的優勢。我們只需改變外植體的形式,就可以輸出不同的產品。具體如下示意圖所示。當外植體材料是花藥時,就可以得到單倍體植株;提供雜種細胞可得到雜種植株;提供轉基因細胞時可得到轉基因植物,為作物育種提供新的途徑。當人們提供的外植體是優良品種體細胞時,可以實現優良作物微繁;提供分生區細胞,可以為植物脫毒;提供胚狀體加人工種皮,可以得到人工種子,為植物繁殖提供了新途徑。
通過這些與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現代生物技術,既鍛煉了學生在生產實踐中自我圖式的認知建構能力,又真正意義上讓其體會到知識符號背后的價值意義。
[本文系教師教育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重大疫情危機中的教師教育應對策略研究”項目“大概念視域下‘幼小初高大一體化生命教育課程建設研究”(項目編號:CITE20200105)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2]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普通高中生物學課程標準(2017年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3]唐軍榮,等.植物組培快繁實例[M].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