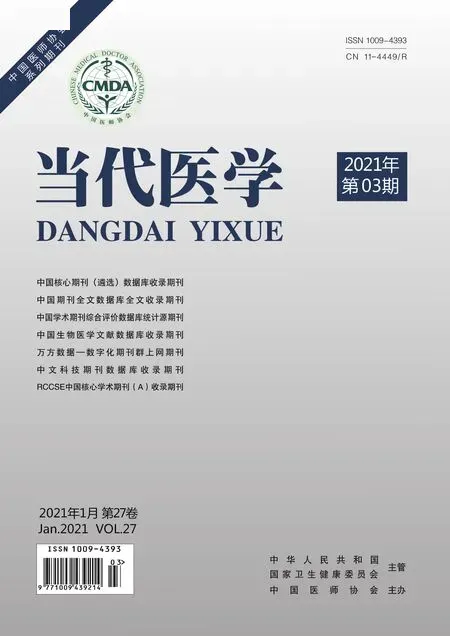冠脈支架再狹窄的影響因素與治療策略
管樺,李波,孫林
(昆明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心內科,云南 昆明 650101)
1 ISR預測因素
1.1 病史及家族、個人史 某些基礎病史、家族史及個人史作為CAD的危險因素,同樣可影響接受冠脈支架植入術的患者ISR的發生發展。
1.1.1 心肌梗死 家族史ISR 的關鍵機制是新的內膜增生[1]。動脈粥樣硬化和心肌梗死的機制可由某些基因突變導致[2],這種突變將心肌梗死與動脈粥樣硬化和新內膜增生聯系起來,并最終導致心肌梗死家族史與支架內再狹窄之間的相互關系。雖然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包括所有類型的疾病)不能預測ISR,但心肌梗死家族史是一個支架內再狹窄的強有力的獨立預測因素[3],對有心梗家族史的患者,需定期行冠脈檢查以盡早發現可能存在的ISR。
1.1.2 糖尿病 糖尿病是冠心病的已知確定危險因素之一,同樣與ISR 的發生具有相關性。Maayan Konigstein等[4]的bionics隨機試驗分析中表明在158位接受13個月血管造影隨訪的患者中,與非糖尿病患者比較,糖尿病患者再狹窄患病率高3倍(15.2%vs.4.7%),糖尿病患者的ISR發生率明顯高于非糖尿病患者。在接受冠狀動脈支架置入術的糖尿病患者中,HbA1c水平≤7%的患者在PCI隨訪2年后可能具有較低的再狹窄風險,并具有更好的臨床效果[5]。血糖控制情況可作為ISR的預測因素之一。
1.1.3 慢性腎臟疾病 患有慢性腎臟疾病(CKD)的患者罹患CAD的風險較高。腎功能受損的患者,尤其是血液透析患者,發生再狹窄和出血并發癥的風險顯著增加[6]。可能因為CKD 患者的不完全血運重建率較高,其在PCI 后鈣化病變和狹窄殘余量較大[7]。
1.1.4 吸煙 吸煙已明確作為冠心病的高危因素。對于冠脈支架植入術后仍不戒煙的患者,ISR 的發生率明顯升高。加強健康宣教,盡早戒煙是預防ISR的重要環節。
1.1.5 D 型人格 D 型人格的患者在負面情感(NA)和社會抑制(SI)方面得分均很高,歐洲心臟病學會已將D型人格作為CAD 的社會心理危險因素。在病理生理上,D 型人格與內皮功能受損和炎癥危險生物標志物水平升高顯著相關。這些特征可能導致支架內新動脈粥樣硬化。Wang Y 等[8]研究表明D型人格是PCI后1年和2年ISR的獨立預測因子;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聯系得到加強。
1.2 炎癥血清學指標 ISR是冠狀動脈支架置入后的不良結局,是由于炎癥和氧化應激而發生,導致支架區域內平滑肌細胞增殖,該過程由支架置入后血管壁的損壞觸發。冠狀動脈支架置入刺激局部炎癥,隨后發生全身性炎癥反應,在血清學檢查中可以監測到相應的炎癥指標。
1.2.1 超敏C反應蛋白(hs-CRP) 血清C反應蛋白(CRP)是一種急性期反應蛋白,由肝細胞合成和分泌。血清hs-CRP是CHD 的獨立危險因素,已被納入ACCF/AHA 指南中,以識別可預防冠心病的一級人群,ISR的發生與高水平的hs-CRP顯著相關[9]。
1.2.2 白細胞介素-3(IL-3) 活化的T淋巴細胞合成的白介素3(IL-3)是慢性炎癥的介質,并被懷疑會促進動脈粥樣硬化。Tanja Rudolph 等[10]研究顯示,發生ISR 的患者IL-3濃度高于具有血管造影正常冠狀動脈的受試者,表明IL-3在ISR發生中的影響作用。
1.3 血脂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是導致CAD 的重要因素之一,Park SH等[11]通過研究表明,高濃度的LDL-C與支架再狹窄的發生密切相關。
1.4 其他血清學指標
1.4.1 血清尿酸(UA) UA 是人體內源性和外源性嘌呤在黃嘌呤氧化酶作用下的代謝終產物。UA的升高可造成血管內皮的損傷、刺激血管平滑肌細胞增生,同時機體在合成血尿酸時伴隨大量氧自由基的產生,而后者參與炎癥及動脈粥樣硬化形成,由此可見UA 是導致CAD 的因素之一。同時,血清尿酸水平是再狹窄的獨立預測因子[12]。
1.4.2 骨形態發生蛋白-2(BMP-2) 近期研究發現,BMP-2信號轉導與血管疾病有關,包括動脈粥樣硬化,血管炎癥,血管鈣化和斑塊不穩定[13]。Wei-ping Zheng 等[14]研究顯示,CAD 患者的BMP-2 水平升高與ISR 獨立相關。血漿BMP-2 水平可能有助于預測ISR。
1.5 心外膜脂肪厚度 心外膜脂肪組織是真正的內臟脂肪,沉積在心臟周圍,尤其是在冠狀動脈周圍,并通過幾種生物活性分子的表達介導動脈粥樣硬化[15]。心外膜脂肪厚度可以通過心臟超聲進行測量,心外膜脂肪厚度與冠狀動脈疾病(CAD)的嚴重程度和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的程度相關[16]。通過 Julio O Cabrera-Rego 等[17]研究顯示,心外膜脂肪與支架內再狹窄關系密切,在預測再狹窄方面具有可接受的準確性。
1.6 生物、機械及技術因素
1.6.1 生物因素 生物因素主要指耐藥性及過敏,耐藥性是指由于某些遺傳基因突變導致患者對藥物涂層支架(DES)中的藥物敏感性降低;而過敏是指冠脈支架中的任何一種成分均可能引起超敏反應。以上兩種情況均可能導致ISR 的發生。
1.6.2 機械因素 機械因素主要包括支架擴張不足、DES藥物分布不均、支架梁斷裂(可能與病變本身相關,比如病變角度過大)。
1.6.3 技術因素
(1)支架未完全覆蓋預擴張球囊擴張范圍 已有研究表明未覆蓋預擴張球囊擴張的整個區域的支架暴露邊緣是再狹窄的主要部位。
(2)連續支架的間隙 植入連續多個支架時,可能會導致支架的覆蓋不連續,在間隙部位,血管壁中的局部藥物沉積最少[18],從而導致ISR的發生。
2 ISR的治療策略
已經有大量的技術嘗試進行冠狀動脈ISR的治療,包括介入治療:重復DES 植入,藥物涂層球囊(DCB)血管成形術,普通球囊血管成形術,切割球囊血管成形術,血管內近距離放射療法[19]以及冠脈搭橋術等。
2.1 藥物涂層球囊(DCB) Harald Rittger 等[20]一項隨機單盲多中心研究表明,紫杉醇涂層球囊(PCB)的治療優于普通球囊血管成形術,其晚期損失分別為(0.43±0.61)mm 和(1.03±0.77)mm(P<0.001)。再狹窄率從58.1%顯著降低到17.2%(P<0.001),綜合臨床終點從50.0%顯著降低到16.7%(P<0.001)。也有研究指出,紫杉醇藥物球囊(PCB)和西羅莫司涂層球囊(SCB)在DES 的ISR 中治療效果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1]。PEPCAD China ISR 試驗入選220 例DES的ISR 患者,患者分組接受紫杉醇藥物球囊(PCB)和紫杉醇洗脫支架(PES)治療,結果顯示,二者在晚期管腔丟失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然而,與PES 組比較,PCB 組在2年時死亡率較低(0%vs.4.9%,P=0.03)[22]。
2.2 切割球囊 切割球囊和普通球囊形似,不同的是其表面有3~4 個金屬片。擴張時,刀片會沿血管縱軸方向由內到外依次切開內膜、斑塊纖維帽、彈力纖維和平滑肌,進而減少血管彈性回縮、局部的炎癥反應、內膜的增生反應,最終減少再狹窄的發生。
2.3 血管內近距離放射療法 血管內近距離放射療法是采用射線近距離照射病變部位,或使用攜帶放射核素的支架植入,但有研究顯示,其與藥物支架治療ISR 療效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且設備昂貴、需要經嚴格培訓的專業操作人員,目前已明顯減少使用。
對于ISR 治療方案的選擇需因個體差異進行權衡。2018ESC/EACTS 心肌血運重建指南中指出:推薦DES 可用于BMS 或 DES 的 ISR(IA)、藥物涂層球囊治療 ISR(IA)、應考慮使用血管內超聲和/或OCT 檢測支架相關機制問題(IIaC)、對于反復發生ISR的患者優先考慮冠脈搭橋術(IIaC)。
對冠脈支架再狹窄的研究還需繼續進行,尤其是分子生物層面,相信在將來會有更多更好的技術及方法被引入臨床,為進一步降低和救治ISR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