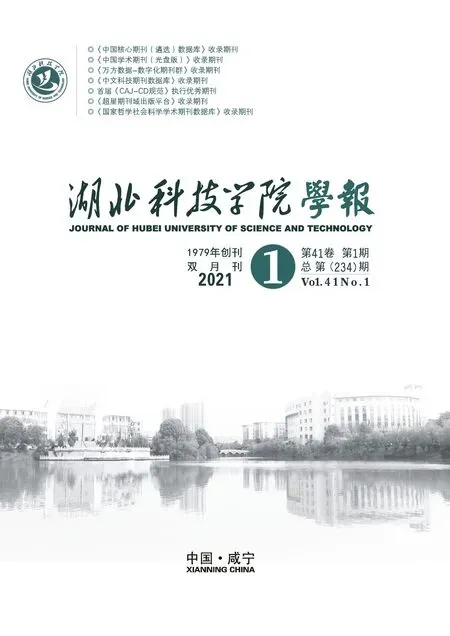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犯罪問題的媒體呈現
——以《泰晤士報》涉謀殺案報道為中心
王宇平
(南京大學 歷史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維多利亞時期是英國工業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在自由主義思想的指導下,社會改革滯后于經濟發展,社會犯罪率迅速上升,犯罪及其治理成為貫穿維多利亞社會的重要議題,犯罪問題由一項個體的安全問題深化為國家和社會治理的緊要層面。19世紀蓬勃發展的報刊業,為犯罪問題社會角色的成熟提供了必要的生存土壤。作為全國性報刊的《泰晤士報》將謀殺案及其刑事司法進程作為呈現重點,建構起探討轉型時期工業社會道德爭議與司法困境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目前國外學界對于維多利亞時期犯罪史的研究已比較成熟,犯罪報道是其重要分支,相關成果頗豐,但對謀殺案報道未給予足夠重視,對謀殺案報道特征及影響論述不足。國內學界對于維多利亞時期的犯罪問題已有一定的研究,相關研究成果陸續涌現。陳力丹、姜德福等學者對19世紀英國新聞傳播發展情況予以關注,但尚無對維多利亞時期犯罪報道及其影響做出論述的相關論著。基于此,本文試圖將謀殺案報道置于社會轉型期的特殊背景下加以考察,對維多利亞時期發行量最大、受眾最廣的《泰晤士報》的謀殺案報道進行文本分析與內容闡釋,勾勒出中產階級對謀殺行為的道德與法律闡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謀殺問題公共領域的建構,如何重塑家庭、性別等價值觀念,并成為延續英國法治精神的開拓性實踐,試圖為理解中產階級如何從道德、法治雙重層面推進社會控制進程提供新的視角。
一、謀殺狂熱:《泰晤士報》犯罪報道概況
19世紀,英國大眾傳媒時代拉開序幕。伴隨著技術的進步與識字率的提升,報刊閱讀超越上層階級的特權,成為各階級公眾獲取信息主要渠道。憑借著雄厚的資本優勢與先進的管理經驗,《泰晤士報》成為這一時期發行量最高、受眾最廣的公眾讀物,逐步確立起了國家報刊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泰晤士報》是英國歷史進程的見證者與引路人,其對社會事件的關注與呈現,深刻影響著維多利亞社會的演進。謀殺案作為 “低俗怪談”(penny dreadful)、“犯罪大字報”(crime broadsheet)等廉價讀物為博取眼球而貫用的主題并不罕見。這一時期,以追求真相、用詞嚴謹著稱的主流報刊《泰晤士報》卻也對充滿“人情味”(human interest)與“轟動性”(sensation)的謀殺案給予了密切關注,圍繞謀殺案及其刑事司法程序,呈現出社會犯罪問題的擬態現實。
(一)《泰晤士報》犯罪報道主題的謀殺案轉向
1. “第四等級”報刊與社會犯罪報道
維多利亞時期是英國社會轉型的重要時期,由于社會制度建設落后于經濟發展速度,貧困、犯罪等問題頻發,社會問題嚴重。與此同時,隨著印刷技術水平的進步,維多利亞時期報業發展迅速,各類社會問題成為報刊探討的重要內容,由此,嚴肅報刊被稱為對政治和社會事務產生重要影響的,獨立于議會之外的“第四等級”(The Fourth Estate)。其中,《泰晤士報》逐步確立起全國報刊的地位,依托廣泛的社會影響力,成為中產階級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途徑。《泰晤士報》由約翰·沃爾特創建于1784年,起初定位為以刊登商業信息為主的經濟類報刊,19世紀以來,在沃爾特二世與托馬斯·巴恩斯(Thomas Barnes)的管理下,《泰晤士報》開始成為一份自由、獨立的日報。《泰晤士報》憑借其堅實的資本優勢引進蒸汽印刷機,率先采用輪轉印刷機技術,搶占了報業技術革新的先機。到1847年,(沃爾特二世)率先采用輪轉印刷機技術,同年就使報紙達到每天12版,這在當時整個世界上都是少見的[1]。維多利亞時期是英國工業社會突飛猛進的時刻,但與此同時,各類社會矛盾也陸續爆發,犯罪率迅速提升。作為一項嚴重的社會問題,對于犯罪及其治理的探討占據了《泰晤士報》核心報道的一席之地。發生于社會貧困階層之中的財產類犯罪,是維多利亞時期的主要犯罪類型。經濟結構變化導致失業問題嚴重、基礎設施建設缺乏導致的生存環境惡劣,是底層階級為解決生存問題進行小規模偷竊的重要原因。維多利亞時期評論家們所描繪的犯罪階級在很大程度上是貧窮工人階級的同義詞,尤其是那些靠臨時工作生存的工人階級。社會上層人士普遍認為,在底層階級中,存在著一個犯罪階級。這一犯罪階級極度貧困且道德感低下,生活在一種“及時行樂”的氛圍之中,不懂得延緩欲望與享受。他們在貧困、酗酒的累積之下,最終走上犯罪道路。《泰晤士報》也對犯罪問題的呈現與探討給予了較大關注。《泰晤士報》每日發行一版,從1830年每版4張到1890年每版12張,綜合而言,犯罪報道與議會討論、重要社論同處于報紙的中間頁面。
2. 由搶劫到謀殺:《泰晤士報》犯罪報道選題的轉變
相比于創刊初期,維多利亞時期《泰晤士報》的犯罪報道主題明顯呈現出一種“謀殺案轉向”。在各類犯罪行為中,謀殺案及其司法程序得到了《泰晤士報》的青睞。從報道數量上來看,涉謀殺案報道數量遠高于其他犯罪(參見圖1)。《泰晤士報》年均涉謀殺報道約741篇,遠高于同時期從數量上看更為嚴重的“偷竊”(Theft)、“搶劫”(Robbery)等的年均報道數,分別僅為117篇、338篇。從變化趨勢上看,報道數量波動上升。19世紀80年代報道數量整體較高,年均報道數量達1 051篇。這與80年代以來“新新聞主義”(New Journalism)的興起密切相關。文學要素被引入新聞創作之中,為犯罪報道提供了更大的發揮空間。彼得·金(Peter King)在對18世紀謀殺案報道開展研究后認為,報道一半以上都關注攔路搶劫……謀殺及謀殺未遂的報道只占百分之五左右[2](P101)。可見,密切關注謀殺案是一種始于維多利亞時期的新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謀殺案的數量在維多利亞時期并未呈現出明顯上升的趨勢,這便與《泰晤士報》的報道重點產生了一種矛盾。維多利亞時期,以偷盜為主的生存型犯罪是較為嚴重的犯罪類型,謀殺案并未呈現出明顯上升趨勢。相比于歐洲其他國家,19世紀英格蘭謀殺率更低。在1857-1890年間,在警察處得以被記錄的謀殺案每年基本不高于400起,而在1890年前后,平均數量則低于350起[3](P42)。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謀殺率僅在1865年達到了萬分之0.2。通常情況下,謀殺率僅保持在約每萬分之0.15,至1880年下降到萬分之0.1,在19世紀末期,謀殺率更低[5](P42)。謀殺案的社會影響范圍也日益縮小,多發生于底層社會熟人之間,發生于陌生人之間的謀殺案件數量下降。有學者十分確信地指出,暴力犯罪開始受到更多的社會限制, 雖然到1800年還不完全是下層社會的特權,但貴族或城市精英肯定不太可能參與其中[6]。 由此可見,維多利亞時期,犯罪報道呈現出了一種“謀殺案轉向”,即報道重點由發生頻率高、所影響社會范圍相對更廣的財產類犯罪轉向了發生頻率低,所涉社會范圍相對有限的人身侵害類犯罪,對犯罪行為本身的關注超越對犯罪行為社會危害的關注。基于此,《泰晤士報》涉謀殺案報道呈多層次展開。

圖1 《泰晤士報》涉“謀殺”(murder)報道文章數 (1830—1910)
(二)《泰晤士報》涉謀殺案報道的內容概述
現代英國早期,木刻版畫(woodcuts)、小冊子(pamphlets)、犯罪大字報(broadsheets)、敘事民謠(ballad)等公眾讀物是公眾接觸謀殺案的主要途徑。以上讀物的犯罪敘事要點可歸納為兩方面。第一類,如木刻版畫、犯罪大字報等僅強調刑罰結果以達到威懾、警示作用。第二類,如小冊子,則將犯罪過程文學化,注重案件本身的道德教化目的。維多利亞時期,在社會轉型造成的道德爭議與司法困境成為新的社會問題這一背景之下,以《泰晤士報》為代表的主流報刊對謀殺案的關注也呈現出了新的視角。
1. 勾勒刑事司法體系
《泰晤士報》涉謀殺案報道分布欄目廣泛,體裁豐富,基本勾勒出了維多利亞時期的刑事司法體系概貌,從制度與執行兩個層面作出了詳細記載(參見圖2)。19世紀,英國設立中央與地方各郡兩級體系負責受理全國范圍內的“可訴訟案件”(indictable offence),謀殺是這一級別犯罪行為受審的重要內容。在中央層面,倫敦設“老貝利”(Old Bailey)負責受理情節嚴重的刑事案件。在18世紀50年代,‘老貝利’一年約開庭八次。1834年起,‘老貝利’擴大并移建,成為我們如今所知的中央刑事法庭(Central Criminal Court)”[5](P14)。而發生在地方各郡的刑事案件由中央刑事法庭下設的“巡回法庭”(Assizes)受理,由兩名法官分理民事與刑事案件。在18、19世紀,英國每年會設立兩次巡回法庭,在大多數郡的郡縣舉辦(county towns),時間分別在‘大寨節’(Lent)以及夏季[5](P14)。《泰晤士報》在巡回法庭方面設有“北方巡回法庭”(Northern Circuit)、“米德蘭巡回法庭”(Midland Circuit)、“牛津郡巡回法庭”(Oxford Circuit)等專欄,對開庭期內涉謀殺案情況只做簡要概括。從程序上看,從警察獲知消息、偵查、審訊、處決各內容均有所涵蓋。對特別關注的案件,以上四方面進程篇幅均較長。一般案件,則側重報道庭審過程,忽略其他信息。社論則多從道德、法律兩個層面對案件進行輿論導向極強的評論。通過報刊閱讀,英國刑事司法體系的設置及運作得以再現。配合讀者來信的刊登,以報刊為載體,以謀殺案為中心的相對完善的“公共領域”初步形成。

圖2 《泰晤士報》涉謀殺案報道分布概況(1830-1900)
2. 內涵外延豐富的報道內容
《泰晤士報》以獨特的視角重構謀殺案,報道主題多樣,內涵外延豐富。曼寧夫婦兇殺案,即柏蒙西謀殺案(Bermondsey Murder)發生于1849年8月9日。曼寧夫婦被指控因財謀殺并于自家廚房處理了曼寧夫人的情夫歐康納(O’Connor)的尸體。該案件曾轟動一時,《泰晤士報》對此共作出了52篇詳細報道,報道具備完整性、連貫性。以此為例,《泰晤士報》重大刑事案件報道基本遵循以下邏輯推進。案發初期,集中于對案情的回顧,包含對案發過程、逮捕過程的冗長敘述,遵循理出案件疑點、對執法人員進行監督批評的框架。如“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關于追捕兇手成功的消息。這可怕的事件所引起的興奮還沒有消退,房子簡直被渴望看到它的人包圍了。大門由警察把守,看來以警察的能力只能壓制公眾的好奇心”[8]。“追蹤潛逃者的過程缺乏警惕,令人遺憾”[9]。對兇手、被害人生平的敘事同樣占據了大量版面。女性殺手瑪麗亞·曼寧(Maria Manning)被描繪為“一個勾心斗角的女人”[10],并稱曼寧先生“與瑪麗亞·曼寧結婚的唯一誘因是想要在政府中獲得一席之地”[11]。審判前,二者的形象已被提前判定。在漫長的庭審記錄后,便是對“死因裁判法庭”(Coroner’s Court)、“中央刑事法庭”(Central Criminal Court)庭審過程的客觀陳述;隨后,記敘死刑過程,包括行刑當天兇手的心理描寫及細微的動作描寫、現場的公眾反應等;最終是對案件細節的回顧與評議,包括對刑事司法程序、涉案雙方的探討。以上內容中,對追緝、審判過程的記述符合重大刑事案件呈現的基本邏輯框架。在此基礎上,與案件本身無關的細節轟動性描寫也占據了大量版面。
《泰晤士報》謀殺案報道主題復雜,其轟動性描寫可以看作對英國傳統犯罪讀物風格的繼承與延續。但其所呈現出的對刑事司法體系的專業性記錄,卻是一種維多利亞時期的新現象。這一現象的出現,得益于司法體系與傳媒界的密切結合。司法體系中的個人與新聞界中的個人是《泰晤士報》謀殺案報道的兩大重要來源。“律師新聞記者”(lawyer reporter)是《泰晤士報》謀殺案報道中與刑事司法進程相關部分的主要撰寫者。律師新聞記者為報刊供稿,是維多利亞時期法律界默許的現象。“在我們的法庭上,可以看到,在一個特殊的隔間里,一個忙碌的筆記員正在記錄訴訟過程,這個人也同樣正在為新聞界準備稿件”[12]。聘用律師新聞記者為報刊撰稿符合司法界與傳媒界的共同利益。19世紀二元律師制度確立,成為一名出庭律師(barrister)所耗費的時間、金錢成本極高,“在律師界謀生絕非易事”[13]。由此,為報刊撰寫法律新聞成為律師謀生的重要手段。這與《泰晤士報》強調報道專業性的需求不謀而合。1847年約翰·德蘭恩(John Delane)任總編輯以來,多次對報刊進行改革,聘請最好的作家為報刊撰寫稿件,努力使報紙辦得高雅不俗[1](P116)。法學對專業性要求極高,英國歷來采取會館制培育法律人才,正規的法律教育是唯有少數精英得以享有的奢侈品。19世紀抗辯制、交叉問詢融入刑事司法體系,愈發加大了普通文人撰寫法律新聞的難度。以上背景下,都認為自身具有社會道德維護者使命的法律界與新聞界一拍即合,律師群體撰寫法律新聞這一專業、高效的舉措由此誕生。
通過《泰晤士報》的謀殺案呈現,英國刑事司法體系躍然紙上。在早期現代社會中,作為謀殺案載體的犯罪大字報是一種簡短與虛構性并存的文學體裁,公眾與謀殺行為保持疏離感。《泰晤士報》謀殺案的媒體呈現拉近了公眾同犯罪及其法律問題之間的距離,建構起一個對社會犯罪問題進行探討的公共領域,為探討社會轉型時期的道德爭議與司法困境提供了絕佳素材。
二、《泰晤士報》謀殺案報道的三重維度
彼得·金指出,在英國人眼里,一提到“犯罪”便會聯想到“謀殺”[4](P105)。直至18世紀末期,謀殺案作為低俗怪談、犯罪大字報等廉價讀物的重要主題,在道德教化、社會娛樂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與社會矛盾的轉變,犯罪問題及其治理愈發復雜。盡管少數讀物仍注重謀殺案博取眼球的商業利益,各類嚴肅報刊已開始對謀殺案加以利用,作為形塑輿論、有力傳達其編輯理念的秘密武器。19世紀致力于提升政治與社會地位的中產階級執掌《泰晤士報》,承擔著辯白中產階級身份合法性、開化獲得政治權利的底層階級的雙重任務。從這一層面而言,謀殺案被賦予了獨特的寫作意義與傳播價值,成為一種多維、復雜的敘事文本。
(一)對維多利亞時期主流價值觀的宣傳與強調
維多利亞時期,英國中產階級迅速發展,并形成了一套專屬于自身的價值體系。在工業文明迅速推進的背景下,中產階級標榜自律、審慎作為自我新興階級合法性的象征,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獨特的家庭觀及性別觀。《泰晤士報》是中產階級宣揚自身言論立場的重要陣地。在《泰晤士報》對謀殺案的報道過程中,以上因素也通過新的方式得以呈現。
1. 維多利亞時期家庭觀念的反面教材
以家庭觀念為核心,以性別分工為主要內容的中產階級道德觀念,是《泰晤士報》謀殺案報道的重要指導思想。謀殺案件性質是否符合中產階級對轉型社會的道德關切點,是報道主題抉擇的重要依據。維多利亞時期,謀殺案類型可劃分為發生在熟人之間即夫妻、母子、主仆之間的謀殺行為,發生在陌生人之間的由公眾斗毆、工作沖突、搶劫、罷工等行為引發的謀殺兩類。其中,發生在家庭內部的謀殺案比率較高,在19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之間約占謀殺案總數的55%,而18世紀這一比例僅為28%[14]。發生在熟悉成員或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殺案、毒殺案是《泰晤士報》謀殺案報道的重點。1855年被害者為兇手好友、兄弟、岳母、孩子等七人的魯奇利毒殺案、1842年兇手殘忍肢解情人的羅漢普頓謀殺案等,都是《泰晤士報》的重點報道案件,報道篇數分別為48篇、20篇。報刊對情殺、毒殺案的聚焦,使家庭內部矛盾可視化。
謀殺行為暴露了發生在“家庭領域”(domestic sphere)的通奸、暴力等行為,對維多利亞時期賴以維系的家庭觀念提出挑戰。工業革命促成了傳統農業社會經濟模式的瓦解,家庭手工業被工廠手工業代替。家庭的生產職能弱化,情感職能增強,成為中產階級道德觀念中的核心內容,被稱作工業生活巨大壓力下的私人避風港[15]。情殺案與毒殺案意味著家庭領域背叛者的出現……只有家中熟人、密友才能執行這一親密舉動[16]。實際上是一種家庭領域的叛國罪(Domestic Treason)[17]。值得注意的是,毒殺案在維多利亞時期發生概率極低。在1849年英格蘭及威爾士地區超過20 000起的無法解釋的非自然死亡中,有415件被認為與毒殺有關。在排除自殺行為及誤食毒藥之外,只有11件被指控為毒殺案,且并非所有案件最終都被判處有罪。因此蓄意毒害大概只占據非自然死亡中的3‰[18]。 由此可見,經由《泰晤士報》的呈現,對案件細節與人物矛盾進行詳細描寫,提升了以往相對隱蔽、社會影響力較小的兩類謀殺行為的可視性。
2. 維多利亞時期性別角色的異類
《泰晤士報》謀殺案敘事文本建構過程中,強調了維多利亞社會賴以維系的性別觀念。社會預期的性別角色內涵,成為報刊平行于法律程序外,對案件嫌疑人進行“道德審判”的“不成文法律”。19世紀工業社會賦予了“男子氣概”(masculinity)新的內涵,“自控”(self-control)成為理想男性氣質所應具備的重要內容,為整個社會所推崇,正如馬丁·威納(Martin Weiner)所言,“正在形成的新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秩序使個人自律、秩序和非暴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寶貴和必要”[19]。自律即擁有理智的頭腦、控制自身的暴力傾向,成為中產階級男性所推崇的重要特征。1855年,醫生帕爾默被指控毒殺其好友、兄弟、岳母、孩子等七人,以騙取保險金。在這一轟動事件塵埃落定后,《泰晤士報》在評論中寫到,“他的一生和他所犯下的罪行,是一個可怕的教訓。一個人職業生涯的下滑如此生動地呈現在公眾面前,實屬罕見。我們唯有以此案為例,以警示那些即將釀成大錯的人”,“從賭博到資不抵債,從資不抵債到偽造文件,從偽造文件到謀殺,他成為了最下流的人。他充滿戲劇性的一生,令人深思”[20]。由此可見,賭博、偽造等自律喪失的行為,被與謀殺行為建立直接聯系。
《泰晤士報》謀殺案的詳盡報道使女性經歷以人物外貌與社會經歷為對象的道德審判。維多利亞時期的理想女性被稱為“家庭天使”,她“最大的功能是贊美”[21]。她們被要求保持優雅,并擁有“克制容忍”[22]的態度。對女性犯人的描述可大致劃分為兩類,“受憐憫者”與“性別異類”。出身高貴舉止優雅或柔弱的女性是典型的“受憐憫者”。同樣是毒殺丈夫的案件,并涉通奸行為,《泰晤士報》對待出身高貴的梅布里克夫人(Mr.s Maybrick)與夏洛特·哈里斯(Charlotte Harris)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梅布里克夫人被稱為“絕不是低能或愚笨的,相反,不管她那迷人的頭腦所要達到的目的有多壞,她都是相當聰明的”[16]。這樣的評價很大程度上由于梅布里克夫人出身高貴,并在庭審過程中注重自身優雅克制的形象。而夏洛特的行為則被稱為“一種迄今為止聞所未聞的暴行”[23]。 另一類“性別異類”,她們的謀殺舉動被與性別倒錯特征相聯系。瑪麗亞·曼寧被稱作“既不端正,也不女性化”[10],“作為一個女人,她具備一切女性不該擁有的異端特質”[24]。這種“道德審判”與劃分顯然以“家庭天使”標準,即中產階級對理想女性的期許為依據,使女性罪犯在刑事司法進程中的一切細微舉動備受關注。
(二)對維多利亞時期司法體系的還原與評述
除涉及潛移默化的道德要素外,《泰晤士報》對謀殺案的報道還是轉型時期司法改革的鏡像。依托謀殺案報道,《泰晤士報》將各項刑事司法進程的運作過程詳細呈現在公眾面前。在案件發生初期,《泰晤士報》會對嫌疑人做出迅速判斷,“我們懷疑犯下這項可怕罪行的是丹尼爾·古德”[25],并在“附加細節”(Additional Particulars)中刊登嫌疑人的基本信息。在案件的偵查取證階段,警方公正執法的工作態度得以詳細展示,“督查”(superintendent)“巡視員”(Inspector)“小隊長”(Sergeant)“巡警”(Constable)的工作匯報各占特定篇幅。報道以“警方正以全力追擊兇手”[25]為報道收尾,對各方作用的發揮給予肯定與強調。同時,報道注重引導公眾對案件的理性參與,在刊登懸賞令的同時,對小報的不實信息予以核實勘正。在案件的審訊階段,報道對庭審過程全盤再現,法官、辯護律師身份、開庭時間得以詳細記錄。法官、嫌疑人、陪審團宣誓、交叉質詢、驗尸報告被全文刊登,但與《中央刑事法庭審判集》所記載庭審資料略有區別,報道往往融合了直接引語、間接引語的方式,在適當時刻對當事人做出特寫。在罪犯的處決過程中,讀者基本能夠坐在家中“觀看”到罪犯如何從監獄走向刑場。這一過程中罪犯與獄卒、長官、行刑者進行的對話、罪犯的情緒變化等細節被詳盡刻畫。絞刑現場的血腥場面也被細致描繪。在案件結束后,《泰晤士報》會在觀點與社論中對案件法律環節的得失做出評判。
《泰晤士報》注重引導讀者從專業視角解讀相關案件,對案件中司法程序及判決疑點提出質疑,為司法改革設置輿論導向。以柏蒙西謀殺案為例,在中央刑事法庭進行公開審理前,《泰晤士報》濃墨重彩闡明這一審判結果在刑法史中的重要意義。報道提出,“我們應該已經觀察到了。丈夫和妻子將會同時站在法庭上受審——這一情況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夫妻同時受審十分罕見,而且這關乎如何劃定案件中的法律行為責任。在英國法律中,已婚女子享有很多特權,同時也受到諸多限制。而在目前的這一案件中,存在如下可能性,即盡管她已犯下犯罪的罪行,但她可能免于法律的懲罰”[26]。 法律判決的性別差異在維多利亞時期備受爭議。諸多研究者達成共識,“一直以來,易被判以人身侵害罪的多為男性而非女性”,“在刑事司法進程中的任一階段,女性都傾向于被從輕處置”[27]。 這與當時犯罪學家對女性特質的詮釋與女性法律地位的模糊性密切相關。維多利亞時期犯罪學家認為“從進化論的角度來講,女性一向柔弱,相比男性她們不易犯罪”[28]。而從具體的法律規定而言,“已婚女子(feme covert)婚后沒有獨立的合法身份……這意味同丈夫一起犯下重罪的已婚女子,可以此為理由獲得赦免”[5](P94)。《泰晤士報》借曼寧夫婦二人受審這一事實,敏銳地捕捉到了維多利亞時期法律執行過程中的爭議,引導公眾對此作出思考。在1889年發生的利物浦毒殺案中,《泰晤士報》提醒公眾注意毒殺案證據模糊性及審判程序的漏洞。“我們相信,大部分人不會相信對梅布里克夫人(Mr.s Maybrick)作出的有罪判決……在證據如此有限的情況下,理應因‘無法證明’而作出無罪判決”“如果法庭允許對梅布里克夫人實施交叉問詢,我們大概會更接近真相……希望這悲慘的一切至少能夠換來一場法律的改革”[16]。 由此可見,通過對刑事司法進程的詳細記錄,謀殺案成為公眾司法教育的重要素材。對刑法爭議的合理把控,也使《泰晤士報》成為轉型時期刑事司法改革的辯論場。
(三)對轟動氛圍的創造及渲染
《泰晤士報》謀殺案報道作為新聞產業化的產物,在工業化迅速推進的背景下,商業利益固然成為其追逐的重要價值。在謀殺案報道過程中,《泰晤士報》以文學性極高的筆法,提升了報道的轟動性與可讀性。1828年紅谷倉事件的兇手威廉·科德(William Corder)在謀殺情人案件中,《泰晤士報》運用各類描寫手法,直接引語、間接引語混用,描繪了一個在審訊過程中“聲音略有顫抖”地為自己開脫,在交叉詢問環節“垂頭喪氣”的狡猾、受教育程度低、帶有愧疚與心虛的罪犯形象。在行刑日對其的報道中,主要采取敘事抒情方式。“在行刑的前一晚,他講述了自己婚姻的細節。”報道提及了在殺死情人后,他通過報紙廣告征集另一半提出“會穿特定的裙子去教堂,并且會坐在特定的地點等待”“他說他按照要求前往了教堂,但由于記錯了禮拜的時間沒能見到那位夫人”[29]。 該報道還刊登了他給現任妻子的信,臨行前的兇手變成了一個忠于婚姻、有血有肉甚至令人同情的“人物”。《泰晤士報》犯罪報道文學性極強的報道方式的形成,是自由主義經濟背景下,報刊商業競爭的產物。19世紀,以謀殺案為對象的非虛構類作品頗豐,轟動性敘事是犯罪小報、廉價報刊等讀物的慣用手法。在應對以上讀物在犯罪報道領域對《泰晤士報》提出的競爭的過程中,《泰晤士報》對轟動性的報道方式加以揚棄。
綜上所述,《泰晤士報》謀殺案報道特征極為復雜。在早期現代社會中,讀者能夠接觸到的謀殺案十分有限,對謀殺行為保持疏離感。在以《泰晤士報》為代表的主流報刊的建構下,謀殺案在日常社會中的“可視性”提升。高發于家庭領域內,緊扣維多利亞時期備受爭議的道德與司法爭議的謀殺案,拉近了一名普通公眾與謀殺的距離,也拉近了其與刑事司法體系的距離。當距離被拉近,無論是因謀殺案產生的恐慌情緒,還是對社會司法體系的認知,都將產生重大變化。
三、誡與罰:文明社會下謀殺案角色的轉變
在西歐社會,約從17世紀早期開始,致命暴力行為顯著下降,諾貝特·伊萊亞斯(Nobert Elias)稱此為“文明的進程”(civilizing process)。通過國家集權的建立及隨之而來的各類“規訓機制”(disciplining institutions)對社會生活的滲透,自制(self control)得以維持,這被認為是西方文明社會誕生的關鍵因素。自制與否實質上成為衡量不同歷史時期個體行為是否符合主流價值觀念的標準。內在思想與外在形制控制的加強,是實現自制的重要途徑。維多利亞時期,《泰晤士報》對謀殺案的關注與解讀賦予了謀殺案在推進文明社會進程中新的作用。
(一)中產階級價值觀入法的催化劑
《泰晤士報》的謀殺案報道對社會主流價值觀向刑事司法領域滲透產生了一定影響。從立法層面看,維多利亞時期法律對家庭領域的干預顯著增強。即使到19世紀初期,家庭內部暴力問題仍是一項法律邊緣問題。1830年,格拉斯哥地方法官在對一名家庭暴力者的判決過程中指出,“如果被起訴者對其他人而非他妻子施行了家庭暴力,他確實應被嚴懲,但他毆打的不過是他妻子”[30],最終施暴者僅被處以較小數額的罰款。對家庭領域(domestic sphere)的維護,即是對中產階級身份合法性的辯護。《泰晤士報》向來提倡對丈夫對妻子的人身侵犯行為加以嚴懲。在一次家庭暴力案件后評論道,“人身侵犯行為目前并未在法律中得到適當的懲罰”[31]。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中產階級眼中,家庭領域發生的謀殺行為是維多利亞時期一項極具道德爭議的問題。維多利亞男性被認為是家庭與道德的守護者。19世紀以來,打妻子的人越來越被妖魔化,被認為是一種工人階級的問題[5](P104)。家庭領域的暴力行為與工人階級酗酒、暴力的形象相聯系,成為中產階級道德規訓的重要層面。依托對家庭領域內謀殺行為的關注,《泰晤士報》提升了這一類謀殺行為的可視性,為國家立法對家庭領域加以干預提供了輿論基礎。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直至維多利亞末期,特別是從1853年開始,基本每十年便會通過一部新的立法。以上立法以保護柔弱的女性與改造暴力的男性為主旨,成為規范家庭領域道德秩序的強制性力量。
從司法實踐中看,《泰晤士報》謀殺案報道對女性殺人犯形象的塑造往往激起強烈的輿論反應,是否具有社會公認的性別特質,成為影響女性罪犯司法判決的重要因素。這種輿論導向對司法判決施以壓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司法判決結果。以巴恩斯懸案和利物浦毒殺案為例,兩案在審判過程中均面臨著證據不足的困境,而輿論對于審判的預期卻大相徑庭。在巴恩斯迷案中,凱特·韋伯斯特的異邦、非女性化特質被反復強調重點,無疑增加了公眾先入為主的厭惡感。《泰晤士報》稱,凱特·韋伯斯特一案的證據是“盡管冗長卻不薄弱,形成了間接證據鏈,陪審團完全有勇氣由此判定她就是這一罕見暴行的實施者,不會有人懷疑他們判決的正確性”[32]。而在梅布里克案判決后,《泰晤士報》指出,“我們相信,大部分人不會相信對梅布里克夫人(Mr.s Maybrick)作出的有罪判決……在證據如此有限的情況下,理應因‘無法證明’而作出無罪判決”[16]。輿論影響了面對女性犯罪者的司法實踐的差異,這一差異進而成為維持主流性別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
薩義德在論及東方主義時曾言,“任何一種文明的發展與維系均需要另一種相異、相爭的‘另一個自我’(alter ego)的存在”,“身份的建構……涉及建立一種相反的‘他者’(opposite),而這種差異性實質上是通過不斷解讀、重釋與‘我們’的區別建構起來的”[33]。《泰晤士報》借謀殺案對社會道德的“他者”加以曝光、探討,推動了部分中產階級視角下的家庭觀念與性別觀念以立法形式固定下來,并成為影響司法實踐的重要因素。由此,在某種程度上,《泰晤士報》的謀殺案報道成為核心價值觀影響立法與司法實踐的重要途徑之一。這賦予核心價值觀權威性,強化了主流價值觀念的道德規訓作用。
(二)維多利亞時期法制現代化的燈塔
1. 揭露維多利亞時期的司法改革困境
19世紀被認為是“英國及其司法制度同初步實現經濟工業化、政治民主化的社會現實之間的一次整合運動”[34]。面對經濟基礎的變革,司法體系面臨的困境接踵而至。在一個階級矛盾激化的社會中,司法公正性成為激進報刊質疑的對象,法律權威性岌岌可危。“北極星報”(the North Star)“憲章通訊”(the Chartist Circular)等報刊作為傳播工人階級理念的前沿陣地,作為階級權力象征的法律是其質疑重點。質疑論調在其刑事案件報道中顯而易見,“北極星報中充斥著窮困潦倒的被視作受害者的罪犯,這讓其讀者產生盡管法律不會令人挨餓,但它經常把瀕于饑餓的人逼向謀殺和自殺的絕境”[35]。 囿于社會改革的滯后性,以地方治安官為基本單位的刑事司法體系在日益嚴峻的犯罪問題面前捉襟見肘。盡管1829年羅伯特·皮爾起草《1829年大都市警察法》,但受制于傳統地方與中央權力爭端等因素,其實際執行阻力重重。現代警察被上層社會與統治階級政治精英嘲諷為“一個在君主控制下的常備軍”[36]被底層民眾蔑視作中產階級的“家仆”(Domestic Missionaries)。從犯罪問題的刑罰方式來看,以輕罪重罰為特征的“血腥法典”(Bloody Code)不再適用于新的犯罪現實,針對新的刑罰制度的定奪與死刑廢止問題的爭論持續了一個世紀之久。總之,對英國司法體系的改革貫穿于整個維多利亞時期,涉及法院組織及相關司法制度、訴訟程序等各層面。改革過程中,《泰晤士報》的謀殺案報道搭建起了一個對刑事司法體系呈現、探討的平臺,并有意識地制造、引導輿論討論熱點。
2. 提升公眾法律素養的有力素材
《泰晤士報》謀殺案報道對提升公眾法律素養、提供司法監督渠道具有重要意義。19世紀以來,隨著選舉權的擴大,“法律界人士均認識到將刑事司法體系及相關變革更為方便快捷地傳遞給政治上十分活躍的城市居民的重要性”[37],限于精英階層的傳統司法教育已無法滿足公民權擴大的社會現實,司法教育被提上日程。從《泰晤士報》讀者來信區域中對刑事案件及刑事司法改革的探討來看,其提出的通過閱讀使讀者“領會司法過程的艱辛,評價司法程序”[38]的意圖獲得了極大成功。讀者從證據有效性、程序爭議性、判決有效性等多個層面發表意見,如“出于對公正與真理的追求,我冒昧地對此案的證據作出如下評判……”[39]。利物浦毒殺案判決后,海倫·丹斯莫爾(Helen Densmore)在1898年專門撰書回顧此案,正是在日常閱讀報刊時瞥見該案的讀者來信引起了他的興趣,從此之后“每天閱讀該案的法律細節,對庭審過程中記載的不公正十分在意”[40]。該案引起的公眾輿論壓力,使最初的絞刑判決更正為終身監禁。由此可見,謀殺案極大提升了讀者參與刑事司法體系探討的興趣,《泰晤士報》借謀殺案建構了一個對司法體系展開廣泛探討的公共領域。通過《泰晤士報》的謀殺案報道,公眾獲得了司法監督的有效途徑。在《泰晤士報》的引導下,公眾與刑事司法體系進行理性溝通,感受到輿論對追求正義與真相的力量,這有效地疏導了公眾對司法體系的不信任情緒,對于重建司法體系的權威性至關重要。
3. 延續英國法治精神的開拓性實踐
《泰晤士報》還借由謀殺案報道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轉型時期英國刑事司法體系的失序狀態,加強了刑事司法體系對犯罪的有效控制力度,成為延續英國法治精神的開拓性實踐。1842年《泰晤士報》對羅漢普頓謀殺案中警察辦案不力加以批判,提出“公眾有權要求看到一個更好的警察隊伍——如今這支隊伍數量龐大,且對國家大規模的人財物力僅是一種平白浪費”[41]。這一公開譴責激發了社會各界對警察制度偵查兇手能力的不滿。迫于輿論壓力,結案兩月內,梅恩便向內務部要求在警察內部新設一個專門負責偵查工作的新部門。1842年,一個偵查分支建立了,這一警察隊伍中的分支有八名長官。1868年增為十五名[42]。 1829年建立的現代警察制度采取分區監管制度,主要目的是維持公共秩序并對擾亂公共秩序的潛在罪犯加以控制。《泰晤士報》通過羅漢普頓謀殺案發覺到了警察制度的功能漏洞,影響了警察職能由巡邏向偵查的轉變,警察制度的有效性顯著提升。在刑罰制度層面,公開處刑制度與死刑制度的廢止是維多利亞時期的主要問題。《泰晤士報》對行刑過程的細致描繪,以言語的形式延續了法律的威懾力,解決了提倡保留者的擔憂。《泰晤士報》敏銳地捕捉現有刑事司法體系中的各項問題,有效引導改革輿論,刑事司法體系日趨完善。維多利亞末期,英國犯罪率得到顯著控制,這是作為社會控制重要手段的法律體系有效性的最佳證明。
維多利亞末期,報刊迫于經濟壓力對轟動性案件的密集報道與細致關注,使相關案件的社會影響擴大,以轟動案件為原型的大眾文化產品層出不窮。這難免催促了一種基于階級、性別的刻板印象及針對特定“危險個人”群體恐慌在公眾腦海中形成。家庭中的危險女性成為社會防范的對象。1851年《銷售砷管制條例草案》在上院進行三讀討論。這一過程中,卡萊爾伯爵認為法案應該明確規定砷只能售賣給成年男性,因為多起凄慘的事故都是由被派去買砷的兒童、女性家仆所制造的。女性毒殺犯瑪德萊娜·史密斯也被認為是喬治·艾略特《掀起的面紗》(the Lifted Veil)懸疑小說的靈感來源。這種對于罪犯標簽化的方法,在遵從判例法的英國尤其危險。
德與法是社會調解體系中的兩種重要調節杠桿。同為社會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者規訓社會的方式相得益彰。維多利亞時期《泰晤士報》謀殺案報道是融合道德與法律治理作用的的開拓性實踐,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工業社會轉型時期社會價值觀念與刑事司法體系的整合。對推進中產階級話語體系下的社會文明進程意義重大。
馬特·庫克(Matt Cook)曾指出,“刑事案件有利于樹立社會規范,并重新定義性別、階級、國家觀念。”維多利亞時期是英國走向工業化社會的重要時期,在新的經濟社會條件下,以道德習俗、法律制度等為代表的社會上層建筑也正處于自我調適與重塑過程之中。在這一背景下,《泰晤士報》起到了一種燈塔的作用。《泰晤士報》在謀殺案報道過程中,通過切中時代痛點的案件選取標準、極具可讀性與引導性的案件報道技巧、注重法律專業性的案件分析方式,發揮了謀殺案實現社會道德規訓與法律控制的雙重作用。由此,轉型時期,傳媒的社會控制作用得以發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媒體時代,各類媒體是激發刑事案件蘊含無限潛能的關鍵。公眾對刑事案件有著普遍的好奇心,媒體對刑事案件的呈現方式,決定著謀殺案究竟僅是一種“娛樂至死”的感官刺激,還是發人深省,從而對社會控制具有潛移默化影響的有效素材。當前,中國正處于全面依法治國的推進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使法治和德治在國家治理中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入法入規,可為公眾提供有效的價值引導,從而加強法制建設。另一方面,提高公眾法律素養也是深化依法治國的重要手段。從這一意義上看,刑事案件是對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全盤顛覆,其刑事司法進程則是檢驗刑事司法體系合理性的照妖鏡。利用好刑事案件報道,使其成為兼具道德法律雙重意義的社會控制工具,對加速實現社會文明進步與依法治國進程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