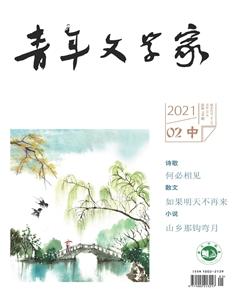喧嘩的都市,無奈的愛情
摘? 要:上世紀90年代,身居現代大都市廣州的張欣順商潮而上,及時地抓住了商業活動給城市生活帶來的變化以及對人們心靈的沖擊,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基于現代城市化社會基礎之上的小說話語模式,成為了城市書寫隊伍中的舉大旗者。她的小說以都市愛情為主要主題,為讀者敞開了一扇瞭望現代都市生活的窗口,但這種描寫又是浮光掠影式的,尚未洞察事物的本質,尚未上升到審美的層次。
關鍵詞:都市;愛情;張欣;小說
作者簡介:李振紅(1973-),女,山東萊蕪人,副教授,碩士,研究方向:語言文學、教師教學與發展。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1)-05-0-02
上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急劇加速的現代化進程使城市成為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核心。作為文學主流的小說順應時代潮流把描寫的焦點調到了城市書寫上。張欣順流而上,成為了城市書寫隊伍中的舉大旗者。她的小說的確為我們敞開了一扇瞭望現代都市生活的窗口,但這種描寫又是浮光掠影式的,尚未洞察事物的本質,尚未上升到審美的層次。
一、喧嘩的都市,單調的敘述
張欣的小說無一例外地難逃城市商業活動這一窠臼,帥哥美女、名牌服飾、豪宅名車是小說不二的主人公與道具,彩燈旋轉的咖啡廳、酒吧間或T型臺是人物活動的主要場所。這些人物在這些場所里出出進進,演繹出一幕幕乞丐變成富翁轉眼又成乞丐的鬧劇或今日恩愛夫妻明日形同陌路的悲歡離合,到處是機遇,到處是陷阱,愛情隨處可遇,轉眼煙消云散。所有這一切共同組成了一幅生動的現代都市喧囂的畫面。
金錢是張欣筆下城市最重要的基石,沒有錢,這個城市瞬間崩塌。林紫淑只用一萬元港幣就摧毀了尹修星和寒棣的愛情,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愛情。對金錢利益無休止的欲望像一只翻云覆雨手,隱藏在人們的心中操縱著人們的喜怒哀樂,它甚至使有些人放棄了可貴的做人的尊嚴與良心。《愛又如何》中貌似高傲的詩人肖拜倫為了獲得可供自己享樂的金錢,竟不知羞恥地欺騙愛宛的感情,依靠女人來生活;而富有的愛宛落到了只能用金錢來購買感情慰藉的地步。良心—這束縛人們惡性的最后一道防線,卻被艾強看作了背負的最沉重的十字架,并把自己背負良心債的原因歸結為“沒有錢”。張欣小說中的人物從不避諱金錢的重用,甚至公開認同“金錢至上”的人生信條。《浮華背后》中清純可愛的少女莫億億,其母給她取名“億億”的本義是“一一”,希望她事事得第一,但她卻不以為然,認為“第一有什麼用,多點錢才是真”。雖然在《今生有約》里,張欣讓我們看到了一絲溫情。但她卻沒讓這種溫情繼續下去,就在團員與侄女米奇即將血肉相連之時,米奇卻死去了。作者雖然期盼真情的存在,但面對惟錢是圖的都市,又難以說服自己徹底相信毫無利益關系的真情的存在。作者對美好的希望的狠心掐滅,讓我們在痛惜中體味了現代生活中人際關系的冷酷,看清了金錢對人們一向推崇的溫情的人際關系的摧毀。
在對人性物化的書寫中,張欣自己似乎也難逃利益的誘惑。伴隨著她的作品被搬上熒幕所帶來的巨大利潤,作者的小說創作也呈下降趨勢,作品越來越呈現“愛情+暴力+傳奇”的公式化,作品的主人公、情節、敘述話語等都出現了嚴重的雷同化,書寫手法趨于單調化,有人指責張欣的小說就是大陸版的瓊瑤或嚴沁。之所以如此,與其在寫作上的急功近利不無關系。
張欣雖然用敏感細膩的筆觸向我們展現了一幅多彩的現代都市之圖,但她筆下的廣州,缺乏自己的個性;雖然她也寫了城市人們的焦慮,但沒有真正寫出因城市生存的復雜、思想秩序的錯亂、人性內涵的迷惘而產生的焦慮,尚未上升到審美的焦慮。[1]她雖然寫的是繁華的大都市,卻散發出了鄉村的氣息,并沒有完全的城市化。作者自己曾說過:“有時,我們會產生錯覺,生在城市,長在城市,難道還能體驗出鄉村的感覺來?其實這一點都不奇怪,我們的城市相當年輕,還完全沒有自己的規模,更談不上風格和韻味。而我們的行為風格倒常常是純粹‘農民式的——這里指狹義上的陳舊與;偏見”。[2]這段話反映了作家在城市寫作中對鄉村的極度排斥。其實,我們的城市雖然年輕,但在它浮華喧囂的表象之下,是存在著不變的秩序的,不過這些不變的東西是嵌藏在巨變事端的縫隙中的,常常被忽略了。作為一名作家。只有讓自己的心沉靜下來,拋棄追名逐利的浮躁,才能敏銳地捕捉到城市跌宕生活中那些的最終決定事物動向的東西。要想寫出真正城市化的東西,作家身上反而應該保留一點淡泊的鄉村味道。
二、悖離的思想,無奈的愛情
婚姻愛情是張欣的城市小說中的重要主題,是她透視城市生活的重要媒介之一。作者將她的主人公置于城市語境中,寫出了傳統的愛情婚姻價值觀在金錢利益的挑戰下所面臨的空前危機。《免開尊口》中,一向對丈夫情深義厚的妻子,被“淘金熱”異變成了“兇神惡煞”的母老虎,逼著丈夫必須發財。昨日舉案齊眉今朝同床異夢,就算勉強維持婚姻,溫情也已消失殆盡。《掘金時代》里琴瑟和鳴的穗珠和穆青在下海經商的大潮中家庭趨于破裂。《愛又如何》里的可馨和沈偉,曾是“現代梁祝”,但隨著可馨失業帶來的家庭經濟危機,美滿的婚姻幾近分崩離析。《致命的邂逅》中的徐寒池和章邁算得上是真心相愛的,但在牢獄之苦與愛情的抉擇前,章邁主動地放棄了愛情。張欣就是這樣豪不遮掩地向我們展現了愛情在金錢、自由等利益面前的脆弱與無助,展現了商業經濟社會里,都市愛情的不堪一擊和無可奈何。這正如《愛情奔襲》里的主人公所說:“現代人的感情根本是不堪一擊的┄不能說愛是虛假的,但與利益相比,它卻顯得很輕很輕”。
雖然張欣寫出了現代都市中愛情在金錢等利益面前的蒼白無力,但作為一個現實中的平常女人,張欣不可能不對美好的愛情懷有童話般的幻想。作者并非不期望真愛,而是因為把愛情看得太高太好,反而成了一個虛無的美夢。正如《永遠的徘徊》中,作者通過陸豐和谷憶禪、紀剛剛與林子的情感糾纏,要寫的并非是愛情本身,而是想敘述一個深藏在每個人心底的彌漫著古典氣韻美夢。在《免開尊口》里,作者則通過醫生賈丁、病人的養護人林弟弟之前的感情糾葛把愛情寫成了神話與宗教。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身處紛亂的商潮中的現代都市人依然對美好純潔的愛情存有美好的向往和默默的期待。
在《但愿心如故》中,張欣曾講過這樣的話:“我是一個較傳統的人,因為生活在一個開放的城市,無形中被許多新觀點所包圍,所以自己常常會成為一個矛盾體”,這種思想上的矛盾同樣也成了貫穿在其小說中的一個矛盾。這表現在作者受傳統觀念影響,在揭示都市的浮華與陰暗面后,仍極力想在小說中樹立起愛情追求的傳統道德意義,但另一方面,在周圍現實生活的逼迫下,又對這一意義持有強烈的懷疑態度。這一點在小說《如戲》中可以看出來。佳希在丈夫下海后,在害怕失去往昔幸福生活而于生活的邊緣認識了匡云濃。二人的相愛似乎是基于對藝術的共同追求,這似乎也是作者極力想向我們證明的:真正的愛情在共同的追求中是存在的,但小說的結局卻讓我們若有所失:佳希在傳統道德的招引下硬生生地跨回了剛越雷池的腳步。佳希的回歸好像是基于丈夫的理解,但連作者自己似乎也不很相信這樣圓滿的結局。透過整篇文字,我們看到的是一顆在情感、欲望和傳統道德的沖突中搖擺不定的心靈。佳希的道德保全顯然并不很符合故事的自然發展,是作者有意維護的結果。這種故事發展與結局間的中斷反映出了作者思想上的矛盾,反映出了作者對愛情的態度:作者是把愛情與婚姻看成了現代都市人得以休憩的最后一片停泊地。為了給身心疲憊的都市人一份溫馨與希冀,更是為了想維持住作者自己內心情感道德的大廈,作者不惜強行介入小說中,生硬地拉斷故事情感的自然發展,給故事加上了一個光明的尾巴。
張欣畢竟是一個朝夕生活在現代都市中的作家,耳濡目染的種種太過現實的都市愛情,讓作者再也難以自欺欺人、掩耳盜鈴了。在小說《浮世緣》中,作者終于說服了自己,徹底打碎了人們對愛情美妙的幻想,寫出了現代都市人實際上已經沒有了任何一處靈魂的棲息地。《浮世緣》可以說比較真切地表達出了張欣對現代都市愛情的看法與觀點。落虹為了愛情遠離家鄉來到城市,而瑞平在前途與金錢的誘惑下卻舍棄了落虹,投向了夢莉的懷抱,這中“陳世美”版的愛情在現代都市中是俗而再俗的了。與此相比,落虹與亞肯的愛情可以說是童話般的純潔美好,二人在患難中建立起了真摯的感情,毫不摻雜利益的塵垢,特別是亞肯給落虹的愛是何等的無私高潔,作者還在亞肯給落虹的信中公開地發表了自己的愛情宣言:“愛是一種能力,……有些人喪失了這種能力。其實,純粹而忘我的愛情并沒有消失,她存在著,……就在我們身邊,在我們平淡的生活里。”作者用二人未受到任何世俗觀念和金錢權勢羈絆的愛情,告訴了我們真愛的存在,還用信強化了這一信念。但作者最終還是殘忍地讓亞肯死去了,美麗的愛情最終灰飛煙滅,留下的除了心痛還是心痛。就是這樣,作者仍不放過我們,連一絲幻想也不留下,在故事的結尾,作者讓落虹與瑞平在現實生活的逼迫下,竟然破鏡重圓了。這是多么冷酷無情的設計,但又是多么貼近現實啊!張欣就是這樣決絕地告訴我們,現代都市人的真情已經被洶涌的商潮利益吞噬地片甲不留了。因此,在《不太麻煩的愛情》中,主人公對愛情的要求竟然只是一份不太麻煩的愛情。通過這玩笑似的宣言,作者展示給我們的是都市愛情的無奈。
愛情在張欣的小說中雖然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卻并非單純地為愛情而寫愛情。愛情在她的小說中是象征、是拯救,是價值持守和裂變的晴雨表。作者通過展示都市愛情的無奈,完成了對都市人價值持守和裂變的象征。
參考文獻:
[1]黃發有.準個體時代的寫作[M].上海三聯書店,2002.
[2]張欣.慢慢地尋找,慢慢地體驗[J].中篇小說選刊,199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