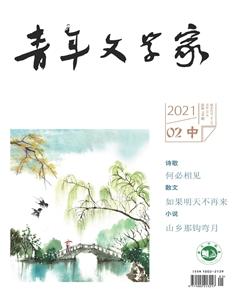論小說《游園驚夢》的音樂敘事與悲劇意識
摘 要:跨媒介分析的方法為文本解讀提供了新思路。白先勇的小說《游園驚夢》具有音樂與文學之間跨媒介敘事的特征,本文以文學為本位,從跨媒介的角度分析小說《游園驚夢》的音樂敘事。在內容層面,主人公藍田玉受到了音樂精神的激發,由此產生生命流逝的悲劇意識;在創作層面,短句和重復手法的運用使意識流具備了音樂形式,形式即內容的表現手法強化了悲劇意識。
關鍵詞:白先勇;《游園驚夢》;音樂敘事;悲劇
作者簡介:鈕蕓(1996-),女,漢族,江蘇蘇州人,江蘇師范大學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1)-05-0-02
白先勇是當代著名的美籍華裔作家,其作品以糅合中國古典美學思想與西方現代寫作技法著稱,短篇小說集《臺北人》因描繪了歷史變遷百景圖而廣受關注,其中《游園驚夢》一文更以其細膩的文風、嫻熟的手法、悲天憫人的情懷而成為中外學界關注的焦點。他們以不同的文學批評視域,從白先勇的生平經歷、創作手法及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命觀與歷史觀、作品影視改編等多個角度對這部小說加以闡釋。用不斷更新的理論與視域考察白先勇及其文學創作,深化研究,使其在社會歷史大背景的演變中煥發出新的闡釋意義。
白先勇從小受到音樂的影響,尤其熱愛昆曲藝術,在他的小說中常見音樂的身影,作家本人在談話、散文中也常提及音樂對他人生以及創作的影響。因此,以白先勇文學創作中的音樂敘事為切入點,為白先勇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路徑。李雪梅梳理了音樂在不同層面參與白先勇小說意義建構的表現,陸正蘭指出音樂在白先勇小說中扮演了一種多情境符號,參與了文本中的社會文化空間建構。
白先勇曾說:“由于昆曲《游園驚夢》和傳奇《牡丹亭》的激發,我便試圖用小說的形式來表現這兩出戲的意境。”[1]可見,白先勇有明顯的“出位之思”,以文學藝術展現戲劇藝術的意境,在跨媒介中尋求情感形式之間的類似。本文也將從《游園驚夢》的音樂敘事出發,探討小說文本如何在內容與形式上體現出音樂特征,并由此論證《游園驚夢》的悲劇意識如何從音樂精神中誕生。
一、“出位之思”:音與詩的跨媒介問題
關于文學、音樂的起源及音樂與文學的關系古今中外的相關討論從未停止。古代西方著名理論家亞里士多德提出“摹仿說”,認為史詩與音樂都是模仿。我國古代文藝理論也認為詩、歌、舞、樂等各類藝術相互影響,有所聯系。
當代研究者也試圖從文學與音樂的本源上探討二者的關系。在西方,叔本華、尼采等哲學家在各自搭建的世界觀中論述了音樂的性質、音樂與文學的關系。叔本華尤其將音樂視為意志本身,道出了音樂藝術的高度抽象性特征。他的后繼者尼采在此世界觀基礎上認為悲劇——被公認為文學藝術的最高峰——誕生于音樂精神之中。簡言之,西方文藝理論認為音樂表現為意志,而文學受到音樂精神的影響而產生。國內研究中,龍迪勇以西方小說為例探討小說的音樂敘事,認為一些小說家在創作小說時,“通過模仿或借鑒音樂藝術的某些特征,在‘內容或‘形式上追求并在很大程度上達到像音樂那樣的美學效果。”[2]
作為當代華文文學作家,白先勇經常有意識地運用西方文學的創作手法,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存在音樂敘事。葉維廉在《“出位之思”:媒體及超媒體的美學》中強調從不同媒體角度觀賞作品以獲得更加齊全完整的美學經驗。因此,跳出文學中心論,從音樂的角度考察白先勇的《游園驚夢》是如何達到獨特的美學效果、展現悲劇意識的,不失為一種“出位之思”。
二、生命之思:音樂時間性與悲劇意識
白先勇對昆曲的熱愛始于童年時期,他的昆曲情懷在小說《游園驚夢》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文學與音樂得以完美結合。小說《游園驚夢》圍繞著戲曲藝術展開,在文本中,與音樂有關的人物、一系列的戲曲行話、頻繁出現的演出地點、反復引用的戲曲名篇名段,諸多音樂要素使文本形成了音樂文化空間,音樂精神激活了主人公錢夫人(藍田玉)的自省。
藍田玉的意識流進程與音樂的推移有關。藍田玉在欣賞徐太太演唱的《游園》時,意識時而游離,時而回歸。一段音樂在線性時間內是不斷前進的,而意識回歸的時刻具有隨機性,這就導致藍田玉的意識隨著隨機感受到的音樂幻象而產生混亂的變化。例如在徐太太唱“潑殘生”的那一刻聯想到了多年前自己唱到“潑殘生”的那一刻,發現了妹妹與心上人的戀情。藍田玉的情緒片段在音樂的行進中得以拼湊,在意識游離與回歸的撕扯中,過往的崢嶸歲月與如今的落魄失意形成強烈對比,生命的盛衰變化產生了巨大的張力。
整體而言,文本中藍田玉的情緒和回憶是由唱詞文本和音樂文本共同激發的,難以被讀者直接感知的音樂文本對故事人物產生了巨大影響,昆曲《游園驚夢》唱段和器樂部分表達了杜麗娘的哀婉情緒并誘發了錢夫人的感傷情緒。就唱腔而言,魏良輔改革后昆曲形成了“水磨調”,擴大了唱腔的表現空間,<皂羅袍>是昆曲《游園》中的代表作,音調起伏、變化豐富、拖腔繁復。“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一句,“音色轉為黯淡,與情詞悲調相契合,……行腔低回,低音區真假混聲”。[3]從器樂角度分析,《游園驚夢》常以笛簫箏胡為配樂,笛箏音色明亮、簫胡低沉婉轉,在不同音色的配合中形成既輕快又低回的混合音效。“笛子和洞簫都鳴了起來,笛音如同流水,把靡靡下沉的簫聲又托了起來”[4]184,黯淡低沉的唱腔音調與整體明快上揚的笛簫樂聲形成對比,“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樂與“奈何天”、“誰家院”之悲共存,以樂襯悲凸顯悲涼凄美。
蘇珊·朗格認為,每一種大型藝術都具有幻象,音樂生產出的首要幻象便是“由生命活動本身標示的時間”[5],在《游園驚夢》的演唱產生的幻象中,本應姹紫嫣紅的鮮活生命已在斷井頹垣之間消逝,如果說青春的消逝引起的還只是嘆惋,那么美景無人欣賞而白白浪費引起的就更多的是痛惜,正如藍田玉對自身本應享受愛情的青春年華被耗費而心生悲憫。《游園驚夢》從唱詞、唱腔到節奏、器樂無不展示的是生命從絢爛逐漸到凋零的幻象,正是這幻象引起了錢夫人藍田玉對自身生命歷程的感傷情緒和悲劇意識。
三、創作之思:音樂形式與情緒強化
小說《游園驚夢》音樂敘事的第二個方面體現在形式上。英國唯美主義作家和理論家沃爾特·佩特認為一切藝術的至高境界是消除形式與內容的區分,而音樂的表達方式就是以形式表現內容,因此好的藝術應該向音樂藝術靠攏,有意識地追求音樂的狀態。白先勇在談及《游園驚夢》的創作經驗時說道:“我想用意識流的手法把時空打亂來配合音樂上的重復節奏,……第五次寫,就用了這個方法跟昆曲的節奏合起來,她回憶的時候,跟音樂的節奏用文字合起來。寫后我把小說念出來,知道總算找到了那種情感的強度。”[6]白先勇的思路與佩特的理論不謀而合,《游園驚夢》的意識流部分在表達上達到了音樂敘事的效果,音樂形式強化了悲劇意識。
白先勇運用短句和重復的手法展現藍田玉的意識流。例如“錢鵬公,錢將軍的夫人啊。錢鵬志的夫人。錢鵬志的隨從參謀。錢將軍的夫人。錢將軍的參謀。錢將軍。”[4]185短句急促,節奏加快,增強跳躍性,猶如音樂中的快板部分,激發審美主體的緊張感,調動審美主體的情緒。以“錢”字引領的眾多短句形成首字押韻,與不同詞語組合反復出現,形成長短不一、強弱不一致的眩暈效果。以不同的稱呼反復呈現三個人物,表意性縮減,以無序排列體現人物間錯綜復雜、糾纏不清的人際關系和情感糾葛。人物關系又以“錢鵬志”“錢將軍”為主導,“夫人”、“參謀”附屬于“錢將軍”,左右游離,象征著后者只能隨著前者而起伏,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大環境下不具有主體性。不規則重復手法的運用帶來了此起彼伏的強弱聲效,營造出酒醉后眩暈的特殊效果。短句和重復將人物情感推向高潮,強化了錢夫人日常生活中被壓抑的情感。
“沒亂里春情難遣,驀地里懷人幽怨,……”“笛子聲愈來愈低沉,愈來愈凄咽,好像把杜麗娘滿腔的怨情都吹了出來似的。”[4]186音樂展現的幻象既表達了杜麗娘的“怨”,也誘發了藍田玉的“怨”。錢志鵬、瞎子師娘、妹妹月月紅和藍田玉自己的簡單話語雜亂無章地重復出現在意識中,錢志鵬寵溺、瞎子師娘惋惜、月月紅諷刺、藍田玉痛苦。瞎子師娘句中的“榮華富貴——”一詞交織在各人話語中若隱若現,又不斷被其他話語打斷,像一個不和諧的單音無規律地反復出現在一段旋律中,干擾著正常的意識發展,正如藍田玉渴望一段正常的戀情卻不停地被榮華富貴的誘惑打斷一樣。短句不規則循環使藍田玉的不勝酒力和意識混亂躍然紙上,也體現她在鄭參謀與錢將軍、愛情與富貴、認命與虛榮之間的矛盾掙扎。
一個整體必然由內容和形式構成,音樂以形式表達純粹的情感,以淡化內容、突出形式的方式表達人物意識流動,能夠增強情緒抒發。藍田玉的意識流是其悲傷情緒的集中體現,過往具體的事件在時間的洗刷下已經不夠具體,抽象為某種情緒,這種情緒在音樂產生的幻象中再一次被調動出來。以純粹形式表現內容,體現出對實質內容的拒絕,也意味著藍田玉對現實的抗拒,既不愿接受過去心上人被親妹妹橫刀奪愛的現實,也不愿承認當下的自己已經美人遲暮,是時候該退出戲曲舞臺、社交舞臺、人生與歷史的舞臺了。
四、結語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臺北人》的題詞表明,社會與歷史在時代浪潮的翻涌中起起落落,個人的命運被浪潮裹挾前進,作為整體的社會與歷史在個體盛衰榮辱的不斷更迭中循環上升。唯有人類心靈中的情感是相似的,一代又一代的藝術家們意識到了人類永恒的痛苦并加以表現,白先勇本著“希望把人類心靈中無法言說的痛楚轉換為文字”的寫作初心,用音樂敘事再現人類對生命流逝、世事無常的悲劇意識,使其在音樂精神中尋找到了寄托之所。
注釋:
[1]白先勇.白先勇文集[M].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
[2]龍迪勇.“出位之思”:試論西方小說的音樂敘事[J].外國文學研究,2018,40(06):115-131.
[3]王婷.昆曲折子戲經典唱段賞析——以兩支曲牌為例[J].北方音樂,2018,38(21):78+88.
[4]白先勇.臺北人[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5]蘇珊·朗格.藝術問題[M].滕守堯,宋疆源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6]白先勇.樹猶如此[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