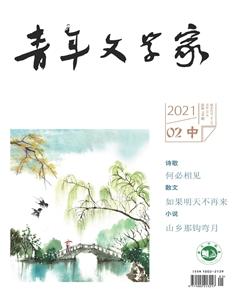論唐傳奇小說和詩歌的關系
摘? 要:唐傳奇與詩歌之間天然存在著密不可分、互相依附的關系,詩歌與傳奇的密切融合,使得小說頗具抒情性和意境美,同時也增強了詩歌的敘事性,使得詩歌的內容和風格朝著現實性、世俗化的方向發展。二者息息相關,相輔相成。
關鍵詞:唐傳奇;詩歌;息息相關
作者簡介:張紅(1999-),漢族,山東省臨沂人,本科,寶雞文理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1)-05-0-02
唐傳奇小說的創作者不僅在小說創造方面造詣極高,在詩歌創作領域也具有十分高超的才能。反過來,大多數的詩人在小說撰寫方面也頗有功力,能夠利用余力來進行小說創作,并融入自己部分詩歌領域的技巧。唐傳奇與詩歌的密切結合,使小說作品具有了詩歌那種朦朧的抒情美和意境美;同時也擴充了詩歌的體裁,增強了詩歌的敘事性,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詩歌的藝術風格,推動了詩歌的保存與傳播。
一、詩歌對傳奇小說的影響
魯迅先生曾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道:“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于搜奇記逸,然敘述婉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魯迅認為,六朝的志怪和志人小說都是記錄事實的文章,而到了唐朝,小說則是人們有意為之的作品。此外,唐傳奇小說長且曲折,與之前的文體相比大不相同,實在是一大進步。
唐傳奇的繁榮有著諸多的原因,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故世間則甚風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謁時或用之為行卷。”所謂“行卷”就是舉子初到京,先把自己得意的詩抄成卷子,拿去拜謁當時的名人,如果得到稱贊,那么他的身價就會攀升十倍,之后便會有及第的希望,所以“行卷”在當時被看的十分重要。到開元天寶年以后,人們漸漸對于詩,有些厭棄了,于是就有人把小說也放在行卷里,不多久,傳奇小說就盛極一時了。在此,魯迅先生認為“溫卷”“行卷”之風是唐傳奇繁榮的重要條件。這應歸屬于社會原因,如果要從文體方面對唐傳奇小說進行探究,那么就會發現詩歌對唐傳奇的興盛和發展產生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唐傳奇抒情性增強
“一切藝術都是創造出來的表現人類情感的知覺形式。”唐傳奇小說的創作者獨具創造性地將詩歌中的抒情特色引入小說的創作當中,使得唐傳奇小說一改往日重在鋪陳敘事的傳統,更加注重小說的抒情性的表達。如此一來,唐傳奇小說也成為了古代文人抒發情感,表達自我的文體形式。
沈亞之的作品正是唐傳奇小說中極具抒情性的代表,他的作品中散布的部分詩歌不僅在內容與結構上能夠和文章融為一體,不顯突兀,而且這些詩歌能夠為傳奇小說本身營造一種基于作者情感基調的抒情氛圍,極具抒情特色。例如,沈亞之傳奇代表作《秦夢記》、《異夢錄》等“皆以華艷之筆,敘恍惚之情,而好言仙鬼復死,尤與同時文人異趣”。其小說中所載詩歌極為優美,渲染出迷離彷徨的情思氛圍,體現著作品的審美情趣。以《異夢錄》為例,其主體部分寫邢鳳之夢。邢鳳于夢中見到一位古裝美人,“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為古裝,而高鬃長眉、衣方領繡修帶紳,被廣袖之孺”。寥寥數筆勾勒出女子的形象與神態,并隱隱透露出對往昔歲月的追憶與愁思。她為邢鳳舞弓彎數拍,既罷,“法然良久,即辭去”。字里行間流露出女子的落寞惆悵與人生苦短、繁華易逝的淡淡悲哀。這篇傳奇文不僅在行文間蘊含濃郁詩意,其中所載詩篇《春陽曲》更為全文增添了無限情思,成為作品的亮點所在:“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卻,羅衣空換九秋霜。”詩為文眼,文衍詩意。該詩體現了沈亞之在情感的表達與抒發方面的造詣,宛轉悠揚,為后人傳頌至今。
(二)唐傳奇重視意境的構筑
中國傳統詩學以創造詩歌意境為主要的審美意識,并以“形象之外”和“想象之中”的結合作為創作要求。王國維曾提到,“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自成高格,自有名句”,這正是在強調意境的創造對于詩詞的重要作用。唐傳奇小說作者深受詩歌意境理論的影響,切身貫徹言近旨遠理論,將情感與人活著具體的十五融合在一起,致力于打造出優美且深入人心的獨特意境。
許多唐傳奇小說能夠給夠讓人有余味無窮,思緒萬千之感。正是由于作者在創作時注重對小說意境的營造,例如元稹的《鶯鶯傳》中鶯鶯與張生之間那些充滿青春活力的情書:“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配。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拘,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情,永以為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鐘,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為嘉。慎為自保,無以鄙為深念。”這封信寄托托物寄情,描繪出真切呈坎,感人至深的優美意境,極易使讀者產生共鳴。
(三)唐傳奇語言華美多姿
唐傳奇對詩筆的借鑒還表現在語言運用上,這也一反志怪小說古樸簡約的特征,表現出“敘述宛轉,文辭華艷”的特點。不僅是對駢文、古代散文極易民間俚語中有生命力的詞匯的傳承,而且也吸收了前輩們在語言結構方面對細致靈活、凝練準確的審美要求,形成了唐傳奇崇尚華麗多彩、準確生動的獨特語言風格。董乃斌先生把唐傳奇的語言作為標志小說文體獨立的特征之一:“它在敘述語言的運用上,除繼承史述的莊嚴持重風格外,更創造了多種別調,從而使小說具備了其孕育者歷史散文所無的豐富色調和語境。”如裴铏《傳奇·元柳二公》中的場景描寫:“長鯨之髻,搶巨鰲之背,浪浮雪嶠,日涌火輪;觸鮫寶而梭仃,撞蜃樓而瓦解。擺簸數四,幾欲傾沉,然后抵孤島而風止。”這一類作品大多采用華美的辭藻和對偶排比等整齊的句式,使得描寫變得十分優美細膩,讓人讀來朗朗上口,深得人心。
詩歌的加入,使得唐傳奇小說一改往日直抒胸臆的敘述方式,渲染出言近旨遠的優美意境,極具詩意,賦予了唐傳奇小說優美的審美意境。因此,詩歌使唐傳奇具有了言外之意、文外之韻,增強了其文本抒情的感染力。
二、傳奇小說對詩歌的滲透
隨著“溫卷”“行卷”之風的盛行,使得唐傳奇在社會上的影響越來越大。詩歌自然也會或多或少的受到傳奇的影響,但是沒有詩歌對傳奇的影響那樣顯著,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到中晚唐時期,唐傳奇發展到繁榮時期時,傳奇對詩歌的影響才形成潮流。由于中晚唐的一些主流詩人身兼傳奇作家之一身二任,都參與了傳奇或小說的創造,造成了傳奇小說影響詩歌的必然。例如,元稹創作了《鶯鶯傳》,陳鴻創作了《長恨歌傳》等。
(一)詩歌敘事性增強
詩歌的敘事性深受唐傳奇小說的影響,逐漸得到強化,具體表現為:有不少的詩歌配以較長的序,序以敘事,詩以抒情。這些詩序類似于小說,具有相對完整的故事情節,更有甚者,會有一部分虛構的內容,趣味無窮。當然,也有一些詩作本身的結構就極具敘事性。以白居易的《琵琶記》為例,該詩借助于描繪一位歌姬的情感變化,表現出主人公色衰愛弛的凄苦的人生經歷,具有以往政治抒情詩的色彩。但是,整個詩歌的敘事性卻是相當明顯的:表層故事是詩人偶然遇到這位歌姬,通過與她交談,產生了共情的心理,發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感慨,真切感人;深層故事是琵琶女從聲名鵲起的著名歌姬,逐漸為情所困淪落為商賈之婦的過程,暗含了詩人對她的惋惜和同情。
(二)詩歌題材的擴充
中晚唐時期,白居易、李商隱等人的詩歌運用大量雜記、野史和傳奇中的故事,使得文壇上出現了多種問題之間相互交融滲透的現象,也就是詩歌吸收已經流傳的小說故事作為創作題材。材料是前人的或是他人的,并且因為這些故事有書本或傳說為依據,讀者對于故事能夠有所了解。詩歌對于唐傳奇小說內容的借鑒,主要內容包括神仙鬼怪的生活、普通人的愛情經歷以及部分歷史故事等多個方面,但仍以愛情內容為主。中晚唐詩人大多都創作過以愛情為主要題材的詩歌,例如元稹的《崔徽歌》、白居易的《長恨歌》、李紳《鶯鶯歌》、劉禹錫《泰娘歌》等等,這些都是歌行體的長篇敘事詩。當然,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短詩,篇幅雖然不及前者,卻“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比如元稹《桐花落》、《雜憶》,白居易《江南喜逢蕭九因話長安舊游戲贈十五韻》等,元白之作被視為艷詩,影響甚廣。
(三)詩歌藝術風格的俳諧
中晚唐時期的元白詩派風格化雅為俗,韓孟詩派則變平普為奇怪,同時還有一種表現就是化莊嚴為俳諧,也就是“以文為戲”(裴度《寄李翱書》)的立場。
比如韓愈曾經在《寄盧仝詩》提到,他認為盧仝“怪詞驚眾謗不已”,“盧仝的特別長處只是他那壓不住的滑稽風趣,同他那大膽嘗試的精神”。其創作心理和創作態度是自覺追求俳諧趣味,從根本上說,這真實再現了他們無可奈何、自我調侃的心態,追溯這其中的來源,從意識形態內部來看,小說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上述傳奇影響詩歌的三個層面:敘事性的增強,世俗性題材的擴充以及詩歌俳諧風格的傾向,其實都是現實性、世俗性的具體表現。
三、唐傳奇與詩歌息息相關
唐傳奇與詩歌之間的影響絕不僅僅是單向的,它們之間天然存在著密不可分、互相依附的關系,詩歌與唐傳奇相輔相成,相互成就,二者的密切融合不僅使得唐傳奇的特色得到彰顯,提升了唐傳奇的審美意蘊,增強了唐傳奇的傳播效果,對后世文學創作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同時,傳奇故事帶動了敘事詩的繁榮,同時小說中的許多典故材料亦成為許多敘事詩的內容,使得詩歌呈現出嶄新的面貌并大放異彩。
參考文獻:
[1]魯迅撰,郭豫適導讀.《中國小說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4.
[2]吳懷東.《唐詩與傳奇的生成》[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222.
[3]余恕誠,吳懷東.《唐詩與其他文體之關系》[M].北京:中華書局,2012.195.
[4]劉光耀,孫麗萍.《論詩歌對唐傳奇創作的影響》[J].寧夏大學學報,2003.
[5]孔敏.《唐代傳奇與詩歌的共生關系》[J].北京:1980.
[6]吳懷東.《唐傳奇與詩化小說》[J].社會科學研究,2011.6.
[7]劉光耀,孫麗萍.《論詩歌對唐傳奇創作的影響》[J].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222.
[8]黃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4.35.
[9]蘇姍·朗格.藝術問題[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