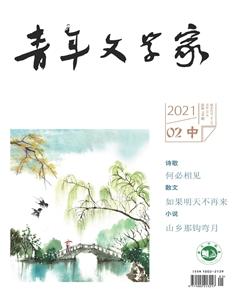弗羅伊德精神分析下《達洛衛夫人》中的褪變和“死亡”主題
楊振陽 張德旭
摘? 要:《達洛衛夫人》是英國著名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所創作的一部實驗性極強的現代小說。在這部小說中,伍爾夫以其女性視角和獨特的創作思想對現代小說的寫作技巧進行了革新。小說主要是使用意識流和自由間接引語來展現人物內心世界,并通過非線性敘事的技巧在不同人物之間進行轉換和描寫。該小說主要圍繞克拉麗莎一天里的內心活動,向我們展現了她過去和現在的精神世界以及周 圍環境對人性的壓抑和扼殺。本文主要通過分析克拉麗莎和賽普蒂默斯的精神世界的崩潰和幻滅,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角度來表達出小說所蘊含的精神褪變和“死亡”的主題。
關鍵詞;克拉麗莎;賽普蒂默斯;褪變和“死亡”;弗羅伊德精神分析
作者簡介:楊振陽(1993-),男,漢族,河南柘城人,東北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指導老師張德旭(1984-),男,黑龍江海倫人,東北大學副教授,哲學博士,主要從事英國文學、文學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1)-05--03
一、引言
如果說詹姆斯·喬伊斯筆下的《都柏林人》表達的是關于英國殖民統治下愛爾蘭“癱瘓”的主題,那么弗吉尼亞·伍爾夫所創作的《達洛衛夫人》則是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國的“死亡”主題的小說。“死亡”這一主題在《達洛衛夫人》中集中表現肉體上的死亡、精神上的滅卻、自我情感反抗失敗后的壓抑和妥協。為了表現這一主題,伍爾夫運用和革新實驗性的現代小說寫作技巧,以及巧妙地編織人物關系網絡來展示人物內心世界。這部小說不僅具有較高的文學審美價值,而且還有深刻的社會現實意義,尤其體現在對女主人公克拉麗莎和弱勢群體的代表賽普蒂默斯精神世界的刻畫上。這部小說的獨特結構就是伍爾夫對克拉麗莎和賽普蒂默斯的刻畫描寫是兩個平行系統--盡管他們從未相遇過,但卻有著相似之處。誠如伍爾夫在日記中所言要“探討瘋狂與自殺的根源,比較常人同狂人各自心目中的世態”。在《達洛維夫人》中,充滿著關于“死亡”的描寫,這也跟伍爾夫本人精神抑郁和厭世有關,在思想上,她也曾受到弗洛伊德關于壓抑的潛意識等學說頗深的感染,從而助長了她的孤寂之感和陰郁的心理。
二、克拉麗莎的精神世界褪變--本我的崩潰與死亡
伍爾夫的作品聚焦人物的內心世界,呼吁人們:“向內心看吧,生活似乎遠非‘如此。小說《達洛維夫人》不僅使我們了解到克拉麗莎的精神世界,也可以深入了解伍爾夫本人創作理念和精神世界。婚前的克拉麗莎的內心是充滿激情與希望的。婚后的她隨著年紀的增長,心理狀況更加矛盾和復雜。除了自身疾病的問題,她也時常感到丈夫的冷落,還有心愛女兒的問題等,外邊任何一件小事,甚至都能擊垮克拉麗莎脆弱而敏感心理防線。作為女性,社會和家庭賦予她的角色讓她覺得自己的生活更加壓抑和窒息了。當她被稱為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主婦”,她還曾為此哭泣。克拉麗莎雖然貴為上流社會家庭的女主人,但她并沒有為此而感到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對她來說,尤其經歷了戰爭之后,她更加渴望激情。然而現實生活的種種壓迫使她倍感孤獨和孤立,這尤其反映在她的孤芳自賞和矛盾心理上。她的矛盾心理正是她精神世界斗爭的體現。她一方面厭惡和恐懼孤獨,一方面又通過距離和獨立來與壓抑她本性的力量作斗爭。她認為“凡是人都有一種尊嚴,都有獨處的生活,即使夫妻之間也容不得干擾”,而且必須尊重這種權利。
克拉麗莎的矛盾行為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自己“本我”與“自我”的矛盾;另一方面是自己作為個體而與外部整體之間的矛盾。伍爾夫曾受弗洛伊德學說頗深影響,在這本小說里也有具體的反映,我們可以從弗洛伊德的心理分度角度來闡釋。
弗羅伊德認為,本我是生物性沖動和欲望的貯存庫, 是人格中最早和最原始的部分。其遵循“唯樂原則”活動,即不顧一切地要尋求滿足和快感,這種快樂主要指性、生理和情感方面的愉悅。在小說中,克拉麗莎常常通過回憶和依戀來保持自我,她對18歲時在布爾頓生活的那個夏天記憶尤其深刻。她想起了她的好姐妹薩利和她的乖戾和叛逆行為,甚至對這種性格的薩利有著愛情般依戀和情懷。這種感情使她的眼光整晚都沒有離開薩利,對她來說,薩利擁有著她最愛慕的獨特的美,即近乎放浪和毫不顧忌言行的性格;這種性格也正是她所缺乏和她一直羨慕的。然而,對于生活在上流社會的克拉麗莎來說,薩利的性格和行為只能是她在內心羨慕的。因此,她不能在這個等級森嚴和充滿種種束縛的社會體系中做任何逾矩的事情。尤其對內心極其敏感和小心翼翼的她來說,做出這樣的事是有違自己身份的,更是不可能做得出的。畢竟,往蛇形湖里扔一枚硬幣這樣的事都會讓她感到死亡般的恐怖。
克拉麗莎對任何能挑動自己敏感神經的事是疏遠和拒絕的。這也可以從她拒絕彼得的求婚而選擇呆板和保守的理查德這件事看出。盡管富有浪漫氣息的彼得,能夠使克拉麗莎的生活充滿激情,“跟他在一起無限融洽、輕松”;如果嫁給了她,這種快樂將會整天伴隨著她。但是出于對現實的思考和享受世間的快樂與滿足,她最后放棄了能帶給她激情和浪漫的彼得。做出這樣的決定,對渴望那種激情生活的克拉麗莎來說是痛苦的。乃至在婚后一直在思考關于婚姻的抉擇問題,時時回憶起彼得。因為嫁給沒有浪漫情調和呆板的理查德,她的內心一直存續著對激情和浪漫生活的渴望。
弗羅伊德認為本我在人格結構中具有自私、貪婪和攻擊性的特性。克拉麗莎由于不能從丈夫身上獲得某種情感需要,便視與丈夫和他人保持距離和獨處是一種正當的權力。但她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是一個本我與自我的不斷斗爭的結果。其實正是由于這種矛盾,才加劇了她的孤獨感,對她來說,能夠與人“溝通”才能使她繼續熱愛生活,充滿激情。即使年過五旬,她也能夠把自己的情感融入歡快的小鳥,綠葉和花朵的生命世界里,甚至能從周圍一切事物中汲取活力。從結婚以來,她的內心一直飽受壓抑和孤獨之感。當她走出壓抑她的房間時便覺得“多美好,多痛快”。在她去買花的路上,她是如此的快樂,看到周圍的一切讓她得到了釋放,她變得喜歡“此時、此地、眼前的現實”,覺得自己也屬于素昧平生的人們。一個人在家的時候,她通常閱讀莎士比亞的作品來感受生活的激情,但是家庭的束縛和壓抑,讓“她有一種荒誕的感覺,感到自己能隱身,不被人看見,不為人看見,不為人所知;現在再也沒有婚姻,也不再生兒育女,剩下的只是與一群人令人驚異而相當莊嚴地向邦德街前進”。這種令她窒息的壓抑,讓她覺得自己甚至“不再是克拉麗莎,而是理查德·達洛衛夫人”。她的孤獨和壓抑感已經讓克拉麗莎不再覺得身心完整。她急需渴望能與外界“溝通”。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論,他認為“自我是是從本我中分化出來并得到發展的那一部分,它處于本我和世界之間,根據外部的需要而活動,它是調節本能要求與現實社會要求之間不平衡的機制”。克拉麗莎不僅通過回憶和留戀過去的來保持“本我”,而且還通過與周圍的壓抑環境保持距離。首先她討厭家庭女教師基爾曼,是因為她認為基爾曼的信仰會通過伊麗莎白而影響到自己本身,她認為那是一種會令人冷漠無情,使感情麻木的信仰。所以盡管基爾曼小姐在某方面是克拉麗莎所不及的、會讓她羨慕和佩服的,但克拉麗莎仍然排斥她。還有對于生活中的人,克拉麗莎也總是內心鄙棄他們的所作所為,不愿與其世俗觀念同流合污。這就如文中所說,克拉麗莎如“一把刀子,插入每件事物之中,同時又置身局外,袖手旁觀”。這是她的特殊能力,使自己能夠保持精神的獨立。這也從她“虛偽”、“兩面”的行為中看出:在外人面前,她始終如一地釋放著自己的正能量,把勢力、妒忌、虛榮和猜忌小心翼翼地藏起來,但內心深處,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她是一個多么矛盾的集合體。
克拉麗莎掙扎于本能欲望與現實生活的矛盾中,她會按照“現實原則”行事,竭力用理性壓抑來自本我的非理性沖動,盡管她內心無數次感想“要是能重度人生,那多好啊;甚至還能改變自己的面目呢!”可當壓垮她精神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到來時,她的“本我”被徹底粉碎了——賽普蒂默斯自殺消息的傳來。對她來說為“本我”而戰實在是太危險了,她的“靈魂,自我意識”、“生命的中心”會很容易被威廉爵士、霍姆斯、布魯頓夫人、休·惠特布雷德之流如同賽普蒂默斯般被判處“死刑”。當死亡的消息傳到她的晚會上,她覺得他的死對她是災難、恥辱和懲罰,因為她不會為了保持“生命的中心”而像他一樣選擇自殺。克拉麗莎有過這樣的想法:“我退隱了,我消失了;可是倫敦不答應,它把尖刀刺向夜空,捆住夜色,逼迫她投入歡樂的倫敦之夜。” 盡管她也想過死亡,渴望死亡,但對她來說,“人是孤獨的,死亡倒能擁抱人哩”。在小屋子里她從賽普蒂默斯的死亡中獲得了啟示。盡管她對現實的庸常和世俗不滿,但她也知道世俗是對自己最好的保護。“過去的某種憂傷;對現在的某種關注,使她把個性隱藏了”是克拉麗莎獲得啟示。她是通過降低對人性的追求,精神世界里的“本我”死去,從而獲得另一種形式的存在和新生。在新世界里的她“不再怕驕陽炎熱,也不怕隆冬嚴寒”。
伍爾夫曾在日記中透露出小說最初的安排是克拉麗莎自盡而死,最后卻讓她選擇了活下去,這在伍爾夫看來,這樣更能升華主題的意境,更能使小說表現它的批判和諷刺效果,更加凸顯了英國階級制度及其它的代理人的給人死亡一般的壓抑感和逃離感。
三、賽普蒂默斯的死亡抉擇
賽普蒂默斯是伍爾夫在《達洛衛夫人》里的男主人公。伍爾夫通過賦予克拉麗莎特殊的能力,讓她和賽普蒂默斯聯系了起來,共同展現了伍爾夫的創作目的。克拉麗莎能和從未談過的人息息相通奇異的本能,讓她準確而又富有同情心地給我們展現了賽普蒂默斯的精神世界。
伍爾夫曾在日記中透露小說最初的創作中沒有賽普蒂默斯這一角色,增加了他是為了讓他體現“狂人的真諦”。賽普蒂默斯和克拉麗莎最明顯的共同之處就是讀莎士比亞的作品。傳統的英國社會壓抑人的情感,所以他們都喜歡從莎士比亞的作品中找到一種活力和激情。伍爾夫曾這樣評價說,“戰爭對男人而言是一種職業,是快樂和興奮的源泉,也是男子漢品格的實現”。早年的賽普蒂默斯欣賞莎士比亞,甚至渴望成為一名詩人,他頭腦中的英國概念,幾乎完全是莎士比亞戲劇,以及像“穿著綠裙子在廣場散步的伊莎貝爾·波爾小姐”那樣充滿著浪漫和詩情畫意。于是他懷著激情奔赴了戰場,為保衛他的“伊莎貝爾·波爾小姐”而戰,為英國而戰。然而在戰爭中經歷的一切,讓他看清了戰爭的真相,感悟到了生活的“真諦”。戰爭的殘酷,朋友的陣亡,完全摧毀了他以前的浪漫世界,而他也患上了嚴重的精神疾病。因為飽經戰爭的創傷和周圍環境對他人性的摧殘,使他一步一步走上了死亡的道路。
富有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賽普蒂默斯最后選擇了死亡,在弗洛伊德看來,死亡在人的潛意識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并且人對死亡也有著迷般的耽戀。“死之本能”不僅僅是指結束生命,其不限于殺人和自殺,還包括自我懲罰、自我譴責、對權威的反抗等。這同拉康的“忘我”,即人對反思性自我的擦除的含義一樣。戰爭的經歷必然部分地塑造了賽普蒂默斯的這種心理。由于戰爭的傷害,賽普蒂默斯的精神世界被完全摧毀,他選擇了通過愛情來彌補內心世界的創傷。雖然很多愛情的開端都是以積極的生存本能形式而存在,但是他不愛他的妻子。當欲望無法滿足,就會感到焦慮壓抑,而唯有死去才有希望完全解除焦慮,緊張和掙扎。這是一種逃避和放棄的心理防御機制。賽普蒂默斯一直以來都在于壓抑自我,不斷與自我作斗爭。
當他和妻子在去找威廉·布雷德肖醫生求助的路上,他內心已經麻木和彷徨,他覺得“世界已經高舉鞭子,不知將抽向何方”。布雷德肖卻只給了他們三刻鐘的時間,之后就拋棄了他們。這是世間怎樣的冷漠。賽普蒂默斯對戰爭的譴責,并沒有讓世人更加清醒的認識戰爭,甚至仍抱著無比崇敬的心理看待戰爭。賽普蒂默斯不由得發出來“靈魂死了”。伍爾夫本人也親身經歷過心理醫師的治療。在伍爾夫眼里,作為精神心理醫生的威廉爵士只是理性話語的一個符號。她描寫布雷德肖,神靈的助手,傳播科學的大法師,滿懷“感化”、裝出兄弟般仁愛的面貌;渴望權力,粗暴低懲罰異己分子或心懷不滿的人;賜福馴良之輩。賽普蒂默斯在被施加“平穩”治療時,在他看來,他已被“人性”判處死刑。
戰爭是在保護什么,一直是賽普蒂默斯揮之不去的問題,他渴望能與人“互通消息”,對他來說互通消息意味著健康,幸福。然而打著治病救人的幌子,暗地里卻無情地吞噬和控制他人靈魂的布雷德肖醫生,希望病人皈依、順從;忘記自己,忘記他們對戰爭或帝國的事業的懷疑,使他明白了自己是“替罪羊”,“永恒的受難者”。最終他不堪種種壓抑,通過自殺保持了靈魂的完整。在死前他希望告訴首相,這一英國社會的象征,“博愛,乃是人世間的真諦”。而他的死亡被稱為是“文明的勝利”,這更加表現了伍爾夫對舊英國社會制度和統治階級所謂的文明的批判和諷刺。
四、結語
正如伍爾夫所言,她要在這部作品里表達的很多的觀念。她要“描述生與死、理智與瘋狂;我要批判當今的社會制度,揭示其動態,而且是最本質的動態……”她通過兩個主人公克拉麗莎和賽普蒂默斯不僅完美地實踐她的“書的本身”是形式與內容的合一的創作理念;而且還通過兩位主人公表現了統治階級對人性的壓迫和人際隔閡,以及折射出當時英國社會的現狀以及人物的精神狀態。伍爾夫通過高超的寫作技巧,批判了和譴責了男權社會對下層人民和女性群體的壓迫設傷害,全書表達了當時社會歷史背景下主人公的精神褪變和“死亡”的主題。
參考文獻:
[1]金英. 關于生存與死亡的思考—試析伍爾夫的《達洛維夫人》[J]. 東北農業大學學報, 2009.
[2]朱華. 心靈的自我救贖—弗吉尼亞·伍爾夫《達洛維夫人》主要人物內心世界解析[J]. 遼寧行政學院學報, 2014.
[3]弗吉尼亞·伍爾夫(著). 孫梁 蘇美譯.達洛衛夫人[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5.
[4]張懷斌,郭柳妞. 《達洛維夫人》的世俗壓迫主題[J].外語教學,2014.
[5]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引論.張堂會編譯北京出版社,2007.
[6]周慧. 政治無為、審美救贖和道德相對性—《達洛維夫人》中克萊麗莎的生存困境[J].中山大學學報,2016.
[7]劉愛華. 克拉麗莎的自我追尋歷程—用弗羅依德的人格理論解析《達洛維夫人》[J].安徽文學,2009.
[8]弗吉尼亞·伍爾夫, 王斌等譯:《伍爾夫隨筆全集III》,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2001.
[9]李榮睿. 故事與話語的斷裂—從第三人稱敘述者看《達洛維夫人》的生命與死亡主題[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2.
[10]朱立元. 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