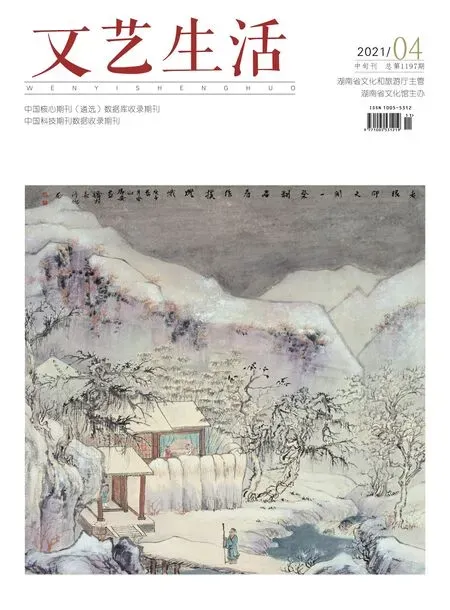淺談“說不好”與“不好說”
羅 雙
(三峽大學 文學與傳媒學院,湖北 宜昌 443000)
一、前言
沈家煊(2001)提出了“語言的主觀性與主觀化”,他認為語言有表達個人情感態度的“主觀性”成分,而其特性的表達離不開相關形式結構的應用。“說不好”、“不好說”都是現代漢語口語中的常用結構,在歷史演變中語義逐步虛化表主觀性極強的揣測、預估義。
目前關于“說”、“好”、“說不好”語義演變及其相關結構如“說不x”、“不好x”構式發展問題學界存在較多研究,但是對同表“不確定”義的“不好說”結構的探討目前還沒有。
基于此,本文將主從同表“揣測”義的“說不好”與“不好說”的語法、語義、語用及語法化特點等方面進行對比分析,探討二者的差異及成因,并闡釋相關構式發展的共通規律。
二、“不好說”與“說不好”的歷時演變與語法化軌跡
(一)“不好說”與“說不好”的歷時演變
“不好說”與“說不好”都在宋代就有應用,但那時使用較少,到了元明時期使用頻率才大幅增加。元明清時二者中的“不好”和“說”的實詞義都很強,且詞間停頓明顯,可插入其他成分如“不好去說”、“不好多說”。據BCC語料庫及語料庫在線統計分析,元代時“不好說”多與“得/的”連說單獨成句,或放在主語后作謂語,語義主觀性較強,來表達說話人“不好意思去說什么”或“不方便說什么”的無奈之情。明清后才開始多接代詞或短語做“說”的賓語,或接補語如“出”修飾“說”,如:
(1)沈文道:“不好說得,是管家李公寄信來。”(元明《初刻拍案驚奇》)
(2)張七嫂道:“老身不好說得,這大戶人家,不是你少年人走動的。”(元明《喻世明言》)
(3)因這時女親都在內里,也不好說什么,只說:“叫他歇著去罷。”(清《紅樓夢》)
(4)姚五爺笑道:“今日我在這里陪先生,人都知道的,不好說在別處。”(清《儒林外史》)
(5)玉樓道:“也不是假撇清,他有心也要和,只是不好說出來的。”(《金瓶梅》)
“好”字在《現代漢語大字典》中的解釋有14個,由上面看,“不好說”的“好”在古漢時期主要是表14個義項中的“便于、宜于”義。而現漢中“好”表示“容易”義“不好說”的使用大幅增加。其短語從表示“對某件事的實施有難度”的“不好說2”時,“好”的“容易”義還很凸顯,而進一步虛化的“不好說3”更偏向表主觀性較強的“推測義”,和口語化的“不一定”語義有相似性,即表示主觀者對事情的正反可能性兼具的推測。如:
(6)整個東西顯得荒誕離奇,但卻自成一體。再具體就不好說了,因為它特別靈活,無法捉拿。(卡夫卡《家父之憂》)
(7)“我有話和你說。”“什么?”“電話不好說。”(渡邊淳《異戀》)
(8)人家日本有軍艦,將來這安慶怎么樣還不好說。(王火《戰爭和人》)
(9)除了我秀吉,到底還有沒有人能順應萬民的意愿,順應天下太平的歷史潮流,還真不好說。(山岡莊八《德川家康5·龍爭虎斗》)
(10)廠商是外國人,但是不是真正的外國人那也不好說。(莫言《蛙》)
有關“說不好”的歷時演變研究較多,如寇麗婭(2015)、魏雪(2016)都在“說不好”的表主觀推測上達成一致,其中魏雪(2016)提出了“揣測性副詞”概念,對“說不好”語義演變分為四個階段,動賓狀態、述補狀態,及深度虛化做揣測副詞狀態。歷史的角度來看,元明清現時“說不好”多做動賓結構,“不好”代指“評價者對某事某人不如意的看法”,常帶口語化“底”連用,表現說話者評價時婉轉的態度。而現代漢語后動賓結構出現頻率變低,述補形式出現更頻繁,語義范圍也更廣。從表言說者口語上表達不清楚某件事到表“可能”義來主觀推測未發生的事件,其發展演變和吳福祥(2003)提到的語法化過程中也伴隨著語義抽象性及主觀性上的增加。如:
(11)八戒上前道:“師兄,師父說不好,你只管說好!”(元明《西游記》)
(12)人偏是這樣羊性,你若一個說好,大家都說起好來;若一個說是不好,大家也齊說不好。(元明《醒世姻緣》)
(13)可話早說開:說好了別感激我;說不好,也別埋怨。(李新民《第一個春天》)
(14)對不對我也說不好,反正這種做法我不能接受,我覺得這樣太對不住死去的親人了,自己的良心也會感到不安。(馮中平《墓地采訪手記》)
(15)你別喪氣,說不好這次能中獎呢。(生活語料搜集)
(16)我連忙又往外扳槳,因為說不好巴蘭薩公路上就有稅警,免得他們看到。(海明威《永別了,武器!》)
(二)“不好說”與“說不好”的語法化成因
《說文解字》對“說”的解釋是:“說,釋也。”《現代漢語大詞典》對“說”的解釋除了其基本義外,還有介紹、責備和主張的意義。這些意義的形成都夾雜著言語者自己的理解與思考。它作為古代一種議論文體,其作用也是為了表現作者的見解。筆者認為,正是在“說”的這種語義虛化的軌跡下,“說”字越來越與表示個人認知的理解、主張和猜測義相關聯,也是現代漢語短語“說不好”與“不好說”詞匯化的動因之一。
彭彬(2017)分析“好”字詞義在一條引申線上例證了“愛好”到“適宜”到“容易”義的變化,這個變化對其相關結構“不好說”的詞義演變及詞匯化傾向有一定的推動。同時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到,雖然“說不好”不論是虛化還是成詞化傾向都高于“不好說”,但是二者的歷時變化中受內部結構影響的特點還是一致的。江藍生(1999)的語法化研究成果表明,實詞的虛化往往會伴隨著語音的弱化、簡化、模糊化,甚至消失。“說不好”與“不好說”由于最初是由“不好”和“說”構成的短語,中間間隔明晰,后隨著使用頻率的增加,口語化應用習慣的養成,導致它們之間發音更緊湊,實詞的語義更模糊寬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說不好”與“不好說”的語法化。
三、“不好說”與“說不好”的句法位置與句法功能
“不好說”在句中多出現在句中和句尾,也可單獨成句,用來加強語氣。一般說來,多做謂語。當其“說”為表言語實義時,其主語多為人稱詞、表工具方式的名詞或表特指的人或事或者句子,后經常帶“什么”、“別的”之類的詞作賓語,也可不帶賓語。而“說”字表估計義時這也是我們與“說不好”的比較重點,其主語還可以是時間名詞,也可以是“什么”、“怎樣”或“這、“那”等詞指代前文談及的事件或事物,還可以形成如“V不V+還(也、就)+不好說”及“能不能+V+還(就)+不好說”類的句式。但這些句法分布與條件還都要結合具體的語境來看。
“說不好”可以做謂語、狀語、插入語,可接賓語也可不接,其后可以是動賓短語、形容詞或句子。可位于單句句首和復句分句句首,也可以放在句首用逗號隔開引起聽話人的注意。和“不好說”一樣可以和“V不V”和“能不能V”等構成句式,但它還可以放在分句間,表示假設性小句,引出當事人請求或可能發生的情形。常出現在對話及話題句里,省略主語獨自出現。他的句法位置比“不好說”更靈活,口語表現色彩更濃。如:
(17)“你弟弟能趕回來吃飯嗎?”“不好說。”(生活語料搜集)
(18)張宗琪還能不能挺得住,那就不好說了。(畢飛宇《推拿》)
(19)壯烈不壯烈,所說的審判又沒真搞成,誰也不好說。(大江健三郎《日常生活的冒險》)
(20)上海弄堂的閨閣,說不好就成了海市蜃樓。(王安憶《長恨歌》)
(21)茶莊保不保得住不去說它,性命保不保得住都說不好了。(王旭烽《茶人三部曲》)
(22)如果他能振作起來,說不好,他能扳回一局。(生活語料搜集)
四、“不好說”與“說不好”的語用分析
首先就二者出現的語言環境來說,“說不好”后多帶“就”、“還”等副詞,接的一般都是表達肯定的事件,且多為好的結果。帶有一點僥幸、碰運氣的意味。它的趨向與作者積極態度的方向靠近。如:(1)這件事說不好就成功了。(2)這件事說不好就失敗了。兩個句子我們的習慣用法是(1),是對未知事情的正向猜測,這種猜測結果和作者心理期望一致,帶有僥幸、安慰的心理。
副詞“還”、“也”、“真”、“確實”等一般出現在“不好說”前面,它可以表達肯定的心理傾向,也可以表達否定的心理傾向。其前后文語境的限制沒有“說不好”那么大。如前面的(2)例子說成“這件事失敗了也不好說。”更符合我們的使用習慣。
兩個結構前面提到都可以和“V不V”構成句式,表征意上是對“V”和“不V”兩種情況做預料判斷,但實際主要是偏向“V”這個事件的可能性做預估。如:(3)今天周末,圖書館開不開還不好說。(4)今天周末,圖書館開不開還說不好。兩個句子都是對圖書館明天開門這個假定事實做主觀判斷,意為“明天圖書館會開門這件事還不確定。”這里二者的語義特點是相似的,都含有較強的主觀性與猜測性。但是“說不好”的詞匯化強于“不好說”,它詞匯化成詞后的語義特點也從原來的表模糊的、不確定的“猜測義”轉向“可能義”,即對一件事可能發生的主觀判斷。而“不好說”的詞匯化還沒那么強,它仍處在主觀性較強的“猜測義”中。
李衛君(2012)提出現代漢語來看,副詞在承擔了焦點凸顯功能中占了很大比例。“說不好”作為一種揣測類副詞,一定程度上表現了說話人對前面提到的事件的不確定的猜測態度,進而讓聽話的人注意到事件傳達下的新信息,起到凸顯命題的作用。同時漢語在日常生活的表達習慣上較委婉,通過前面語境的分析,我們能看到“說不好”在一定的語言環境中能有會話中的“合作原則”與“禮貌原則”的體現,這些語用上的特點與功能都相對于語法化程度還沒那么深的“不好說”更加明顯。
五、結語
“說不好”和“不好說”都伴隨著“說”詞義的虛化,從古漢語時期表言說義的短語逐步虛化為表猜測、可能的結構。其中“說不好”的詞匯化更加明顯,結構也更加凝固。二者在古漢語時期結構、用法還存在較大差異。到了現代漢語時期,二者在表示個人主觀猜測義的構式用法上使用頻率都更高,相似性也更高。但在句法條件和語義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偏差。類似的“V不C”構式使用頻率也很高,口語性很強。它們和“說不好”的詞匯化路徑與特點有相似點。這些短語的詞匯化和高頻使用,能看出一些動詞的詞義虛化對其構造的短語有一定推動作用,需要我們注意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