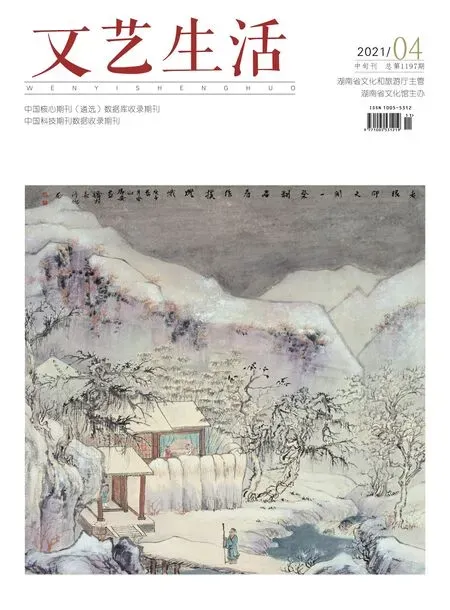談戲曲表演的“四功五法”
哈吉軍
(青銅峽市演藝公司,寧夏 青銅峽 751600)
戲曲演員在刻畫戲曲人物前,須做足戲曲在塑造人物形象時,首先應該有扎實的“功”,然后才可以在這基礎上進行人物的刻畫。可見,成功的戲曲演員在刻畫戲曲人物前,需做足功課,包括手、眼、身、法、步等“五法”以及戲曲舞蹈、戲曲鑼鼓經、戲曲發音、戲曲節奏等,從而為下一步借助于歌舞的方式游刃有余地在舞臺上酣暢淋漓的表演打下基礎。
一、戲曲角色的客觀性
從表演的預備性基礎功課起,便已經客觀地包孕了演員特殊性的體驗,且這種特殊的客觀性主要必須經由戲曲演員對日常生活進行藝術化的處理才能夠顯現出來,包括道白、動作以及語調等各個方面,在遵循“借助于歌舞媒介展演故事”的原則下,構建起戲曲獨到的程式,最終搬上舞臺。因而,戲曲演員要擁有特殊化的表演體驗,必須打下扎實的表演技巧基礎。倘若戲曲演員沒有“四功五法”等表演技能的基礎。
戲曲演員特殊性體驗的獲得與其扮演的角色存在著內在的關聯性。換而言之,演員須讓自己飾演的角色真實、飽滿、鮮活、感人,他們這才可以收獲特殊化的體驗。阿甲先生曾評論道:戲曲演員并非直觀化地、簡易地呈現出自然界原生態環境下的生活體驗,而須關注到戲曲本身內在的規律,將生活體驗轉化成別具一格的、與藝術范式相吻合的角色化體驗,也就是說,此類型的特殊化體驗,必須與審美理念以及表演技巧有機地融合為一體,凸顯出戲曲歌舞化的藝術性體驗。戲曲演員呈現于舞臺上的是戲,而非現實生活。
因此,戲曲演員在精熟自己專業技能的基礎上,還應該融入藝術真實的感情,用心去感受角色的特殊化體驗,而非簡簡單單地滯留于常態化的情感體驗領域內。
當然,戲曲人物角色又和話劇、影視劇中的角色存在著差異性,其特殊性在于演員必須做到形神兼備,經由高度化的提煉之后,將全部的心理活動充分地借助于外形體現出來,同時,還應該生動形象而又準確地采用唱、念、做、打等各個程式傾情地展演出來,達到人物個性以及具體情境的有機統一,要讓觀眾喜聞樂見,感受到戲曲的藝術之美,凸顯戲曲的特色。
二、戲曲表演的程式化
(一)一般性的技巧體驗
戲曲演員首先應該擁有必備的基本功,主要有唱念技巧(共鳴、節奏把握、氣息以及噴口等)、腰腿技巧(目的在于培養較好的協調度、柔韌度以及爆發力等)、各類舞臺器具的使用技巧(主要含納文、武兩個領域,諸如靠、把子、云帚、翎子、厚底、水袖、帽翅以及甩發等)。這些大量繁瑣的戲曲技巧的訓練,需要演員投入大量的時間與精力,正體現了“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讓戲曲演員十年如一日、默默地辛勤耕耘著,力圖達到技藝驚人的境界,在這個過程中積累的是一般性的技巧體驗。著名京劇武旦劉琪便是典范,為了成功地演繹《扈家莊》,他每天不是在跑圓場便是在耍槍花,目的在于嫻熟地耍啟三娘所經常使用的圓場,同時,也游刃有余地表現出女將角色的出眾武藝與傲嬌之氣。又如,享有四大名旦之譽的程硯秋在意外地出現了倒倉情況以后,仍舊保持著每日練嗓的習慣,無論是城墻根還是水潭中,都留下了他的裊裊余音,最終從讓人心悸的“鬼音”陰影中走了出來,并成為一時風靡的“程腔”風格。
一般技巧性的體驗培養了戲曲藝術家們的意志與毅力,同時也是他們成功演繹的重要技術性保障。當表演達到純熟的地步之后,技術性因素變為戲曲演員的“第二天性”,精通而又自如地運用技巧,惟妙惟肖地塑造人物形象。將五官與肢體訓練到好似存在著筋肉思想式的敏銳程度,將所有的心理觀念融入到技巧性高的筋肉與骨架中。換而言之,戲曲演員在舞臺表演的歌舞與故事,是凸顯出情感內蘊的物質化模式,不具備扎實的一般性技巧,是無法真正地表演戲曲的內容的。
(二)刻畫人物形象的技術性
戲曲的程式之美體現在形式之美與技術之美。優秀的戲曲表演家都能夠駕輕就熟地應用戲曲的程式之美。梅蘭芳唱腔形式優美,端莊柔麗中又蘊藉深沉,別有雅致風韻,程硯秋唱腔悠揚委婉,抑揚起伏,將柔和綿麗與凄槍悲涼二者有機結合,靈活地應用形式美的內在章法,凸顯出審美價值。
在戲曲表演中,僅僅停留于形式之美與技術之美,而未能考慮到相應的情境與角色的情感因素是不夠的。作為行動的舞臺藝術,戲曲主要借助于舞臺這個平臺來表現演員的心理行動、形體行動與語言行動等。動作,語言行動指的是的演員的臺詞。而心理行動則將上述二者有機地統一在一起所呈現出最后的舞臺角色形態。
戲曲藝術家塑造角色的中介是行當,行當亦為戲曲程式的集中性體現,也是歷代戲曲表演家經由體驗以及表演探索之后所塑造的角色體系,整合了相類似角色的共同的個性。由于行當自身包含著許多演技的程式,且以技術體驗的途徑加以傳承。可見,行當有機地把角色體系與程式體系加以統一。戲曲表演家也須對行當展開技術層面上的分工,以更好地了解多元化類別的表演技術,演員必須懷有一顆體驗技術角色之心去感悟。
三、戲曲表演的歌舞技巧
如何完美地將歌舞的演技和現實生活加以有機的整合與演繹,是戲曲演員所遇到的一個難點,難就難在“似真非真”之間,即須與現實生活的情理相吻合,同時又應借助于審美體驗來加以體現。根據元代著名戲曲家胡抵通針對戲曲表演者提出的“九美”要求可知,戲曲演員必須對戲曲角色人物有比較深入的體驗,尤其是角色的內心世界,即能夠將人物角色微妙的體驗與高難度的演技有機地統一起來。
著名表演藝術家張春華成功地演繹了《秋江》中的梢翁角色,比較出彩的是他在該劇中細膩的行船肢體動作,他輕輕地用篙桿一點,同時碾動同步的云步,產生小船慢慢地遠離河岸的視效,輕移小碎步時,膀子、腰部、膝蓋以及腳尖也隨之微微地搖晃,生動形象地演繹出在登上小船后略微搖蕩不穩的狀態;然后,搖曳船槽,腦袋也隨著輕晃,雙腳則表現出快速奔跑以及倒步的架勢,顯現出小舟于急速水勢的水面上疾駛并帶有崎嶇顛簸的情境,無論是演員的面部神色、肢體動作,還是優美的歌聲,觀眾的情緒也都會和他發生同步的反應,或緊張、或舒坦,與內心深處產生共鳴。
如在《周仁獻嫂》中秦腔老派演法中表演都很有特點,唱念表演很有講究,其中動作幅度較大,舉手投足,重拙夸張,反襯出內心活動的矛盾劇烈,所謂須生應工,優勢即在這里。念唱以氣勢勝,不事雕琢,大刀闊斧,體現出心潮起伏,負屈聲高,念白中[梢子音]的應用十分頻繁,富有韻味,亦有利于突出,人物激憤波動的心態。唱腔著重以情帶聲,不以花哨取悅觀眾,而以深沉真摯感人。如“苦戲”,唱[軟音]為主,但偶爾卻以[硬音]點染,劉毓老的《悔路》就如是,像“他將我推虎口”句,就突以[硬音]出之,對表現周仁的滿腔義憤十分有力,老輩演法更注重的,還是人物氣質的把握。
四、情感表現力的運用
戲曲表演的程式是把各種人物的情感借助于外化的程式動作沉淀后的產物,亦為戲曲人物精神生活的形態賦予。無論是演員的形體還是心理,必須保證二者的有機統一與內在聯系,既是平行共時的,也是相互勾連與促發的,這就促使戲曲外化的程式動作折射在演員內化的自我體驗。藝術家在表演的有些片刻能夠通過程式化的動作所構建的模式,迅捷地闖入劇中人物形象的心理天地,將以往所經歷過的舞臺人物的情感外化出來,從而達到動作和內心世界的統一互融。
比如,《龍門寺》這還是一出典型的抒情性“性格喜劇”,其戲劇效果的產生,井不依靠令人體腹的滑稽情節或低級趣味的油嘴滑舌,而是源于男女主角心靈性格的碰撞及其夫妻生活情致,從而引發觀眾會心一笑,更浸潤著雋永的感情芳芬。宋、楊正是把握了這個要害,所以演來不溫不火,亦莊亦諧,意趣盎然。
戲曲表演情感表現力的運用主要是以實踐具體劇目的形式來加以體現。從其內在的緣由來看,對戲曲表演采用具有價值性的訓練方式,讓表演者體驗到該行當多種角色的表現模式與創作方式,從而對戲曲表演的情感表現力的特點有一定的掌握。在表演劇目時,應該充分地訓練有關唱、念、做與打等基本的技巧,還須讓表演者了解劇中的鑼鼓、舞臺調度、唱腔板式以及服裝扮相等要領,可以從多個層面分析情感表達的多種手段。再者,不單單重視縱向的教學方式,還須注重加橫向知識點的訓練,從而讓表演者獲得心靈體驗以及作品理解能力的雙重強化。因而在平日訓練的過程中,應有意識地把表演基礎性技巧轉變成情感體驗流程的因子,在融匯貫通之后,有效地加以運用,培養表演者的情感表現力。
戲曲表演表演者須充分地發揮自身的潛能,注重獨立性、主動性以及積極性所起到的作用,在指導者的循循善誘下,對戲曲的形式、內容、方法及其內在結構等方面都應有比較全面地了解,依循內在良好的情感指向訓練情感的表現力。形成以情發聲以及以情促舞的格局。同時,京劇藝術能夠經由潛在或外顯化的情感體驗來積極地引領表演者的審美感知形成與成熟,持續性地完善自我主體的情感。毫無疑問,情感表現力的形成并不可能一蹦而就,而是一個日積月累的漫長過程。它始終貫穿于演員全部的訓練與登臺表演之中,無論是戲曲的表演內容還是相關的表演技巧,都需要演員以切實有效的方式去實現。
五、結語
總之,四功五法”是戲曲藝術的靈魂,戲曲表演程式,以「四功」為經,「五法」為緯,交織而成系統性的網狀結構形態;在具體運用過程中,是互相配合的綜合性的整體。戲曲演員要熟悉掌握“四功五法”的基本要領,適時適度、恰到好處和自如嫻熟地將之運用,賦予戲曲劇目強大的藝術表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