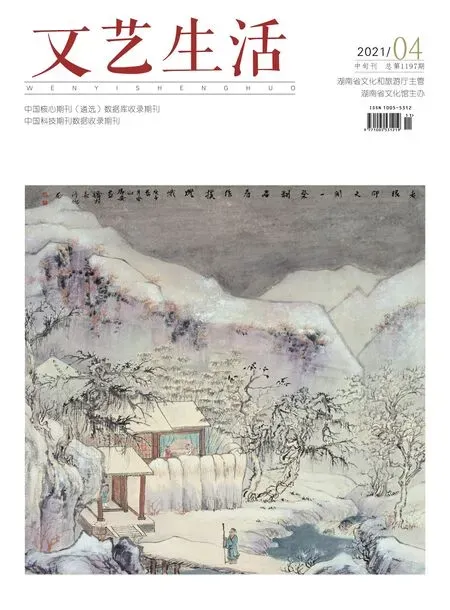從音樂表演的美學原則角度淺析貝多芬的《悲愴》
李知妍
(延邊大學,吉林 延邊 136500)
一、前言
貝多芬是眾所周知的世界音樂巨匠之一。他一生創作了許多非常優秀的作品。其中奏鳴曲《悲愴》是他早期奏鳴曲中的一個代表性作品,這部作品充分發揚了貝多芬獨特的個性特點,與此同時還加入了他大膽的創新思想,使得曲目突破了傳統的曲式特點,但又不失古典奏鳴曲的內在統一性,種種因素成就了這部作品的重要地位。
本文通過對貝多芬奏鳴曲《悲愴》相關文獻的整理與分析后發現,國內外音樂學者對這部作品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的內容基本上只是止于對作品的曲式研究、音樂風格研究、演奏技巧研究等等。研究層面比較單調,并不是很全面。因此,本文在此基礎上還加入了音樂表演創造中的三個美學原則來進一步深入分析貝多芬《悲愴》。
二、音樂表演創造中的美學原則
(一)真實性與創造性的統一原則
真實性與創造性的統一原則中,真實性就是表演者對原作的忠實性,關于“忠實性”,它是音樂表演美學原則中出現頻率最多的一個詞,可見人們對這個詞的重視以及它的重要性。創造性,顧名思義就是表演者對作品的二度創作,這也是音樂表演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點,也是一個人表演中的一大亮點。由此可以看出,真實性與創造性二者都非常重要。實現真實性與創造性的統一,就是在音樂表演創造過程中,演奏者既要表達原作曲家賦予作品的真實情感,也就是要讀懂作曲家的思想,同時在這基礎上投入自己全部的才能、智慧以及熱情去對作品進行二度創作,使得自己的演奏區別于他人并且具有獨特的個性色彩,只有這樣,自己的表演才能在眾多的表演中脫穎而出。
關于真實性與創造性的統一問題,在古典主義時期與浪漫主義時期呈現兩種不同的現象。古典主義時期,演奏家們更注重表現原作的真實性,而到了浪漫主義時期,以李斯特為代表的演奏家們就比較重視自己個性的展現,也就是更看重對作品的創造性。由此可以看出,怎樣去協調與統一真實性與創造性的關系問題,就是我們每一個表演者始終面臨的一個難題。但此問題是沒有標準答案的,沒有一個人或一本書準確的提到在一部作品中忠實于原作的成分占多少,表演者自己創新的比例又占多少。因此,關于這一問題,演奏者只能自我去體會、去感受從而找到一個適合的組合比例進而達到二者之間的平衡。
(二)歷史性與時代性的統一原則
歷史性與時代性的統一原則中,歷史性指的就是音樂作品所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的特定音樂風格。時代性是指表演者所處的時代所具有的時代精神以及受當代因素影響的審美情趣。換句話來說,如果我們站在觀眾或聽眾的角度,那么時代性就是我們想要在音樂作品中聽到的符合當代因素的音樂處理方式;同理,歷史性就是我們想要聽到的符合作品創作背景的傳統的音樂處理方式。這個就是我們在音樂表演階段,包括演奏前階段、登臺瞬間、演奏后階段種要做到的三個尊重中的尊重聽眾心理。那么,作品中歷史性與時代性的統一,就是演奏者在演奏音樂作品時,不能偏離作品創作時期的特定歷史風格,同時還要夾雜著一些當代的時代背景下所具有的獨特的色彩風格。其實,對此,我們可以理解為這并不是自發的、刻意的音樂處理方式,而是一種無形之中必然會形成的結果。因為作曲家在創作作品時,他的創作風格等會受到當時歷史背景等等因素的影響,所以只要演奏者正確理解了作品,那么他的演奏必然帶有歷史性;同理,演奏者一定會受到他所處時代的社會風尚、審美情趣等因素的影響,那么他的演奏也必然帶著時代性特點。所以,筆者認為事實上二者的統一是自然融合的結果。
(三)技巧性與表演性的統一原則
技巧性與表演性的統一原則中,技巧性,很好理解,就是表演技巧。表演性,又稱之為藝術表現,它包括表情、肢體語言等等。關于技巧性與表演性的統一問題,人們都一致的認為技巧只是基礎,它不是表演通往成功的唯一條件。而表演性也就是藝術表現是表演的命脈,是表演的靈魂。在音樂表演的美學原則中,不論是真實性與創造性,還是歷史性與時代性,人們都不能準確的說出它們的側重點,所以合理的去組合、去協調與平衡二者之間的關系是需要智慧的。但唯獨在技巧性與表演性的統一原則中,絕大部分人都認為表演性更重要,只有一小部分人堅持認為表演技巧更重要,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也只有張建華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說法強調了技巧在音樂表演中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都是側重于表演性,他們認為,表演技巧是基礎,是一個優秀的演奏家必備的條件。也就是說,每一個優秀的表演者一定是具有高超的表演技巧的,但并不是所有具有高超表演技巧的表演者都能成為杰出的表演者。
三、貝多芬《悲愴》中的音樂表演美學原則
(一)《悲愴》中的真實性與創造性
貝多芬《悲愴》共有三個樂章,大致概括起來,第一樂章渲染出悲壯沉重的氛圍伴隨著痛苦的嘆息、哀求與呻吟。而在后面的樂句中也突出了對自由的向往憧憬以及決心要戰勝黑暗勢力的氣勢。第二樂章整體情緒都平靜暗淡,是接受了黑暗的現實。第三樂章前半部分似乎還在徘徊,沒有堅定的立場,但最后結尾還是表明了不屈不撓、抗爭到底的決心。這些描述以及譜面上的所有符號語言我們可以初步認為是這部作品的真實性,就是貝多芬想要表達的內容。但實際上我們畢竟離貝多芬的時代也比較遙遠,如今使用的譜子也可能是改編過許多次的版本,因此,我們現在看到的、知道的關于《悲愴》這部作品的內容也不一定是貝多芬當時最真實的想法。所以這之間的差別,不得已而進行的變化,就可以理解為是創造性,這種創造性不是自發的,是受到外界因素干擾而得到的結果。那么,關于自發性的創造,就是怎樣去解讀譜面的內容,是要放大強調哪一部分的情感,要含蓄收斂哪一部分內容等等就是創造行為。所以,一首曲子可以看到許多不同的詮釋,甚至同一位演奏家在不同時間地點演奏同一首曲子都可能不盡相同。這點其實也可以聯系到音樂表演的不可重復性,也就是說演奏者的每一次表演都應該不一樣,都應該較之于上一次有所突破,即使上一次的表演已經十分成功,但仍然要有新的進步的成分在下一次的表演中,實現自我超越。
(二)《悲愴》中的歷史性與時代性
貝多芬《悲愴》這首曲子寫于法國大革命時期,此時社會動蕩,是一個暴風驟雨般的革命年代。這就是這部作品的歷史背景。同時對于貝多芬個人而言,此時也正是他生活非常艱苦的時期。父母接連去世、聽力下降、愛情失意等一系列事情的接連發生給了貝多芬重重的打擊,而在這種背景下,貝多芬堅持的迎難而上,與命運抗爭到底的英雄主義精神在21世紀現代也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的。這也正是這部作品一直受歡迎的原因,每個年代都會面臨著每個年代的困難,而不論在哪種情形面臨哪些問題,貝多芬式的不屈不撓抗爭精神始終是我們要學習的榜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攻克難關,迎來我們所憧憬和向往的生活。
(三)《悲愴》中的技巧性與表演性
《悲愴》是一首極具演奏技巧的曲子,尤其是左手大量的八度震音、左右手的交替演奏等等都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關于表演性,在這部作品中最重要的就是演奏者在演奏時的“表情”。我們從曲目名稱就可以看出這首曲子的主題及烘托出的大致氛圍就是“悲”。因此,在演奏時,表情也要到位。那種悲慘的嘆息、凄涼的哀求以及痛苦的呻吟等等,都要表現出來。
四、音樂表演美學原則在《悲愴》中的啟示
從音樂表演的美學原則角度去分析貝多芬《悲愴》,可以知道關于真實性與創造性的統一,需要演奏者投入全部的才能、智慧、想象去將譜面上的各個音樂符號、我們所能了解到關于這部作品和貝多芬的信息詮釋出來,并且在此一過程中加入演奏者自己的個性色彩,使得演奏具有特色但不失傳統;關于歷史性與時代性的統一,就是作品中所表達的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及同命運作斗爭的英雄主義氣概都值得當代青年的傳承與發揚。這正好呼應了歷史風格與時代精神的結合;那么關于技巧性與表演性的統一,我們知道一定是通過平時的勤奮刻苦練習中提高自己的演奏技巧,在此基礎上,重視表演性,就是要求演奏者做到“心里專注”,將音樂演“活”,賦予它生命,使之直擊靈魂、觸動心弦,帶領聽眾與觀眾感受更深刻的音樂內涵。
五、結語
在音樂表演的創造中,美學原則的合理應用可以不斷美化音樂作品,不斷增強音樂表演的影響力和感染力,將音樂作品的內涵充分彰顯出來,使觀眾產生心理共鳴,拉近音樂表演與觀眾之間的距離,從而獲取觀眾較高的滿意度。最后,作為一名音樂表演者或演奏者,具有高超的演奏和演唱技巧只是基礎,還要不斷的提升自己,尤其是要注重美學修養的提高,通過合理運用音樂美學知識,充分發揮其作用,向聽眾和觀眾傳達出音樂作品的內涵,從而使他們對音樂的理解達到一個嶄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