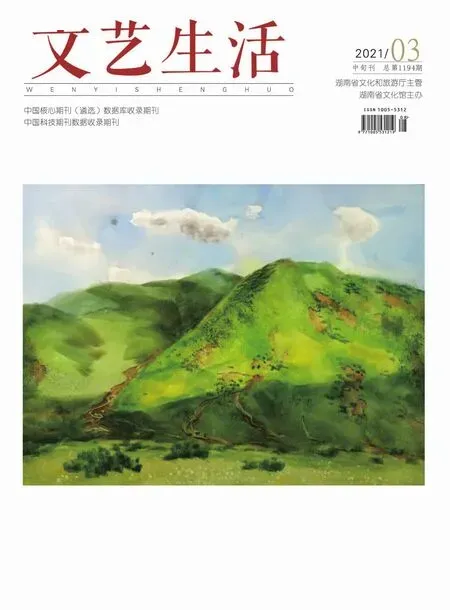中國女性書法的沿革
楊藝璇
(四川大學 藝術學院,四川 成都 610207)
一、前言
古代女性受到“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傳統緊固與束縛,女性地位低下,女性的藝術才華得不到充分的展示,更得不到重視和認可,女書法家屈指可數,寥若星辰,藝術風格也大多依附于男性,隨著思想解放,女性地位提高,越來越多的女性在書壇中涌現,她們逐漸也有了創新意識和獨立性,不依附于誰,而是自成一派,成為書壇的中堅力量,是書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女性在書法的歷史發展中不斷成長。
二、古代傳統女性書法
女性書家在中國古代長期處于從屬地位,古代女性“相夫教子”成為亙古不變的信條,“男尊女卑”、“夫為妻綱”等封建綱常倫理,使得男性掌握家族的統治權,女性在經濟、物質生活中,都處于完全從屬的地位,這無不影響和制約著女性在藝術上的發展,更不用說女性之于書法了。古代女性囿于閨閣,家庭幾乎成為她們生活的全部,被禁錮在深院中的女性,她們的言行舉止也嚴格受到了制約和限制,對于文化藝術,接觸極少,對于書法更是如此,她們幾乎都不是文化藝術的參與者,僅有極少數女性能夠對書法有所涉獵,一般來說,古代女性參與書法活動,主要有兩種:第一種香世家和官宦氏族擁有豐厚的家學傳統和文化資源,這些家庭中的女性夠擁有接受教育的機會;第二種則是青樓女子,為了生存生活的需要,來學習書法藝術。
(一)受家族影響下的女性書法
趙孟頫夫人管道升工尺牘,擅長行書和小楷,風格極像趙孟頫,清代孫承澤在《庚子消夏錄》之《管夫人墨竹》中稱,管道升“字法似子昂”。董其昌說:“管夫人書牘行楷,與鷗波公殆不可辨同異,衛夫人無后儔。”管道升在《管仲姬竹卷后跋》中寫道:“侍吾松雪十余秋,傍觀下筆”,又言“操弄筆墨,故非女工。然而天性好之,自不能已。竊見吾松雪精此墨竹,為日已久,亦頗會意。”可見趙孟頫的書法對管道升的書作有著極深的影響,甚至是決定了管道升的書法走向。
《書史會要》中記載,元仁宗“嘗取夫人書和魏公及子雍書,善裝為卷軸,識以墨寶,命藏之秘書監,曰‘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婦、父子皆善書也’。”可見管道升作為女性書家名滿天下,且作為“夫婦”皆善書可謂少之又少。管道升行書《秋深帖》,秀美圓潤,溫婉暢爽,用筆扎實,甚至有學者認為,此貼應為趙孟頫替夫人所寫,足見兩人筆跡極為相像。
晚明的女書家邢慈靜是書法家、文學家邢侗的胞妹,她處身名門閨秀,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藝術熏陶,其行書穩健,用筆靈活豐富,氣勢磅礴,清乾隆《武定州志》記載:“慈靜,博學善屬文,詩有清致,書畫俱稱絕品,與兄齊名”;清代錢謙益在《列朝詩集》中稱:“慈靜仿兄書”,可見其亦是學其兄書。
另外,書法家劉墉的側室,嘉興黃氏,其用筆書跡也極似劉墉,“惟工整已甚,韻稍減耳,劉墉晚年書跡多出黃手,小真書竟至莫辨,世人罕有知者。又有家書十冊,夫人書后,諸城批答,皆妙絕。”足見黃氏書法與劉墉極為相似,且能夠“以假亂真”,其書法水準必定不低。還有其他類似環境的女性,自身的文化修養和藝術水平相對較高,她們的書法大多受家族影響,以氏族傳承為主,她們的書法風格都依附于男性,在書法上未能有自己的風格體現和獨到見解,很難具有獨立性,難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書法風貌。
(二)名妓女子的書法
古代部分妓女招攬客人的資本并非美色,而更加注重技藝才能,她們從小接受專門的訓練,琴棋書畫等等藝事成為往后謀生的手段。陳東原在《中國婦女生活史》中說:“娼妓的思想與精神是自由的,解放的,流動的……”可見妓女在精神層面的追求非同一般,她們的書法相對氏族大家中的女性而言而作為青樓女子,反而在書法中有自己獨特的藝術見解,更具獨立性和個人特色。
唐代薛濤,能詩能文,關于薛濤的書法,《宣和書譜》中有記載:“婦人薛濤,成都娼婦也。以詩名當時,雖失身卑下,而有林下風致,故詞翰一出,則人爭傳以為玩。作字無女子氣,筆力峻激。其行書妙處,頗得王羲之法,少加以學,亦衛夫人之流也。每喜寫已所作詩,語亦工,思致俊逸,法書警句,因而得名,非若公孫大娘舞劍器、黃四娘家花,托于杜甫而后有傳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萱草等書。”獲如此評價,可見其書法是極好的。她還作“薛濤箋”,如今仍存。宋代官妓王英英,曾得到“宋四家”之一的蔡襄的指點,《書史會要》中記載:“學顏魯公書,蔡襄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在當時其大字已有一定的名氣。
明末清初女妓柳如是更有自己的風骨,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稱:“河東君之書法,復非牧齋所能及”柳如是的書法中又有濃厚的書卷氣,散發出深厚的文化底蘊。錢謙益在《有美一百韻》中稱柳如是“詩哦應口答,書讀等身便。緗帙攻文選,綈囊貫史編”。書法自然超邁不群,用筆多用中鋒,受到董其昌的影響,但卻不軟媚,用筆精妙,具備了一個藝術家的文化人格和審美情趣,翁同龢贊許柳如是書法“鐵腕拓銀鉤,奇氣滿紙”。薛濤等為代表的青樓女子,她們的才情在無拘無束中被施展出來,她們不依附于家族門庭、氏族之風,更開放、自由地進行藝術創作,更具獨立性。
中國古代女性書法家以氏族傳承和青樓女子兩類為主要代表,氏族傳承中的女性依附于男性,其書法風格較為單一,接近于所學之人;而青樓女子無拘無束,不僅要通過書法提高修養和技藝,滿足狎妓之人對文化的需求,她們的作品也往往更寄情達意,隨性灑脫,別具一格。
三、近現代女性書法
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用槍炮轟開國門,傳教士將男女平等等觀念滲透國人,給中國女性帶來了追求獨立的火把,指引婦女解放的方向。加上早期改良主義的鼓吹,開始沖擊傳統的中國社會,在戊戌變法中,康有為、梁啟超等,以進化論和“天賦人權”的學說作為武器,積極呼吁女性解放,中國近代思想家、教育家梁啟超也提出“欲強國必由女學”,認為女學與國家之強弱成正比關系。嚴復則提出:“使國中之婦女自強,為國政至深之根本”;梁啟超也說:“吾推及長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人不學使”,他們都意識到女性對于發展的重要意義。
在紛爭戰亂的清末民初時期,隨著社會的進步與部分封建思想的瓦解,女性不再束縛于閨閣之中,開始參與社會活動,如革命家秋瑾、吳芝瑛、何香凝、張默君等,她們是革命者,把巾幗熱血揮灑到民族解放的運動之中,同時又是書法家,有著不俗的書法造詣,幾乎都受到了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她們的書法作品風格各異,大多以帖派風格為主,溫文爾雅,用筆細膩;她們在傳承經典之余,嘗試加入自己的理解和表達,逐漸帶有自己的書法風格,為清末民初的書壇增添了色彩。
伴隨著婦女解放運動的深入,女性逐漸有了相對良好的社會氛圍和良好的成長環境,涌現出一部分較為獨立的女性書家,同時碑學興起,為女性書家提供了更多的取法來由,這些女性書家一改傳統女性書法風貌,出現了雄強質樸的女性書法風格,如“南蕭北游”。蕭嫻師承康有為,書能開張大氣,不落俗套,大字極佳,蕭嫻號“蛻閣”,為退出閨閣之意,她用作品和書跡,讓世人領略她走出閨閣,邁向藝術的榮光。游壽不僅是我國著名的女性書法家,也是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其書法主要傳承李瑞清、胡小石一脈,將“求篆于金,求隸于石”了然于胸,并付諸實踐,書法汲取碑派金石之氣,頗為大氣。作為民國女性,她們也有形成了一定的個人的風格,但沒有完全脫離自己的老師,獨立性不夠,但也為現代的女性書法家樹立的先鋒和榜樣。
改革開放后,經濟蓬勃發展,文化的土壤也更加肥沃,男女逐漸平等,女性獲得了更多書法方面的教育,越來越多的女性書家猶如雨后春筍般在書壇活躍,以充滿獨立性書法面貌展現在世人眼前,如周慧珺、張改琴、林岫、孫曉云、胡秋萍等,與之前不同,她們開始有完全的獨立性:周慧珺雖是沈伊默學生而不完全像沈,孫曉云是外祖父朱復戡先生,孫也能融“二王”書風,自稱一派;張改琴的字開張大氣,充滿“丈夫氣”,雄渾有力,完全不輸同時代的男性……她們的書法有了鮮明的個性,較之前的女性在書法上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她們不依附于男性的風格,而有完全獨立的思想,書法風格能夠將古代經典融會貫通,自成一派,能與同時代的男性相匹敵。
在高等教育中,書法專法的女性占比極高,而書法專業的女碩士、女博士也不在少數;在書法展賽中,女性書家也越來越多,所占的比例也越來越大,其中1985 年中國書協設立“全國婦女書法”專項展至今已舉辦6 屆,每一屆的投稿人數和投稿數量也在增加,投稿作品整體水平不斷增高;部分省、市也開始設立女書法家協會,組織相關展賽和活動,這些都是女性書法崛起的表現。
四、結語
事實上,古代整體女性書家,相較于男性書家在書法史上的數量和成就稍顯遜色,有明顯的滯后性,藝術風格頗是受限,多是以傳承傳統的書法為主,幾乎沒有自己的風格,而現在,女性書家的數量相較古代而言人數驟增,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群體。
如今女性與男性擁有同樣的社會地位,所接受的教育資源是相同的,在書法學習中,女性擁有和男性同樣的書法學習范本,學習方法和創作方法。與前代相比,女性書法家已經與男性書法家擁有共同的學習環境與藝術環境,她們銳意進取,追求自由,取法各異,碑帖兼通,女性書法家的群體也逐漸朝著知識化、年輕化發展,越來越多有個性有創新的女性書家在書壇不斷涌現,在書壇占據著重要的地位。
總體來看,我國女性書法從古代以傳承為主,書法風格有家族性、依附性演變到如今風格多樣,百花齊放,女性書家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具有獨立思想、獨創精神,更具個人風格,女性也能夠在書法領域展露鋒芒,無疑的,女性書法家們給中國書法史增添了一抹亮麗的色彩。相信會有更多的優秀女性涌現,并創造出具有女性特色的書法作品,開創新風,女性書法事業也將蓬勃發展,欣欣向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