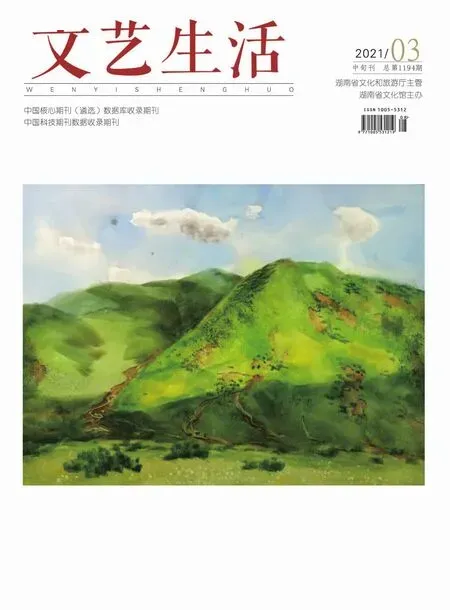舞蹈生態學視閾下過山瑤“非遺”舞蹈“跳九州”的發展現狀初探
寧 靜
(湖南師范大學 音樂學院,湖南 長沙410006)
一、烽火九州,喧鳴鑼鼓
(一)江華的生態環境及文化背景
“江華古為馮乘,始建于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迄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作為省內唯一的瑤族自治縣,“江華瑤族自治縣位于南嶺北麓,瀟水上游,湖南省最南端,與粵、桂接壤……東北接藍山縣,東南鄰廣東省連縣、連南瑤族自治縣、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西南界廣西壯族自治區之賀縣、鐘山縣、富川瑤族自治縣、西抵江永縣、北枕道縣、寧遠縣。”三省通衢,是瑤族向南遷徙的主要通道;地處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區,春多陰雨,夏無酷暑,冬期不長,多有晨霧;春去秋來,氣候溫和且濕潤;人們在此安居樂俗,故而江華是湖南省瑤族分布最為集中的地區。
古邑江華,山清水秀,人文薈萃,今有“神州瑤都”的美譽。而誕生于這片土地的“跳九州”,傳習人員大多居于湘江鄉,湘江鄉地勢呈南北走向,北高南低,山地氣候明顯。從江華驅車前往需花費數小時,地處深山,山路崎嶇顛簸,途經湘江鄉的南大門,也就是千年勉古寨——桐沖口,桐沖口位于江華九江之一的麻江河,作為過山瑤聚集的村寨,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瑤族《盤王大歌》《長鼓舞》傳承基地。在此還可以一品長桌上的洪沙大席,一嘗瑤族十八釀,可謂與世隔絕的一片盛世桃源。在政府的扶持和湖南廣電扶貧工作隊進駐幫扶下成功創建了國家級三A景區,村寨煥然一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學者前來體驗當地的風土人情。
再深入山林行駛半個小時,就到了田沖村,如今的田沖村是2016 年由歐菜坪和田沖村兩村合并而成。演藝隊伍多以田沖村村委會為傳承和習練基地,“跳九州”動作幅度大且多有調度,因此多在露天的空地上練習;在田沖村文化廣場上有一席簡易的磚石民間舞臺;有時也會在云霧繚繞的山頂坪地中一遍遍練習,那里是田沖村的活動中心,坪地不遠處就是一片無盡的清香柚子林。沿著山路往上不遠就是省級“非遺”傳承人盤財益的家,年高望重的盤老今年已經九十多歲了,已然耄耋之年。老一輩傳承人的徒弟們擔任起了“跳九州”表演隊核心骨干的角色,其他的表演者為當地務農的村民,日常練習多是隊員自發組織或由村干部組織。
南宋湖廣戰亂,為躲避官兵追殺,瑤族先民被迫第二次漂洋過海,離開千家峒撐船過湖進入湖南,逐漸形成“南嶺無山不有瑤”的局面;江華歷史上“七姓瑤人進九沖”也緣由于此。“跳九州”源于“走潮”,用以驅邪祭祖;紀念瑤族先民漂泊無定、尋覓家園的苦難歷史,以前還有“鯉魚上灘”的程式。多在春節“耍正月”及盤王節等瑤族重大節日時候表演。從正月初一跳到正月十五,走村串寨,主客相迎,主人將隊伍請入廳堂表演,有祈求五谷豐登、吉祥幸福的寓意。作為瑤族人民身份認同的符號,也是村寨往來溝通的橋梁,具有團結民族同胞的凝聚力。
(二)過山瑤“跳九州”的藝術形態
“跳九州”是舞蹈及樂器于一體的綜合表演藝術,古樸粗曠的舞姿看似隨意,但是井然有序的程式和畫面調度體現了民間藝人們的勞動智慧,是瑤族人熱情彪悍且情感細膩的性格特質的外在顯現。“跳九州”舞蹈男女老少皆宜。早期的表演沒有樂器形制的道具,把一切可發出的聲響的道具都可作為樂器,隨著過山瑤遷居,瑤民不斷遷移,不知不覺中融合吸收了他者文化。樂器的種類也隨之豐富,有手持的牛皮小鼓,環以竹釘,敲擊聲潤亮悅耳;此外還有洪亮回響的大銅鑼、清脆利落的竹梆、高昂嘹亮的小鈸等樂器。早前的跳九州整套程式要來回四到六遍,目前刪減到里只演出一遍一套程式,表演時長為七到八分鐘。“跳九州”上舞臺前都會訓練足月份。最少一人領鼓四人跳,至少五人才可練習。領鼓人“嗓!”提醒表演者的隊形整齊。全程鼓樂齊鳴,交相跳躍走位,熱鬧非凡。表演者都為過山瑤瑤民,可同村村民或者合村共同組織練習,當地有時以“跳九州”舞蹈慶祝豐收,以舞傳遞喜悅之情。
據傳承人盤玉金口述,如今表演的“跳九州”分為七個程式步驟:“拜四方”、“穿四角”、“穿五角梅花”(在當地又稱“搓繩”或“穿花”)、“雞公啄米”、“雞公擺尾”、“五龍歸位”、以滿懷誠意的“謝恩”作為結束。場地中央的擊大鼓者就是口述文本的提供者——當地有名望有技藝的民間傳承藝人盤玉金,擊鼓指揮隊伍,掌握著整個表演的節奏和進程;另有四位老藝人分別為兩個隊列的隊頭隊尾,其他的表演者跟著隊頭邊擊邊舞,膝蓋微曲,步伐輕快,腳下富有彈性;開場先向觀眾行禮以示表演的開始,眾人雙手持樂器敲擊,聽著鼓聲的節奏祭拜四方,跟著領隊的隊頭穿廳房四角,紀念瑤族先民們的艱難遷徙歷史;兩個隊頭相向繞身而過“穿五角梅花”,每每相對,兩人手持樂器側身繞過;直至隊尾的人全部穿完,隊伍甩出長弧線的尾巴繞回中場位置,分散排列成整齊的數列縱隊,鼓王居中敲擊著大鼓統一舞步,老藝人們出腳前點地,高舉樂器邊俯身拜禮邊擊奏,“雞公啄米”之后左右擰腰“雞公擺尾”。這套動作在整個程式分別排成縱列和橫排共表演了兩遍,結尾前老藝人帶隊“五龍歸位”收攏隊形,俯身“謝恩”結束。瑤人不忘先祖,心有瑤族同胞,是緬懷民族歷史,知恩感恩的良好品格的具體外化。
二、活態流變,社會迭代
(一)適應社會環境的發展
“跳九州”的傳承依附于當地的民俗活動,受客觀的文化環境和表演場域的限制。當下社會文化大背景下,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享受權力話語權之下的便利。“非遺”文化及傳統保護的法律條款趨于完善。地方政府及民間文化企業常組織民俗活動及舉辦相關比賽。推動地方傳統文化事業的發展,為當地文化旅游產業轉型升級注入新的動能。舞蹈作為社會生活的文化產物面臨著日新月異的社會環境,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發展,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表演空間的變遷、人們精神生活的需要和審美習慣的轉變都是誘使“非遺”舞蹈活態流變的重要因素。
從文化自身的因素來說,作為一種“活態”藝術,離不開人、時間、空間這三個要素,而人、時間和空間并不是恒定不變的。不同民間藝人的即興發揮和對藝術審美理解各異,因此樂舞的內容和表現形式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活性”。音樂舞蹈由當地藝人表現當下的社會生活,其具有自身的創新續航力。專業編導人才的補給,學院派的風格也逐漸滲透。在創新和現代轉型中激活文化造血的能力。文化的落實回歸當下民眾生活和藝術實踐里。人文關懷作為樂舞表達的固有屬性,向公共文化靠近的道路上,情感的表達尋求更容易引起民眾共鳴的形式。
“非遺”舞蹈為適應場域的轉變,舞蹈形態發生變化;舞蹈開始往舞臺表演形態轉變,得以升華成為舞臺藝術,活態流變賦予了傳統文化更持久的生命力。固有的表演形態不適應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發展,出于傳統民族文化的傳播需要,“跳九州”從鄉間田野、屋舍廳內搬上了舞臺空間,表演場域的變化也對地方傳統樂舞的表現形式提出了要求,有了更為廣大的受眾面。
為滿足本土經濟的發展需求,除本土農業或其他資源產業之外,文化產業也是帶動經濟發展的優質選擇,文創產業迎合市場進行現代轉型,以及生產性保護的方式成了挖掘傳統文化商業價值的主要方式,例如民族劇團、民族舞團、民俗文化旅游等。水口鎮的愛情小鎮就是江華文旅產業打造品牌的實例,其中包含“跳九州”、瑤族長鼓舞、瑤族婚嫁習俗、瑤族攔門酒等瑤族特色表演項目;將“非遺”舞蹈的多重身份賦予了文旅的商業價值。以文化消費開拓市場,為江華文化生態旅游深度融合做出了新貢獻。
(二)適應新興的網絡生態
在信息時代的大背景下,衍生出一個新的概念——網絡生態系統。科學技術水平的發展,逐漸綿延至數字化數據結構的線上平臺,搭建起一個虛擬世界。海量信息在其間飛速傳遞,文化的傳播力度和影響力大大增強。即使地處偏遠地區的湘江鄉鎮也能跟進實時的熱點事件,山區生活也可以通過線上平臺向外界分享。網絡是對外界宣傳的快捷窗口,大力宣傳當地的民族樂舞文化,推動了當地舞蹈事業的發展。有利于增強當地的文化產業的品牌效應傳播,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
每逢江華舉行盤王節或大型民俗歌舞活動時候,舉辦方會通過地方電視或是網絡直播的傳媒渠道向全國人民展現江華瑤族人民斗志昂揚的精神面貌,實時直播或錄播盤王節、民俗等大型活動的表演畫面。一年一度的盤王節,夜晚霓虹燈璀璨。在江華圖騰廣場上表演的“跳九州”隊伍,為適應舞臺場域上的演出形式已經做了相應的取舍和創新的編排。為提高舞臺欣賞的視覺效果,使用全國人民的欣賞習慣,邀請職業舞蹈工作者協助進行編排,轉變為舞臺表演形態的“跳九州”舞蹈。在外飄蕩無法歸鄉的瑤族游子通過網絡參與盛會,感受家鄉熱情和力量,打破實質的現實距離,強化本民族身份認同感。
反之,網絡生態的影響也有其弊端,網絡信息的恣意,紛繁復雜的外來文化對本土文化帶來極大的沖擊,難免出現為了一味迎合觀眾,擴大影響和受眾面,導致舞蹈的表演丟失其民族特異性的個例。
三、結語
原生態舞蹈的發展如今面臨的生態環境不再單單指地理和氣候的自然生態環境,還包括更為多元化的社會人文環境以及紛繁復雜的網絡生態。“跳九州”藝術形態孕育于生態環境大環境下的勞作生活,受到場域轉移的客觀因素和傳承人審美變化的主觀因素影響,傳承的實施與當下社會環境接軌是不可避免的命題。地方對于“非遺”傳承的重視、以及傳承對于現代審美的妥協相互作用,在當代文化大背景的時代語境下形成傳承現狀的復雜局面。即便在外來文化強有力的沖擊之下,民間舞的發展也不能剝離掉其民族本來的特質,舞臺表演形態的轉變需建立在保護原生態舞蹈的基礎上創新發展,尊重其文化原型,把握好傳承與發展的“尺度”。當地在推動舞臺表演形態的“非遺”舞蹈創新發展的同時,也應注重原生態舞蹈原貌保護和傳承,明晰兩者之間的界線,在共時語境下兩道并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