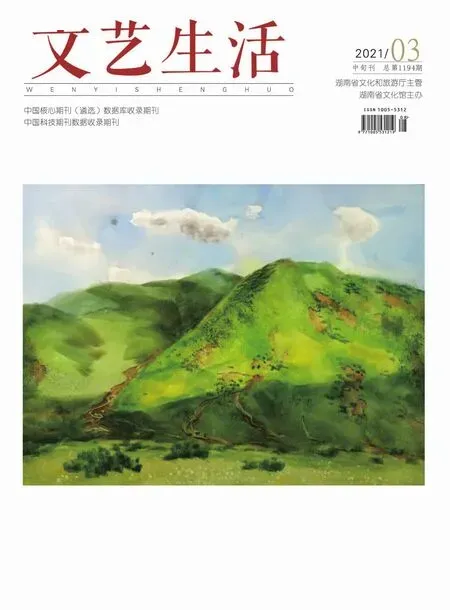談《動物兇猛》及《陽光燦爛的日子》
張朝輝
(安仁縣電影發展有限公司,湖南 安仁423600)
一、青春
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都在告訴我們一個道理——這就是青春啊。
小說《動物兇猛》開篇的那一段話:“我羨慕那些來自鄉村的孩子…”便讓我感嘆萬千,故鄉對我們每一個長大后離家在外的游子而言,都是一個魂牽夢縈的地方,眾生都有故事,萬物都有故鄉。在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片頭的旁白也有這樣一段話:“北京,變得這么快!20 年的功夫,它已經成為了一個現代化的城市,我幾乎從中找不到任何記憶的東西,事實上,這種變化已經破壞了我的記憶,使我分不清幻覺和真實。我的故事總是發生在夏天,炎熱的氣候使人們裸露的更多,也更難掩飾心中的欲望。那時候,好像永遠是夏天,太陽總是有空出來伴隨著我們,陽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陣陣發黑。”我們將自己過去的記憶悄悄的安放在心中,即使日后遠在他鄉,也會拿出來細細品味一番。
小說與電影雖是兩種不同的藝術表現手法,但都會給人一種“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的心情,魯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曾說:“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后來我在久別之后嘗到了,也不過如此。唯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一種聲音或味道就可以將人們帶入真實的過去,兒時傍晚田野池塘里傳來的片片蛙聲、白天家門口小孩的成群打鬧聲,廚房里飄來的縷縷香氣和煙囪里升起的薄薄青煙,這些都是我記憶中熟悉的聲音與味道。每個人終究都有著屬于一個地方的珍貴青春記憶,有著一股強烈的熱血勁頭。每個人的青春在時間軸上都是固定的節點,但是會因為每個人的不同而發散出各種光芒,我們這代人比如:打架都是小打小鬧不敢上磚頭;曠課,一定會找個合理的借口;追女孩,會偷偷寫信不會明目張膽。每個人終究會經歷懵懂、敏感、彷徨、叛逆、躁動、虛榮,天真還未走遠,成熟卻又蹣跚而至。當我們回憶青春的時候,時間帶來的變化慢慢在摧毀了我們的回憶,我們甚至不能確定什么是真實存在過的,什么是自己憑空臆想出來的。稍不留神,青春就已落在時光的塵埃當中,分不清真實與虛幻的我們手足無措,懷念起那些陽光燦爛的日子。
每個時代都有每代人的獨特青春記憶,個體從時代產生于時代,是那個時代最鮮活的寫照,對于電影中的“馬小軍”而言,在北京大院里成長的斑斕歲月就是他最難以忘懷的那段青春,父母教育時會說“你這樣會犯錯誤”,追女孩許諾時會說“我向毛主席保證”,這就是那個時代的語言氛圍。野蠻成長的年代,揮灑不盡的荷爾蒙,肆意妄為的青春。當人們講述青春故事時,很可能是已經被大腦加工過多次的回憶,而這一切都源于那濃烈的、純真的、浪漫的理想主義。記憶可能模糊了真實與幻想的界限,但一首老歌,一件舊物,一個場景,都能迅速回到那個青春時代,既陌生又親切。青春的日子未必陽光燦爛,卻異常的浪漫。
二、虛實
小說故事開始于倒敘,三十歲后的“我”參加一個中學同學的聚會,“當一個個陌生男女走進那個房間,笑容滿面地彼此握手,特別是聽到其中有一個人叫出我的名字,我有一種脫離現實的感受”。在聚會上大家通過一個個名字的道出,開始回憶起那激昂的青蔥歲月,那充斥著肆無忌憚,但內心卻又無比的空虛的歲月,沒有我們現在的規矩束縛和對未來的迷茫不安。渾渾噩噩的日子與被框定的未來,他們所能做的在這美好的時光里盡情的浪費揮霍這激情的歲月,用最直接的方式去釋放自己的青春。王朔說這本書是寫給同齡人看的,其實更能產生共鳴的是那些已經逝去了這段記憶但是又時常憶起這段記憶的成年人。因為王朔將他們在少年時代的隱私、沖動、叛逆、性幻想全部曝光了,電影是以第一人稱的旁白按故事順敘播放,中間穿插和反轉,前面的青春記憶用的是浪漫的暖色,而成年后則是黑白影像。這也暗示著一代青春的結束,青春終究還是美好的,正如影片中的那個長鏡頭——“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電影最大的手法就是“我”的“自我懷疑與質問”,這種敘述風格給讀者一種冷靜客觀的態度,理性的去思考這場青春。青春這個東西很有意思,即便年齡不同地域不同,但是每個人的青春大體還是相似的。電影中的男孩那種貪玩調皮、對女孩的青澀情感、傾盡所能想討好女孩但卻不知如何相處、對性的幻想、告白、沖突、被孤立、長大后又相聚的各種感情都體現得恰到好處,看似松散無章法卻利用時間線串起了一個動人的故事。
在談及自己的電影時,姜文說:“我不能發誓要人老老實實地講故事,可是說真話的愿望有多么強烈,受到的干擾就有多么大。我悲哀地發現,根本就無法還原真實,記憶總是被我的情感改頭換面,并隨之捉弄我,背叛我,把我搞得頭腦混亂,真偽難辨。”他悲哀的發現根本無法還原真實,記憶總是被他的情感改頭換面,并隨之捉弄他、背叛他,把他搞得頭腦混亂,真偽難辨。電影畢竟不同于小說,一閃而過的畫面容易讓人錯失細節。王朔的小說對內心的剖解更加細致,已成年人的視角去回憶青春歲月的故事。故意將遺忘和記憶交織在一起,虛虛實實,卻充滿了藝術感。
三、欲望
看完小說和電影后我不得不佩服作者王朔與導演姜文,一個敢寫、一個敢拍。或許在我們的文化中就有著談性色變的歷史,無論是一直被誤解的《金瓶梅》,還是那亙古不變的“你是爸媽撿回來的”似乎都在逃避談論“性”這個話題。
于北蓓和米蘭是馬小軍對性的認識的兩個體現。于北蓓是第一個遇見的個性鮮明的女孩子,但她看起來是放蕩和低俗的象征,畢竟她跟任何人都可以嬉笑,甚至于給“我”上過一堂最生動的思想政治工作課。當“我”第一次用自己配的一把“萬能鑰匙”開盡別人家門鎖的時候,他從中找到了無比的滿足與快樂。于是他變得不亦樂乎,直至當他打開米蘭家的門,看見米蘭的照片,然后笑逐顏開,因為那一刻他就戀上了這個照片上的女孩不能自拔。他頑固認為米蘭是自己夢寐以求的女孩。當主人公真的遇上米蘭,他不斷夸大或捏造自己的經歷,展現出的是急于表現和成長的心態,這是因為他希望被肯定被崇拜,此時他正在經歷從對世界的認識基于幻想的孩子漸漸變成一個接受現實的男人的過程,所以他給了她們現實載體的幻想形象。他喜歡的是神秘高傲的米蘭,把她想象成自己的女神,跟蹤、守候、暗戀,甚至為了顯示自己的勇氣爬上高聳的煙囪,跌落下來也興高采烈。這一情節就像雄性動物在發情時會在雌性動物面前顯示自己的威力一樣,是一種本能反應。他在自己的意識里對米蘭意淫,發泄著青春期的性渴望。人都是頑固不化和自以為是的,相安無事的唯一方法就是欺騙。馬小軍一步一步陷入對性的迷惑與失落之中,當馬小軍大概感覺到米蘭真的把他當做弟弟了,這種現實擊碎了他,對米蘭的因愛生恨,也是因為他發覺米蘭聚焦的重點并不是自己。他開始對米蘭用莫名其妙的暴躁和怒吼來表達自己的憤怒,他找了很多理由來讓自己厭惡她,于是在他的印象里她的身材開始變得臃腫,臉上也多了很多皺紋和暗斑,就連她身上讓他著迷的香味也變得臭不可聞,性的美麗外衣一層層的被剝落,當這一切不再美好,就有了想要摧毀它的想法。最后,馬小軍選擇了最極端的方式去得到米蘭——強暴米蘭,當反抗的米蘭大喊到:“你覺得這樣有勁嗎?”,“你活該!”,然后馬小軍轉身摔門而去,完成了這件事后,馬小軍滿臉都是猙獰的笑,似乎心中一直以來的刺被拔掉了,對于馬小軍來說,米蘭不過是一場夢,一個青春的符號,它可以是于北蓓的樣子,也可以是米蘭的樣子,無論她在片中說過什么話,穿過什么衣服,是否真的戴了墨鏡,是否真的穿了暴露的紅色泳衣被馬小軍一腳踢下水,她始終是個符號,存在于少年模糊的青春記憶里,就像是青春里縹緲的荷爾蒙,年少時我們曾摒棄過的夢,日后竟也開始拋棄我們來。
小說寫出來的是人身上那種具有強烈破壞了的動物本能,畢竟這是世間也存在類似的事,文字的趣味在于,它的想象力是超意識形態的。有的時候如果你看文字的描述,真的按照這個方式呈現在影片中了,就奇怪了,甚至讓影片的調性不倫不類,但寫在書里那種比喻那種描寫就貼切很多,這樣的文字是拒絕視覺化翻譯的。因為它們本身的個性過于凸顯了卓越的想象才華。“動物兇猛”,或許可以解讀為從保守到開放的過渡時期的青年人無法宣泄的欲望內化成的潛意識,就像久久關在籠子里一下被放出的猛獸,攻擊成性。而電影對小說做了這樣的一些改編,原因有很多,但我更愿意相信是電影想要通過一些場景、鏡頭設計去宣傳一些正能量,畢竟人作為動物有道德和法律的約束,這也是我對《動物兇猛》和《陽光燦爛的日子》各自題目的一些理解了。
四、現實
“我閉著眼睛往前一躍,兩腳猛地懸空,身體無可挽回地墜向水平“呼”的一聲便失蹤了,在一片雅雀無聲和萬念俱寂中我“砰”地淺落在水面。水浪以有力的沖擊撲打著我,在我全身一朵朵炸開,一股股刀子般鋒利的水柱刺入我的鼻腔,耳廓和柔軟的腹部,如遭凌遲,頃刻徹底吞沒了我,用刺骨的冰涼和無邊柔情接納了我,擁抱了我。”
小說最后,“我”從高臺跳下了水,一碧如洗的晴空也沒能與他身下的水融為一體,水柱刺入的眼睛,口鼻,逼著人掙扎。而在影片的最后,姜文把結局設計的非常富有意味,馬小軍在一個泳池里想要探頭上岸的時候,每次都會被朋友用腳蹬回去,像是正在被孤立和馴服,在經歷這些痛苦絕望之后,孤獨的他無比懷念之前的那種友誼,可他卻再也沒辦法回去了,無法融入到以前的那個集體中了,曾經荒唐殘忍的青春終究是過去了,回憶結束回到現實,整個畫面顏色卻從流彩的黃色變成了黑白色,成長的滋味如何?或者如兇猛的動物一般,鋒芒銳利,在青春歲月里橫沖直撞,傷害到他人;又或者如燦爛的陽光一樣,激情奔放,在青春歲月里熱烈張揚,明亮了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