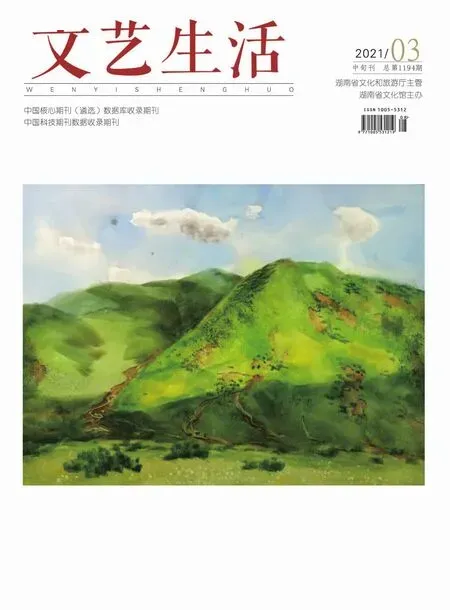當代招貼設計中的東方審美情懷
——留白空間
吳可凡
(哈爾濱師范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150080)
一、前言
招貼作為一種視覺傳達藝術,是信息傳達的載體,同時招貼作為現代實用美術的一種,具有較強的功能性和觀賞性。在視覺藝術走向多元化的今天,招貼風格多樣品類繁多,是運用當代西方藝術設計原理服務于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手段,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現出與本土文化相適應的特征。
伴隨著科技、產業、文化的高度發展,視覺藝術的審美趨勢面臨同質化和當代性的轉變,在中國乃至東亞,根植于中國古典哲學思想的視覺傳達藝術,其審美取向與文化血脈有著不可割舍的聯系,沿襲著東方傳統美學寧靜、典雅的古老氣息,“留白”就是其中之一。
西方視覺藝術孕育下的當代招貼,更加注重功能,即招貼本體形式與內容的主從因素,以及招貼對信息傳達的準確性。在信息社會高速發展的今天,龐雜的信息量侵占了人們的視野,復雜的訊息令人望而生厭,為了迅速準確地傳達作品的設計訴求,“留白”成為圖像繁簡對比,烘托主題的獨特手段。招貼作為視覺形式的一種,其根源來自于現代主義對美學原理研究成果。自包豪斯學院建立以來,三大構成設計成為藝術設計專業的基礎,平面構成對點、線、面的詮釋,豐富了平面作品的表現視域,也直接迎合了人眼的視覺感知原理。“留白”在這一體系下更多的是構成中“面”,在圖像的對比下促使招貼醒目、信息明確,并且在東方人文情懷的包裹下,作為舶來品的招貼藝術有了本土文化的特征。
二、“留白”的東方文化內涵
“留白”是中國傳統藝術作品中常用的一種藝術表現手法,指的是為使書畫作品整體章法結構更為協調得宜而有意留下的空白,畫中“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給人以想象之空間。“留白”蘊涵了東方哲學辯證統一的思想,老子在《道德經》中有云:“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中國古代繪畫中畫家“計白當黑”,常常借用留白指代實體的茫茫江水,悠悠天空,更多的是營造一種“空”的心靈意境。
根植于“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中國文人藝術,善于運用留白組織畫面前景、中景和遠景的空間構成,畫中的留白既烘托了作者詩一般的心境,又給觀者留下無限的解讀空間,如南宋馬遠的《寒江獨釣圖》,畫中只有一舟一翁以及船邊寥寥幾筆水紋,卻讓人覺得煙波浩渺、寒氣逼人,給人濃郁的詩意。又如齊白石的蝦,畫蝦不畫水,大量的留白卻使畫紙方寸之間盡顯大象,留白之處仿佛水波浮動,“無筆墨處見筆墨”,充分體現出創作者的遷想妙得,表現出了留白手法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魅力所在,這是對繪畫審美意趣和藝術構思特點的高度概括,也是中國繪畫的一個重要的美學原則。
(一)增強作品的意蘊美
中國傳統繪畫就極其重視留白,寥寥幾筆使主體物達到了意無窮的效果,以虛實相生的處理手法形成一種特殊的畫面意境形式。事實上,將水墨畫“不著一墨盡得風流”的留白表現手法借鑒到招貼設計上,同樣有增強作品意蘊美的效果,能夠突出鮮明主題,同時在紙張上體現出物體所具有的藝術審美性。
以香港設計大師靳埭強的《澳門回歸》招貼為例,簡單素雅的畫面上,中間是一片蓮花花瓣,花瓣落在水上泛起水紋,水紋環繞成兩道漣漪,細看是一大一小兩個“九”,遠觀是漢字的“回”字,聯想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區花是蓮花,又于九九年回歸祖國,突出“九九歸一,澳門回歸”的主題,讓人迅速明白這是澳門回歸之作。招貼畫面運用大面積留白,簡單素雅卻意蘊無窮。從設計大師靳埭強的這幅招貼中我們可以看出,將傳統的留白意象觀與現代招貼設計理論相結合,不僅突出升華了要表達的主題內容,也使作品呈現出極具東方韻味的意蘊美。
(二)提升作品的格調情趣
相比于繁復多變的設計元素,運用留白的表現手法反而使設計簡潔明了,提升了設計品位,給消費者以舒適的視覺體驗,深受消費者的青睞。日本品牌“無印良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無印良品”在設計上總是很少宣傳品牌的概念,而是注重人文關懷和人性化體驗。原研哉任無印良品藝術總監后,將其“空”承載的物質形象不斷地變化,眼看無物卻擁有豐富的文化內涵。無論是在包裝、產品設計還是招貼設計,“無印良品”都運用了大量的留白手法,設計簡約質樸,凸顯出產品的本質特點,給人格調高雅的心理感受。
以2003 年發布的“無印良品”地平線系列招貼為例,此系列招貼利用的是真實圖片場景的留白,與畫面平行的地平線將招貼上下均勻地一分為二,少女的背影作為一個“點”元素立在地平線之上,在寬廣的地平線的映襯下,人物顯得尤為渺小,人與自然的關系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大面積的藍白色,呈現出一望無垠的空間感,人們的視野也隨之變得開闊起來。留白表現手法的應用使畫面體現出一種高雅質樸、寧靜自然的氣韻,彰顯出作者高雅的文化品格和審美情趣。原野哉在其著作《白》的“空”一章中講到:“什么都沒有,其實其中充滿了一個什么都有可能性的空空的容器,它真正體現了可以容納萬物的潛在力量;在這種空之中,更包含了溝通和傳達的力量。”可見他對“空”、“白”理念的情有獨鐘。他的招貼并不局限于視覺感官的體驗,而是更強調營造整體氣氛,令人將注意力集中于產品本身,感受生活的哲學。
三、“留白”在當代招貼設計中的藝術作用
(一)營造作品的空間感
無論是傳統繪畫還是視覺招貼設計,空間都是作品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必需品。而留白也被稱為“虛空間”。傳統繪畫里“虛”就指代“留白”,利用“虛”來凸顯畫面中的“實”物,形成虛實空間的對比,豐富畫面的層次感,為在方寸之間體現出無限的空間感創造條件。留白的“虛空間”是招貼設計作品的“言外之意”,看似是隨意為之的無心之筆,實則皆是作者反復斟酌推敲獨具匠心的產物。合理的“留白”能切割作品的空間,達到“疏可走馬,密不透風”的效果,增強畫面的節奏感,營造作品的空間感。
德國著名的設計師崗特·蘭堡的書籍系列招貼,用單一的橙色作為背景,在大面積橙色襯托下招貼正中半開的書籍從顏色到圖形都尤為醒目,書籍打開的縫隙勾起了讀者的探究欲,成為整張招貼的視覺中心。可見,留白的“白”,并不單指色彩上的白色。另一幅社會招貼則利用書籍開口與密密麻麻的背景人群形成疏密對比,同樣起到突出書籍成為畫面視覺焦點的效果。人群好似在緩緩地往觀者面前移動,呈現出涌出紙邊的運動趨勢。讀者在欣賞招貼不動的圖紋式樣的同時,又感受到了具有傾向性的張力。同構型圖案的陳鋪也是另一種“無”的概念,運用得疏密得當不但營造了空間感,且更富動感、更添張力。因此,留白絕不是指留“空白”,利用非白的顏色或同構圖案形成的陳鋪背景同樣是留白表現手法的體現。
(二)強化作品的傳達效果
任何一件招貼作品都有一個想傳達給觀眾的主題,一切視覺表現皆圍繞主題進行表現。有的人以為,只要版面上的文字、圖形占比越多越大,主題理念就會表現越強勢奪目。然而就像沒有光亮何來陰影,一味地增添文字說明只會堵住畫面的氣口,使畫面變死,也令讀者難以吸收招貼的訴求。相反,在主題內容周圍合理運用“留白”有助于讀者注意力向“主題”集中凝聚,形成一種引導路徑,左右觀眾的閱讀方向,引領觀眾的視線,這就是藝術處理上的以少勝多,讀者反而能最快接收作品要傳達的主旨。
此外,對留白內容進行有章法的設計,能夠讓觀眾的想象力得到充分發揮,營造出一個愉悅的氛圍來欣賞藝術作品,讓作品達到深度傳播的效果。倘若招貼僅僅是被文字和圖形所填充,那么讀者就會產生厭煩情緒,作品要傳達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四、“留白”在招貼設計中的應用原則
(一)注重畫面構成要素的協調統一
“留白”的布局在一定程度上決定整個設計作品的情感基調,要與整體和諧統一。文字的大小、字體、所占據的位置、圖形的大小、色彩的運用等都要與留白相輔相成。在平面設計實踐中,作者應使畫面中各構成要素與“留白”無形的氣場協調統一,使“留白”部分對主體產生反襯或者映襯效果,更加鮮明地突出主題,否則就失去了留白本來的意義。
(二)根據主題與效果適當增刪調整
盡管“留白”有很多優點,但應用時需要避免形式主義的留白。“留白”面積過大,設計元素間間距太遠,不僅使畫面空洞平淡,而且無法準確傳達訴求信息,產生負面效果,讓讀者覺得內容簡單淺薄、形式單調無趣。若是設計中“留白”過少,設計元素間距太近,會使空間關系紊亂,畫面缺乏層次感,從而導致讀者產生視覺疲勞,接受信息不適。因此,不能不加分析,套路留白,還需根據實際主題,版面整體效果,加以刪減調整,使平面設計作品獲得最佳的畫面呈現效果。
(三)符合審美規律提升視覺效果
在運用“留白”的過程中,要尊重人們的視覺審美規律,不能是為了“留白”而“留白”。不加編排胡亂使用,過多或過少都會使作品的整體效果大大降低。過多顛覆的設計是容易造成人的反感,設計時應根據實際主題需要,與作品中的其他元素恰當搭配,給受眾以舒適的感官體驗,這樣設計出的作品才是合格的招貼作品。
五、結論
留白這種表現手法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占據重要地位,對現代設計及審美具有深遠影響。在現代招貼設計中,遵循運用技巧和原則,適當地使用留白手法,通過留白營造視覺和心理活動的焦點,構筑想象空間,從而深化設計作品所要傳達的信息內容,提升作品承載力,為作品賦予更豐富內涵,能使人們在招貼有限的畫面中擁有更舒適的視覺感官體驗,感受到新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