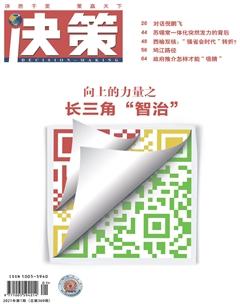蘇錫常一體化突然發力的背后
吳明華

蘇錫常太湖隧道項目又迎來重大節點,在三市的務實推動下,蘇錫常一體化進展迅速。
剛剛過去的2020年,蘇錫常兩次聚首,連續召開兩屆蘇錫常一體化發展合作峰會,此舉非同尋常。蘇錫常突然發力,如此急切地推動一體化,到底是為什么?
蘇錫常都市圈概念提出已有近20年。20年來,“蘇錫常”已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固定詞組,三座城市在文化習俗、發展水平和交通區位等方面十分接近。從夜景衛星圖中看,蘇錫常早已連成一片,形成了連綿150公里的“耀眼光區”。然而三市似近實遠,20年來瑜亮之爭、暗自較勁,競爭大于合作是不爭的事實。
如今,峰會給當地人帶來了希望。人們期待蘇錫常“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共同打造一個能夠問鼎一線的“超級城市”,為新一輪城市競爭做好準備。這一次,蘇錫常一體化能否破局?
“不做老大、不爭盟主”
2020年4月21日,首屆蘇錫常一體化發展合作峰會在“江蘇第一高樓”蘇州國金中心召開。這場不尋常的圓桌會,揭開了蘇錫常一體化的新帷幕。
出人意料的是,僅僅7個月之后第二屆峰會便召開,打破了尋常會議一年一屆的慣例。11月24日,三地黨政領導再次聚首,不僅簽署了一系列合作協議,還宣布共建太湖灣科創帶。
非常之舉必有非常之事。蘇錫常打破慣例迅速推動一體化,其背后的決策背景值得關注。
在當地觀察家看來,兩次峰會體現出蘇錫常“三兄弟”推進一體化發展的高度共識和強大合力,也帶給人們更多期待。不僅如此,兩次峰會的地點也頗值得玩味:第一次登高望遠,象征著蘇錫常勇爭第一的高度和雄心;第二次泛舟太湖,意味著以合作為舟,向著高質量一體化乘風破浪前進。
事實上,“蘇錫常都市圈”早在2000年左右就已提出,但目前更多地還是停留在2002年《蘇錫常都市圈規劃》的階段。這些年來,蘇錫常一體化進程一直比較坎坷。
盡管三座城市地緣相近、人文相親,曾共同創造了聞名全國的“蘇南模式”,但內部卻紛爭不斷。從新加坡工業園之爭到蘇南機場之爭,再到“太湖之爭”,多年來三市明爭暗斗,發展也是你追我趕。
特別是由于三市行政級別相同,經濟實力一度不相伯仲,導致誰也不服誰。2002年,一篇名為《誰是蘇南老大》的文章轟動一時,曾卷起了一場論戰,甚至驚動了兩市的主要領導,兩市領導不約而同地邀請作者進行交流座談。結果出乎意料,作者程松只是一名在校大學生。如今的程松已經走上領導崗位,成為無錫下轄區縣的一名副處級干部。
多年來,“誰是蘇南老大?”一直是橫亙在蘇錫常之間的問題。在蘇州人看來,蘇州經濟實力最強,理所當然應當是“龍頭”;而無錫人強調的是,無錫位于蘇錫常的“地理中心”。為了平息二者間的矛盾,江蘇省實施了諸多“平衡蘇錫”政策,但最終效果不盡人意。
這種矛盾直接影響了都市圈建設。由于缺乏有效的協調管理體制,蘇錫常一體化進展緩慢。三市基本上是“各自為政”,存在城市規劃不銜接、產業同質化、布局分散等諸多問題。
2016年,在國家發改委發布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2015-2030)》中,先是明確了蘇錫常三市組成一個都市圈,但又提出“推進滬蘇通、錫常泰跨江融合發展”。“滬蘇通”、“錫常泰”的新提法耐人尋味。
從蘇州方面來看,跳出傳統“蘇錫常”的羈絆,緊密融入上海,打造“滬蘇通”核心圈成為新的戰略選擇。從無錫方面來看,由于在蘇錫常框架下無錫已無“出頭之日”,爭取主導“錫常泰都市圈”,也不失為一種備選方案。常州則轉頭向西積極對接南京,甚至主動建議將下轄的金壇區和溧陽市納入南京都市圈。
對于江蘇省來說,重新構筑“滬蘇通”“寧鎮揚”和“錫常泰”,既符合蘇南、蘇中跨江融合發展的需要,也順應了對接上海的戰略要求,因此也積極推動。此后,“滬蘇通”和“錫常泰”成為媒體熱詞,而蘇錫常逐漸談出人們視野,官方文件和媒體報道中均鮮有提及。蘇錫常一度面臨分道揚鑣的局面。
20年來分分合合,三座城市的競爭糾葛都已成為人們口中津津樂道的故事。在4月21日的峰會上,時任江蘇省委常委、蘇州市委書記藍紹敏特別指出,蘇錫常的一體化是“不做老大”“不爭盟主”的一體化,是平等的共贏的一體化。但蘇錫常能否就此消弭內部紛爭,放下多年“心結”,“相逢一笑泯恩仇”,仍有待觀察。
大城時代“蘇南困局”
此次蘇錫常突然重啟一體化,其決策過程雖未披露,但城市發展自有其規律,從蘇南發展困局和城市競爭大勢的分析中,不難看出蘇錫常一體化的緊迫感與深層動力。
從數據上看,蘇南地區已經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2019年三市GDP之和達到38489億元,超過上海,是南京的2.74倍,達到全國第一。人均GDP、城市人口等指標也全國名列前茅,蘇錫常合起來實際上是“中國第一城”。然而,這種靠數量、規模和人口堆砌起來的第一,并沒有太多的實際意義。
“盡管GDP總值和人均GDP均略高于上海,但蘇錫常三市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僅為上海的52%。在一些前沿科技領域,差距更加明顯。以國家級重點實驗室為例,上海有21家,蘇錫常加起來只有4家,不到上海的1/5。”首屆峰會現場就自曝其短,曬出了這樣一組數據,引起三市的強烈共鳴與危機感。
在當下高質量發展階段,蘇南地區在產業結構升級與城市能級躍升上存在很大瓶頸。經過多年高速發展,蘇南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問題愈發突出,經濟增長逐漸放緩,環境容量嚴重超負荷,發展空間嚴重不足。從三次產業結構來看,蘇錫常二產比重很高,三產比重相對較低,中心城市服務功能較弱,對區域的輻射帶動作用不強。同時,二產中存在產業鏈短、附加值低,位于價值鏈頂端的產業集群數量有限等缺陷,產業轉型升級艱難。
特別是在大城時代,中心城市和省會城市的快速崛起,讓蘇錫常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由于蘇錫常只是普通的地級市,行政級別較低,無法獲得像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一樣的關注和資源傾斜,在區域發展重大問題上往往“城微言輕”。
有媒體做過梳理,在2019年12月中央發布的《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及上海50次、南京14次、杭州14次、合肥13次、寧波11次,而蘇州僅6次、無錫僅2次。在2020年4月國家發改委發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交通運輸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規劃》里,上海被提及了54次、南京47次、杭州32次、寧波32、合肥24次,而蘇州只有13次,無錫只被提及了6次,遠低于南通。
更讓人失望的是,蘇州機場又“夢碎”,蘇州夢寐以求的機場還是沒有得到批復。近年來,蘇州試圖通過爭奪上海第三機場,“曲線救國”圓機場夢,但最終還是南通勝出。由此,媒體把蘇州評價為長三角“最郁悶的城市”。
蘇南地位日漸衰落,危機感或由此而生。如果不能獲取中心城市發展所需的高端資源要素,蘇錫常如實現何城市能級躍升,未來又如何與資源優勢明顯的省會和副省級城市競爭?
“眼下,城市發展的‘馬太效應越發明顯,只有抱團發展才能共同做大做強。”峰會上三市迅速達成共識:蘇錫常三兄弟必須攜起手來,化“單向獲益”為“互利共贏”,化“被動等待”為“主動出擊”,化“單兵作戰”為“協同作戰”,共同把“蛋糕”做得更大。
對于蘇錫常來說,亟需做大做強中心城市,提升對高端資源要素的吸引、聚集和整合能力,才能在大城時代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而通過抱團取暖、一體化發展,實現1+1+1>3的效果,或許是破解“蘇南困局”的一條現實可行的捷徑。
一體化如何“破圈”?
心之所向,劍有所指。峰會剛結束,蘇錫常一體化工作就緊鑼密鼓啟動了。2020年4月26日,蘇錫常召開了醫療保障服務一體化發展合作研討會。隨后,三市又相繼召開了科技創新一體化交流會、住建領域一體化工作交流會、醫療服務價格一體化發展工作交流會等。此外,居民服務“一卡通”、成立行業聯盟等也在加速推進。
“區域經濟競爭無法避免,我們不做做不了、不想做的事,多做可以做、大家想做的事。”一言盡顯蘇南干部的務實作風。在三市的務實推動下,蘇錫常一體化進展迅速。
相比規劃、交通、公共服務等常規領域一體化,有一個“大動作”尤其值得關注。在首屆峰會上,蘇錫常便做出了重大宣示,要“攜手打造具有國家功能和重要影響力的大都市區”。其中“國家功能”四個字涵義深遠,針對性極強。“國家功能”代表了蘇錫常城市能級的重大躍升。
隨后,在第二屆峰會上,三市共同發布《蘇錫常共建太湖灣科創帶倡議書》。目標很明確,就是要創建國家級新區,成為蘇錫常都市圈“國家功能”的重要載體。在專家看來,這是蘇錫常一體化邁出的關鍵一步,可以用“破圈”來形容。
太湖灣科創帶原本是無錫首提的新戰略,并在2020年初上升為無錫市一號工程。此次能破除“門戶之見”,旗幟鮮明地把共建太湖灣科創帶,定位為“全面塑造創新驅動新優勢的重大舉措,加快落實蘇錫常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抓手”,頗為不易,足見蘇錫常一體化的決心。
城市競爭關鍵在于創新。蘇錫常各自都有科技創新雄厚的基礎,無錫擁有國家超級計算無錫中心,常州正推動建設寬禁帶半導體國家工程中心常州分中心等產學研合作平臺,蘇州正在加快建設太湖科學城、材料科學姑蘇實驗室、中科可控等重大科創載體,三市扎實的產業基礎提供了豐富的科研成果轉化應用場景。如果三市能擺脫各自為戰,聯合建設太湖灣科創帶,就可以發揮區域協同創新的強大力量。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此舉讓當地專家對一體化前景滿懷期待,“此時宣布共建太湖灣科創帶,可以說是把關乎蘇錫常各自未來競爭優勢的‘王牌放到明面上,大家一起‘明牌開打”。
科創協同是做“加法”,相對容易。而產業協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要做“減法”,往往是一體化中的難點,對于蘇錫常來說更是如此。
蘇錫常產業結構高度相似。據統計,三市工業同構率高達80%以上,尤其是錫常兩地高達95%以上。在產值排名前5位的工業支柱產業中,蘇州和無錫全部相同,常州與蘇州、無錫有4個相同。不僅三市之間缺乏水平分工,而且各市與縣區之間也缺乏垂直分工。由于產業缺乏分工,導致產業群而不集,同質化競爭激烈,這是制約蘇錫常一體化發展的最大瓶頸。
從目前來看,三市在產業定位和發展方向上仍未達成共識。蘇州希望共同培育發展5G關聯制造、信息技術、軟件應用等新產業;無錫希望在物聯網、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攜手推動產業鏈向“高”攀升;常州則聚焦智能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等領域,希望共同研究推出產業集群培育計劃。不難看出,在產業協同中,三市既有交集,也存在很大分歧。
對于蘇錫常來說,破解區域間產業重構、同質競爭,既是一體化要啃的“硬骨頭”,也是聯手打造世界級產業鏈的重要契機,而這考驗著三市的智慧。對此,無錫市委書記黃欽樂觀表示,“三個城市共同打造世界級產業鏈,完全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