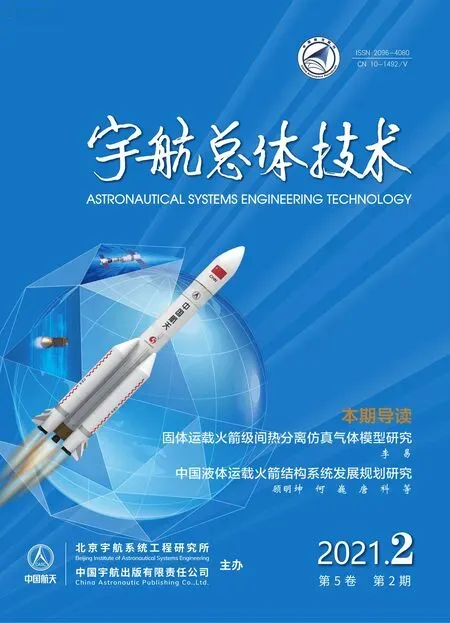發動機噴流干擾對底部熱環境影響研究
王 迅
(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空間物理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76)
0 引言
中國航天經歷了60余年的發展,具備發射近地軌道、太陽同步軌道、地球靜止軌道等多種軌道不同量級載荷的能力。近年來,隨著商業航天、軍民融合的蓬勃發展,國內外多型小型運載器的研發呈現呼之欲出的態勢。作為火箭的心臟,發動機是提供推力,保證火箭系統運載能力的核心。對于小型火箭發動機,噴管噴出的高溫燃氣向尾部膨脹,隨著高度上升,環境壓力逐漸降低,噴流膨脹角逐漸增大,燃氣邊界與火箭外流可能形成局部氣流反卷,形成對流加熱。火箭發動機燃氣溫度較高,液體火箭發動機燃氣中的CO和HO等極性分子有較大的熱輻射能力,可對底部形成輻射加熱;固體發動機尾焰含大量固體粒子,輻射加熱明顯高于液體火箭發動機。底遮板、尾罩等多個部位均處于尾部噴流加熱的影響范圍內。火箭底部加熱問題歷來是火箭技術的一個難點,對底部熱環境估計不足,熱防護措施不到位會給底部設備的安全性帶來嚴重威脅,甚至導致發射任務的失敗;而估計余量過大會增加設備質量,降低發射效率。
針對發動機噴流引發的對流加熱問題,國內外學者均進行了相關研究工作。Negishi等針對日本H-IIA火箭開展了主發動機與助推器發動機底部氣動熱環境仿真,使用CFD數值模擬和P1輻射模型分別評估了對流和輻射加熱,并指出了仿真結果與遙測結果存在明顯差異。楊學軍等分析了固體火箭尾艙熱環境特點,提出了一種線性化熱學參數的單介質模擬方法預示固體尾艙對流熱環境。周志壇等結合液體運載火箭底部飛行試驗數據,驗證了使用CFD方法和離散坐標法對底部對流和輻射加熱預示的有效性。呂俊明等對火星進入氣體輻射加熱的研究進展進行了總結分析。
為進一步提升對小型運載火箭底部熱環境的認識,本文結合數值計算分析及飛行試驗結果,開展了底部對流加熱相關研究。首先,分析了典型流動狀態下,發動機噴流流場結構及底部對流加熱的影響因素;然后,從流動機理出發,提出了一種降低底部對流加熱的外形優化方法;最后,結合飛行試驗結果,對底部加熱的來源進行了初步分析。
1 底部對流加熱評估方法
本文使用計算流體力學方法開展流動仿真。采用有限體積法求解積分形式的三維可壓縮N-S方程。空間無黏通量使用Roe格式離散,黏性通量采用中心差分格式進行離散,時間離散采用隱式格式。計算中采用量熱完全氣體假設。計算使用結構化網格,為準確獲得壁面對流加熱,壁面首層網格壁面法向高度為1×10m。計算域含整箭體外形,并根據幾何特征尺度進行適當簡化,經過試算保證尾流區域網格范圍可涵蓋尾部流場特征。發動機噴流計算網格表面特征如圖1所示。噴管出口燃氣比熱比及氣體常數分別為1.18和286 J/(kg·K)。為考慮燃氣介質與空氣的差異,計算中將燃氣噴流等效成空氣噴流,噴流入口取為發動機喉道,參數為壓力5.8 MPa,速度為1 059.7 m/s,密度為5.87 kg/m。各物面均采用300 K壁溫,不考慮內部結構傳熱。
按照典型特征選擇了如表1所示的條件開展數值仿真。仿真中僅考慮對流加熱,暫未考慮高溫氣體輻射的影響。

圖1 發動機壁面網格

表1 仿真狀態表
2 發動機噴流流場特征研究
圖2為發動機工作時7 km和15 km高度下對稱面馬赫數分布云圖。由圖可知,隨著高度的增加,來流動壓逐漸降低,發動機噴流的膨脹范圍隨之增加。

(a) H=7 km, Ma=2, A=0°(發動機工作)
圖3為發動機噴管附近對稱面溫度云圖與流線。由圖可知,發動機噴管與殼體間的空腔內存在低速回流,在發動機工作時,空腔內氣流溫度在500 K左右,速度在100~150 m/s間;而發動機關機時空腔內氣流溫度和速度均降低,溫度約為320 K,速度僅為10~20 m/s。
圖4給出了一級尾段內壁的熱流分布。當發動機工作時的殼體內壁熱流大于發動機關機時殼體內壁熱流,噴管罩內為低速對流換熱。根據傳熱學原理,低速對流換熱受密度影響明顯,高度7 km發動機開機狀態艙內氣流密度明顯高于15 km飛行狀態,低空艙壁內對流熱環境明顯高于高空狀態。發動機關機時,艙內氣體溫度較低,不會產生明顯的氣動加熱。

(a) H=7 km, Ma=2, A=0°(發動機工作)

(a) H=7 km, Ma=2, A=0°(發動機工作)
圖5給出了發動機在高空(50 km)工作時的Ma
數分布云圖。與圖2相比,當發動機工作在高空段時,來流動壓很小,因此發動機噴流膨脹范圍明顯增大,呈典型的欠膨脹噴流流場,與圖6所示的欠膨脹噴流流場結構類似。隨著攻角由0°增加至4.5°,發動機噴流范圍略微上移。
(a) H=50 km, Ma=6.0, A=0°(發動機工作)

圖6 欠膨脹射流流場結構示意圖
圖7是在H
=50 km,Ma
=6狀態下發動機噴管附近對稱面溫度云圖與流線。由圖可知,發動機噴管外壁及底遮板形成了典型的底部回流流動,底遮板回流的氣流溫度在817 K左右,而由于底遮板的遮擋作用,發動機殼體與噴管間的空腔內氣流溫度明顯低于底遮板回流區溫度,僅為308 K左右。當攻角變大時,噴管噴流向上偏移,導致迎風側底遮板回流和空腔內的氣流溫度明顯小于背風側。背風側底遮板回流區溫度約926 K左右,高于迎風側(約556 K)。
(a) H=50 km, Ma=6.0, A=0°(發動機工作)
圖8為H
=50 km,Ma
=6,A
=4.5°狀態下的底部內壁熱流分布。由圖可知,攻角對流場的影響使得底遮板和空腔內壁熱流呈現出迎風側低于背風側的特征。底遮板背風側熱流最高達到了20 kW/m,略高于相同位置的殼體外壁最大熱流(15 kW/m),迎風側熱流在1~5 kW/m之間;由于底遮板的遮擋作用,空腔內壁熱流很低,最大熱流不超過2 kW/m。
(a) 底遮板
3 尾段局部優化對底部對流熱環境的影響
由第2節可見,發動機底遮板與高溫燃氣直接接觸,使用不考慮輻射的CFD計算數值結果顯示,底遮板表面存在約2~16 kW/m的對流熱流。考慮高溫燃氣和高溫壁面的輻射加熱后預計熱環境將更高,為了防止底遮板受熱損壞導致高溫氣體進入內部艙體,對底部發動機附近艙體進行局部優化。
由圖7和圖8可見,在底遮板后面的艙體內壁,由于高溫氣流受到阻擋,速度和溫度均明顯低于外部氣流,這使得內壁熱環境明顯降低。借鑒此原理,通過改變底遮板局部結構外形,降低流動速度溫度,預計可以達到降低底遮板熱流的作用。考慮到底遮板附近流動受到外流和發動機噴管流動的共同影響,在不改變噴管和整體外形的基礎上,通過增長擋板對外形優化,對優化前后的外形開展CFD數值計算,評估了尾段擋板增長對底遮板對流熱環境的影響。
擋板增長前后的外形對比如圖9所示。除擋板外其余部件和原始外形保持一致。

圖9 擋板優化前后外形對比

(a) 優化前
在H
=50 km,Ma
=6,A
=0°來流條件下,擋板外形優化前后的流場對比如圖10所示。由此可見,擋板增長后,底遮板、噴管外壁形成的方腔渦流的溫度由817 K降低至486 K。與優化前相比,由于渦流外側的剪切層被增長后的擋板固壁替代,抑制了此部位流動能量,所以此區域流動溫度明顯降低。優化前后的底遮板熱環境對比如圖11所示。優化后底遮板熱流明顯降低,大部分面積的對流熱流在0.1 kW/m以內。局部外形優化對底遮板熱環境影響明顯。在本文所述的來流參數范圍內,使用優化后的外形后底遮板對流熱環境可以忽略。伸長后擋板邊緣熱環境可能會很高,防熱設計需要關注影響。
4 底部加熱的飛行試驗結果分析
某小型固體運載火箭在飛行過程中,底遮板布置了熱流測點,可以獲取的熱環境數據同時包含對流和輻射加熱。測點位置和測點處熱環境數據如圖12所示。t
+0.5 s時刻發動機點火。從試驗結果看,在0.5 s內底遮板熱環境從0 W/m增加至C
kW/m附近。后續可采用僅測量輻射熱流的傳感器進一步研究。
(a) 優化前

圖12 底遮板測點位置示意圖和熱流測量結果
該小型固體運載火箭已使用了增長后的擋板,在圖12所示的發動機點火時間段內彈道參數無明顯變化,而熱環境明顯上升。由于已經使用了優化后的擋板外形,經過數值計算底遮板在發動機點火對應的飛行參數下,對流熱流幾乎可以忽略。故遙測熱流很有可能為輻射熱流。
由此可見,即使經過外形優化可以明顯降低對流熱流,在實際飛行條件下固體發動機噴流依然可以產生一定量值的輻射加熱,對輻射加熱的準確估計對底部防隔熱設計來說非常重要。
5 結論
本文針對小型運載火箭底部熱環境開展了若干研究工作,得到的結論如下:
1)經過計算流體力學數值計算表明,發動機工作時,底部對流熱環境明顯高于關機對應的底部熱環境,飛行攻角可以明顯改變底部對流熱環境分布;
2) 噴管外壁、外流剪切層和底遮板壁面包圍的渦團是底遮板對流加熱的主要來源,通過增加發動機噴管附近擋板的長度,可以有效降低底遮板附近氣流溫度和速度,進而明顯降低底遮板對流熱環境;
3)在本文研究的飛行條件下,固體火箭發動機噴流使得底部輻射加熱顯著,在底部防隔熱設計時應該充分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