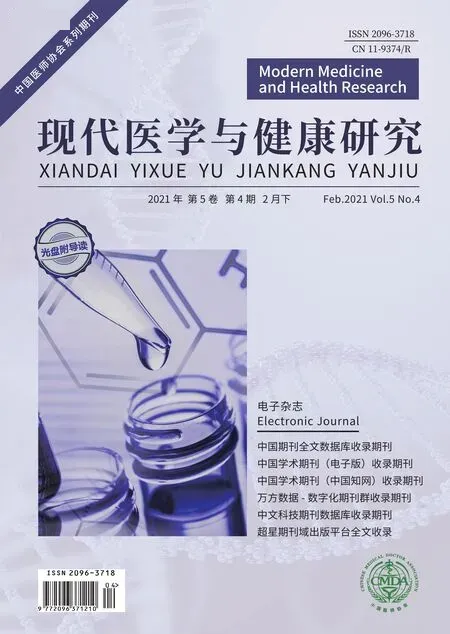超聲引導下連續股神經阻滯聯合局部浸潤麻醉對全膝關節置換術患者疼痛介質水平的影響
鄧明瑞,李 云,袁 靜
(1.安徽醫科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2;2.安徽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麻醉與圍手術期醫學科,安徽 合肥 230031)
全膝關節置換術是將關節假體置入人體替代病損關節的手術方法,該術式能夠有效改善膝關節疾病患者的膝關節功能,且遠期效果良好[1]。有研究指出,全膝關節置換術后60%的患者會出現疼痛,30%的患者存在中度疼痛,嚴重影響患者術后的康復鍛煉和關節功能恢復[2]。近年來,超聲引導下連續股神經阻滯被廣泛應用于全膝關節置換術患者的鎮痛中,在減輕患者疼痛方面具有顯著效果。但臨床也發現,由于膝關節周圍神經叢豐富,單純進行連續股神經阻滯并不能完全鎮痛。局部浸潤麻醉可以增強鎮痛效果,減輕患者術后疼痛情況,利于減輕手術對患者的生理干擾,對于提升患者手術效果具有重要影響[3]。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討超聲引導下連續股神經阻滯聯合局部浸潤麻醉對全膝關節置換術患者疼痛介質水平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安徽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行單側全膝關節置換術的50例患者的臨床資料,按麻醉方式不同分為A組和B組,每組25例。A組患者中男性16例,女性9例;年齡58~76歲,平均(67.32±6.56)歲。B組患者中男性15例,女性10例;年齡59~77歲,平均(67.38±6.61)歲。兩組患者一般資料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納入標準:符合《實用骨科學》[4]中的相關診斷標準;符合全膝關節置換術手術指征且為單側全膝關節置換;無精神病史與語言溝通障礙;局部皮膚無感染癥狀;無局部麻醉藥物過敏史等。排除標準:合并其他骨科疾病;合并心、肝、腎等其他器官嚴重病變者等;妊娠或哺乳期婦女等。本研究經院內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
1.2 方法 A組患者入手術室后開放上肢靜脈通路,連接多功能監測儀,監測患者的生命體征。在麻醉誘導前,采用彩色超聲引導系統,使用10 Hz高頻探頭,置于患側肢體腹股溝韌帶下方2 cm處,探頭長軸垂直于下肢縱軸,清晰顯示股靜脈、股動脈、股神經的橫斷面超聲圖像,以22 G短斜面神經阻滯針采用平面內技術進針,超聲引導下確認針尖到達股神經處,回抽無血后試推生理鹽水確定穿刺成功。注入局部麻醉藥物0.25%鹽酸羅哌卡因注射液(AstraZeneca AB,注冊證號H20140763,規格:10 mL:100 mg)20 mL,20 min后檢查阻滯平面,確認阻滯成功。置入鎮痛導管,妥善固定后,待阻滯起效后行麻醉誘導和全憑靜脈麻醉,然后進行置入人工膝關節手術。術畢連接自控電子鎮痛泵,維持鎮痛48 h。B組患者在A組超聲引導下連續股神經阻滯的基礎上,在置入人工膝關節前進行局部浸潤麻醉。麻醉藥物配方:1%鹽酸羅哌卡因注射液30 mL、注射用帕瑞昔布鈉(浙江普洛康裕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193065,規格:40 mg/支)40 mg、鹽酸嗎啡注射液(東北制藥集團沈陽第一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1022436、規格:1 mL:10 mg)5 mg、鹽酸腎上腺素注射液[遠大醫藥(中國)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42021700,規格:1 mL:1 mg]0.3 mg,以上藥物混合后加入150 mL生理鹽水稀釋,分別在后關節囊與股骨髁間窩內軟組織內、內外側副韌帶周圍、縫皮前切口內肌肉、深筋膜、皮下等處注射進行麻醉。其余步驟同A組。
1.3 觀察指標 ①采用視覺模擬疼痛量表(VAS)評分[5]評估兩組患者術后12 h及術后1、2、3 d靜息狀態和持續被動運動狀態時的疼痛情況,滿分10分,分數越高表明疼痛程度越嚴重。②采集兩組患者術后即刻、術后3 d空腹靜脈血3 mL,放置于ETDA抗凝管中,靜置15 min后,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測定促疼痛介質水平,包括組胺、5-羥色胺、前列腺素E2。③測定兩組患者術后即刻、術后3 d疼痛抑制相關介質水平,包括大麻素、β-內啡肽、Resolvin E1,血樣采集、檢測方法同②。④觀察兩組患者術后不良反應發生情況,包括惡心嘔吐、皮膚瘙癢。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以[例(%)]表示,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以(±s)表示,采用t檢驗,多時間點比較用重復測量方差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靜息狀態、持續被動運動狀態時VAS評分 術后12 h 至術后3 d兩組患者靜息狀態和持續被動運動狀態時VAS評分均呈先升高后降低趨勢,B組顯著低于A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靜息狀態、持續被動運動狀態時VAS評分比較( x±s, 分)
2.2 促疼痛介質水平 與術后即刻比,術后3 d兩組患者組胺、5-羥色胺、前列腺素E2水平均顯著降低,B組顯著低于A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促疼痛介質水平比較( ±s)

表2 兩組患者促疼痛介質水平比較( ±s)
注:與術后即刻比,#P<0.05。
組別 例數 組胺(pg/mL) 5-羥色胺(nmol/L) 前列腺素E2(ng/mL)術后即刻 術后3 d 術后即刻 術后3 d 術后即刻 術后3 d A 組 25 162.32±4.56 121.19±6.73# 344.45±10.61 244.47±16.89# 205.32±18.56 167.62±27.94#B 組 25 161.89±4.62 74.84±5.19# 342.75±10.68 176.98±15.77# 203.89±18.62 133.53±26.17#t值 0.331 27.269 0.565 14.603 0.272 4.453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3 疼痛抑制相關介質水平 與術后即刻比,術后3 d兩組患者大麻素、β-內啡肽、Resolvin E1水平均顯著升高,B組顯著高于A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疼痛抑制相關介質水平比較( x±s, pg/mL)
2.4 不良反應 A組患者出現2例惡心嘔吐、1例皮膚瘙癢,不良反應總發生率為12.00%(3/25);B組患者出現1例惡心嘔吐,不良反應總發生率為4.00%(1/25),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總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272,P>0.05)。
3 討論
全膝關節置換術是治療膝關節退行性病變的主要治療方法,通過植入人工假體,可有效改善膝關節的生理解剖結構和力學承受能力,恢復關節的正常活動功能,患者術后需早期進行康復鍛煉,以減少關節內粘連、肌肉萎縮或關節囊萎縮等情況的發生[6]。但術后疼痛感會影響患者術后的康復鍛煉,因此良好的鎮痛效果對于減輕患者生理干擾、提高手術效果具有重要意義。
超聲引導下連續股神經阻滯的鎮痛效果顯著,在超聲引導下操作可清晰地觀察到神經結構、穿刺針位置及導管位置,可確保局麻藥物成功分布在股神經周圍,可進行精準阻滯,提升了阻滯效果,有效減少了麻醉藥物的使用量,可以有效抑制股四頭肌痙攣,故近年來其在全膝關節置換術中得以廣泛應用;但是,膝關節是由股神經、閉孔神經、坐骨神經共同支配的,周圍神經叢豐富,而且在手術過程中切口通常在股外側皮神經的支配區域,因此超聲引導下連續股神經阻滯并不能完全緩解膝關節疼痛的問題。局部浸潤麻醉彌補了超聲引導下連續股神經阻滯的不足,對膝關節周圍局部浸潤麻醉采用的藥物是以局麻藥物為主,包括羅哌卡因、腎上腺素及帕瑞昔布鈉等,這些藥物的鎮痛效果好,而且局麻藥物于術后48 h內在椎間代謝,殘余的麻醉藥物能夠減輕局部疼痛感,避免因術后疼痛劇烈需額外使用麻醉藥物的情況,具有較好的穩定性與可控制性,而且不會出現藥物積蓄[7-8]。本研究中,術后12 h至術后3 d B組患者靜息狀態和持續被動運動狀態時的VAS評分均顯著低于A組;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總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明超聲引導下連續股神經阻滯聯合局部浸潤麻醉對全膝關節置換術患者的鎮痛效果確切,且不增加不良反應發生率,利于患者預后。
手術操作與人工關節的置入等均會導致多種促疼痛介質合成增多,因此機體疼痛感受較強烈。組胺、5-羥色胺共同參與調控疼痛的發生和程度;前列腺素E2會增加末梢神經的痛覺敏感度,因此組胺、5-羥色胺、前列腺素E2水平與疼痛程度密切相關,組胺、5-羥色胺、前列腺素E2水平降低,表明疼痛感較輕;大麻素通過與受體結合抑制疼痛信號的傳遞;β-內啡肽能抑制P物質的分泌,減輕疼痛;Resolvin E1與受體結合后可降低白細胞三烯B4所介導的疼痛效應,大麻素、β-內啡肽、Resolvin E1水平升高,則鎮痛效果較好,疼痛感較輕。而采用連續股神經阻滯復合浸潤麻醉可有效抑制機體內促疼痛介質的合成,提高抑制疼痛介質的水平[9]。局部浸潤麻醉通過將麻醉藥物注射至患者后關節囊與股骨髁間窩內軟組織內、內外側副韌帶周圍等處,可直接緩解患者術后疼痛,抑制患者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功能,抑制患者交感-腎上腺髓質系統過度興奮,從而減輕患者的應激反應與疼痛癥狀[10-11]。本研究中,與術后即刻比,B組患者術后3 d組胺、5-羥色胺、前列腺素E2水平顯著低于A組,大麻素、β-內啡肽、Resolvin E1水平顯著高于A組,表明超聲引導下連續股神經阻滯聯合局部浸潤麻醉能夠有效減少全膝關節置換術患者促疼痛介質的生成,相對提高疼痛抑制介質水平,鎮痛效果確切。
綜上,超聲引導下連續股神經阻滯聯合局部浸潤麻醉能夠有效減少全膝關節置換術患者促疼痛介質的生成,提高疼痛抑制介質水平,鎮痛效果確切,且不增加不良反應,但本研究樣本量較少,仍需擴大樣本量進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