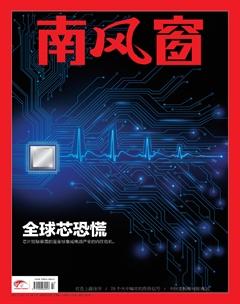房地產是金融體系最大灰犀牛
房地產是金融體系最大灰犀牛
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
本文節選自3月2日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會直播文字實錄
郭樹清表示,房地產的核心問題就是泡沫比較大,金融化泡沫化傾向比較強,是金融體系最大灰犀牛,很多人買房子不是為了居住,而是為了投資或者投機,這是很危險的。持有那么多房產,將來這個市場要是下來的話,個人財產就會有很大的損失,貸款還不上,銀行也收不回貸款、本金和利息,經濟生活就發生很大的混亂。所以必須既積極又穩妥地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不過他還稱,房地產金融化泡沫化勢頭得到遏制,2020年房地產貸款增速8年來首次低于各項貸款增速。“這個成績來之不易,相信房地產問題可以逐步緩解。”

郭樹清稱,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全球經濟出現了比較大的振蕩,總體上是下行。中國經濟去年遭遇了挫折,比較大的一個下滑在第一季度、第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逐步恢復到正常狀態,全年經濟增速比往年大幅度下降。歐美發達國家、疫情嚴重的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都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我們都能理解,因為畢竟要把經濟穩下來,宏觀政策必須采取這些措施。但他同時表示,在政策力度上、后果上可能要考慮的更多一些,因為畢竟還會產生一些副作用,現在看這些副作用已經逐步顯現。一是金融市場,歐美發達國家金融市場高位運行,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道而馳。金融市場應該反映實體經濟的狀況,如果和實體經濟差別太大,就會產生問題,遲早會被迫調整,所以我們很擔心金融市場,特別國外金融資產泡沫哪一天會破裂。二是流動性增加以后,由于經濟已經高度全球化,中國的經濟和其他國家的經濟密切相連,外國資本流入中國數量會明顯增加,我們也看到增長確實比較快。中國經濟目前還是恢復性增長,我們的資產價格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其他國家相比利差比較大,外國資本流入是必然的。但是到目前來看,規模和速度還是在我們的可控范圍內,我們也在繼續研究怎么采取更有效的辦法,一方面鼓勵資本要素跨境流動,越來越開放。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造成國內金融市場太大的波動,我們有信心把這個工作做好。
郭樹清稱,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很快進入老齡化社會,超過65歲人口占到12%以上,比日本、歐洲、美國要低。但是按照專家分析,用不了一些年我們會超過美國。所以人口老齡化確實是很大的挑戰,也在積極研究推進,從多個方面考慮。郭樹清說:“我們鼓勵出生,但現在人和過去的人不太一樣,鼓勵出生他也還是不怎么愿意增加提高出生率,這就是很大的挑戰。我們還會采取其他的措施,其中一項就是要發展第三支柱養老保險。”他表示,將進一步開發符合人民群眾需要的銀行產品,規范發展第三支柱養老保險等保險服務。他還稱,2020年年末,全國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余額15.3萬億元,增速超過30%,其中5家大型銀行增長54.8%。行政村已基本實現基礎金融服務全覆蓋。大病保險已覆蓋11.3億城鄉居民。
郭樹清表示,因為整個市場的貸款利率在回升,估計今年貸款利率會有所回升,可能會有所調整。但“總的來說利率還是比較低的”。他稱,收費方面不會有太大變化,降低的費用一般不會恢復;通過支持財務重組、債務重組、企業重組,包括債轉股,還有很多舉措出臺,這也會降低企業負擔。將以多種形式繼續支持企業發展。
郭樹清介紹,截至2020年年末,人民幣貸款比年初增加19.6萬億元,累計6.6萬億元貸款實施延期還本付息,在5個試點省市發放應急貸款242.7億元,全年實現向實體經濟讓利1.5萬億元目標,有力支持復工復產和“六穩”“六保”。
重思美國政治中的沖突與“極化”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段德敏
本文節選自《學術月刊》2021年第1期
美國政治中的極化現象是“壞政治”的體現,但極化中的“沖突”本身卻是美國政治的日常內核。如果我們追溯美國的建國理念及其歐洲政治思想的前身,我們會發現,沖突本身并不是一定要被克服的對象。在美國以及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中,沖突很多時候都被認為有助于政治的長期穩定,甚至有助于和諧。人性中既有共通之處,也有難以磨滅的個性化、異質化因素,對于后者而言,強行地壓抑、否定是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這一問題本身即有爭議。對于馬基雅維利、孟德斯鳩等人來說,或許可以恰當地以體制化的方式包容這些人性中“自然”互相沖突的部分,讓權力與權力之間互相對抗、制約。這一思想也體現在美國的建國理念及憲制結構中,對抗和沖突本身是其政治的常態,也可以說導致了諸如羅伯特·達爾等人所說的“正面”效應。然而,同時也需要注意的是,沖突的“正面”效應的前提是它是公開的、公共的沖突,而不是單純黨派私斗,換而言之,沖突不能“極化”。如何使沖突不至于極化?密爾認為需要借助于單一民族所形成的“聯合公共輿論”,而在托克維爾看來,19 世紀美國社會普遍的宗教信仰提供了使沖突朝向公共善的前提條件,這種信仰本身與政治無關,主要是私人的精神生活,但它卻恰因此而具備了政治上的作用。這一洞見也使得我們可以找到一個觀察當代美國政治極化的更恰當的視角,即它可能并不是因為人們“過度”地追求所謂政治正確,也不是因為右翼保守勢力突然沉渣泛起、死灰復燃,盡管與這些都有關聯;美國政治極化的更深沉的原因可能和那不大可見的共同價值、社群歸屬感的削弱有關。極化政治的一個特點即在于,不同派系的人看上去在互相辯論或爭論,但他們往往各說各話,實際形不成真正的、有建設性的“對話”。
對未來中國養老照護需求的估計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 喬曉春
本文節選自《人口與發展》2021年第1期
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需要照護且處于高收入的老年人有669萬,其中超過一半的人屬于80歲及以上的高齡群體;這一人群到2025年會增長到932萬,2030年達到1320萬,2035年會進一步提高到1822萬,到本世紀中葉的2050年會達到3609萬人。如果單純針對這一群體來計算養老產業市場規模的話,每年至少都會超過萬億元人民幣。

有照護需求的中等收入群體屬于政府公共服務和市場化服務的“夾心層”,會處于相對尷尬的境地,他們既不是政府公共服務的重點對象,更不是養老市場所青睞的人群。然而他們的規模巨大,一旦出現生活不能自理且家庭中無人照護,則會成為真正的“老無所依”群體。這部分人群在2020年為2682萬,到2035年增加到6954萬,2050年迅速提高到1.24億。
實際上,為這些需要照護老人提供支持不僅僅是“錢”的問題,更多需要考慮的是服務,特別是供給側所能容納的老年人規模。在2020年5月12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辦的政策吹風會上公布:截至2019年年底,我國養老服務床位數已經超過76萬張,養老機構超過3.4萬個,其中社會力量占比超過50%。然而2020年全國需要照護的老年人高達4637萬人,而需要照護的低收入老年人就達到1286萬,現有的養老機構,特別是公辦養老機構數量和床位數量更是遠遠滿足不了需求。
然而,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作用,導致老年人的子女數量在迅速減少 ,比如目前80歲以上的老年人,他們平均存活子女數是5人,而目前60~64歲老年人的平均子女數量只有1.94人。中國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讓家庭子女數量減少到了只有上一代人的40% ,而第一代獨生子女的父母已經進入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