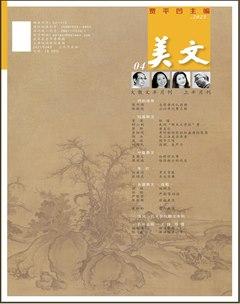《扶桑》:旁證與反證華人老移民的歷史(上篇)
劉艷 嚴歌苓


按語:
筆者在此前的寫作中,曾經提到過筆者與嚴歌苓的最初結緣,是因為她那本《扶桑》(中國華僑出版社1998年7月版)。1998年那個夏天,我本科畢業,以山東大學中文系四年七次大考總分第一(最后一個學期沒有考試),發表文章總分也第一的成績,免試直升碩士。沒有了找工作的問題,便專心在買書、看書上了。時光飛逝,即便20年過去了,我依然清楚地記得自己是從學校的三聯書店買了這本《扶桑》,封底還被蓋上了一個紅紅的大印:“三聯書店店慶50周年售書紀念(1948—1998)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說實話,到現在我仍然記得,我當時被這個小說的寫法給迷住了。沒過多久,剛讀碩士幾個月,又買了《人寰》(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10月版),也是喜歡。①
雖然嚴歌苓在1989年出國留學前,就已經寫作發表和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尤其是被稱為“女兵三部曲”的三部長篇小說——《綠血》《一個女兵的悄悄話》《雌性的草地》,起步即是不凡,已經在小說藝術造詣上達到了相當的水準。尤為不容忽視的是《雌性的草地》(嚴歌苓迄今都堅稱這是她自己所最為喜愛的作品),可以說是嚴歌苓在不足30歲時,即已達至一個后來也不曾抵達的藝術創作和小說敘事藝術層面的巔峰狀態。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大家只格外注意到了嚴歌苓是作為新移民文學代表人物、海外華人代表作家的寫作,并沒有意識到嚴歌苓出國前的創作即已頗具水準并對其加以研究,亦沒有意識到那三部長篇小說的重要性。很多人的印象和記憶里,嚴歌苓在國內引起普遍的關注和廣泛閱讀,還是從《扶桑》這部小說在內地的出版開始,也由此而引爆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興盛不衰的“嚴歌苓熱”和“嚴歌苓現象”。嚴歌苓這部書寫第一代華人移民歷史的長篇小說《扶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扶桑》還不單單是一部舊作。2020年,嚴歌苓已經完成《扶桑》英文劇本的寫作,《扶桑》電影的融資、投拍也都在具體操作實施當中了。
圍繞《扶桑》,做了一篇嚴歌苓訪談。但是由于可談的情況甚巨,還是作了上篇和下篇之分。還有一個情況,此前的“嚴歌苓訪談”是嚴歌苓本人親自寫作作答。本期開始,系嚴歌苓錄音整理完成。②
劉 艷:盡管對于嚴歌苓的作品,我往往讀了不止一遍。但在《扶桑》這次的訪談之前,我還是再次重讀了《扶桑》,并且認真做了筆記。
即便過去這么多年,我依然能記得1998年讀到《扶桑》(中國華僑出版社1998年7月第2版)時那種全新的閱讀體驗,耳目一新之感。無論是從讀慣了國內當代作家的小說角度,還是從閱讀海外華人作家作品的角度,都那么“震撼”乃至“震驚”的閱讀體驗。您在以往參加書展或者在大學舉辦的文學活動中,都或詳細或簡略提到過您為什么寫作《扶桑》這樣一部小說。比如2017年8月17日您參加上海書展時,在上海著名的文化地標鐘書閣,曾經暢談“我為什么選擇講這樣的故事:從《扶桑》《媽閣是座城》到《芳華》”。而此前2016年3月6日,您在北京大學做過“糟糕的歷史與優美的文學——嚴歌苓、高曉松、史航對話”的講座活動。其中,“嚴歌苓《扶桑》:苦難中的美國華人移民”與“扶桑是最強大的女人”是當時幾場活動的主題和嚴歌苓自己所表達的訪談主題。
對于為什么選擇寫作《扶桑》這樣一部長篇小說來反映第一代美國華人移民的歷史?以前您曾或多或少涉及過這個話題,您有沒有其他仍然可以補充的,還請多補充一點來自您的第一手材料。(您選擇以一名妓女的人生遭際來書寫第一代華人老移民的歷史,讓我想到了您以“金陵十三釵”——女性的被強奸被蹂躪這樣獨特的角度來反映南京大屠殺和日軍侵華的歷史)由一張舊金山唐人街張貼的清朝打扮的中國女子——當年舊金山最有名的中國妓女的照片(相比較而言,我更欣賞和喜歡英文版《扶桑》的封面,就是那張“扶桑”的老照片),您找到了寫作的靈感。當時有沒有覺得寫作的難度?或者說當時決定從“扶桑”這樣一個角度來寫老移民的歷史時,您覺得最大的難點是什么?該如何去找好那個寫作的點?
嚴歌苓:《扶桑》應該說是我在美國進行寫作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非常偶然的機會我跟我老公約了吃午飯,他在上班我說中午一塊吃飯,我到的比較早就出去溜達,在舊金山唐人街那里無意當中走進一個地下室,我發現迎著大門就是一張巨大的照片,是比真人還要大的照片。
這張照片上就是一個清朝打扮的中國女子,非常的端莊,也帶著一種神秘色彩,那個時候她是回頭率很高的一個女人,當時這個下面有一行字,說是當年舊金山最有名的中國妓女,我說這個中國妓女可不太像妓女,像一個貴夫人,非常雍容華貴的,我來找一找這個女人是誰,我回家以后就把很多有關舊金山淘金時代這些歷史書籍找來看,書都讀完了也沒有找到這個著名的妓女是誰。
但是在讀的過程當中我就發現,就像你們一樣,根本不了解美國當時是怎么樣對華人驅逐、迫害、歧視的,包括美國很有名的小說家叫杰克·倫敦,都說中國人是一種比較低劣的人種,看到這些東西我當時就非常憤怒,我說這跟希特勒整個否定猶太人一樣,而且用偽科學的東西說華人這個人種為什么不能在美國國土上生存,把我們中國人叫成狼才會說She或者是He,我就覺得非常的震驚,從此我就開始研究第一代中國人在美國各地的移民史,我就寫出了這部《扶桑》,因為我看了很多史書,我也找不出哪一個故事是特別有意思的,有一行字說:中國陸陸續續被拐賣來到舊金山的,走私到舊金山來的中國女孩兒有三千多個,跟她們有定期的幽會的白人男孩子從8到14歲,應該算他們的第一個情人,或者說性啟蒙的女性就是中國女人。
我覺得這樣一行記載一下子點燃了我,我覺得這個太詩意了,太有意思了,這段秘密的情史是東西方都不知道的,什么樣的白人男孩子會愛上中國的姑娘呢?可能是中國女人的母性給了他們那種西方女人給不了的一種東西,我就寫了《扶桑》。《扶桑》這本小說在西方各個媒體的評價都是很高的,去年有一個加拿大非常有名的導演,他讀了這本小說決定拍攝《扶桑》。這就是我為什么寫了《扶桑》。③
所以我覺得我對我們民族的那個——得過且過,過去了就忘的這種民族性啊,我覺得是很糟糕的,也真的想到魯迅為什么會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吧,這就是我當時想寫這部小說的激情的發源點。當然了,我寫妓女也是因為,當時全世界的民族去美國西部淘金的時候,是幾乎沒有女人去的。因為開發西部,哪怕從美國東部過去的那些男人也都不帶家眷,所以呢,唯一常見的女人,就是妓女。而且據記載,那個時候馬路上看見妓女,男人都是要脫帽的。我們就覺得當時的男人是很金貴女人的,因為四十六個男人比一個女人的這個比例嘛,女人就成了特別珍稀的一種生命,很珍稀的一種動物吧。那個時候的整個的社會的風氣就是這樣的。如果我寫作《扶桑》那個時候,有別的、有關別種女人的那種能反映老移民歷史的故事,我可能也是會寫的。可惜準備寫作那個階段,查閱老移民的歷史,沒有什么惹人注目的女人的傳奇和故事。當時的一個說法就是“好女不上街”,在路上走的,都不是什么好女人啊。中國那個時候赴美的都是勞工啊,勞工是不能帶家眷的。還有就是一些商人,也是很少很少的商人,他們帶的女人,也都是不出門的,因為當時的這個開拓者的群落呢,是非常粗獷也是非常野的。所以呢,那個時候能夠有故事并被記錄下來的,都是妓女。
劉 艷:與您合作多次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劉稚,曾稱《扶桑》是“書寫殘酷的移民血淚史”,據稱,彼時您在美國苦讀寫作學,攻讀藝術碩士學位。也常常處于近乎瘋狂的寫作狀態中。您的長篇小說《扶桑》正是寫作于此時,完成之后您陷入嚴重的自我懷疑。后來您看到臺灣《聯合報》征文啟事,遂以一個無名的寫作者投稿,竟意外地斬獲第一名10萬元大獎。您還說如果沒有這次貿然投稿,《扶桑》的手稿也許會和您寫作的其他好多成品半成品一起被塞在地下室某個箱子里,永不見天日。④
請問您當時,為什么會寫作完成《扶桑》,卻陷入嚴重的自我懷疑?不能理解已經寫作出版了三部長篇小說,尤其是有《雌性的草地》,為何會是“陷入嚴重的自我懷疑”?在我的理解里,《扶桑》在小說敘事藝術方面,雖然造詣頗深,但繁富程度和難度,并沒有超越《雌性的草地》。換句話說,能夠已經寫作出版《雌性的草地》,我覺得《扶桑》對嚴歌苓來說,是小菜一碟兒……為什么會這樣自我懷疑呢?另外,請多回憶和講述一下您當時的寫作狀態。《扶桑》所斬獲的這個第一名,在當時,對您的影響和激勵作用蠻大的吧?
嚴歌苓:我是看了兩三年的書才開始寫《扶桑》的。那個時候是1995年吧,在那之前我已經得了四個大獎,《少女小漁》得了一等獎,然后《紅羅裙》《海那邊》和《天浴》都得了獎。那么在那個時候,我想到因為一直在讀有關移民(華人先期移民)的這些書,所以我想要寫一部小說。但是我覺得用一般的小說形式寫,特別不能讓我感覺到能表達我當時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從第一代移民到我們當時應該算第五代移民吧——就是當時我們中國的這些留學生應該算第五代移民。不同代移民都有同樣的一種焦灼感,同樣的身份認同的錯位感,還有就是朝不保夕的生活狀態、與離散者相類似的那種痛苦。我覺得其實移民的生活方式,是一種特別獨特的存在。從第一代赴美華人移民到我們那一代,應該有一種貫通的東西。我一直沒有落筆的時候,我想到如果就寫一部歷史的、華人移民史的那種小說,我覺得特別不能夠反映我當時也是同樣具有的那種焦灼和痛苦。當時那種感覺,其實我在一篇散文里說到過,感覺是自己的一把根,都還沒有扎進冷土,那個根須都是暴露在空氣里的,所以它格外的、特別敏感。一點點的別人的那種眼色也好,表情也好,肢體動作也好,都能夠深深地讓你感覺到那種缺乏歸屬感,和不是這塊土地主人的那種痛苦。所以我覺得中國的第一代移民和我們后來的這些留學生,應該是有一種貫通的那種通感,就是作為移民的那種痛苦,那種膠著,就是一種全世界移民都有的那種狀態和感覺。暫時不能扎根,不能入流,但又已經從故土拔出了自己的根,就是這種感覺。那么我在沒有想好這種小說該有的形式之前,我就沒辦法動筆。
我記得那年我得了聯合報的第一名、得了另一家時報的第一名這些獎之后,我就去倫敦去歐洲去參加我的一個朋友的婚禮,碰到了虹影和趙毅衡。然后我就跟他們講起我要寫的這個《扶桑》,但是當時小說還沒有名字,我就說我想要寫一本長篇小說,當時我說我想用我自己和扶桑的對話這種形式來寫。這樣子的話,我覺得如果我能夠用這樣的小說形式,就能擁有一種比較獨特的角度,來敘述這樣一個歷史人物的故事。否則的話,我覺得我沒有什么必要非要寫這部小說,小說不該是要去控訴什么血淚史。
我記得趙毅衡和虹影當時還都挺鼓勵我的,我說我要用當代移民來訪談五代以前的那個最早期的華人移民的那種方式,他們都覺得挺有趣的。當然了,自從《雌性的草地》以后,我再也不可能安分地老實守著一種小說形式,我希望每一本我的小說,存在于我的個人的文學史上,都是要有一個它必須要存在的意義。否則的話,我覺得就沒什么寫頭。所以一直到1995年的春天,我才開始動筆寫《扶桑》。在那期間,我記得姜文也來了舊金山,舊金山當時是舉辦電影節。當時他帶著他第一部電影,好像就是《陽光燦爛的日子》,記得每天下午都和姜文他們玩兒啊什么的,聊天啊,等等。但是呢,每天早上我都是特別早地起來寫這部小說。那時候真的是激情所致吧,所以每天都能寫五六千字,感覺寫得特別特別地順。但是在最開始的時候,我確實是覺得難度很大。
我寫到大概前二三十頁的時候,都還找不到感覺,寫到用“你”來敘述這個故事,就有感覺。寫到用第三人稱敘述的時候,就沒感覺。當時寫作時我特別不能夠在腦子里形成這種畫面。因為畢竟是圖片資料特別少,然后呢,對扶桑生活時代的妓院的這種描述和當時那個唐人街的描述,都是文字的,所以我特別難找到這種畫面感。如果在我腦子里不出現圖像,我是寫不了東西的,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是這樣?我覺得我的腦子里永遠都是必須是要有圖像的。所以當時腦子里形不成圖像,我真的就是多少次在心里問自己,我為什么要寫這個東西,把我自己難成這樣。
但是寫到了大概1/5的時候,我就進入狀態了,姜文來的時候,和陳沖等人,我們經常下午在一起聊天和各種活動,那個時候我已經進入了特別好的狀態,所以就不管下午是聚會還是什么活動占用時間,上午我的寫作都是非常地一氣呵成。這之前的寫作糾結期,大概就是所說當時我的自我懷疑吧。其實我每寫一本書,在中間都會有一個自我懷疑的階段,像寫《陸犯焉識》,我就曾幾乎寫不下去了,然后我就停下來,當時我想我大概是已經江郎才盡了,我心里是不想完成這部作品,我覺得很無聊,不想完成。我記得當時我跟我先生說,我為什么要寫這么一本無聊的書,我不想寫了。然后我先生就說你每次都這么說,他說你每次都闖過去了,他說你過兩天再看吧。我說我已經沒才華了,我說我寫不了了,我說我覺得很絕望,這本書也許就是我的麥城吧,就是我的滑鐵盧吧,然后就哭啊什么的。但是我先生說,你過兩天你再來看自己,會覺得很可笑。所以果然也是像他說的,過了大概一個月吧,我又重新撿起來,我突然發現這不是寫得挺好的嗎?怎么就忽然產生那么絕望的念頭?
而在寫《扶桑》那個時候,我還是比較年輕,我對自己還沒有那么完全地了解。所以在剛開始寫《扶桑》的時候,我確實有點畏難,在最開始1/5之前的階段我確實就想停下來不寫了。我覺得我為自己設計的這個難度是非人的,我沒必要非要戰勝這個難度,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幾乎是想放棄。好在我比較有毅力,性格上我是一個很堅強的人,所以呢,每次也都闖過了這種自我懷疑自我放棄的階段。現在已經不會這樣了。我覺得從《陸犯焉識》之后吧,我就比較少再出現這個問題了。
曾經,我每一部作品寫到中間,都會產生一個很嚴重的自我懷疑階段。當然我也明白這種時刻,都會過去的,因為我每次都過去了,可能也就幾天的時間就過去了。后來我也認識到,人的精力、體力和創作力,它不是每一天都一樣的,因為你畢竟是一個肉身凡胎,你肯定會有高潮和低潮的時候,不能夠要求每一天都像最好的狀態的那一天一樣,要允許自己有低落的時候。所以我現在就想,這種低落的時候,就接受吧。而且現在這種低落的時候已經比較少了,因為自己對自己的了解越來越深了,也越來越透徹了,就不再懷有那種抱怨或者是覺得苦不堪言的狀態。現在我寫作基本上是非常快樂的,而且覺得不寫不行。
劉 艷:“扶桑”這個女性形象太特別了。李碩儒在采訪您時曾提到扶桑身上有一般女性所沒有的“妓性”,您當時很客氣,只是說他的這一看法“很別致”。您的觀點是更有道理的:扶桑雖然被迫為妓女,但她身上從來沒有妓女常有的“賤、嗲、刁、媚和那種以靈肉做生意的貪婪”——所以說扶桑具有“妓性”不合適。扶桑身上具有的是雌性、母性,甚至是佛性。《扶桑》里面,克里斯的視角,其實他在不斷發現扶桑的母性、雌性和貌似跪著卻寬容、悲憫,弱勢,敞開自己任你掠奪和侵害——你自以為欺凌了弱勢、自認為你可以拯救弱勢,但自以為強的(西方和西方文化),并不一定就贏了或者就可以想當然地拯救你們自以為處于落后和弱勢的東方文化:
六十歲的克里斯嘴上的煙斗一絲煙也不冒,眼睛卻像在濃煙中那樣虛起。他看著心目中這個女人,明白了他投入這女人的原因。竟是母性。
極端的異國情調誘使少年的他往深層勘探她,結果他在多年后發現這竟是母性。那種古老的母性,早一期文明中所含有的母性。
他心目中的母性包涵受難、寬恕,和對于自身毀滅的情愿。
母性是最高層的雌性,她敞開自己,讓你掠奪和侵害,她沒有排斥、不加取舍的胸懷是淫蕩最優美的體現。
六十歲的克里斯叼著煙斗,一動不動。就像他十四歲動不動看著窗內。看著她怎樣敞開自己 ,給人去毀去踐踏。十多個人。還有更多。在她被毀盡的一瞬間,她直瞪瞪朝向他的眼里有什么在怒放。她的本性怒放了,倏然從被毀滅的自己、被踐踏成土的自己躍然騰空,整場的毀滅帶來的竟是這剎那間脫韁奔放的奔放的自由!⑤
而克里斯十七歲時,這樣來回看和思考扶桑所謂的卑屈,其實可以意味著慷慨地布施、寬容和悲憫。
許多年后,七十歲的克里斯在老年性失眠的一個夜晚,又一次看見扶桑跪著的形象。扶桑仍穿著那件淺紅衫子,身體比他年輕時印象中的要小。她那跪著的寬恕是他風燭殘年時最感到動人的。他一生沒有寬恕太多人和事。他善于在別人和自己身上發現罪惡,到老,他悟到他正直的一生是被一個妓女寬恕下來的。他在那個失眠之夜更感到跪在遙遠年代里、著淺紅衫子的女子是那樣不可忍受的楚楚動人。
他看著七十歲的自己像條垂死的魚,在她寬容的網里掙扎。
原來寬容與下跪是不沖突的!他在七十歲這個失眠之夜突然悟到這點,在跪作為一個純生物姿態形成概念之前,在它有一切卑屈、恭順的奴性意味之前,它有著與其他所有姿態的平等。它有著自由的屬性。
它可以意味慷慨地布施。寬容和悲憫。
他想,那個跪著的扶桑之所以動人,是因為她體現了最遠古的雌性對于雄性的寬恕與悲憫;弱勢對強勢的慷慨的寬恕。⑥
其實,《扶桑》不止書寫和反映了移民備受欺凌和被欺辱的血淚史。小說尤其扶桑身上寄寓了嚴歌苓對東西方文化和弱勢與強勢的深入思考,您沒有按通常的移民史文學書寫的做法,一味地“寫慘”“賣慘”,其實是在內心深處有一種深深的倔強——你們西方文化、強勢群體憑什么就認為是高高在上、可以欺凌我們?甚至是打著“拯救”的旗號來對待我們的?一向被你們認為弱勢、污垢的東方文化和華人,不是在人性的很多方面比你們更悲憫、包容和能夠化解一切的能力嗎?您在《無出路咖啡館》等作品中也表達和書寫過類似的心態。扶桑身上還包含著您對女性、男性以及由此所牽涉到的女性主義女權主義的思考。我一直認為您的作品,是不能從女性主義女權主義角度去解讀和分析的——會陷入理論和邏輯的死胡同。您心底里似乎是將女權主義認為它其實還是男權的產物,反抗男權最終卻陷入一種更不堪的困境。我覺得您在扶桑身上,以及此后的少女小漁、王葡萄、小姨多鶴、護士萬紅、馮婉喻等一系列女性人物身上,都在寄寓這種思考——女性是有自給自足完整的生命世界和外柔內韌的生命力的。
請談談您對《扶桑》中所寄寓和所作的東西方文化的思考。您在扶桑身上所作的這些完全不能從女性主義女權主義角度去考量的思考。
嚴歌苓:你讓我談一談我對東西方的這種思考,其實那個時候我剛跟我先生結婚,然后呢,我是從1993年之后,開始讀那個舊金山華人移民史,還有舊金山淘金和那個大鐵路修建的歷史的,在那個時候呢,我其實都根本不用思考,就是很奇異的這種對話也好和非對話也罷,有的時候經常感覺到就是因為不能夠產生針尖對麥芒那樣的一種針對,所以常常會產生錯位對話,也會產生錯位感覺,所以就感覺那個東方人和一個西方人,尤其像我這樣一個格外敏感的這個東方女人吧,就感覺到兩個人沒有那樣的針尖對麥芒似的那種針對、針對性,也就吵不起架來,因為吵吵吧,就覺得好像我們都擦著邊兒就過去了,好有意思啊,所以這個就是不是一個東西方文化差異,覺得就是每分鐘都存在在我們的生活里,比如西方人拿香蕉、吃香蕉,是從那個香蕉的把兒,就是下面開始剝香蕉,我們是拿著那個把兒,然后從上面頂上剝,還有呢,就是我們在打手勢的時候有很多也都是相反的,這個就是那個時候我就覺得非常好奇啊。
就像《扶桑》里那段故事,我寫到《扶桑》里面的那段對話,真的就是我和我先生發生的。我說你買的豆腐,哎呀,以后不能再買這個日本豆腐了,他說:I'm sorry。然后我說我不是講你不好,我是講這個豆腐不好。就是這樣子,就發現這個架是吵不下去,也是一個好事兒吧。我就覺得當時我對這種情況的感覺呢,我覺得是一種美妙的誤解,所以呢,就是說人種的不同,有的時候容易產生那種迷戀吧,但是也容易兩個人近距離接觸以后呢,產生這種誤解,這種誤解有的時候會導致這個關系的深入,有的時候這種誤解會導致稀里糊涂的這個和解,有的時候又會造成極大的不滿足,就覺得好像沒有說透,這種意思都沒有表達透。當然了,后來我們相互之間的那個語言,就是各自把對方的語言習慣呀,還有就因為在兩種不同的語言當中逐漸完善了彼此的表達,所以后來這種誤解的情況就越來越少了。
但是我在寫《扶桑》的時候,恰恰是我最最敏感——對這個東西方的這種不想沖撞的時候發生了沖撞,你以為這個沖撞會升級的時候,它又突然之間自己化解啦,所以就這種狀態吧,讓我感到特別特別的好奇,也有的時候就覺得無助,有這種感覺,特別是在一個我的口頭表達不夠流暢,但內心卻擁有非常非常多的感覺的時候呢,就是外部的這種淤塞塞住的那種感覺,而內心的那種不斷的產生新的那種感覺——就是特別矛盾。
越是表達不出來呢,越是內心就走向內心化,走向內向,然后內心就格外的豐富,格外的復雜,格外的多情,也格外的多怨吧,就是這種狀態。我在那種狀態下寫出了《扶桑》。當然了,那個時候的狀態,我在過去我所作有關《扶桑》的演講當中,我也說了,我當時看到這些白人對華人的這種歧視迫害,我就指著我先生說,我說你們怎么可以這樣、那樣?然后我先生就會說,你別指我,我可沒有歧視華人啊,然后實際上就是《扶桑》真的是一氣呵成,一鼓作氣,一股激情和這種怒氣把它寫出來的。
還有就是說,因為我們是移民,特別是中國的移民,中國人實際上難民意識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就是他要不斷地勤勞,不斷地在節省,我對中國人的勤勞和節省啊,感受太深,我對中國移民的那種勤勞和節省,是特別有感觸的。就是一個人大概有一千多塊錢,可以養活一大家人;要在西方人那里呢,可能就是完全不可思議的,養活一個人都不夠哈。所以說美國人對這樣的一種移民,特別是那些習慣穿著睡衣睡褲就出來的唐人街的中國人,他們就是非常地瞧不起,而且編造一些故事,比如說穿過唐人街那趟公共汽車叫30路公共汽車,說那上面有耗子有蟑螂,所以說當時就聽到很多這樣的西方人的議論。他們有時候用打趣的、用玩笑的方式來說,但是呢,這是特別讓我感覺到民族自尊是有所傷痛的。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就寫了《扶桑》這個作品。
當然,還有就是我當時的那個感覺就是,東方文化是一種陰柔的、成熟的,甚至是已經有一點衰病的那種感覺,所以呢,我想象的就是Chris和扶桑這兩個形象就是這種代表。扶桑身上那種成熟氣息,這種藏污納垢的包容感,這種毫無條件的寬容和悲憫,所以我覺得她……真的,你講得很對,就是她身上具有一定的佛性,我覺得是這樣的。而Chris,我覺得他是一個小男孩,是一種年輕文化的代表,但是呢,他是這種充滿了理想,充滿了優越感,在愛一個人的同時,他又是那么地自我優越感,所以這種愛,實際上是有很多條件限制的,就是“你”必須要脫離“我”認為是一個卑賤的身份或事,“我”必須要把“你”從這樣的一個身份里拔出來,使你脫離這樣的一個身份。那么就是說,在這種有條件的、充滿優越感的這個愛當中呢,也就是扶桑為什么最終離開了他,就是扶桑為什么是不能接受這種愛的原因。盡管可能扶桑她一輩子所擁有過的真正的愛情,也就是對這個小男孩兒。
(根據嚴歌苓錄音整理完成)
注釋:
①參見劉艷:《欲將心事付瑤箏,知音少,弦斷有誰聽——嚴歌苓與我之文學知音緣起》,《長江叢刊》2018年第7期。
②參見嚴歌苓與筆者的微信交流。2021年1月26日,嚴歌苓給筆者微信:“我得了肘關節炎,很疼,等于五十肩長到胳膊肘上。醫生讓我停止在手機上操作任何,微信也不要回了,電腦上打字也要停止,養兩個月。兩個月以后再看。”“有個投資人預訂了一部小說,預付了影視版權費,合同規定3月15日之前交稿,我都無法完成,實在打不了字,做飯也不行,不能握菜刀和鍋鏟,醫生說我現在養不好,以后一輩子都寫不了,慢性長期的疼痛。”故此,該期開始,嚴歌苓訪談,系嚴歌苓錄音整理完成。
③嚴歌苓語。參見人文社,鳳凰網:《嚴歌苓:我為什么選擇講這樣的故事——從<扶桑><媽閣是座城>到<芳華>》,“嚴歌苓讀書會”微信公眾號2017年8月19日。④參見瓊花(筆者注,瓊花即劉稚):《<扶桑>書寫殘酷的移民血淚史——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瓊花/評》,“嚴歌苓讀書會”微信公眾號2017年3月30日。
⑤嚴歌苓:《扶桑》,第97頁,中國華僑出版社1998年版。
⑥嚴歌苓:《扶桑》,第233—234頁,中國華僑出版社1998年版。
(責任編輯:馬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