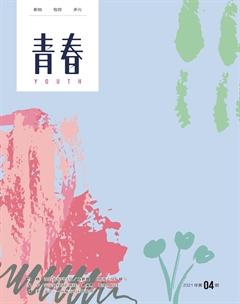從復蘇到新潮:1976—1992年文學思潮與小說創作
張光芒 陳進武 趙磊
一、新格局建立與文學思潮演進
隨著國家文藝路線的調整,南京的文藝領導機構、文學組織相繼恢復。1978年11月20日,南京市文聯第三屆委員擴大會召開,標志著南京市文聯及所屬協會恢復運行,為南京文學復蘇提供了組織保障。1979年3月至4月間召開中國作協江蘇分會文學創作會議,對“探求者”文學群體錯誤的政治定性予以糾正,也對重新確立南京文藝的發展方向發揮了積極引導作用。恢復后的南京市文學工作者協會通過建立業余創作組,編印刊物《創作新稿》,推動文學創作,創辦南京市文學創作講習所,培養文學青年。程千帆、劉舒任正副所長,趙瑞蕻、邵燕祥、公劉、蕭軍、張弦、梁曉聲、彭荊風、何士光等作家開設講座。該講習所吸引了大批文學青年,培養了新生文學力量,推動了南京文壇的復蘇。1984年,南京市文學工作者協會又創建了青春文學院,編印《文藝學習》(后改稱《青春文學》)。同年,南京市作協與青春文學院聯合創辦《朗誦報》,發表詩歌、散文等,為南京文學力量的成長提供了平臺。

1979年10月召開的全國第四次文代會是一次重新確立當代文藝發展方向的轉折會議。1980年11月28日召開的南京市第四次文代會積極落實全國文代會精神,為南京文學發展提供了政策保障。1985年1月,南京市文學工作者協會改為南京市作家協會,5月23日至25日,南京市作家協會召開成立大會,進一步健全了南京文藝組織體系。南京市作協成立后,先后設立南京散文詩學會、散文學會、雜文學會、臺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會等機構,并舉辦“金陵詩歌節”“揚子詩會”等活動,不斷推進文學各領域的創作、研究與交流活動。除各類組織及活動,1986年設立的金陵文學獎也對推動文藝復興發揮了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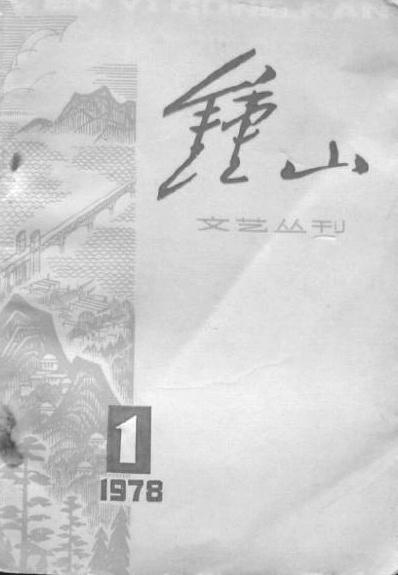
一批文學刊物相繼復刊或創刊。1978年,《雨花》雜志復刊,把握文學潮流,相繼推出了產生重大影響、占據文學史地位的作家和作品。巴金、陳白塵、韋君宜、汪曾祺、馮牧、艾煊、憶明珠、海笑、陸文夫、高曉聲、方之、邵燕祥、張弦、王蒙、陳忠實、劉心武、趙本夫、路遙、梁曉聲、李銳、張抗抗、賈平凹、儲福金、朱蘇進、蘇童、遲子建等,都在《雨花》發表過成名作或代表作,產生全國性影響,與南京文壇產生不解之緣。1978年《鐘山》雜志創刊,先后引領傷痕、反思、先鋒等諸多文學潮流。1985年《鐘山》與多位中青年作家簽署“十七人協議”,首開市場化改革先河,并先后倡導“新寫實主義”“新狀態文學”等藝術新潮,在全國范圍內產生了巨大反響。該刊物長期扶持中青年作家,發表了高曉聲、趙本夫、王兆軍、朱曉平、王安憶、蘇童、朱蘇進、余華、蘇童、韓東等作家的代表作品,奠定了《鐘山》在全國文藝界、期刊界的中堅地位。吳調公、劉夢溪、陳遼、吳功正、黃毓璜、丁帆、王彬彬、南帆、蔡翔、張頤武、吳炫等學者、批評家活躍于《鐘山》,引領了批評話題,頗受注目。《鐘山》也成為我國當代文化批評、文學批評的風向標。1978年南京市文聯創辦《南京文藝》。1979年10月,在《南京文藝》的基礎上,《青春》雜志正式創刊,刊名采用魯迅手寫體的“青春”集字。自創刊以來,《青春》就拉起“這是青年作者的領地,是青年作者馳騁的戰場”的文學旗幟,對促進青年作家的成長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王安憶、林斤瀾、賈平凹、梁曉聲、周梅森、鄧海南、顧城、蘇童、嚴歌苓、肖復興、余華、葉兆言、于堅、王大進等都曾在《青春》上發表早期或代表作品。1980年1月刊,《青春》發布“青春獎征文”啟事,拉開了青春文學獎的序幕。1983年4月刊發布第四屆啟事時,正式稱為“青春文學獎”。其中簡嘉1981年一等獎作品《女炊事班長》,同年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梁曉聲1983年獲獎作品《今夜有暴風雪》,張平1984年獲獎作品《姐姐》,分別獲得1984年全國優秀中篇、短篇小說獎。1979年創刊的《譯林》為我國翻譯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南京作為江南文化重鎮的歷史地位、兼容并包的城市氣質與自由、灑脫的生活方式,吸引了各地中青年作家如蘇童、朱文、趙本夫、范小青、周梅森、儲福金、黃蓓佳等人匯聚于此,創作了有重要影響的作品。經過短暫的“傷痕”“反思”的控訴與揭露階段(以《內奸》《“漏斗戶”主》等為代表),南京作家開始尋找新的藝術創作基地。高曉聲寫了《陳奐生上城》等反映農民精神“勝利法”的小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南京的“他們”詩群及其詩歌理論成為“第三代詩歌”現象的典型代表,引起詩壇的極大反響。經過1985年“方法年”洗禮,南京文學也開始了文學現代性嬗變。眾多青年作家借鑒現代主義的創作理念和方法,葉兆言、蘇童等成為先鋒文學的代表作家。總體來講,葉兆言、蘇童、余華、格非、馬原、莫言、殘雪、孫甘露等共同推動了80年代先鋒文學的形式革新和語言實驗。此后,畢飛宇、黃孝陽、魏微等南京作家在創作起步時都不同程度受到先鋒文學影響。在時代感召和文學新潮的推動下,南京老中青作家在全國范圍內產生了重要影響,南京文學由此呈現出繁榮局面。
二、理論探索與文學觀念的建構
進入新時期,南京文學理論批評界也經歷了一個思想解放和框架結構更新的過程,包括對“文學的人道主義”“異化”“文學的主體性”“向內轉”等問題的研究與討論。1985年前后的“方法論”熱潮也擴展到了南京,各類現代主義、先鋒性的文學理論與創作方法受到青睞,推動了南京文藝批評視野與方法的更新,形成了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并存與相互融合的研究格局。陳白塵、陳瘦竹、吳調公、吳奔星、葉子銘、許志英、鄒恬、陳遼、董健、王臻中、胡若定、葉櫓、黃毓璜、包忠文、吳功正、徐兆淮、何永康、朱曉進、費振鐘、高永年、汪應果、江錫銓、丁柏銓、周曉楊、姜耕玉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對南京文學的歷史發展、思潮流變以及代表作家作品,進行了極具獨創性的研究。南京理論批評家大力宣揚文學的審美性,提倡文化批評,極大推動了南京文學創作的發展,也對擴大南京文學的影響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4年前后,“第三代詩潮”興起,各地新的詩歌群體和詩歌理論不斷涌現。南京的“他們文學社”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詩群,他們在《藝術自釋》中提出創作理念:“我們關心的是詩歌本身,是詩歌成其為詩歌,是這種由語言和語言的運動所產生美感的生命形式。”這一詩群將關注詩歌本身作為基本立場,認為語言是詩歌之所以成為詩歌的核心。韓東在《〈他們〉略說》中提出“詩到語言為止”的詩歌概念,標志著“第三代詩潮”理論的正式確立。這一創作理念突破了朦朧詩的英雄主義、啟蒙主義的價值指向。如韓東《山民》《有關大雁塔》《你見過大海》等以口語消解了詩歌固有的宏大敘事和激情,揭示生活本來的平庸面目和悲劇色彩。經過同屬“他們”詩群的朱文、呂德安、陸憶敏、楊克、于小韋、吳晨駿等人的共同努力,形成了南京日常化、市民性與口語化的詩歌生態,并對后來的“底層寫作”“民間寫作”潮流產生了重大影響。
南京文人的底層意識、民間關懷在“新寫實小說”潮流的倡導上更明顯地體現出來。1989年,南京《鐘山》雜志針對當時一些描寫困頓人生的小說進行理論概括,率先提出“新寫實小說”概念。這一概念一直被后來的文學史和理論批評界所沿用,成為當代文藝批評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寫實小說”現象首先被南京文壇進行理論總結,既來自南京開放、自由的文化土壤所形成的文藝敏銳力,又與作家的底層意識和現實情懷相契合。南京城市性格的市民化、閑適的生活狀態對作家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造成了南京文壇對現實生活和普通個體的格外關注,對反映生活原生態的新寫實小說創作極為敏感,并從理論上引領了這一重大文學現象。南京“新寫實小說”的創作現象與理論倡導,雖得風氣之先,卻沒有突出文學的激進性和反叛性,而是立足于自身文化基地的新創造,其態度平和,視野向下,仍是契合于南京文化氣質的新的文學潮流。
在“他們文學社”成立前后,南京詩壇上涌現出一批新的青年詩歌群體,成為第三代詩群的重要組成部分。“日常主義”詩群在《日常主義宣言》中闡述了“日常性”“日常主義”的詩歌理念。這也是南京文壇產生的有重要影響的詩學概念。“東方人”詩群在《東方人詩派宣言》中提出建立具有東方氣質與風格的詩歌主張,對探尋當代詩歌路向具有一定參考價值。“新口語”詩群將“口語化”視為詩歌的本質,可看作五四“白話”入詩理論倡導的當代余續。“超感覺詩”群認為感覺、表象是無法抵達靈魂深處的負面因素,這是一種新的對當代詩歌變革的理解方式。“闡釋主義”詩群提倡對生命與世界的哲學關照,而現象、定義和概念則是影響詩歌創作的否定性因素。這無疑是對西方闡釋詩學的一次呼應,反映了當時詩壇向西方學習的藝術立場。“色彩派”詩群以“色彩”為支點,探尋世界的豐富性與復雜性。“呼吸派”則從主體對客體的情感介入角度談論詩歌的存在狀態。“新自然主義”詩群對詩歌的變革采取順其自然的態度,認為去除刻意和造作才是詩歌形成的前提,充滿樂觀主義的精神。可以說,南京青年詩群站在朦朧詩潮的對立面,在現代主義的地基上,提出了許多新鮮有價值的詩歌主張,對當代詩歌理論概念的豐富起到了一定促進作用。
三、南京小說創作的復蘇與發展
在經歷短暫的徘徊之后,南京作家們以敏銳的歷史嗅覺和藝術創新力融入、引領了一個個小說熱潮,個人化風格逐漸形成,在全國范圍內引起巨大反響。新時期的南京小說經歷了恢復發展期和創新期兩個階段。1976—1985年為第一個階段,南京小說是當時全國“傷痕”“反思”“改革”小說潮流的優秀代表。1985—1992年為第二個階段,南京小說創作進入創新期,成為引領全國小說新潮流的佼佼者。這兩個階段是承前啟后的,既呼應了全國性的傷痕小說、反思小說、先鋒小說等不同的創作思潮,同時又表現出南京小說的自身特色,就是長期形成的人文傳統、對日常細節的逼真展示和整體意境的營造。這一時期較有代表性的作家,有高曉聲、方之、胡石言、梅汝愷、趙本夫、黃蓓佳、范小青、周梅森、蘇童、葉兆言、儲福金等,形成老一輩作家和青年作家齊頭并進的良好創作局面。




復出的“探求者”群體取得了最初的實績,揭開了南京新時期小說的序幕。方之的《內奸》是反思小說思潮的代表作,引起了全國反響。高曉聲創作了“陳奐生”系列小說,包括《陳奐生上城》《陳奐生轉業》《陳奐生包產》《陳奐生出國》等,在挖掘農民身上的精神病癥方面取得新進展,是農村題材小說創作的重大突破,也保持了長久的影響力。與此同時,高曉聲還創作了《錢包》《魚釣》《山中》等當時未引起足夠重視卻頗具哲理意味的小說。這類小說表明,高曉聲一定程度上跳脫了當時流行的傷痕、反思小說模式,探究生命的無常、精神的戕害與價值的破碎等具有本體意味的哲學命題,這在當時的文壇是難能可貴的。陸文夫的《小販世家》《美食家》則關注了民間底層個體戶的悲喜劇和江南飲食文化風俗的變遷史,成為當時文化風俗小說的代表性作品。正是由于“探求者”小說群體的努力,南京新時期小說一開始就處于全國文壇的潮頭位置。
20世紀80年代初到中期,南京作家的小說作品一經發表就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等轉載,在全國產生了較大的影響。1981年,趙本夫反映農村新變化的處女作《賣驢》一經問世,就受到廣泛關注,獲得當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進入80年代中后期,趙本夫更加注重從文化層面思索黃河故道的歷史興衰、農民的命運沉浮。正是在這一方面,當代文學對國民性問題的探索又深入一步。此時較有影響的還有如張弦《被愛情遺忘的角落》、顧瀟《夢追南樓》《依稀往事》、徐乃建的《楊柏的“污染”》、李潮《面對共同的世界》、楊汝申《少校之死》、孫華炳《重賞之下》、董會平《尋找》、惲建新《麥青青》,等等。此外,姜滇、梁晴、賀景文、張昌華、蘇支超、王心麗、丁宏昌、孫觀懋、沈泰來、黃旦璇、胡丹娃、胡存廉、劉健屏、程瑋等南京作家的小說作品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80年代中后期,年青的小說家開始嶄露頭角,顯現出不同于現實主義的創作新風貌。葉兆言《棗樹的故事》、蘇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為先鋒小說的代表作,葉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和蘇童的《妻妾成群》則被視為“新歷史主義”小說的代表作。在“新寫實主義”小說寫作大潮中,方方《風景》和蘇童《離婚指南》成為其中的佼佼者。出生于南京的張賢亮創作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王安憶《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谷之戀》則是當時性愛小說的代表作。而黎汝清《湘江之戰》《皖南事變》、艾煊《鄉關何處》、胡石言《漆黑的羽毛》、海笑《紅紅的雨花石》、梅汝愷《青青羊河草》等都是此期的重要作品。此外,南京出色的中青年小說家還有趙本夫、范小青、儲福金、朱蘇進、周梅森、聶震寧、黃蓓佳、梁駿、薛冰、徐乃建等。正是中青年作家的崛起和小說佳作的接連不斷,南京成為當時新時期小說的重鎮。
作者簡介 張光芒,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陳進武,江蘇第二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趙磊,南京師范大學繼續教育學院講師、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責任編輯 陸 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