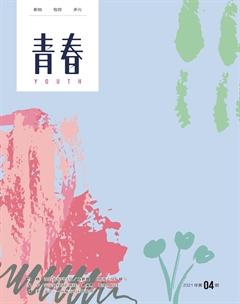文學:一座城市的有情地理
2019年10月,南京入選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學之都”。這是中國獲此稱號的第一城。為什么是南京?是和南京古都建制等長的文脈傳統(tǒng)?是當代作家創(chuàng)造的江南傳奇?是大學、書店、文學教育、公共圖書館、民間讀書會等等百姓的日常文學生活?執(zhí)一端,慢慢捋,都是一個城市的文學故事。
《舊時燕》,如其書名,是歷史過往,是當年明月。南京之為“文學之都”,有其悠然深郁的前史。虎踞龍盤,占盡形勝;人物風流,如“王謝子弟”。文人雅士,浸潤其中、滋養(yǎng)其中、“愛住”其中,所謂“六朝古都”“十朝都會”活在生生不息文學之南京里。程章燦教授的《舊時燕》非應景之作,而是15年前《古典文學知識》上連載的南京文化散文的修訂再版。這期間,程章燦教授還寫作了《山圍故國》和《潮打石城》,這兩種可和《舊時燕》并稱“南京三書”。
吳福輝先生在其《關于都市、都市文化和都市文學》一文談及“都市文化為何各個不同?在于它的地方性、民族性的豐富多樣。這種不同城市以不同的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為依托,皆以歷史悠久的傳統(tǒng)文化作為根基。因此對都市文化的個性,應注意挖掘傳統(tǒng)的地域意識和鄉(xiāng)土文化根系。注意到對文化基因的闡發(fā)”。城鄉(xiāng)之別是現代之后的事情,每一座有一點歷史的中國城市都扎根鄉(xiāng)土中國,其“城市形象”之清晰可辨可能恰恰是因為歲月悠長的地域意識和鄉(xiāng)土文化。它們具體而微,一座城市流動的氣息和腔調,滲透到市民日常生活的肌理和細節(jié)。“我城”之為“我城”大抵如此。所以,能夠理解程章燦教授在《舊時燕》所說:“城市不僅是一種地理的概念,空間的概念,更是一個文化的概念,時間的概念。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個性,自己的形象,自己的韻味。”
緣此,程章燦教授取徑文學,因為文學遺存一座城市最多的文化記憶。說南京文學,《舊時燕》從王氣、形勝和水氣始,在歷史和地理上先做溯流,誠如他在《山圍故國》中所言:“紫金山、青龍山、棲霞山、清涼山、將軍山、牛首山、幕府山、頂山,東西南北,群山圍繞故國。”“每座山都有自己的傳奇故事。無數傳奇故事,大大小小,圍聚纏繞,編織成一部南京城的歷史,有大歷史,也有小歷史。” 這些山中有“金陵王氣”,有寺廟、有香煙、有高士、有隱居處。而“六朝煙水”關系“煙籠寒水月籠沙”的秦淮河,也關系“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樓臺煙雨。山石、城池、屋宇氤氳著水氣,“散淡而瀟灑,風流而靡弱”的六朝文化古意卻歷久彌新,是一座氣質最佳最獨異處。南京因為文學而靈動。趙翼說袁枚的“愛住金陵為六朝”,林則徐稱“官愛江南為六朝”。所以,南京如何成為南京?是因為“城市山林籠罩在六朝煙水里,歷史內涵有了,文化底蘊有了,與眾不同的風姿自然有了。把南京與其他城市放在一起,它的古雅風和文化氣是不言而喻”。
去往歷史,取徑文學,《舊時燕》所述的中心不離南京城的文人、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活動,故此可見南京城的歷史的書寫,離不開文學的參與。“從文學的訴說中,從文化的圖景里,看一看城市的形象。讓城市來敘述文學和歷史,也讓文學和日常生活故事來敘述一個城市。”一座城市在文學的時間里生長,文學成為城市的精魂。方山的羈旅離別,促發(fā)詩章;石頭城的登高遠眺,宣發(fā)胸懷,所謂“悠然遠想,有高士之志”。南京城的山水使文人流連引發(fā)詩情文思,而詩賦文章形塑了南京城的品性氣質,更無論后來《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小說,更具象的金陵人文圖卷的鋪展。
“歷史和文化在傳說中被創(chuàng)造。”勝棋樓的對弈,雨花臺的法師講經,落花如雨,落地成石……文人書寫之外,傳說和故事是另外的更古老更民間的文學。也因為如此,大眾可以參與一座城市的文學想象。《舊時燕》的作者雖居大學,文史修養(yǎng)確信無疑,但他卻不棄不廢民間文化。程章燦教授說:“每座城市都有許多典故,有很多傳奇,有很多故事。這是城市文化精魂的凝縮,是城市的根。數典述祖,就是城市的文化尋根。”而“歷史上真真假假的演說,都在重復和深化這些城市論述”。如談到蔣王廟的由來,關于“青骨成神”的傳說是民間信仰和政治征用的共同造神。蔣子文于是化為一個文化符號,一個文學隱喻,其王侯之尊被用來隱喻歷代帝王和統(tǒng)治者,尤其和南京有關的“一國之君”,在后來的文學書寫中具有了特定意味。“有女莫愁”“莫愁變臉”,由傳說而溯源莫愁作為文學符號的形成。在傳說中,莫愁由《莫愁樂》中住在城西的歌唱的少女,而演變成歌妓,又成為《河中之水歌》中的盧家少婦,最終正式落腳于南京水西門外。莫愁湖在人文地理上的誕生,使文人來往如織,題詠如繡,愈見密麗。
城市的文學傳奇,中心自然是“人”。以金陵為背景《儒林外史》人物身上的六朝遺風,文人雅集,既承城市前史,也可在近世種種中見到可為印證的人事,如1929 年元旦在鼓樓雞鳴寺發(fā)生的“豁蒙樓七老聯(lián)句”。陳伯弢、王伯沆、胡翔冬、黃季剛、汪辟疆、胡小石、王小湘七位先生邊喝酒邊作詩,聯(lián)成按照年齡長幼排列的二十八句 。其中王伯沆、黃季剛、胡小石也是出現在《舊時燕》中的人物。流寓南京的袁枚,“異日將官易此園”,將據說原為曹雪芹的叔父、原江寧織造曹頫的曹家花園的“隋園”買下改建成隨園,修亭臺、廣植梅、巧布景,使其成為一代名園,而發(fā)生在隨園的交游雅集、文學活動也豐富了南京城市文化地圖。《舊時燕》中遠可見六朝人物,王謝子弟,近可見袁枚、吳敬梓、黃季剛、王伯沆等前賢。僧人,如瓦官寺的竺法汰、青園寺的竺道生、定林寺的釋僧祐和惠地和尚(劉勰)……山林既屬僧眾,亦屬高士,彼此惺惺相惜,引為知音。名僧成就名剎,名剎成就名山,共同成為城市的傳奇。而王安石與金陵的幾度結緣,最終葉落半山。“休論王謝當年事,大抵烏衣只舊時。”金陵的氣息合乎其生命的節(jié)奏,離朝堂而親山水,直至生命終了。
美國詩人惠特曼曾因為痛心市民不知愛惜城市的過往寫作了布魯克林史。可是,我們每一個生活在自己城市的人又有多少能記憶起那些自己城市惠特曼“布魯克林史”式的詩篇?南京入選“世界文學之都”,類似《舊時燕》的寫作可以理解為一種召喚——喚醒一座城市的文學記憶,也是喚醒一座城市的記憶。閱讀一個城市散落在光陰縫隙的文學,那些文字,那些文字中流動的情與思。關于我們的城市,我們是有記憶的人,我們和城市不再彼此生分,“城”即是“人”。“都市變成一個大‘我,將大眾結合在一起,化為文物,人的博物館,左右鄰居變成意義的‘地方化,每一來往的人物皆可找到活生生的記憶,‘帶感情的地理。”(廖炳惠:《紐約:從惠特曼到伍迪艾倫》)在這個意味上,《舊時燕》以文學的方式完成了對南京山河、歷史和文學的一場漫長的追憶,使之因“帶感情的地理”而呈現了文學之都的真正意味。尤可提及的是《舊時燕》守正、端雅,作者語以“舊聞新語讀南京”,其滲透點染輕靈自在,既秉持文史散文求真、廣博的傳統(tǒng),又文風散淡放達,恰恰配得上金陵文氣之真妙。
本文原發(fā)表于《光明日報》2021年2月3日,原標題為《南京城在文學的時間里生長——讀程章燦散文集〈舊時燕:文學之都的傳奇〉》。
作者簡介 何平,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中國作家協(xié)會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江蘇省評論家協(xié)會副主席。著有《散文說》《何平文學評論選》《無名者的生活》《重建散文的尊嚴》等。
責任編輯 陸 萱